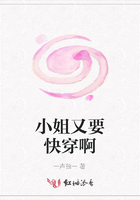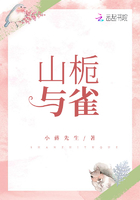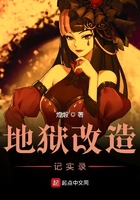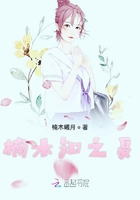发“新潮”于“旧泽”――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对我国传统文论的消解与重构
刘全福
清末民初年间,内忧外患日趋荦然,其时众多文人志士上怀国政纷乱之忧,下感民不聊生之苦,于是纷纷东渡或西游,以期“求新声于异邦”,或曰“借火助燃”,从“西学”中觅得救国民于涂炭的良策。正是在这种大的语境下,周氏早期的文学思想开始雏形,就在鲁迅刚推出《摩罗诗力说》以后,他也于1908年在《河南》第4、5期上付梓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下称《论文章》)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取消解与重构之道,采吐故纳新之法,以酣畅的笔调和清晰的思路首开先河地就文学的意义及使命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廓清,其中既有对现代“西学”理念的批评与吸纳,更不乏对传统“国故”的消解与扬弃。在整个论述过程中,作者采取了一种客观的融合态度,尽管行文上些微缺少了《摩罗诗力说》所特有的激情,却更能让人感到一种浸润着理性思辨的学者式的敦厚与温良。此外就重要性而言,值“文字之事日就式微”之际,作为一篇“有为而发”的文论,《论文章》在理论上无疑是光彩夺目的:“周作人从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对‘文学’这一概念作了一次全面的界说,这在整个近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是独一无二的”。鉴于此,本文拟以《论文章》为切入点,试就周作人对我国传统文论的消解与重构过程进行全面的归整与梳理。
2.先声:尚“精神之美大”
甲午战争后,科学救国理念渐至淡出历史舞台,人们不无悲哀地看到,中国的问题实不在缺少坚船利炮,而在于国民精神匮乏。所谓“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黄遵宪:《东沟行》),“开启民智”以造就“才智之士”遂成为一种共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大儒打出了“文界革命”的思想改良旗号。就其宗旨而言,“文学救国”一说似不乏一定的理据,但就其本质而言,急功近利的取道则无疑会损害文学,使其因失去审美性而削弱了感染力,结果离本来的目标反而更远。
至1908年,当周作人推出《论文章》一文时,作为“小说界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已问世10个年头。这期间,中国文坛可谓变化纷繁,以小说为例,即出现了“三分天下”的现象:其一,作为对政治小说的反动,泛情主义自1906年始成风气;其二,改良派学说在以王钟麒为代表的南社革命派那里得到了继承,王氏的诸多言说其实就是“小说救国论”的翻版;其三,南社派的徐念慈一反功利风气,提出了“小说固不足生社会”、“惟有社会始成小说”的观点。
从时间上来看,应该说徐念慈先于周作人提出了审美的文学观。早在一年前,徐氏就已将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运用于小说文体功能的阐释,指出合乎理想美学及感情美学的小说才是真正的上乘之作,从而首开先河地将小说批评引向了文艺美学领域。然而由整体上观之,周氏的思考显然更为全面且更具有思辨性与开拓性,因而其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前者。《论文章》首先探讨了作为“美大之国民”要素的“质体”与“精神”的演化过程及相互关系,指出“质体为用”虽“与精神并尊”,但精神才是一个民族的国魂,因为质体死亡精神则可再生,反之精神不在,质体将形同虚设。正因为此,在民族兴衰的历史长河中,“文章”无疑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东欧众多弱小国家虽久处异族羁轭之下而仍能立于不败之地,即是因了“特美所重,乃在艺文”的缘故。作者由此得出结论道:“灵明美伟者必兴,愚鄙猥琐者必耗。”换言之,文风渊朗,国民精神则“进于美大”,“国魂”不亡,国运自会永远昌盛,“文章”之于振兴民气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推出“精神之美大”这一命题的同时,周作人实际上也消解了盘踞我国文坛两千余年的传统文学思想。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功能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如《礼记?乐记》中所载:“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其中“音”字所指即是“文章”或文学,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也即是文学之道与政通。而在《论文章》一文中,作者的观点是具有解构性的。在他那里,“文与政通”中的“政”的原始意义被消解,既而被赋予了“国民精神”这一更宽泛的主题。如此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文”的被动地位及作用即被淡化,从而获得了“文”通“国魂”或“国民精神”的时代意义。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论文章》自然也没能完全摆脱改良派文学观点的影响,换句话说,周氏在对传统文论思想进行消解时走向了某一极端,比如在处理“质体”、“精神”及“文章”之间的关系时,即流露出了“精神”超越论的观点。但尽管如此,在清末文坛上,当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整体上仍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时,周作人则较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文学发展的时代走向,从而在对现代西方文学思想的反思与借鉴过程中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崇尚“精神之美大”的崭新观念,这“在当时中国文学思想中确是最为先进、最能从本体论角度切近文学本性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就其开拓意义而言,《论文章》不啻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夕早早进入人们视线的第一只“春燕”了。
3.消解:“及旧泽之不存”
西方诸国无不“文风渊朗”,其原因即在于西人“特美所重乃在艺文”且推崇“精神之美大”。而反观中国思想,则“拘囚蜷屈,莫得自展”,文运“拘挛臣伏”已垂数千载。所以如此,儒教为祸中国文运久矣:《风》原数三千余篇,篇篇美感至情,“乃至删《诗》,而运遂厄”。通过“删《诗》定礼”,孔子最终厘定了诗的礼治观,自此论文者少有人能够跳出“思无邪”及“兴观群怨”的窠臼了。以《周易》为例,其中即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及至汉代,为迎合儒家诗教,肢解“旧泽”蔚成风气:如作为《国风》开篇的《关雎》即被当成为颂扬周文王太姒“之德”而作,所谓《关雎》以出,“风之始也”,美感至情之作遂成为裁定一切礼教的俗语。所谓物极必反,六朝文人多刻意于雕琢,似以“文”偏离了儒道,但尽管如此,成规依旧,如梁代萧纲虽对儒家诗教颇有微词,却仍念念于“王政”、“人伦”:“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谓之人文。”这该是孔子“无邪”思想极正统的注释了。
唐代将“便于时用”同“宜于歌咏”融合起来,形成了“文辞”、“政教”合一的局面,而“道”则依然为首。至宋朝,周敦颐首次提出“文以载道”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艺”自然应从于“实”。事实上,宋人是以“道”将“文”打发掉了:即使文章俪巧,言语工巧,也“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元代对于“诗无邪”的思想也极为推崇,如杨维桢就认为诗应以教为尚,指出如“虞廷载赓”,则“君臣道合”,如“五子有作”,则“兄弟义章”。明清时期,诗文之外又兴说部,但就思想而言,论者仍多附会于“助风化”、“补朝纲”之类的“文”之于“治”的老调。
由此可见,文学自古以降始终未曾突破“思无邪”的藩篱:文正而理彰,文规于正方可化成天下。对此周作人指出:“此所谓正,特准一人为言,正厉王雄主之所喜,而下民之所呻楚者耳!”删《诗》定礼而“阴以为帝王之右助”,必然会“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于是论著者无不“折情就理,唯以和顺为长”,即使偶有闲情绮语,著于文章,则也不敢有些微“逸轨之驰”。儒家诗教规范“文章”,导致了“文艺之作,靡不润色鸿业,宣布皇猷为用”的腐败局面,长此以往,则势必文运凋敝,国运衰微。
更为甚者,“儒风扇虐”为害尚不止一端,其遗毒于“文章之士”者亦非浅鲜。古之为文者,或为“致君尧舜之方”,或为“弋誉求荣之道”,人人唯利是图,甚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即使偶有书写真实性情者,其文也绝少“特异其采”。所以未尝有人独辟蹊径,原因不言而自明:“偶有立异,久已为众所排,遂以槁丧。”周作人的慨叹是不无道理的:天才常不为时局所限,每逢时代变迁,必有领袖人物横空出世,创举世伟业,然而此种情状惟独不见于我国文坛,究其原由,即在于中国文运久为儒教所困,加之“道学继起”,制艺遂生,更使文章丧死极致。凡此种种,国民思想翦伐,文章盛业梏亡,一切均不在言下了。
至此,从孔子删《诗》入手,《论文章》对盘踞我国文坛数千载的儒家诗教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在他那里,“旧泽”确乎已绝然“无存”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同鲁迅一样,周作人对于传统的消解显然也不乏过激之处:“无邪”及“载道”思想固然在拆解之列,但孔子删《诗》却也有其功不可没之处,如若不然,《诗经》也许真就荡然无存了。此外,“十三国”虽已不见全貌,但毕竟还有《关雎》遗风,平心而论,“后妃之德”一类的诠释尚不至完全遮蔽其“美感至情”,所谓诗无达诂,读《关雎》者该不会一概沦为儒家诗教的附庸吧。
4.反思:发“新潮”于“弗作”
在周作人笔下,儒家诗教可谓彻底消弭了,而这一点也正反映了那一代人的悲观与矛盾心态:深受传统“国故”浸淫,本应将其弘扬于当世,然“旧泽不存”,思想遂陷入无所依傍的困顿,又环顾上下,目之所及依旧是“辗转未尝蜕古”的“实利之遗宗”。于是在对传统文论进行拆解的同时,他也开始建构起自己的文学观点:将立国之策寄望于工商实为釜底抽薪之举,即使“诸业骏盛”,“宁遂足尽人生之事耶”?目下实利为祸之势不减,国民精神日渐萎靡且有“走阪之势”,而为今之计,“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方不失明智举措。所以如此,仍见于“国魂”一说:精神式微,则“体质徒存”,貌似强盛,而实如槁木。一言以蔽之,唯有“文章”无愧于胜业,国运兴衰,见于文运,文风渊朗,国民精神才能“进于美大”。基于这些思考,周作人将建构的基点集中在对文学意义及其使命的全方位探讨。
在当时,文学的本质等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甚为“杂糅”,所谓“悬解益纷,殊莫能定”,实不易理出个头绪来。鉴于此,周氏主要采纳了美国文论家亨特(T.W.Hunt)的折衷观点:“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届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也就是说,文学有异于学术,前者具“艺术特质”,意在“普及凡众之心”,后者则“过于专业”,“唯供学子研治之用”,故而“文章之不文(Unliterary),盖不必?陋无学(Illiterate),有足贻笑于大方者在也,凡学术专业之词,皆足为文章之?耳”。此言一出,也就廓清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而此举在当时是颇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关于“文”与“质”的关系,他批评了“文家非学子莫胜”及“色相之美优于托物”两种极端观点,指出文学应为“文”、“质”合一,“既不偏于学绩为文之说,亦不至过宗美论,唯主辞藻”。就其本质而言,文学“悦人之意”必须基于“尚美”特质,也即文学所载当为“清明而具美相”的“至美思想”,以使读者从中领略到至理人情。换言之,文学之“文心词致”固然重要,“灵明之气”尤不可少,若文胜质亡,也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了。这样,“文”与“质”的关系就决定了文学的“具神思”(Ideal)、“能感兴”(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三种特征,三者以“意象”、“感情”、“风味”为媒介(Mediums)共生共存,从而汇为上乘“文章”。
关于文学的使命问题,西人常言“著者极致在怡悦人情”,我国则素有视小说为闲书一说,而在周氏看来,“美致”不应代表一切,刻意于兴趣,美感只能使文学作品沦为末流,或陷入“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arts sake)的泥潭。鉴于此,周氏提出了“虽非使用,而有远功”的文学使命观,其具体表现如下:一、裁铸并阐发“高义鸿思”:真正的文学作品应“博大精采”,以传诸人心,使读者能得闻妙理,豁然贯通,并最终“进于灵明之域”;二、阐释时代精神及人情:文学能忠实再现特定时代的国民精神及人生性情,盛世文风势必渊朗,衰时文运自会萎靡,因此文学首在书写人世兴衰及人生悲欢,文学家将人间情状“铸为鸿文”,从而使读者能“朗鉴人事之微”;三、“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进于高尚”:意旨阐发离不开意象化生,文学家只有思入神明,脱绝凡轨,其作品才能“不滞于物”,发扬“神思”既有助于作者祛除名利思想,又可让读者摆脱功利观念。
至此,周作人完成了关于文学诸多问题的全面反思,其中既有对现代西方文学观点的批评与借鉴,更不乏对我国传统文论思想的继承和扬弃。可以看出,周氏文学思想的基点一开始就是搭建在中西对比与对照平台上的,而正是凭借这样的平台,他才有可能在消解中实现建构,并继而完成一种全新的文学思想的重构。
5.重构:溯“本源”于“浊流”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文学的界定一直是模糊不清的,究其大概,可见于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语。自古以来,为文者无不以此为臬极,“上宗经典,非足以弼教辅治者莫与于此”。其结果是,凡论文之士,每言必不敢失于常轨,历世因陈,遂成固习,如《文心雕龙》即因为耽于旧说而落入窠臼。刘勰虽可称“弥纶辟言”,但却依旧“敷赞圣旨”,极力称颂文学的功利效果,所谓“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条条无不为儒家诗教所规。
近代以降,文学或被与科学相提并论,或与一切艺术混为一谈,或曰离开治化文学不能独存云云。凡此种种,至清末年间,我国文论界已不啻陷入一片“浊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作人开始对“文章”(即“文学”)一事进行正本清源并重新建构。他指出,从原始变迁来看,文学发展常与史实相吻合,因而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必有其独特之处。就我国而言,文学的发展之所以滞后于其他国家,“正以唯吾国有孔子故”,自孔子删《诗》定礼始,即如《风诗》一类的诗中极品也常被作为圣人之书而备受推崇。所谓“言必宗圣”,一切均以儒家诗教为指归,就连作为辞赋之宗的文词丽雅的《离骚》也与《国风》一起被归于诗类。此外,尚有两股“浊流”需要澄清:一是“文如其人”,如《中国文学之概观》将宋玉等人贬为“徒富文才而少理想”之流,另如司马相如、建安七子诸人也均被斥为“文不逮行”之徒,在周作人看来,以人弃言终究是无稽之谈;二是“载道明德”,如《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与《中国文学之概观》(陶?曾)均将不切于实用文学创作视为空谈,而周作人则认为,我国传统文学长期“溷于士业”,文学之士人人统于一尊,儒风“扇虐”如此,只能会导致文气衰弊、民气凋丧的后果。
周作人的忧心并非没有道理,如当时虽然译著小说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本源未清,浊流如故,小说或仍被视为文学中的末流,或只徒有文学之名而仍未有真正进入文学之列。以《中国文学史》为例,作者即认为新译小说诲盗诲淫,其恶不可赦,译者当有杀戮之罪,译书也应火而焚之。周作人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谓小说“诲盗诲淫”,荒谬程度实不亚于“诲道德”一说,至于“戮其人而火其书”者,荒唐之极更可与秦皇比肩。此外同样荒谬的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竟将希腊神话视为迷信小说,周氏更是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驳:此言竟出于一代大儒之笔,实在是国人的奇耻大辱。他认为,上述种种怪论无不是功利主义作祟的必然结果,由此他提出了小说的文艺学观点:小说必须能够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譬如历史小说首先当为文学,其意不在教人历史,他如哲理、科学、教育诸类小说也自当如此,然而在文学功利主义作用下,《海外轩渠录》等翻译小说均被译者贯以道德、实业之名,另如《双孝子喋血酬恩记》之类也被牵入政海波澜诸事,所谓“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实令人有不伦不类之感。鉴于此,周作人指出:“夫小说者,文章也,亦艺术也。”换言之,文学是国民精神的体现,精神美大,文学自会繁荣,同样,即使精神衰微,也可借文学加以补救,就其性质而言,文学虽非实用,却能于不远的将来显示其功效。然而观目下情状,却又不能不令人担忧:数千年来,儒道肆虐本已使文运日下,如今新流继起,则文学再次陷入功利主义的浊流,因此于当下而言,文学改革势在必行,改革之道别无他途,一者应将文学从儒学之士手中解放出来,使其亲于万民,用于百姓,二者应将文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从而使其真正进入艺术殿堂,唯有如此,才能借文学开启新机,使国民思想得以舒展、国民精神“进入美大”。至此,通过对“本源”的追溯以及对“浊流”的疏通,周作人顺利地完成了由消解到重构这一崭新的文学思想演绎过程。
应当指出的是,清末民初年间,在西方现代思想的观照下,种种新的理念早已开始崭露头角,就当时情况而言,“旧泽已衰”确乎属实,但“新潮弗作”似乎并非尽然。事实上,当时种种“新流继起”的现象大都是非建构性的。以晚近出现的“诗界革命”为例,作为这场改良运动的肇始者,黄遵宪虽曾对“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的传统观念提出过批判,且发出过“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豪言,但从他所谓的“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以及“凡(古代)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等思想来看,“诗界革命”从一开始即表现出了对传统诗学观进行非本质改造的倾向。
对于改良派旧瓶装新酒或者相反的取道,周作人是不以为然的。与改良派相比,周氏之于传统的态度可谓“爽快”多了,当然,这种“爽快”主要还是表现在消解一面,如果说有什么继承的话,那便是周氏一方面对文学进行了正本清源,同时将功利的“益智”与审美的“移情”说加以改进并融入了自己文学观点的建构。这应该是一种折衷的观点,它的两个极端分别见于梁启超的小说启蒙学说以及王国维的小说与诗歌美学观点,在梁启超那里,小说的“益智”功能几乎成了根治政治及社会痼疾的万能良药,而在王国维眼中,文学的情与美则能“使吾人超然于厉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从而完全进入纯粹的审美观照的空灵境界。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也见于鲁迅《摩罗诗力说》一文,鲁迅一方面指出:“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但同时又将文学的社会功能夸饰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想”,“人文之遗留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然而这对矛盾终究无从在文学能“撄人心”的呼声中协调起来,尽管它所展示的是鲁迅所追求的精神解放与政治图存的双重现实要求。比较而言,周作人把对传统的消解与重构置于整个西方文学思想的大背景下进行操作,这无疑能将上述两种思想更为理想地融合与协调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建设者中,周作人才会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