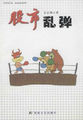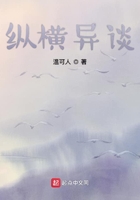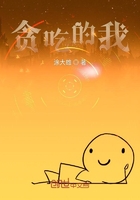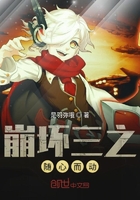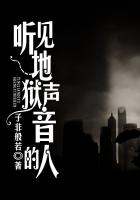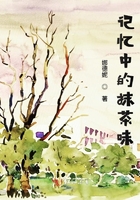“《幽怀》赋好欧公赏,《实录》文高黄子称。《复性》一书几有道,千年真可续韩灯。”这是宋朝诗人徐钧所写的一首吟人七绝,诗名《李翱》。
整首诗平平无奇,然尾句忽掀波澜,于无声处陡落神来之笔,用一句“千年真可续韩灯”,来状写李翱承继师志,以《复性书》为韩愈之学通向后人架竹引泉,接衲传灯,真是精彩之至!
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常常是与柳宗元联袂,并称“韩柳”,他们用不羁之笔横扫千秋,站在“唐宋八大家”之首。
而在中国哲学史上,韩愈却是与李翱并肩,合称“韩李”,他们用心性论排佛挞老,重彰儒旨,高标道统,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意义。虽紧牵韩愈衣襟,将天道观发扬光大,但李翱慧眼独具,又别出心裁,用自己的《复性论》弥补乃师《性三品》的理论缺点,从而推陈出新,打理出儒学深究义理的一番新天地。
一派葳蕤茂盛、云蒸霞蔚的宋明义理之学,最早对之培土施肥、栽花育红的那个人,就是李翱。
欧阳修曾深为服膺地说:“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
一
李翱,字习之,郡望为陇西成纪,里籍则是汴州陈留。生于公元七七二年,唐代宗大历七年,死于公元八四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其先祖为十六国时期西凉缔造者武昭王李暠。史称,李暠“通涉经史”,“玩礼敦经”,尤善文学,是五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著有《靖恭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以《述志赋》最为有名。同时,李暠还颇重儒术,珍才知人,在他倡导影响之下,西凉政权所在地敦煌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五凉文化的鼎盛时期。
陇西李家有这样一位重儒好文的先人在,历经岁月沧桑,终于又走出一位《旧唐书》称之为“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的李翱,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虽然家道中落,累世不耀,而且到其父亲时,甚至连名字也不为史籍所留,但李翱的青少年仍然因循着几乎所有中国传统世家子弟都必走的一条成长线路。他在《复性书》中自道:“吾自六岁读书,但为词句之学。”六岁发蒙,继而接受传统儒家经典教育,在一知半解中吟咏章句,于莫名其妙里领会训诂。
到十五岁时,随着对儒学的逐渐深入了解,他开始廓清思路,不再执著于两汉以来的儒家经典注解、义释之类文字,而是将兴趣点转到了孔孟的原旨性经典文论之中。李翱在《与淮南节度使书》中说:“自十五以后,即有志于仁义,见孔子之论高,弟未尝不以及物为首。”
于李翱而言,这不是个简单的阅读兴趣转移,而是一次于其一生而言都至关重要的学术转身。
正如他在《与淮南节度使书》中所言,十五岁的他相当深刻地认识到:“近代已来,俗尚文字,为学者以抄集为科第之资,曷尝知不迁怒、不贰过为兴学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为贵富之路,曷尝以仁义博施之为本乎?由是《经》之旨弃而不求,圣人之心外而不讲,干办者为良吏,适时者为通贤,仁义教育之风,于是乎扫地而尽矣。”
李翱明白,沦为科考器用的经学形态的儒学,已经背离了其原初本意,丢弃了返身归诚,践形尽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对真理的自我体认与存养。要找寻儒家的原旨,那么就要推开烦琐章句,舍传就经,求经明道。
而这种思想,深深吻合了同时期另一位儒学大师的观念,他就是韩愈。
唐代卢仝曾著《春秋摘微》,写作时他直抒胸臆,解《春秋》而不用传。韩愈就对这种做法深表嘉许,他在《寄卢仝》诗中夸赞:“《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还比如以精通《毛诗》而名震一时的施士匄。他不拘泥成说,不墨守古训,而是按照自己的思想自由发挥,讲解《诗经》。在讲“维鹈在梁”一句时,施士匄说,“梁”系人取鱼之处,义在鹈鹕当自求食,不应于人梁上取鱼,譬喻人自不行善,反贪天之功。韩愈为他写的《施先生墓铭》中大为赞赏:“古圣人言,其旨微密;笺注纷罗,颠倒是非。闻先生讲论,如客得归。”
韩愈自己在《读仪礼》一文中也说过,他曾将《仪礼》一书“掇其大要,奇辞奥妙旨著于篇”,看得出,他所采取的方法显然正是摆脱章句,弃传求经。
如此两个独有己见、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会在人生前行的路上相遇,惊讶地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然后走上前去,双手紧握,从此用牢不可破的友谊永久牵系一处。
只是,此时十五岁的汴州少年李翱,与正在长安应试尚悄然无名的十九岁韩愈,彼此无识,互不知名。
“时光啊,在你的引领下,我一路聚会着我的友人。”惠特曼如此诗意地说过。倘这个声音能够穿越到中国唐朝,李翱与韩愈一定会相视一笑。
二
公元七九三年,贞元九年,李翱参加州府贡举考试,举乡贡拔解后,如同七年前只身赶赴长安寻求功名的韩愈一样,李翱也带着自己的人生希冀来到这里。
长安,会以怎样的怀抱来迎接这个异乡青年?
如同那个时代的每一位属词求进之士,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李翱于科考前,“执文章一通,谒于右补阙安定梁君”。这位梁君不是别人,正是韩愈年轻时向其学习古文之法并在科考中得其大力推荐的名儒梁肃先生。
梁肃,少年即师从天台宗荆溪湛然禅师,他融合儒释,提倡“明静复性”。梁肃在这时已经誉满天下,拿着自己的文章造访其门,求其过目者,盖无虚日。
真是好眼力!李翱文章中所弥漫的飞扬文采、遒劲古风,立刻让梁肃赞誉连连。初见之下,梁肃即说李翱颇得古人之遗风,并期待李翱之名将来会不朽于无穷,当场表示要为李翱“拂拭吹嘘”。
多年后,李翱游走于公卿朋友之间,他往往会听到素未谋面的陌生者说,我早在梁先生嘴里听到过你的大名,李翱方知这位老夫子当初当面许诺“拂拭吹嘘”,真不是一句应酬中的客套话。
然而,这样一位见善能知,知而能誉,誉而逮夫终身之久的伯乐,却于李翱拜访之后短短三个月死去。
梁肃死去后再无人推荐,这使得李翱此后连续五年,一再铩羽考场,“每岁试于礼部,连以文章罢黜,声光晦昧于时俗”。他为此写下《感知己赋》,感叹有古君子之风的梁肃死之太早:“不幸梁君短命遽殁,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谁能相继梁君之志而成之欤?已焉哉!天之遽丧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迍邅厄穷也。遂赋知己以自伤。”
全赋郁愤难抑,苦闷彷徨,读来甚为凄恻:
戚戚之愁苦兮,思释去之无端。彼众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难。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兹之世。独厄穷而不达兮,悼知音之永逝。纷予生之多故兮,愧特于世之谁知。抚圣人教化之旨兮,洵合古而乖时。诚自负其中心兮,嗟与俗而相违。趋一名之五稔兮,尚无成而淹此路歧。昔圣贤之遑遑兮,极屈辱之驱驰。择中庸之难蹈兮,虽困顿而终不改其所为。苟天地之无私兮,曷不鉴照于神?心劲直于松柏兮,沦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岂吾道之已而。
有意思的是,在李翱纡郁不得志地奋笔疾书《感知几赋》时,正在汴州、徐州做佐幕的韩愈,也落落寡欢地写下《复志赋》,叹人生偃蹇,抱志不抒:“固余异于牛马兮,宁止乎饮水而求刍?伏门下而默默兮,竟岁年以康娱。”
两处尴尬境况,一样沮丧心情!
请记住二十七岁的李翱说的这句话:“昔圣贤之遑遑兮,极屈辱之驱驰。择中庸之难蹈兮,虽困顿而终不改其所为。”
一语成谶!他此后一生中的遭际,都将为这句话准确命中。
在学术上,他取资《中庸》而言性,对仁政王道及其性情理论作出学理上的宏大铺排与阐发;在仕途上,他凄凄惶惶,流落辗转,始终位居下僚,忍辱驱驰,困顿不堪。
这中间,他结识了韩愈。
公元七九六年,李翱第三次落第,心灰意冷的他前往徐州,意欲在徐州节度使张建封那里谋个差事,未果后由徐州返回故乡汴州,韩愈此时刚刚出仕,为汴州刺史署观察推官。
两人相遇了。韩愈找到了知音,李翱则找到了老师。
公元七九七年,第四次考场失利之后,李翱回到家乡,正式跟随韩愈学习古文。此时,孟郊恰好寓居在汴州,张籍也游学至此。天意使然,或因考场或因仕途的种种窘困与失意,四位光耀中国文化史的文豪诗宗,竟然齐聚小小的汴州城。
他们以酒设场,谈文论道,彼此诗歌酬答,相互探研学问。李翱与韩愈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师友之情。
公元七九八年,时年二十七岁的资深考生李翱终于登进士第。余光中说过,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红烛昏沉的一打少年听雨,不用去想了;僧庐下的三打白头听雨,也可以暂时用不着去考虑;单是这客舟中江阔云低的漫长而乏味的中年听雨,就已经让人烦不可言。
韩愈就是榜样,他从进士及第到首次出仕,耗时整整四年,而且最后靠的还是自己的学名,以及与汴州刺史董晋的私人交情。历经漫长五年的礼部考试,李翱再也无心恋战出仕前必须经过的吏部考试。
公元七九九年李翱南游吴越,观涛江。南游的途中,他向同行观潮的吴郡陆参说:“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惟节文、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耶?”
陆参深以其言为是,并鼓励他说:“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
一场观潮之行,却促成了一篇中国儒学思想史中有重要影响论著的问世。
在陆参的肯定与鼓励中,李翱为“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于是撰著《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人。如同扬雄写下《太玄》时那份揽辔自雄的神情,李翱也相当自负地认为:“夫子复生,不废吾言。”
三
针对中唐时佛老昌兴,儒学低迷,韩愈在儒家经典《大学》中寻找批判武器,提出“性情三品”说,以此驳击佛教追求清静寂灭的心性说。
然而,当韩愈把人之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之时,其实也就堵住了一条逻辑之路,即人人皆可以修养心性,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不断自我心灵回护与完善,达到人格与道德的自我提升。
那么,这一理论设计就与佛教所倡导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也与道家所声张的“人人可修炼得道”等观念相异,有了理论上的明显缺陷。或者说,韩愈的“性情三品”说根本无法推翻佛教的心性说。
李翱发现了这一明显的理论缺陷,于是他超越老师韩愈向前迈了一步,引借另一部儒家经典《中庸》中思孟学派的思想传统,着重从圣人之性与百姓之性无差别处入手,建立以儒家德性为主体、以性命为中心的“天人合一”伦理价值体系。
他直截了当地提出:“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他认为,人性并不能简单地分为几品,事实上,性的善恶只与情相关,就性的本质说,人人都可为善,只是因为情的遮蔽,于是才有了或善或恶的情之表现。“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变来,故性不能充也。”
“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者邪?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末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
他提出,教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恢复被情所蔽的人之本性。
其实,这也是荀子早就说过的“化性起伪”,同时也是孟子的性善论本源。这就在理论上肯定了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使得儒家的心性论完全可以与佛教的人人可以成佛的佛性论相抗衡。
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李翱用《中庸》中的“至诚”概念,提出人人通过内省心性,然后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由物而及天地间一切,“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如此,便能完成个人的修身养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
李翱为“诚”所下的定义很特别:“诚者,圣人之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则能归其源矣。”返身归诚,既是实现复性的过程,也是复性的最终目的。
之所以说李翱对“诚”所下定义特别,是在他的上述叙述中,明显能听到来自佛道二家经典中的音韵与气息。
事实上,援释借道化为己用,然后以修缮一新的理论站在儒家立场上抗衡佛道,是李翱的显著特色。朱熹比较眼尖,他说李翱“只是从佛中来”,“至说道理,却类佛”。章太炎说得更通俗晓畅,说李翱“里面也取佛法,外面却攻佛法”。
四
尽管援佛入儒,但与范缜、韩愈一脉相承,李翱也是坚定地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极力排斥佛教。
他在《再请停率修寺观钱状》中说:“佛法害人,甚于杨墨。论心术则不异于中土,考教迹实有蠹于生灵。浸溺人情,莫此之甚。为人上者所宜抑焉。”这很像范缜声严色厉所说“浮屠害政,桑门蠹俗”。
在《去佛斋论》中他同样指出:“舍圣人之道,则祸流于将来也无穷矣。佛法之所言者,列御寇、庄周所言详矣,其余则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于中国,则其为作也必异于是,况驱中国之人举行其术也?”原因是,要建立一个上下有致的社会,使得“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存有所养,死有所归,生物有道,费之有节”,那就得回到儒家的道德仁义那里,因为“自伏羲至于仲尼,虽百代圣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举而行之无弊者,此圣人之道,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养之以道德仁义之谓也,患力不足而已”。
但与韩愈的至死不与佛教妥协,虽身万灭而不改不同,李翱虽然基于儒家立场,一生排佛驱道,但他同时又将佛道作为一种有益拓展自己深思的学问而加以积极汲取。
与佛道中人的颇多交往,也正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兼容并包。
比如,就在写下《复性书》的公元七九九年八月,当他北还至泗州时,遭受水灾与火灾而损毁的开元寺刚刚修复完毕,为记其事,该寺僧人澄观铸大钟悬于寺楼,特邀李翱为其题写钟铭,李翱为之写下了《泗州开元寺钟铭(并序)》。没有他们之间历久而弥坚的私人友谊,反佛的李翱不会欣然为庙钟命笔,同样,澄观和尚也决计不会找一个整天对佛嘟嘟囔囔的人来写。
还比如公元八二一年,李翱出任朗州(今湖南常德)刺史。佛教著名高僧惟俨禅师就驻锡他治下的药山道场。
药山禅师,俗姓韩,唐沣州人,少年敏俊超群,素怀大志,曾说:“大丈夫当有圣贤志,焉能屑细行于布巾邪?”遂舍弃世俗,投石头禅师门下修行,后因住在药山而声誉震遐迩。
《宋高僧传》卷十七记载了李翱与惟俨这次充满禅机的相见:
(李翱)初见俨,执经卷不顾,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倡言曰:“见面不似闻名。”俨乃呼,翱应唯。曰:“太守何贵耳贱目?”翱拱手谢之,问曰:“何谓道邪?”俨指天指净瓶曰:“云在青天水在瓶。”翱于时暗室已明,疑冰顿泮。
于是,就有了李翱这两首著名的诗作《赠药山高僧惟俨二首》:“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披云月下,崇冈长啸,后首诗营造了一种独对自然,悟证天地至理的朗阔境界,为后世文人或禅者纷纷效法。
前首诗中“云在青天水在瓶”更是名播千秋的佳句,短短数字,气象无穷,使人胸襟大开,为此引发了后世众多儒学中人与禅门佛子的追慕心仪。宋时僧人北海心作偈:“云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胆向人倾。黄金自有黄金价,终不和沙卖与人。”冯友兰常常应邀给人题字,多选唐人李翱之诗,他尤喜“云在青天水在瓶”此句。
此外,李翱与观中道士也多有往来。他在《赠毛仙翁》诗中写道:“紫霄仙客下三山,因救生灵到世间。龟鹤计年承甲子,冰霜为质驻童颜。韬藏休咎传真箓,变化荣枯试小还。”
这些题赠之诗,反映了生活中的李翱不仅不拒佛道中人,反而心有所向,欣然交接。
也正是在与高僧、道士的交往中,他才能探佛窥道,深悉佛道之说,从而找出佛道思想体系之中的狂悖之处,加以准确批驳,并汲取有益于儒学的成分,援佛道入儒。
他深刻认识到,对于佛老之学,“惑之者溺于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虽辨而当,不能使其徒无哗而劝来者,故使其术若彼其炽也”(《去佛斋》)。
其实,他这是对乃师韩愈的婉转批判。
韩愈不谙佛经,态度坚决乃至粗暴地认为,对待佛教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李翱深知其中的理论缺陷,故而,他能够着重从心性层面来排佛,《复性书》完全可以看作是儒家的性情学说。
在《复性书》中,李翱认为人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圣人制礼作乐就是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是个“尽性命之道”的旅程。而他所做的学术努力,正是对孔孟仁政学说的继承和发挥。
由此,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屹立为一座高峰。
五
但,李翱在现实中却是尴尬而岑寂的。
直到公元八〇〇年,二十九岁的李翱依然顶着个空空的进士及第帽子,无枝可依。
这种飘零状态反映在两个方面:在仕途上,尚没有一官半职,无业可就;在生活上,抱穷独处,还是光棍一条。
深爱李翱之才的韩愈,此时自己也只是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麾下的一名小小幕僚推官,还无力襄助李翱在仕途上落脚。韩愈唯一可做的,就是向孔子学习。孔子将侄女嫁给了德才兼备的弟子南容,韩愈也要给李翱一个侄女做媳妇。
这年五月,韩愈将从兄韩弇的女儿许配给李翱为妻。从此,李翱与韩愈在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上,更上一层楼。辈分上他已是韩愈先生的侄婿,尽管他只小韩退之四岁。
同年九月,李翱被滑州节度使李元素辟为观察判官,正式走上仕途。公元八〇六年,元和元年,唐宪宗即位,李翱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他被任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而且非常让人惊喜,他与韩愈共职,一并分司东都。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牛僧孺、李吉甫之间互起抵牾,并很快扩大并弥漫至朝中两派。在牛李党争中,户部侍郎杨于陵因上书谏牛僧孺之非,被执政所怒,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隐约牵涉牛李党争中的李翱,于公元八〇九年受杨于陵之聘,前往广州,韩愈也同时改任都官员外郎。
临行前,好友孟郊写下《送李翱习之》赠别,其间的“壮年俱悠悠,逮兹各焦焦。执手复执手,唯道无枯凋”,道出了他们之间不忍割舍的深厚友谊。但与韩愈的《送李翱》相比,后者又多了一份年长者对出门远行晚辈的纤细牵挂与担忧,以及对天各一方的深深无奈。
韩愈在诗中写道:“广州万里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揖我出门去,颜色异恒时。虽云有追送,足迹绝自兹。人生一世间,不自张与弛。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宁怀别时苦,勿作别后思。”
通往岭南的路山重水复,路途遥迢,韩愈曾经在被贬连州时亲自品啜过长途跋涉的艰辛。一句“揖我出门去,颜色异恒时”,细腻地刻画出双方各自强压在心中的分别之痛,让种种欲说还休的酸楚滞于心头。“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又道出了诗人叹息人生如寄,不能左右的无奈。
那就什么也不要说,只将这轻轻的一页诗笺,化作自己的无限牵系,跟着李翱一路向南吧。
送行者与被送者早已消遁在历史的沉烟落香中,而这首赠别的诗却还有着当初的温度,仍墨汁淋漓地鲜活在《全唐诗》中,这是诗歌的生命长度。
时光啊,你带得走歌者,带不走诗。
次年,杨于陵很快为唐宪宗原谅,又回到京城做起了他的吏部侍郎,而李翱却因罢幕而失业了。此时,因遭贬而为宜歙池观察使的卢坦向他送来请柬,李翱遂成为他的幕僚判官。
很快,卢坦又升迁回京,入为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留下的,仍然是英雄失路的李翱。此后,他又走到浙东观察使李逊麾下,担任起官职名字颇长,职位却很低下的“浙东道观察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使”。
从公元八〇九年到公元八一三年,自写下中国第一篇日记体游记《南来录》后,李翱像个辛勤而不走运的钟点工,频繁地游走在各家屋檐之下。相对于他元和之初的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此时担任的幕僚之官也更为卑下。穷极无聊之中,他用写史来打发时光。
这种说法其实很歪曲李翱。李翱撰写《唐史》的初衷,绝非是以此消遣岁月,而是出于儒者正天下是非的自任情怀。这很像郁怏孤愤无以寄怀,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的刘知几。
李翱在写给好友皇甫湜的《答皇甫书》中将此襟怀袒露无遗:“仆近写得《唐书》。史官才薄,言辞鄙浅,不足以发明高祖、太宗列圣明德,使后之观者,文采不及周汉之书……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韩退之所谓‘诛奸谀於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
遗憾的是,也许正因他写的是“不刊之书”,所以今天的我们已无从拜读他的《唐书》。《新唐书·;文艺上》只留下了如许评价:“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如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李翱也因其巨大的文名掩盖了其儒家宗师的地位。
他们,原本该在《儒学列传》中拂须端坐。
六
很少人知道韩愈与李翱曾联手注解过《论语》。
他们有部合著叫《论语笔解》。《论语笔解》分上、下两卷,文中先述《论语》原文,再引马融、孔安国、包咸等人之注解,之后是韩愈、李翱的见解。
在韩愈、李翱之前,解《论语》者无数;在他们之后,注《论语》者也无数。但《论语笔解》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一反汉儒家法,侧重以“理”解经,以“心”解经,附以己意,直逼经义,对经文随意增减,对先儒的注疏则是依据自己所谓的“圣道”进行修改。这就对钦定的官方经学,孔颖德的《五经正义》首次进行了学术挑战。
明朝的郑鄤如此说这部书:“昌黎文启八代之衰,李习之一时齐名。读《论语笔解》,始知其原。圣人既往,微言犹存,参而究之,若破坚壁,亦何妨互有出入,乃其得处,已如见圣人之心于千百载之上矣。”
这是段非常重要的学术评论。
因为自韩李注解《论语》,治经之风陡然一变。他们一反两汉以来儒家治经家法,又不同于南朝“玄而为虚”的离经之说,侧重以“理”解经,以“心”相印,然后附以己意,根据自己所抱儒旨“圣道”直接解说。
此法一出,表明了经学研究的方向性转折,注重理义的宋学由此訇然打开大门。
该书对《论语》的解读,呈现出完全迥异于先儒的两个方面:
根据经义上下逻辑关系,认为《论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以讹传讹之嫌,因而他们大胆改动《论语》原文不通之处;对只着眼《论语》字面,而未进行深究的穿凿附会的前儒解释坚决予以摈除。这就是李翱所说的:“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
遵循儒家原旨,以己意解经,这是《论语笔解》的显著特征。
比如,就《论语·学而》中的“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韩愈认为:“正谓问道,非问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释之,则事与道混而无别矣。”李翱认为是:“凡人事、政事皆谓之事迹。若道则圣贤德行非记诵文辞之学而已。”理由是孔子说过:“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此称为好学。”这就比孔安国所注“有道,有道德者。正,谓问事是非”要高明很多。韩愈区分了事与道的不同,李翱则顺题而论,显然不是出于先儒的考据招数,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好学”,不是知识性学习,而是德性之学。
还比如,《论语·公冶长》中的这句:“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包咸曾这样注解:“既然子贡不如,复云‘吾与女俱不如者’,盖欲以慰子贡尔。”
韩愈对之摇头,他提出反对意见:“回,亚圣矣。独问子贡孰愈,是亦赐之亚回矣。赐既发明颜氏具圣之体,又安用慰之乎?”韩愈认为包咸丢失了孔子讲话的原旨。
李翱进一步阐说:“此最深义,先儒未有究其极者,吾谓孟轲语颜回深入圣域云,具体而微,其以分限为差别。子贡言语科,深于颜回,不相绝远。子贡谦云得具体之二分,盖仲尼嘉子贡亦窥见圣奥矣。虑门人之惑以谓回多闻广记,赐寡闻陋学。故复云俱弗如,以释门人之惑,非慰之云也。”李翱的解释,秉承乃师之意,不仅超越了包咸的字面理解,而且深化了孔子的圣境。
《论语·公冶长》中说:“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针对孔子批评宰予白天睡觉,韩愈说:“‘昼’当为‘画’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诛。”韩愈认为,“昼”是“画”字的讹误,因为繁体字中,前者为“晝”,后者为“畫”,非常接近。李翱也引申说:“仲尼虽以宰予高闲昼寝,何责之有?下文云,于宰予言行,虽昼寝,未为太过。使改之不昼亦可矣。”在李翱看来,宰予是孔子的高足,宰予即使昼寝,使其改正也就罢了,何以责怪呢?
这就是李翱与韩愈的别出心裁之处。
而且,他们在对《论语》的解释中,感觉义不通畅之处辄加以修改。他们对《论语》原文的改动,几乎占全书的八分之一,从而开启了宋明时代的疑经风潮。
七。
一个光耀万古的学术大师,他注定在生存的世间蓬头垢面,步步窘困。
公元八一九年,就在韩愈维护道统立场,勇敢上《论佛骨表》而被贬广东潮州之时,李翱回到了长安,重新担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此后,他虽在朝廷短暂担任过考功员外郎、谏议大夫、礼部郎中,但因他“性峭鲠,论议无所屈”的天性,持正方刚,拙于周旋,甚至对当朝宰相李逢吉都当面斥责其过失,所以他“仕不得显官”。李翱先后出任过朗州、舒州、郑州、桂州、潭州、襄州等刺史,他的官场履历更多是消磨在地方,于基层打转。
公元八三五年,六十四岁的他死于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而他的老师韩愈已经谢世十一年之久。从此,“韩李”成为一个专门的词汇恒定在了儒家学术天空之中。
宋人叶梦得并说韩愈、李翱之儒学贡献:“二人要不可偏废,将以正人,则不可无退之;将以自治,则不可无习之。”
韩愈重振儒家孔孟道统,功高盖世,但其理论建设并不完备;李翱援佛入儒,拾柴旺火,弥补了韩愈道统的学术缺陷。在他们共同舍传求经、以意改经、原经求道、依经立义的重大开拓性努力下,逐渐偏于“外王”的唐朝儒学得到纠正,重新着意于“内圣”,向心灵自修与道德提升方向转型——由“五经”系统向“四书”系统转型,起到了示范和引导的作用。
正是李翱的《复性书》,融佛于儒,补充并完善了儒学在心性论方面的理论不足,大大丰富了儒家思想,为讲性究情、辩理别欲、追本溯流的宋明理学首开先声。
韩退之于《大学》的发幽见明,李习之于《中庸》的独有新见,对宋代学者明确《四书》为儒家核心思想的学本,将传统儒学内容从《五经》转向《四书》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李翱曾写《戏赠诗》一首:“县君好砖渠,绕水恣行游。鄙性乐疏野,凿地便成沟。两岸值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砖凿可自修。从他后人见,境趣谁为幽。”
读之,就令人联想到另一首脍炙人口的充满理义之思的宋人之诗。它是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隔着时光的隧道,两位大师隔空传音,前呼后应。也许,这中间所透露的,正是宋明理学在唐朝令人惊喜的首次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