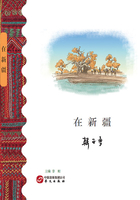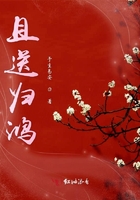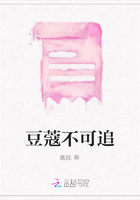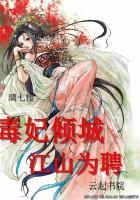“分子”本是来自日文借词,用以指称具有群体属性的个人,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被用来指全体国民的各个成员,反映了世纪初的民族国家意识。当“分子”一词最初出现于汉语世界中,蔡元培就曾说过:“凡分子必具有全体之本性;而既为分子,则因其所值之时地而发生种种特性;排去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则即全体之本性矣。”《世界观与人生观》,《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五四以后,“分子”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转用来代指属于某个团体或具有团体性质的各个人,如“工人分子”、“革命分子”、“中坚分子”等。从“知识阶级”到“知识分子”的话语转换中,权力支配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这个词代指的仍是群体,因而保留了知识者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指称个体,使之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它既可用于“我们”,也可用于“我”。而在“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中,无疑也包含了“我是一个集体的成员”之义。知识者不再被看作一个纯粹的整体,而是被“分子”化了。
就话语构成而言,知识人的“分子”化反映了现代权力运作的本质。正如福柯所说,这种权力既是一种总体化的力量,同时又是一种个体化的力量,在个体化意图上它继承了以拯救为职责的牧师权力。一方面,它抽绎出知识者的特质,使他们合并到规范化和趋同化的知识结构之中。“知识分子”与日语“知识人”的不同,就正体现了这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分野。另一方面,它强加给个人感知自我的方式,即“对个人进行分类,按照他自己的个体性来标识他,将他与他自己的身份联系起来,强加给他一种真理的法则,而这种真理的法则是他必须在自己身上认可的,而且也是其他人不得不在他身上认可的”MichelFoucault,“TheSubjectandPower,”inPower:TheEssentialWorksofMichelFoucault,1954—1984,VolumeThree,EditedbyJamesDFaubion,NewYork:TheNewPress,1997,p331.。因此,“知识分子”一词正是福柯所说的权力的“个体化”形式,其内在含义既为先锋桥梁理论提供了言说方便,也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附理论留下了话语空间。由于个人被束缚于自己的阶级出身与专业身份,知识者的标准不再是传统士人的弘道精神,也不是西方Intellectual的良知意识,而是如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发表的《五四运动》所言:“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通过这种建立在总体化基础上的个体化形式,中国现代知识者遂获得了一种否定性的主体性,其依附性质和工具人格不断增强,而弘道精神或自由意识则不断失落。
当然,阐释仍然在继续,但历史内容已经不过是这一话语构成的填充物。此后的岁月中,“知识分子”被一次次地塑造,从“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再到今天的“知本家”,但这个称谓却始终没有改变。在一个更加严格的身份和科层社会中,它所内含的依附于某个利益群体的葛兰西式定义,构成了话语本身的在先约束。只要我们使用这个称谓,我们就摆脱不了它的权力话语。换言之,在当代中国只有“知识分子”,而没有“知识人”。
传奇的年代
只要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就不难得出结论:相对1949年以来各个时期,小说的创作是繁荣多了。就像在教科书中常见的那样,“新时期文学”依然是一个以政治史划线的概念。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子,是由于政治对生活的影响太大。然而,当代文学提出的问题始终是,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有理由怀疑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价值,倒不是因为它们太过于贴近政治,而是因为它们远没有写出生活的真相。
新时期文学肇始于1977年,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轫作,但标志却是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今天看来,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粗浅的感伤故事,缺乏细密的生活质地。然而就是这种描写政治歧视的主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同情,导致“伤痕文学”问世,如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韩少功的《月兰》、郑义的《枫》、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这些作品大都是揭露“文革”中造反派的残忍和群众的愚昧,目的在拨乱反正惩恶扬善。“文革”的灾难被归罪于“四人帮”的阴谋,被看作是历史进程中一次偶发事件(有意思的是,通常这被称作历史唯心论),生活的冲突因偶然而获得一种戏剧性。时代是沉重的,又是慷慨的,它把过往一切年代的传奇要素都提供给了人们:坏人当道,好人落难,悲欢离合,善战胜恶。
有关“真实”的问题于是被一再提出。在当代中国,真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涉及事物本质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批评家们按照歌颂光明的主旋律,指责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不够典型,违背真实,而读者来信却言之凿凿地证明实有其事。争论的双方都以真实为武器,批评家们不再扣政治帽子,却试图控制“真实”话语,民众也以同一种语言予以回击,甚至显得比主流意识形态还要浪漫迷思(“文革”中还有什么苦难传奇不能发生呢?),仿佛越是生离死别的故事越能引起同情和义愤。在某种意义上,批评家们是对的,真实的概念包含着本质的规定,只不过在他们那里,这本质是被派定的,而不是被发现的。那个时期作家的受欢迎其实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文学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唯有通过它来表达内心的感觉。
然而,伤痕文学显露出来的底子实在太薄,作家们大都是初登文坛的新手,多年的文学教条和封闭隔绝,造成他们的作品激情有余而底蕴不足。情节多半是概念化的,缺少性格的刻画,细节的描写,和心灵经验的重构。伤痕文学可说是一次集体的创伤记忆,因为要符合权力话语,记忆成为可发表的记忆,一种有选择的遗忘。权力者对无权者的暴政,被重构成“文革”当权者对老干部和群众的迫害。这种善恶的二元对立一旦消失,光明自然会随之而来。于是为了记忆的文学,变成了遗忘的工具。几年以后,一位作者回忆当初编辑对其作品的删改,仍然感到懊悔:“我对那个时代特别憎恨,但我却用笔赞扬了它。”Leung,Laifong,MorningSun:InterviewswithChineseWritersoftheLostGeneration(Armonk,NewYork,London,England:MESharpe,1994)一书中对陈建功的采访。这番话倒是有力地印证了福柯的说法,即在权力的操作下,言说主体并非话语的依据,而是被话语所塑造的对象。
一些青年作者,如王安忆、徐乃建、史铁生、孔捷生、陈村、梁晓声等,则着力描写70年代的知青生活。这些人成为作家大都在返回城市之后,一当他们发现,自己既不属于农村又不属于城市,遂产生了强烈的怀旧之情(如史铁生《我遥远的清平湾》)。青春、爱情和革命的迷惘,借着上山下乡的经验,获得了一种时代的成长美学。而一些作者则试图表现知青的理想主义,成为90年代“青春无悔”的先声。张承志《北方的河》被誉为表现了一代人的精神历程,作品里没有什么情节,只有一种激情,那个黄土高原上徒步行走的主人公,毋宁说是陷入了“文革”中那种对大词的着魔状态,在满篇“母亲”和“青春”的召唤下(在革命修辞学中,这两个词往往代表祖国和革命),“张开双臂朝着莽莽的巨川奔去”。然而,在许多读者眼里,这样的激情是不真实的。作者越是豪情满怀,就越是看不清周围的世界和自我,越是成为红卫兵历史的空洞而虚妄的回声。
当一批年龄在五十上下的右派作家重返文坛,小说的创作似乎又进了一步。这些作家大都曾经磨难,如今重执牛耳,痛定思痛,在描写“文革”的劫难外,还写到历次的政治运动,形成从历史纵深去探讨“文革”悲剧的“反思文学”,如王蒙《布礼》、《蝴蝶》,张贤亮《牧马人》,陆文夫《井》,张弦《记忆》,方之《内奸》,高晓生《陈焕生上城》,鲁彦周《天云山传奇》等。个别作品甚至还触及劳改营的生活,展示出这个社会最严酷的一面。然而,缺乏自我意识恰恰是反思文学的特征,比起伤痕文学的平民化,这些作家的公共角色意识更强,常常已经走到真实的面前,却又掉头往回走。从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一部作品中的右派主人公因为所爱的女人曾试图偷越国境,被他看成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贞,与之毅然分手。作者编造这样的情节,是想让他的落难主人公成为政治正确的英雄,通过一种“贞操”的男权话语,表现出对权力的感恩。张贤亮的《绿化树》中,劳改犯人的饥饿感觉写得十分真实,但让人不解的是,主人公最后竟通过学习《资本论》,尤其是通过一个村妇圣洁的爱情,不但食和欲得到满足,更经历了一番灵魂改造,从此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有这么一段苦难的经历,作者本可从中发掘出很有力度的主题,但他却把它写成了一部充满诗意的现代传奇,历经磨难的才子最终获得佳人的青睐,落了个政治和爱情二美双收的结局。作者要把几十年的苦难合理化、崇高化,至少是犯了一个“时代错误”。
王蒙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多是右派或高干,对他来说,50年代初的“布礼”永远是纯洁的,后来的受难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并借人物的话,发明了“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布礼》)的理论。在《蝴蝶》中,一个颇有良知的高级干部,经历了“文革”的被迫害之后,幡然醒悟到自己也曾是一个迫害者。倒不是由于轮回果报,而是由于权力者忘记了人民。根据王友琴的一篇文章,《蝴蝶》中那个高干的前妻海云,其原型是北京某中学的一个教师,被打成右派后被迫离婚,后在“文革”中受尽折磨上吊自杀。小说没有描写原型被迫害的真实细节,对她的死也是一笔带过。事实上,作者未能讲述死者的故事,我们所听到的也不是死者要讲述的故事。错过了这样一个用加缪的话来说“承受历史”的人物,而着眼在“创造历史”的老干部身上,也就失去了真实生活中的悲剧要素——不可理喻的灾难,变成一部反官僚主义的作品。就这个主题而言,它甚至还不如作者早期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者至少还有一种压抑的情绪,而不是这种在内心里完成的光明结局。
在此之前,在大学校园和一些文学小圈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这其中,《今天》的成就和影响尤为显著。为它撰稿的是一些青年诗人,像北岛的《回答》、《一切》,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都曾传诵一时,代表了迷惘一代的情绪。他们不再相信过去的一切,而要去追求未来的某种东西。《今天》也发表小说,这些作品不再从社会的角度,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去描写社会,尤其喜欢通过残疾和死亡之类不寻常的题材去寻求个人价值。他们与上述作家的不同,在于从集体浪漫主义转向个人浪漫主义。舒婷的《教堂里的琴声》,写一个酷爱音乐的老音乐家,在那个年代靠偷偷弹钢琴维持着生存意志。史铁生的《没有太阳的角落》,则是写三个残疾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一种无望的爱,充满温情和善良。尽管他们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已经脱离了主流意识形态,但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感伤、唯美和夸张的抒情,原本就是一种浪漫的迷思。他们所缺乏的,仍然是那种写出事物本来面目的能力。
在中国,“现实主义”一直都是个暧昧的词。早在延安整风之后,新文学的写实一系,便已式微。毛泽东提倡“两结合”,强调文艺的浪漫一面,固然有其个人爱好,却也有其政治考量(如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唱反调)。由苏联移植过来的“干预生活”,西方萨特的“介入文学”,历来都不为统治者所喜,并且常常成为作家的罪状。80年代中,随着理论界文化热的兴起,“寻根文学”开始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想要从中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些联系,同时也拉开与直接现实的距离。然而,在我看来,“文革”的发生既非由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也非由于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一种新文化的结果,因而寻根文学最终也只能是一种新的传奇。在韩少功的《爸爸爸》中,仇恨和无知的氛围有洪荒般的野蛮,渗透于历史的全部。有评论家称,小说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缺少“理性的自觉”。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十六章第二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然而,离开了历史生活的真切描述,挖掘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果真能解释中国近百年来受制于西方历史理性的过程吗?阿城的《棋王》则试图表明,真正的传统文化一直存在于世俗社会,古今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摧毁它。一个古老民族在大地上繁衍不息的秘密。叙述者最终通过世俗的复归大彻大悟,达到一种“道”的境界。但在日常生活的残酷表面之下,去发现平静与和谐,一种当下的永恒,却又让人不免疑惑,我们到底曾活过一个什么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