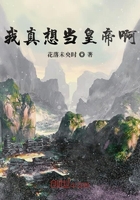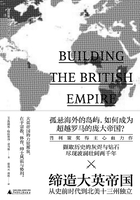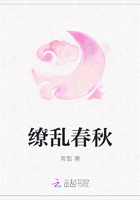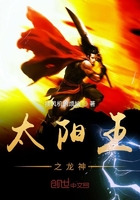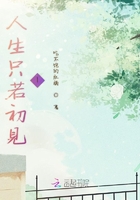韩侂胄用事日久,所引荐之亲信,“率多非类”,不仅士子愤愤不平,民间也生怨气。有一位不知姓名的临安市井画家,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群乌贼出没于潮头。并题上“满潮都是贼”五字,谐音“满朝都是贼”,挖苦韩侂胄领导的南宋政府,乃是一群乱臣贼子。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时政讽刺漫画。画家还将漫画刻成雕版,印制出来,在市场上兜售,一文钱一张,引得京城儿童纷纷买来玩耍。临安府得悉,将那名市井画家找来,打了几板子,便放走了。这个处罚,应该说,也是比较轻的。放在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必定是砍头甚至族诛的重罪。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华夏文明之所以“造极于赵宋之世”,既是文明积累与演进的结果,亦是由两宋比较开明、宽厚的制度环境所培育。华夏文明之“复振”,也必将有赖于重塑宽松、包容的制度与风气。
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议之
“诽谤罪”是一项很古老的罪名了。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意见,诽谤罪入法始于秦,为远古所无。先秦时虽然发生过“周厉王止谤”之事,但一直被当成反面教材,“子产不毁乡校”才是“三代之治”的宪则惯例。秦朝以法家立国,“诽谤罪”确凿无疑地成为法律上的罪名,始皇三十五年,曾有侯生、卢生非议嬴政“天性刚戾自用”,嬴政暴怒:“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即以诽谤罪逮捕了“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的诽谤罪与现代的定义大不相同,现代法学一般将诽谤罪界定为对私人的人格诋毁,是一项自诉罪;古代的诽谤则指对君主、官员以及朝政表达不满与非议,是公诉罪。换言之,一些在现代社会显然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行为,如评论政府,在古代特别是秦制下则被当成“诽谤”,加以治罪。到汉代时,文帝曾经下诏废止“诽谤法”,宣告“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即使有人因为不满官府而诅咒了皇帝,也宽容待之。但从后来的历史看,诽谤罪很快又死灰复燃了,汉武帝时,竟闹出以“腹诽”陷人死罪的荒唐事来。
又过了几百年,隋朝的文帝又一次降敕终止诽谤罪:“诽谤之罪,勿复以闻”。自此之后,不管是《唐律疏议》,还是《宋刑统》,都不再保留“诽谤罪”,因此也可以说,“诽谤罪”在形式上被废除了。但请注意,我说的是“形式上废除”,因为在实际上,历代王朝以“谤讪朝政”为由入罪于人的案子可谓层出无穷。如明代的仁宗皇帝曾对大臣说:“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明仁宗虽反对以诽谤入罪,不过他的话也透露了一个事实:当时因为谤政而“身家破灭”者恐非少数。清代的乾隆一朝,更是大兴“文字狱”,无数人因谤及“朕躬”、“圣朝”、“圣贤”而被杀头乃至灭门!
相比之下,宋朝的舆论环境在历朝中应该是最为宽松的,时政得失,士民皆得议论,通常朝廷并不禁止。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能容忍尖锐的批评,比如王安石集团掌权时,就很讨厌士民议政,认为朝野的议论纷纭,是惑乱民心,干扰了变法大业,所以必须严加镇压。于是我们看到,在应对所谓的“诽谤”时,宋朝官府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来看两个例子——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派当政,为打压异议,替变法扫清障碍,他们“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许多人都因为对新法表示过不满的意思而被捕入狱。新党此举,让旧党领袖司马光大为震怒,他上书朝廷,质问宋神宗:“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子产执政,不毁乡校,何今之执政,异于古之执政乎?”
后宋神宗逝世,宋哲宗冲龄继位,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召司马光归朝执政,问计司马光:新政以何者为先?司马光说,“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最要紧的事情乃是广开言路,应该在京城及各州出榜晓示求言,“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京城的士民可投书于鼓院,州县的士民则投书于州政府,任何官员“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阻挠士民进言。宋哲宗“从之”。这才有了后来的“元祐之治”。
再说回宋神宗元丰年间,旧党阵营中有一个叫做许将的龙图阁待制,到郓州任太守。郓州这地方,大概因为以前的官员施政不得人心,当地的公共知识分子养成了聚在一起非议官政的习惯,“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不过许将对此并不干涉,而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职,有冤理冤,有灾赈灾,施以宽仁之政,最后“民无一人犯法,三圄皆空”,郓州士子“聚肆以谤官政”的风气,也慢慢地改变了。
司马光对新党禁锢言论的谴责,以及许将治郓的实践,正好反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对待“谤政”的方法论:他们固然没有像今人一样从“权利”的角度,提出批评政府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主张,但他们却从“义务”的角度,对政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反过来,如果庶民有议,则意味着政府的施政有了阙失。根据这样的道理,他们要求主政者,面对民间的谤政,应当躬身自问,反省过失,以求重获民众的认同;而不是粗暴地禁止庶民谤政。这便是儒家政治学的逻辑。其实在政治学中,权利与义务是互见的关系,从“权利本位”赋权于民,与从“义务本位”求责于官,显然是殊途同归的。
传统士大夫这种看待诽谤的政治学逻辑,在宋孝宗与执政大臣的一次对话中,有很清晰的呈现。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孝宗宴请几位宰执大臣。宴席上,孝宗说:“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议。近来士大夫又好倡为清议之说,不宜有此。况今公道大开,朝政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何必更言清议?”在这里,孝宗表达了对朝中“清议”现象的担忧,因为在皇帝看来,“清议”常常跟“朋党”勾连在一起,是基于派系利益而非出自公心的政治攻讦。当然以现代政治学目光来看,基于政治派系的“清议”,也是可以发展出竞争性的党际监督的,不过我们大可不必苛责900年前的君主,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宋孝宗虽然不愿意看到“清议”的出现,却也认为朝政“或是或非,自有公议”,“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即承认朝廷之施政,应当接受公议包括民间谤政的考验。
那么执政大臣是如何回答孝宗皇帝的呢?参知政事龚茂良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惟公道不行于上,然后清议在下,此衰世气象,不是好事。”暗示现在朝廷之所以出现“清议”,是因为“公道不行于上”。签书枢密院事李彦颖也说:“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议之,若朝廷所行皆是,自无可议。”也是为谤政辩护。按照儒家政治学的逻辑,如果朝廷施政不公,有了是非,当然人人“得而议之”,而应对之道,就是上至人主、下至执政,先检讨自己的过失。宋孝宗也不敢违背这样的政治哲学,说道:“若有不是,处上之人与公卿,却当反求诸己,惟不可更为清议之说。”虽然他还是认为不应该有“清议”,但这是出于对“朋党”政治的顾忌,并不是反对士民议政,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在这次“宴席会议”之后,孝宗向宰相下发了一道诏书,提出“以朝廷阙失,士民皆得献言”。
如果说,秦人将“诽谤罪”(实际上就是谤政之罪)入法,体现了法家之法对于“不毁乡校”的古老宪则惯例的背叛,那么在秦后一千年中,“诽谤罪”时废时用,最终在律法中被取消,则可以说是国家立法向“不毁乡校”惯例的艰难回归。对“古之执政”抱有强烈认同的传统士大夫,当然反对以“诽谤罪”禁锢言路。他们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民众“有权利”批评政府,却非常明确地主张政府“有义务”善待民间谤政。以此逻辑,作为公诉案的“诽谤”(谤政),自然不应该入罪;那剩下的,便是诋毁他人人格与名誉的诽谤罪了,按现代法理,应列入“民不告官不理”的自诉罪范畴。这属于另外的话题,且不展开评说。
“官不修衙”
今日不少地方的政府办公大楼修得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在全市(县)建筑物中如鹤立鸡群。这要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在古代的县城、府城,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肯定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宋代的城市逛逛,恐怕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的衙门,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尽北宋开封城的繁华,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京师大内、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惟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孟元老只点出开封府衙的地理位置(在浚仪桥之西),笔触立即便转入对市井繁荣的记录。开封府衙淹没在栉比鳞次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如果开封府衙很气派,《东京梦华录》不可能没有记载。著名的北宋城市风情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画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这么多建筑物中,也找不到一栋可以确认为官署的豪华建设,画中城门口有一个三开间的平房,算是《清明上河图》长卷唯一画到的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遍平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逊色多了。
即使是汴京的皇宫,也远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宫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所以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甚至皇宫之内,也不如京师市井之热闹。有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道:“此何处作乐?”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相比之民间酒楼的喧闹,皇宫的夜晚显得冷冷清清,所以宫人都有些羡慕起市井生活来:“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施德操《北窗炙录》)
后来成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州衙更是破败不堪,实在不像是官府办公的地方。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发现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首府,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地方官只好在这“颓毁”的州衙内办公、生活。苏轼当了三年杭州通判,任期满另迁他州,期间未能修缮州衙。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又到杭州当知州(市长),发现州衙仍未整修,更加破烂。他在打给朝廷的报告上说:“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堂堂州政府办公大楼,破落到这个地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苏轼问他的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这一年六月,杭州州衙有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这衙门再不修缮,实在是不能够办公、居住了。所以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准确地说,是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调查、计算了一下,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而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
苏轼在给朝廷的报告上说:“臣非不知破用钱数浩大,朝廷未必信从,深欲减节以就约省”,然而,州衙“弊漏之极,不即修完,三五年间,必遂大坏”,到时再大修,就不是四万余贯钱所能解决的了。所以,苏轼“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朝廷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这次修衙的预算数目太浩大了,四万贯钱,折成人民币,少说也有一两千万元。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这样,朝廷只要拨给杭州度牒,既可赈灾,也可修衙,一举两得,一物两利。苏轼还特别说明了救饥的重要性:“设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饥民之故,特出圣恩,乞与二百道度牒,犹不为过。而况救饥、修屋两用而并济乎?”
这一回,宋廷才同意分配度牒给杭州,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我猜测杭州官衙最后应该是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现在的问题是,苏轼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不行。因为宋朝不允许地方官擅自修建官衙。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坏”,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