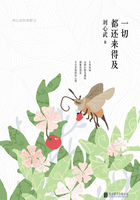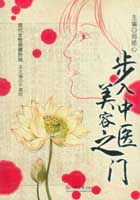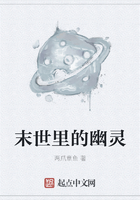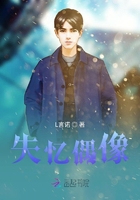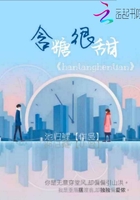我们注意到,“故乡”在维吉尔的故事里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从小说的第一稿和第四稿的标题上(《维吉尔归乡》与《维吉尔归乡之旅》)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们知道,维吉尔并没有真正地返回故乡,而是病故于布仑迪苏姆港,但是作者为什么要用“归乡”这样一个名称呢?既然不是事实上的故乡,那么必然是诗人精神上的故乡。我们看到,让维吉尔感慨,甚至有些抱怨的是,他和“本真生活”的距离愈来愈远。而他之所以与“本身生活”拉开了距离,是因为,“一个更高的命运”将他驱赶出来,驱赶出乡党,使他无法在故乡留下,从而做一个“热爱尘世存在的和平的人,一个在乡党间过着简朴稳定的生活的人”,而这才是他所向往的“本真生活”。诗人用了这样几个词来描述这一生活:“简单、原初和内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词有一个共同的上义词,即“人性”。于是我们明白,那种“本真生活”就是“人性的栖居”,或“人在大地上人性地栖居”。而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人之所以能够在大地上人性地栖居,是因为人能够以神圣,而不是以本然生命为尺度。在这里,维吉尔的故乡实际上就是世界正午时代的象征。所谓“正午时代”与“黑夜时代”相对,表示的是上帝仍然作为世界和人命运基础的时代。从历史顺序上来说,就是文艺复兴前的中世纪。正如布洛赫所言,伟大的宗教时代的主要承载者就是农民,农民对于上帝的虔敬确保了他们能够人性地栖居与大地之上,过着“本真的生活”。我们注意到,在维吉尔的故乡,农民的生活是一种“稳定的生活”(gefestigtesLeben),从词义上讲,这一生活是被某种东西“固定”住了的生活,即这一生活并不是悬于深渊中,而是有其可以依靠和固定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就是上帝。
但是伴随着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兴起,神的日子就开始日薄西山了。在人神互为消长的日子里,世俗的荣誉和幸福成了人性的最高理想,尘世的享乐成了人追求的最高价值,人的自然需求取代了对上帝的祈求,而对宗教文化的维护也被那种对文化的创造或对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所以维吉尔离开故乡,乃是为了追求文化的创造,成为诗人,因为在一个人本主义的时代,艺术就成了自然生命的赞歌。从历史发展来说,维吉尔的故乡代表的正是基督教统治下的农业文明,而他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本身就象征着由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时代的转向,而以人本主义兴起为标志的近代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城市文明。
但是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诗人的心灵却因为人性和神性的对立而感觉苦痛。这与因遭到恶和不幸的痛苦有着本质差别,它是因这个世界与神圣者的分离产生的痛苦。我们注意到一个关键的句子“他胸中痛苦的歌唱”,在诗人胸中歌唱的显然是灵魂,而灵魂之所以痛苦必然是缘于内部的张力。浮士德曾经喟叹:
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想相互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居地。
在维吉尔这里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形:一方面,维吉尔迷恋执着于现世,以赞美人性和本然生命的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另一方面,他又一直渴望“认识的奇迹”,渴望进行与认识相关的、远离艺术的哲学与科学活动(这同时也是作者布洛赫的志向),渴望在“认识中得到救赎”。从本质上说,这实际上是诗人因感领到人性与神性的对立而承受的分裂的痛苦。离开精神故土的诗人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只具有一个神性尺规,而是面对着两个对立的尺规:是固执于人的自然本性?还是祈求上帝,返回神圣之爱?这种因人本主义兴起而造成的两种生命、两个灵魂和两个世界的冲突可以说是近代人的灵魂的原始冲突。
当人面对两个完全不同的尺规时,人的世界也因此被生生分裂为二,人必然为两个世界的分离而操心、忧心,在两个尺规之间疲于奔命。所以,我们注意到,维吉尔慨叹,他“只是生活在自己生活的边缘;他成了一个动荡难安的人,逃避着死亡,找寻着死亡,找寻着作品,逃避着作品,一个爱人,同时却又是一个劳碌命,一个在内外激情的操纵下犯错的人,一个自己生活的过客。”这种边缘的生活感觉正是维吉尔在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之间徘徊的明证。
但是我们注意到,维吉尔内心中一直渴望过上简单纯粹的“本真”生活,一直渴望回到精神的故土。他因为自己离开精神故土、远离神圣的尺度而有罪欠感,认为“恶”遮蔽了他的一生。按照基督教义理,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偏离或断裂。前一种偏离导致人与自身的价值本源(上帝)关系的断裂,这就是罪;后一种偏离导致人与人的互相关联的断裂,是为恶;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偏离必然导致人际关系的断裂,恶是罪的结果。而按照基督教《圣经》的描述,罪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意志自由和妄为,想取代上帝的位置,终至于与上帝为敌,随生命自然而生的意志自由就是人身上的罪因。而在近代,作为人的意志自由的人本主义与怀疑精神的异军突起,造成了人与上帝关系的进一步断裂,使得人逐渐偏离原本的价值基础(上帝),而以神性作为尺规的诗意栖居与本真生活也因此被抛弃,维吉尔也因此必须面对“遮蔽一生”的恶。
罪的沦落遮盖了人的精神视界,使人的在世与神性的原初故乡割裂开来。在罪感中主体心智感到自身丧失了存在的依据,生命坠入深渊的黑暗,进而感到必得赎回自己的生命依据。因此,罪感引起人精神意向性上的一种祈求的意念,渴求生命的重生,渴慕修复与上帝的原初关系。但是伴随着人本主义与怀疑精神的兴起,人性自身的尺规得以确立,神性尺规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因为人的自足意志使人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并且将反映人与神性的原初故乡的割裂关系的本质领域遮蔽起来,人对于自身的罪感已经不能加以认识和承受。人也渐渐遗忘了神性尺规下的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与本真生活。
但是作为诗人,维吉尔却是例外,这缘于诗人的使命。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人的现实性恰恰出现在否定虚无现世的意义活动中,诗就是这种意义活动的原初方式;人天生贪恋现世,主动为世界提供意义,诗便产生了。歌唱的言语是大地自恋的欲望,即便歌唱超脱和厌世,也是贪恋现世的欲望。真正的超脱和厌世拒绝言语的世界,诗的世界属于那些在现世中感到不安、又不愿离弃现世的人的世界。超脱现世与认同现世的人都不需要诗,唯有既不认同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靠诗活着,靠诗来消除世界对人的揶揄,把世界转化为属己的、亲切的形态。诗感发人心在虚无的生存世界的忍受中直观到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诗是一种保证、一种承诺,使不安于现世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在生存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片面和灾难性的遭遇中,与诗的意义真实相遇。诗重构人的世界经验,用诗的语言重构的经验就是诗的经验,使人虽置身于世界的虚无却能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世界。置身于无意义世界中的个体在这种超验经验中才能驱除内心的寒冷和苦涩。而所谓诗人的使命,即作为现世与超验的意义世界之间的中介者,通过诗的象征,人的生命在这个异己的世界中领承到绝对的神圣。而在诗化了的世界中,绝对价值时时处处都内在于人的生命。
但是,在启蒙理性成为时代精神的历史时期,上帝的身位已经转移,上帝因为人的拒绝而身退,人性与神性造成了绝对分裂。这是一个旧的神袛纷纷离去,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的时代,因为它陷入了双重的贫乏、双重的困境:诸神与上帝逃遁了,将来临的上帝还没有出现。作为人的尺规的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神圣的上帝依然真实地存在,但人们已经不闻不问,这样的世界黑夜时刻,恰恰需要一类人——诗人守护对上帝的虔敬,需要诗人无畏地正视无神的境况,滞留于上帝的退隐之侧,在丧失神性的黑夜守护神圣者离去的身影。在这个黑夜笼罩的世界里面,虚无主义成了最可怕的客人,成了纠缠现世的顽症,众人已经遗忘了神性尺规下的本真生活,而坚守神圣者离去身影的维吉尔必然是孤独的,因为他没有遗忘,虽然他无法在神性的故土里持存下去(bleiben),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与故乡分离”(losgelassen),他对精神故土的渴慕并没有被近代理性所抹煞,依然顽强地留存于诗人的心中。不过,在一个“众人绝对我独醒”的世界里,当所有人都已失忆、而唯独诗人仍然保留着对精神故土的眷恋的时候,诗人只能孤身承受这神圣的痛苦,在这样的夜晚,诗人根本无法安睡,维吉尔在临终前所度过的夜晚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晚的象征。
这样的黑夜却也是神圣之夜。在这个夜晚,圣灵作为上帝的恩典过程的力量,不再是能让人崇敬的个体,因而,向圣灵的趋近只能是人的一种自主的返回过程,摧毁还是重建人与上帝的联系都成了人自己的事。谁要在无神性的黑夜时代寻求重建与上帝的联系,谁就得冒险。“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需有入于深渊的人们。”在这样的夜晚,成为真正的诗人就意味着,留下来极其孤独地承担他的使命,追问真理,为民众担当苦难、真切地追问真理,因为神圣的爱的显现就是“真”,“真”的显现就是神圣恩典的到场。这也正是维吉尔的渴望,“那认识的奇迹以及在奇迹中得到救赎的希望”,“认识的奇迹”指的就是诗人认识到了“真”,“奇迹中的救赎”指的就是诗人守护到了神圣恩典的到场。然而,这一希望却被象征世俗与国家权力的奥古斯都打断了,而诗人竟然屈从于奥古斯都的催逼,这是因为,维吉尔一直在“找寻”与“逃避”之间把持不定,他“逃避着死亡,找寻着死亡,找寻着作品,逃避着作品”,诗人的表现是迷惘的,这是一种双重的迷惘:一方面,诗人因为上帝的隐遁而失去了价值支撑,并因此造成了一种“没落的迷惘”;而与此同时,诗人在逝去的神性与凸起的人性之间徘徊不定,试图重新找回确定的尺规,因此具有了一种“找寻上的迷惘”。正是在“没落的迷惘”与“找寻的迷惘”交织的作用下,维吉尔作出了离开雅典的决定。
下面的句子直接体现了诗人的迷惘,“逃避着死亡,找寻着死亡,找寻着作品,逃避着作品”。这虽然是一个表示并列关系的句子,但是排列顺序却不大合乎常规:谈到“死亡”的时候,是“逃避”在前,“找寻”在后;而谈到“作品”,是“找寻”在前,“逃避”在后。这说明,对待死亡与作品的不同态度应该与诗人精神意向的结构有关:很明显,“逃避死亡”与“找寻作品”应该属于同一个精神意向,而“找寻死亡”与“逃避作品”则属于另外一个精神意向。“逃避死亡”就是留恋现世,留恋“生”,而对生的留恋则促使诗人“找寻作品”,赞美和吟唱本然生命,在艺术中刺激、沉醉、怡乐、忘我,而从达到“逃避死亡”的目的。“找寻死亡”则意味着返回泥土、返回母体、返回上帝、返回宇宙,在死亡中得到拯救,但是这种对死的趋向就意味着对生的摒弃,而作品作为护生信念的表达与此是相矛盾的,所以需要“逃避作品”。这种精神意向上的矛盾式的结构充分说明,诗人的灵魂因为人性与神性的绝对分离与对立而分裂为两个灵魂,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尺度。在诗人的身上,天然地集中了审美与救赎两种原初的精神冲突。一方面,他热爱生活,留恋尘世,正是出于对生命本然的执着,他才会“热情地赞美世界”,虽然他早已深晓世界的恶和无意义,但是他仍然赞美世界,这充分暴露出他的诗带有的审美倾向。但是另一方面,维吉尔深知这一切都只是“谎言”,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尼采关于“诗人说谎太多”的论断。维吉尔认为,诗人的任务应该是追求认识,在诗中“如实地展示世界”,这就是“诗人的沉重的、忍受认识、真正的工作。”诗人必须真切地追问真理,因为神圣的爱的显现就是“真”,“真”的显现就是神圣恩典的到场。而这两者的冲突甚至直接反映在他的身体之上:当船靠近长满灌木和橄榄的海岸时,突然有一种感性的、不可遏止的渴望袭上他的双手,想要“在手指之间感觉那破土而出的叶子,永远地抓着它们”,这无疑是对生命与土地的渴望,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致他甚至感觉“他的手很奇异地有了自己的生命”;而另一方面,他的“心”却一直渴望不断向上,进入宇宙流动的光之中,进入关于宇宙的无限知识,接近宇宙的无限。这种手与心的分裂实际上即是维吉尔精神冲突的体现。
但是不管怎样,审美与救赎的冲突依然是人性与神性两种不同的古典信念的冲突,两者都有其确定而又稳固的价值基础。但是在绝对的价值虚无主义来临之时,世界已经为黑夜所掩盖,人和世界都深陷于贫乏的时代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在这个贫困的时代,无论是哪一种信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而在不同古典信念中歌唱的诗人都身陷虚无主义精神的包围圈,被绝对的价值虚无逼上了绝境。在虚无面前,何去何从?在这个贫困的时代,真正的诗人必须找到出路,突围而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吉尔之死》这部作品体现和探询的正是“诗”与诗人的出路问题,因为如果布洛赫是“贫困时代的诗人”,那么他的诗(作品)应该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诗人何为(wozu)?诗人的歌唱正在走向何方?在世界黑夜的命运里,诗人何所归依?
在作品中,布洛赫要完成的就是上述的诗意的追问。但是,“世界黑夜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愈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不光是神圣作为通往神性的踪迹消失了,甚至那些导向这一消失了的踪迹的踪迹也几乎消失殆尽了。这些踪迹愈是消失殆尽,个别的终有一死的人就愈加不能达乎深渊,去摸索那里的暗示和指引。那么,愈加严格的事情乃是,每个人只要走到他在指定给他的道路上所能到达得那么远,他便到达最远的地方了。提出‘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这个问题的那首哀歌的第三节,道出了支配贫困时代的诗人的法则:有一件事坚定不移/无论是在正午还是到夜半/永远有一个尺度适用众生/而每个人也被各个指定/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之所。”这个“适用众生的永远尺度”指的无疑就是神圣作为现世的内在尺度,而诗人将走向和到达自己所能到达之所。所以要回答布洛赫的诗意的追问,首先就当运思,作为真正的诗人象征的维吉尔,当他走向他能到达的地方的时候,他将去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