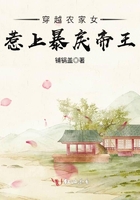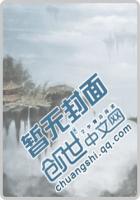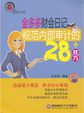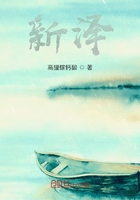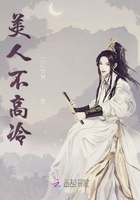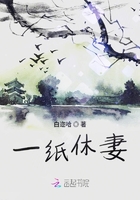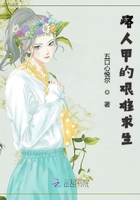叩跪杂拾
清代光绪年间的吏部主事何刚德,有幸参加过皇上的一次生日宴会。时间,甲午年六月,地点,紫禁城太和殿。
说其有幸,并非虚言。主事官阶不过六品,本无资格和皇上套近乎,但其时各部可圈定两名群众代表领受皇恩,何刚德光荣入选,这才开了一回眼。所谓群众代表,其实也有级别,司局级。据何氏在《春明梦录》中回忆,该宴会很是一般,“两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上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他的评语是:“宴惟水果可食。”就是这个只能吃上仨瓜俩枣的皇家宴会,却把人折腾得不一般,盖因礼数太多。与宴者要时刻听从皇家司仪即赞礼者的招呼,该人站在殿陛上高喝一声“跪”,众人便得立马从炕桌即“几”旁站起,然后齐刷刷地跪下去。跪毕,再围着炕桌坐下,继续咂摸歪瓜裂枣的滋味。“赤日行天朝衣冠,盘膝坐,且旋起旋跪,汗流浃背。”这通折腾,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身子骨差点儿的还真顶不住。
中国既为礼仪之邦,官场之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说道,如此方能“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以公文格式为例,皇帝特降之命令为谕,臣下奏请由皇上批复的为旨,专供省级干部传阅的人事任免等通报为廷寄;上级机关对下级催办公事的文书称札;文职机关向上级打的报告为禀,武职为详;下级官员有事向上级领导汇报,需用手折,给皇上的报告则为奏折……这仅是清代规矩,其他的不算。初入官场者,光是弄清这些名堂便够晕一阵的。
当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收到过建德一李姓把总送来的文书。老曾见后激动得赋诗一首:“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移封又称移书,本应用于平级官署之间的交涉。清代总督为正二品,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把总不过七品武职,和总督中间隔着副将、参将、都司、守备、千总、百户等一长串官员。这李把总,平素想给总督叩头都够不着,递送公文居然用起了与之平起平坐的移封,太离谱。无怪乎逗得老曾诗兴勃然。
大清江山尽管是马上得之,但在官场礼仪制度上却一点不含糊。比如,大臣无论年龄大小、品级高低,面见老大一律得跪着说话;再如,如果赶上圣上心情不错,谈论公事之余问及臣子的家事或是赐个仨瓜俩枣的,跪着的臣子必须立即谢恩,程序为先脱帽,后叩头。脱帽必须以花翎指向御座。再往脑袋上戴时,只能用一只手整理帽襻。至于叩头,更须功夫,关键是要带响,而且必须响达御前。若额痛而不响,或响而痛不可忍,蹙眉闭眼,皆为不及格。有记载说,曾经教同治、光绪两个皇帝认过字的翁同龢,下班后“每夜必在房行三跪九叩头五次乃卧”,声称如此可健身醒脑。其根本目的,恐怕还是想多操练操练,免得叩头谢恩时响动不达标,有损两朝帝师的名头。
翁师傅的头磕得虽好,但最后还是被一道上谕革职回了老家,而且严加看管。因为他有点儿嘴碎,得罪了太后老佛爷。相比之下,另一大臣曹振镛则成熟得多。曹大人在嘉庆、道光年间长期担任军机大臣,还当过上书房总师傅,死后被道光皇帝予谥“文正”。清朝惯例,只有进士出身当过翰林且功勋卓著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谥号中才可带一“文”字,而“文正”更是其中规格最高者,只由圣上一人定夺。有清一代,获“文正”之谥的大臣仅七八人,包括曾国藩。可见曹振镛之了得。
曾有门生问曹老师圣眷不衰之诀窍。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话虽不多,绝对经典。这曹振镛虽说开口有限,却总能说到点子上。学问大。道光皇帝当政后期,对臣工没完没了地提意见十分厌烦,当面驳回吧,又怕落个阻塞言路的恶名,让后人说三道四。关键时刻,曹振镛开了一口,建议圣上看折子时对内容不置可否,专挑错字或是表述不合规矩的地方,交由有关部门以“非礼”论处。没多久,满朝大臣再无一人唧唧喳喳,和谐了。大家都非智障,这点小九九再弄不明白,干脆别混了。后世有人评说:“道、咸以还,风骨销沉,滥觞于此。”当时有人私下给曹老师写过“表扬信”:“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这样一个人,最后居然成了“文正”。
清帝逊位,民国诞生,跪拜叩首之陋俗随之废除,不过曹文正公的传人有的依然吃香。也难怪,比起说话不中听的乌鸦嘴来,“多磕头,少开口”者毕竟更招老大们喜欢。世上有些事情,是不会随着朝代更迭而绝迹的。
?
“名刺”谈往
中国许多词语,其实都有渊源。
比如“谒见”,如今属于敬辞,多指晚辈或下官进见或请见长辈或高官。至于谒见程序,并无硬性规定,求见者瞅不冷子给主人塞张“金卡”,抑或寒暄两句即打道回府,均可。但是早年间,谒见却有严格仪轨,求见者必须先将“谒”呈上,由下人转交主人并获得批准后,拜见才能正式开始。“谒”由竹木削制而成,上写姓名、籍贯等个人简况,相当于今日之名片。
谒见一般比较正式,因而请求接见者若吃了闭门羹,会觉得很没面子。楚汉相争时,有一儒生郦食其想谒见刘邦,阐释定国安邦之宏图大计。刘邦让手下传话说,军情紧急,没工夫听儒生瞎叨叨,把他撅了回去。郦食其的热脸贴上了刘邦的冷屁股,不禁气得大声喝道:老子不是什么儒生,是高阳酒徒,再去给我通报。这一声高叫,估计得超过一百二十分贝,直吓得“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刘邦这才召见郦食其,听他絮叨了一番,并任命其为广野君。以后,郦食其去劝降齐王田广,未果,被烹。高阳酒徒于是再也做不成。
“谒”有时也可充当礼单。据《史记》记载,当年刘邦还在老家沛县当亭长时,一次去县长的朋友吕公家参加宴会。当时萧何是操办宴会的秘书长,规定份子钱少于一千者,只能坐在堂下吃喝。刘邦“乃绐为谒贺曰‘贺万钱’,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萧何知道其底细,对吕公说,姓刘的这小子惯会说大话使小钱,用不着答理他。但吕公见过刘邦之后,不但将其引入上座白吃白喝,还把自己的闺女许配给了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吕后。
司马迁说,吕公如此器重刘邦,是因为他会看相,觉得刘邦气宇不凡,前途无限。但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吕公毕竟阅历丰富,明白刘邦之“混混”技能已经出类拔萃,赶上机会,凭此手段定可成就一番事业。萧何则不明此理,因此后来只能给刘邦打打下手,这还是他弯子转得快,不然早被老刘同志收拾了。
到了东汉,“谒”之名称被“刺”所取代,材质仍为竹木之类。有人还在“刺”上添加了官职年龄等内容,专供拜见上峰之用,名曰“爵里刺”。这种官场名片有专门的书写格式,要把所有的内容在“刺”的中央写成一行,不能拆分,故而也叫“长刺”。
其时,民间也多用“刺”向他人表示问候。东汉末年有一名士叫郭泰,字林宗,因其品行端正学养深厚,被读书人奉为偶像。一次他外出闲游时赶上下雨,遂将头上所戴之巾的一角随便垫了起来,结果立即被众人仿效,成为流行式样,被称为“林宗巾”。据《后汉书》记载:“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收到的名刺居然经常用车拉运,这郭林宗的名头确实够大,估计拉回家能省下仨月俩月的柴火钱。不过,郭泰名头虽大,却从未涉足官场,没写过“爵里刺”。结果,当时许多入仕的文人被砍了脑袋,郭泰却能独善其身。比郦食其强。
宋代“名刺”之称犹存,但已改用纸张,因此也叫“名纸”。当时的名刺,大都由当事人亲自书写。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一书中,便记录了秦观、黄庭坚等人拜谒一个叫常立(字子允)的人时,所用名刺的“石本墨迹”。其中秦观的名帖写的是:“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从落款日期看,这应该是拜年所用的名帖。当时,名帖已开始具备贺卡功能,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云:“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其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明清官场之上,以名帖充当贺卡之行径已蔚然成风。明代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对此有具体描述:“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投名帖者。”还有人为此赋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明清“名帖”还有一说道,即当过翰林者才有权用红纸,写大字。大概翰林系御用文人,与众不同。前一段,电视台播放的介绍清末民初著名的洋记者莫理循的文献片中,就能看到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的名帖,真是红纸大字,应该是他在清朝当官时用的。徐世昌中过进士,点过翰林,所以才有资格使用这等名帖。以后,一些仰慕中国文化的老外也用起了红名帖,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便是一个。其名刺正面书“庄士敦”三大字,背面则印“专诚拜谒,不作别用”。
如今,御用文人没了,这些说道也成为往事。其实御用文人并不好当,起码得有些文才。如果文章写得不着四六,则属徒有“御用”之名而无“文人”之实的混混儿了。
宅第之赐
中国历朝历代,为官不捞外快者,少。捞外快不为人知者,难。好在皇上大都知道十官九贪,对此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一方面总要树几个廉吏典型,让大家学习学习;另一方面,对于更多的非廉吏,只要别贪得过分,还能干点正经事,且由他去吧。把当差的都给办了,自己的龙椅也得散了架。
不过,私捞外快者,哪天把皇上惹恼了,即便官高一品,位极人臣,也难逃抄家籍没的下场,因此总有点悬。不过,也有两全其美之法,这就是争取圣上封赏。没有哪个纪检官员敢上奏,说某大臣得了皇上的外快,是贪官,该查办。除非他是不想混了。皇上赏赐的名堂很多,凡与衣食住行有关者,都可作为赐物。仅赐宅一项,就有许多名堂。
有皇上出资帮助臣工建房的。晋武帝司马炎就曾经下诏为王沈、鲁芝等大臣建房50间。王沈是个文人,但干过一件很不文人的事情。他曾经被魏高贵乡公曹髦礼聘入宫,后来曹髦忍受不了司马昭的欺凌,“将攻文帝(司马昭),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不过,王沈为官还清廉,死后家无余物,晋武帝念及他为司马氏取代曹魏中立下的大功,遂帮他的后人修了两间房。
享受此待遇的还有山涛。山涛很有意思,一面当官,一面又不想当官;一面自己总想辞官,一面又让别人去当官。他就曾经想让好友、与他同列竹林七贤的嵇康接替自己的官职,结果遭到书面严拒,这就是传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评价山涛“多可而少怪”,自己则不然。如当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包括早上起不来床,身上有虱子穿不得官服,不愿干杂事,不喜见俗人等等,“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耶”?有这么多毛病还去当官,确实难以“久处人间”。不过,即便是在野,“非汤武而薄周孔”也难为世教所容。嵇康最终仍被诛杀,实非偶然。
嵇康也很有意思,一面写信与山涛绝交,一面对他又十分信任。临刑被诛时,他对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看来,嵇康的绝交书只是发泄一下对当局的不满,另外留下一份证明材料,免得日后自己犯事儿连累山涛吃“挂落儿”。可谓知友甚深,用心良苦。
不过,山涛在经济上大约难给嵇康儿子太多资助。因为他虽然靠着“多可而少怪”,在官场平安混了几十年,但是于捞外快却十分谨慎。曾经有一个叫袁毅的地方官,“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以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因此在他死后,只留下十间旧屋,还不够子孙居住,只好让晋武帝帮忙解困。
修房之外,也有批地的。如唐宪宗曾经一次赐给程执恭20亩地,供他扩建居室,合今天1万多平方米。当时百姓的住宅用地标准大约是三户之家一亩地,一次批20亩地给人扩建宅子,也算是个数了。程执恭本为一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后来交出军权进京居住,使得中央政令得以畅通。宪宗赐地,有奖励兼安抚之意。其用心,较之时下玩弄黑箱操作的批地者还要高尚些。
还有直接赐宅子给臣子的。清圣祖玄晔便为高士奇下过诏令,“赐居西安门内”。高士奇为浙江钱塘人,后到京城参加乡试,被权臣明珠推荐到宫廷干点抄抄写写的事,很快得到康熙赏识。汉人能住在西安门内,当时是莫大的殊荣。清初时为确保紫禁城安全,周边均由旗人拱卫,朝廷汉臣即便是一品高官也只能住在城外,更不用说食六品俸的“小把戏”了。
康熙让高士奇住在皇城左近,是考虑到自己读书时一旦遇到疑惑,传唤起来方便,所赐宅第面积估计有限。因为皇上毕竟不是地产开发商,没有那么多空余楼盘。但有了这一处居所,哪怕是贫民窟,也有了捞取更大宅子的资本。因为这是皇上恩宠的实证。高士奇退休后,御史郭琇曾揭发他四条可诛之罪,其中一条便是收受他人在虎坊桥的瓦房60余间,还动用贿银40余万两,在顺城门外斜街等处大肆购买房产。“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於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疏上,未有下文。
盖因皇上的那只眼此时正闭着。
?
车舆之赐
中国有些事情很有意思。不少东西明明就是废物,当事者偏偏还要硬充宝贝,譬如皇上的专车。
御用之车,讲究颇多。尽管也有车轮,也有车辕,但是不称“车”,得叫“辂”。皇上用辂,多在于拜天祭祖等大场面,有很多名堂。乾隆曾定下规矩,天子之辂分五等:玉辂、金辂、象辂、木辂和革辂。这些花样其实非乾隆原创,据说远在周代之前,皇上还不叫皇上的时候便有了。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论张王李赵,只要屁股往龙椅一沾,必得弄出几样辂来,以表明自己和前朝皇帝一样受命于天,否则便不够正宗。
乾隆的玉辂,实在是气派,总高一丈二尺一寸,光是车顶就有三尺一分,搁到现在,想从立交桥下面钻过去都困难。车身上必须贴金镶玉,以与玉辂之称相符。轿车内部纵八尺五寸,横八尺四寸,环以朱阑,饰间金彩,皇上便端坐在里面的云龙宝座上。不过这个宝座倒不大,高一尺三寸,阔二尺九寸,和炕桌差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