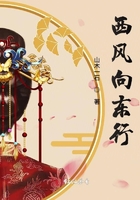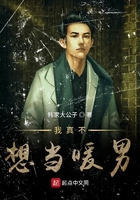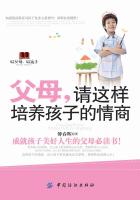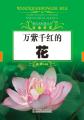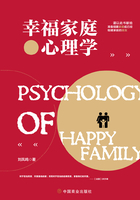“洗涤炎埃宿雨晴,井梧一叶报秋声。气从缇室葭莩起,风向白蘋洲渚生。”
在琳琅大观的唐宋诗词之林,这首题名为《秋》的小诗无声摇曳,蔼然自处,不为任何时代的诗家所注目。读过它的人很少,读懂它的人就更少而又少。
细细品啜,会在这貌似状景绘秋、设笔散淡的字词之间,窥见蒸腾其中的一股冲和静穆、雍容雅正之气。
那就是弥漫于整个宋代学术天空的性理之气。
宿雨涤空,洗尽万千尘埃,最后俱化为匍匐在井台上的片片梧桐树叶。是在暗喻经历了长期竟说纷纭的北宋理学,终于在一场驱杂除埃的秋雨之后,标定正音,一叶示秋。这股性理之气起自斗室,却以化生万物的劲力吹向大地蘋洲,最后秋风风人,秋雨雨人。
这是何等自负的学术自认!放眼宋代诗词界,除了他没有谁可以有这样恬淡冲和的口吻。
不错,诗作者就是程颢。
程颐曾放下弟弟身份,用一个学术大师的专业眼光来审视其死去的胞兄程颢:“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喘,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这个“千四百年”指的是距离孔子的时空长度,暗含着程颢继孔子道统。其实,程颐写给亡兄的碑文,也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一人而已”修正为“二人”更为允当。
来看看《宋史·;道学列传》画就的儒学传承脉系图: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傅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在这个横跨一千四百多年的学术史谱系中,程颢、程颐兄弟二人赫然居中,上承孔孟余绪,下启后世风气,他们并肩站定为中国儒学学术史中一座不可替代的重要里程碑。
具体在北宋这程,经过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的发端,后经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推进,宋代理学整体思维大体形成,而作为一种完备而成熟的学术体系,则要等待程颢、程颐兄弟来携手完成。
他们于“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之中,广采博蓄,察微发隐,参天悟地,心与物同,然后聚徒授课,遍撒学种,开辟了儒学新的纪元。
自此,二程缔造的洛学遂成为万世经术斗杓,自春秋诞生的中国儒学经过两汉经学的繁荣之后,又迎来了第二个阳光明媚、万鸟和鸣的春天。
无疑,程姓兄弟是这个春天的使者。
一。
上帝总喜欢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里,扎堆般缔造出一批人类永恒的大师。集体绽放,又相继陨落,然后是漫漫万古长夜,让人们慵倦的眼神,期待不知何年才又会出现的璀璨夜空。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释迦牟尼大孔子十五岁,赫拉克利特又小孔子二十一年,具体出生年月不详的老子,与孔子也曾有过清茶袅袅的促膝交谈。东西方人类杰出的思想大师在那一刻奇迹般地集体降临。
北宋仁宗年间也是这样一个黄金期。文学“唐宋八大家”之中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其余六位全部生活于此时。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对兄弟学术双子座。张载、张戬;苏轼、苏辙;程颢、程颐,兄弟联手,成双结对。
对前两组兄弟来说,哥哥过于耀眼的光芒遮掩了弟弟本有的辉泽,使得兄弟并不同辉,而程颢、程颐却以并蒂双葩的方式绽放,二人并驾齐驱,遂成等量齐观。
由于共同的理学主张和思想,相同的理学造诣与影响,在后人眼里,他们已不再是两个人,而就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学术整体。于是他们往往被人称为二程。
即使放在世界文明史里,这对兄弟也都堪称奇迹。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生于公元一〇三二年,宋仁宗明道元年,卒于公元一〇八五年,宋神宗元丰八年。
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生于公元一〇三三年,宋仁宗明道二年,死于公元一一〇七年,宋徽宗大观元年。
相差一岁的兄弟俩,一前一后,相约牵手来到这个世界。
程家世代官宦。二程高祖程羽曾跟随宋太祖赵匡胤南征北战,在宋太宗时,官至兵部侍郎,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职开封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珦为官为学均很出众,《宋史》评价其说:“珦慈恕而刚断,居官临事孜孜不倦,温恭待下,率以清慎。”
每一个伟大的人物背后都有着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个人不是妻子,而是教子有方的母亲。
二程的母亲侯氏,系精通儒学的尚书比部员外郎侯道济之女。她静雅贤淑,有知人之鉴。为勉励二程好好读书,她在幼年儿子们的书本上写下“吾惜勤读书儿”。
针对两个儿子各自的性格特点,她又分别在程颢、程颐的书本上写下量身定做的励志之语。程颢幼年名延寿,母亲写给他的是:“殿前及第程延寿”,写给小程的是“处士”。后来,二人分别用自己的成长轨迹验证了其母的早年预断。
知子莫若母!程妈妈的视野如果再开阔一些,她应该用蝇头小楷为儿子们共同写下“理学宗源”。但那样就让人不可信了,如同岳母在儿子背上鲜血淋漓地刺下“精忠报国”,总让人觉得有些泛政治化,被戏剧化的意思。
同时期的苏洵也是一位眼光独到的父亲。他为两个儿子分别取名轼、辙。他在《名二子说》中说:车轮、车辐、车盖和车轸,都是车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轼只是车前用作搭手的横木,无关紧要。苏东坡从小生性旷达,性格外向,其父以此告诫他要像“轼”一样放低身段,不锋芒毕露。次子苏辙性格乖顺平和,为其取名“辙”,取意为可以免祸。
观苏轼、苏辙二人生平,其性格真如乃父所言,苏轼一生旷达不羁,苏辙含蓄深沉;苏轼竞相树敌,于党争中不知自保,落得一生坎坷,苏辙仕宦生涯却要稳当顺利得多,一切都如老苏当初的预料。
有意思的是,程氏兄弟间的情谊也与苏氏兄弟相仿。
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回顾乃兄一生:“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之间已远远超越了兄弟私情的相互雅敬之谊。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扶我则兄,诲我则师。”将苏轼看作亦兄亦师。苏轼则在写给好友李常的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
二苏之间那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惺惺相惜,彼此依恋,临终绝命都发愿“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的兄弟之爱,相信在二程之间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会更加深切,更加密茂。
有所区别的,也许只是内重涵养、外鄙文辞的二程,羞于用二苏弟兄那样的率真言词启齿表达罢了。
天才在其幼年,不是大拙便是大慧。
据《宋元学案·;明道学案》记载,程颢于尚不会言语时,便展示了他非凡的记忆力,“数岁,诵诗书,强记过人。十岁能为诗赋”,“十二岁,居痒序中,如老成人,见者无不爱重”。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也说程颐:“幼有高识,非礼不动。”
安稳,持重,敬笃,是二程性格上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一切学人成长的必备先决条件。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是程颢在诗中自况,也是程颐的精神肖像。
二。
一阵偶然的轻风,将一粒松树的种子吹来,恰好落定在岩石的缝隙,而那里恰好有一点供生命发育的泥土,于是,一株劲松最后破石而出,直指云天。
谁会说一个伟大人物的形成,不是在其生命早期受到过类似种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影响,而最终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幼年的伏尔泰遇到了夏托纳夫神甫,神甫教他读不可知论者卢德所写的攻击宗教的《摩西亚特》,正是这首诗在伏尔泰心中播下了怀疑论的种子,启发他厌恶宗教狂热,勇敢蔑视一切精神权威。
公元一〇四六年,时任大理寺臣兼南安通守的程珦闻听南安军司理参军周敦颐之名,过而相见,“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
朱熹为此说过:“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怀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唯程太中知之。”深为叹服之中,程珦随即将两个儿子送至周先生府上,拜周敦颐为师。
虽然他们师生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仅有数月,但周敦颐的教导却如春风化雨,自此在二程心中生根发芽,影响极为深远。
周敦颐上承“宋初三先生”的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地吸收道家思想,以《周易》“太极”为主体,糅合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创造出一个逻辑范畴的宇宙范式,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真正影响了二程的是周敦颐的无欲、主静理念。正如《宋史·;道学列传》中说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多年之后,程颢仍颇有感触地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是周敦颐让他们找到了“孔颜乐处”。
程颐更因周敦颐的教导,后来写出一份让另一位大儒十分吃惊并赞赏不已的答卷。
公元一〇五〇年,程颐在太学学习,太学教授胡瑗为学生们出了一道题:《颜子所好何学论》。
程颐答道:“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他言明,圣人之道是“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
不难看出,程颐所答的“正其心,养其性、性其情”的本真归静圣人之道,就来自周敦颐四年前的教诲。
他的答卷让胡瑗拍案叫绝,为此甚至“即请相见,处以学职,知契独深”。本为同班同学的吕希哲,当下就不再与程颐同学嘻嘻哈哈,勾肩搭背,而是“以师礼事之”。既而,四方之士从游程颐者越来越多。
就在这年,年仅十八岁的程颐还做过一件令人吃惊的事。
他以布衣身份上书阙下,劝宋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当然,一个无名小子的贸然上书,是不会被送到领袖案头的,否则以宋仁宗之体人善任,起而用之程颐也未可知。当然,这使得他还有机会闲游太学,继续接受胡瑗先生的悉心教导。
公元一〇五七年,二十六岁的程颢赴京师应举,与张载、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进士及第后在京候诏待命之际,程颢、吕希哲、张载于开封相国寺里举办起学术讲座。
《宋史·;道学列传》中有记:“(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年长程颢十二岁的张载虽然来自千里之外的陕西眉县,祖籍却是汴梁,与二程有着亲戚关系,按辈分,张载为二程的表叔。
与二程互论《周易》之后,张载认为二程深明《易》道,于是自谦地说了一句“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然后撤椅罢讲,以示自己对学问的虔敬。同时,在与二程论性谈理之后,他用一句充满自负的“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来点拨二程道学之要。
正是在张载的指点之下,二程于是尽弃此前广泛旁涉的佛道“异学”,专注于儒道,才使得他们的学问自此粹然无杂,湛然淳如。
至此,二程先后从周敦颐、胡瑗、张载等三位同时代大儒那里分别汲取道学的基本营养。
转师多门,兼收并蓄,周纳多包,这是二程最后将自己浩浩荡荡流淌为一路东进的学术大河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洛学最终被公认为理学正朔并广为传播的原因所在。
此之所谓,有容乃大。
三
再缤纷的花园也不是骏马驰骋的牧场。
作为一个学人,官场并不适合安放他不羁的思想与灵魂。但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然后走上仕途,这几乎成为所有读书人的成长必经之路。也只有在仕宦途中被拷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们才会退回书斋,以无比追悔的心情回望人生中的仕宦生涯。
在这方面,程颐显然有着比他人更多的自我警醒。
当哥哥程颢前往鄠县(今陕西户县)担任主簿,走入官场时,他则以难得的淡定心情,于嘉祐四年廷试报罢,再不参加考试,果断停止了自己的场屋事业。这其间,程太中有很多次机会获得了“任子恩例”的指标,即通过朝廷恩荫制为自己子女封官,但程颐绝意仕进,每次都将之推让给族人,仍然以自由人的身份闲游于太学。
到宋英宗治平年间及宋神宗熙宁年间,皇帝身旁近臣也不断有人推荐程颐,程颐却屡屡以“为学不足”拒绝入仕。
宰相吕夷简就不止一次举荐过程颐。
吕夷简判太学时,让众博士集体到程颐门上,敦请他担任太学正,程颐仍固辞不就。公元一〇六四年,吕夷简出知蔡州前又向宋英宗上书:“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太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松桂有嘉色,不与众芳期;金石有正声,讵将群响随。”这是天性!
程颢呢,则在地方官任间游走,一方面静思涵养,完善道德,增进学问;一方面勤勤恳恳为民父母,夙夜在公。
熙宁年间,程颢走入朝廷。宋神宗素知程颢之名,一见之下爱慕顿生,自此频频召见咨访。程颢“务以诚意感动人主,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为此神宗屡屡“俯身拱手”,心悦诚服地说“当为卿戒之!”每次程颢告辞时,宋神宗都会说:“卿可频来求对,欲常相见耳。”
一天,两人相谈甚欢,忘却了时间。听到廷中宦官报午正,程颢这才告辞退出,就连太监都不无嫉妒地对程颢嘟囔:你难道不知道皇上没有进食吗?
王安石准备变法之初,朝中言官持反对意见,对王安石攻之甚力,为此王安石常常被搞得怒不可遏。有一次,程颢被召至中堂议事时,王安石正在声严色厉地训斥人,程颢不疾不徐地说:“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听到这话后,王安石立刻为之愧屈。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多有不合人情处,为此程颢上书宋神宗,在《论王霸札子》中他指出:“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
之后,程颢又上《论十事札子》,认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这已经是在直接反驳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了,正如后来朱熹所评论的:“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
公元一〇七〇年,宋神宗熙宁三年,程颢上书论新法之害。他义正词严地对神宗说:“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无事。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徼幸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
自此,王安石与程颢决裂。但即便如此,王安石仍敬重程颢的人品与学问,并不深加追究,只是将他降职为提点京西刑狱。但程颢固辞,最后改为镇宁军节度判官。
朋友遭黜、贤人远潜之后,朝中鸡鹜满堂,这不能不让人失望加绝望。公元一〇七二年,四十一岁的程颢以回家侍奉年老的父母为名,请求归家。最终,他以监西京洛河竹木务的闲差,罢归洛阳,自此开始了他的退隐讲学生活。
王安石能放过程颢,但邀功示宠的小人却不能。很快,李定、何正臣等一批政治投机钻营者,跳出来弹劾程颢,说他学术迂阔,趋向僻异,更为恶劣的是在新法推行之初,他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引来喧哗一片。朝廷于是再次罢免程颢官职。
程颢从此成了一位全职教师。也就是在这时,一大批日后成为北宋硕学奥儒的青年俊彦,如谢良佐、吕大临、韩维、李端伯、游酢、杨时、林志宁等人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前来追随二程从学。
没有被罢官之后的沮丧,没有仕途失意之后的颓唐,相反,程颢“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虽然遇到仓促之事,他也不动声色,始终从容恬淡,静虚守诚。
胸中充养有道,所抱所执的是大道与正义,是知性和真理。真理在握,心中就会始终光明一片。故而,外在的政治遭际、生活境遇的变故便渺小不堪,其有所失也会泰然,有所得也会淡然。
韩维在《明道先生墓志铭》中记有:“先生之罢扶沟,贫无以家,至颍川而寓止焉。大夫(指程父)以清德退居,弟颐乐道不仕。先生与正叔,朝夕就养无违志。闺门之内,雍肃如礼。家无儋石之储,而愉愉也。予方守颍川,遂得从先生游。”
《龟山语录》也载:“明道在颖昌,先生(指杨时)寻医,调官京师,因往颖昌从学。明道甚喜,每言曰:‘杨君最会得容易。’及归,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宁,出入潞公门下求教。潞公云:‘某此中无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从之。’因使人送明道处。志宁乃语定夫及先生,先生谓不可不一见也,于是同行。”
得天下英才蓄而教之,这是孟子的人生至乐。高徒满座,穷言性理,此时的程颢、程颐心中一定再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图,还有马融雅乐高陈的绛帐授徒图。否则,他不会用马融送何休离开师门时那句充满自负的话“吾道东矣”来送给弟子杨龟山。
公元一〇八六年,宋神宗死,宋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司马光回朝任相为标志,“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作为“熙宁变法”这一政治事件的句点,新党领袖王安石于此年谢世。
作为王安石政治上的仇敌、生活中的挚友,旧党领袖司马光也在这年死去。
而在此前一年,公元一〇八五年,程颢已逝。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苹吹尽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这是程颢罢归后的诗作,此时可以题写在挽幛上送给作者本人。
一
大程的谢幕,意味着一直避世就隐的小程该登台露面了。
早在公元一〇六四年,吕夷简就向宋英宗上书举荐程颐,时隔二十二年后的公元一〇八六年,吕公著与司马光再次联名举荐程颐:“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
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为了一个有才华的人不隐没于市井,父子两代一厢情愿地接力式地坚持向朝廷举荐,这在中外历史上很鲜见。
但程颐执意要做他的“处士”。
被授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推辞;后又授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程颐再次婉拒;继而,太皇太后又任命程颐为崇政殿说书,这次任命书上,太皇太后高氏额外加了备注:不准推辞!
于是,五十四岁的程颐开始当起公务员,成为大宋皇帝宋哲宗的老师。
与程颢平和亲易的性格特点形成强烈对比,程颐在行事待人上持躬谨严,绝无苟且,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平日里,他“衣虽布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致养其父,细事必亲”。
教学中,他将“至诚”作为宗旨,而且不仅表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间,还贯彻在他与生徒的交往款接之中。
有一次,在与弟子游定夫、杨时谈论学问时,可能因为太累,先生于不知不觉中悄然在座上睡去,恭立一旁的弟子既不敢叫醒,又不敢离去,只是呆鹅一样傻站在那里。程颐醒来发现后,也只说了一句:“日暮矣!姑就舍。”二人退出后,门外雪深尺余。这便是著名的“程门立雪”典故。
为此,程颢就对程颐说:“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话说得很委婉,但其中有指责其苛严的意思。
待己与待人都十分苛严的程伊川,现在要为大宋九岁娃娃宋哲宗进讲,会是什么结果呢?
程颐至诚至敬,不容懈怠,每次进讲前,他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皇帝虚心听讲。讲论之中,又常常围绕经典中的义旨,将之延伸到皇帝生活中的细节,进行反复推明。
当听到宋哲宗在宫中洗漱时生怕伤及蚂蚁性命,他及时予以褒奖:“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一日讲罢未退,哲宗童心忽起,折根柳枝随手玩耍,他则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
管得太多、太细、太严,在九岁的宋哲宗眼中,这个一丝不苟的糟老头子一定讨厌死了。
而在宰相吕公著及文彦博等人眼中,则是妩媚景象。有一次入侍经筵,他们听了程颐的讲课之后,退而相与叹曰:“真侍讲也!”
而不通江湖之险、人心之恶的程颐,也欣然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为自己埋下了招致嫉妒,乃至诬陷罗罪的种子。
此时,翰林学士苏轼以其不世出的文采名闻天下,文士多有向归。作家们大都行为狂放,不乐拘检,因而,苏轼门人常常取笑程颐的迂阔,程氏弟子则讥苏轼学不中理,没有规矩。于是,程、苏门下生徒遂恶语相向,在朝中逐渐形成了相互攻讦且势不两立的洛学、蜀学两派。
一根导火索恰在此时被点燃了。
有一次,宋哲宗患病,不坐朝数日,大臣们却不闻不问。程颢于是指责臣宰们失职,这自然就得罪了众人。苏轼门生、谏议孔文仲首先发难,上奏程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巿井目为为五鬼之魁”,要求将之流放千里,以示典刑。
已经不耐其烦的哲宗,趁机将程颐撵走到西京洛阳任国子监。他请求辞官,不获准。公元一〇九〇年,程太中病亡,程颐这才以丁父忧的名义辞职。
公元一〇九四年,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死去,宋哲宗亲政。正处于青春反叛期的赵煦几乎是带着一腔仇怨来对待奶奶执政时所赞赏的一切。于是,变法派章淳、吕惠卿、李清臣等回朝执政,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谥职,吕大防、刘挚、苏辙等流放岭南,并为王安石翻案。
年轻的赵煦同志以为,凡是被保守派反对的则一定是改革派,那么被苏党所排挤的程颐就应该被启用。于是决定任命程颐为秘阁西监,程颐当然仍辞却不就。
自然,新党也绝不会将程颐视为同类。公元一〇九七年,程颐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削籍,“送涪州编管”,被贬到涪州(今绵阳)交地方官管制。
公元一一〇〇年宋哲宗死,宋徽宗即位。皇太后向氏摄政。与先前的太皇太后高氏一样,她也是坚定的反对改革派。于是,宋哲宗时遭受打击的保守人士又得以启用,改革派遭到贬谪。程颐被赦,恢复宣德郎一职,返归洛阳。同年十月,又被任命为职掌西京国子监。
然而受命仅一个月,程颐即托疾辞归。学生尹焞不解老师这是何意。程颐告诉他:“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则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盖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后唯吾所欲尔。”
多年游历官场,他太清楚其间的污浊与嚣杂,也终于知道其间的波谲云诡与反复不定。本身就无仕进之心的他,此时早已厌倦了官场。但新皇帝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一个月赴任后即告别政治,从此在书院里与自己的书籍和学生消磨余生。
公元一一〇三年,宋徽宗亲政,改年号为崇宁,意思是崇法熙宁。像演戏一样,改革派再次压倒保守派,历史上著名的奸相蔡京入朝被启用。
蔡京上台后,对原先的改革与保守派实行双向打击政策。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保守派一百二十人定为元祐奸党,又将元符末年主张恢复变法的官僚定出邪类近二百人,与前者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勒石记丑。
程颐名列元佑奸党,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而且被勒令关闭学院,尽逐学徒。程颐被迫迁居洛阳龙门之南,临行前,他无奈地对跟随他的四方学者说:“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
公元一一〇七年,遭受着巨大政治迫害的七十五岁老人程颐,在孤苦伶仃中悄然死去。
秋高风怒,旷野凄绝,其景其情让人辛酸。
公元十八年儒学大师扬雄别世,寒风中为大师送葬的,还有一个叫侯芭的学生。而程颐此时身边却寂无一人,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钧、吕大临等“皆班班可书”的弟子们,没有一人能到场送行。
五
程颐生前曾对弟子张绎这样说过:“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
这其实是在向后人言明:我所传之学、求之道、行之事,皆与程颢同。
他在所写的《明道先生行状》一文中说程颢:“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
这段话不仅是小程称颂大程的话,也应该是二程共同的为学之旨。此中包含的一个深意是,既然善治要由真儒来恢复,政统要由道统来确立,那么道统之尊要胜过政统的王权之尊。显然,他也将这段话送给了自己。
这就是后世将二程学术融而为一,共称为“洛学”的肇始原因。
《二程遗书》中除个别地方外,所有语录前基本上均不交代是明道还是伊川所言,可见已将其认定为一个学术整体。
二程从“明庶物”开始,致知至于知止,探求自然界的原理,发现“一物须有一理”,进而了悟“天下只有一个理”,“天理”为最高形态的存在,是万物的本源与本质,所有的物理都统领于“天理”之下,也即“理一分殊”。如此,他们就为宇宙间万物找出了一个绝对的独立实体,同时也是一个精神本体。
这个精神本体因其具有“实”与“本”的本质属性,因而绝不同于佛、道的空无与抽象,而可以用世间一切物理之象进行阐释。那么,天理就成为社会伦理道德之上的标准。“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有何异矣。”他们为此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就是控制人形而下的本能欲望,提升人自身的道德回护水准,使人在“天理”朗照之下,不断修正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从而寻求美德与善良。
故而,他们提出识仁、主诚、主敬、定性的为学四要:“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正是在二程的共同努力下,宋代理学才具有了完备而成熟的哲学思想体系,使得“天理之微,人伦之着,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而周、孔、孟氏之传,焕然复明”。
二程为学虽为一体,其道虽同,但造德之法则各自有异。
黄百家指出:“顾二程子虽同受学濂溪,而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
朱熹也说过:“明道宏大,伊川亲切。大程夫子当识其明快中和处,小程夫子当识其初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
性格及行事的差异只是外在表现,学理上的各守其创才是二程之间的真正不同之处。
比如对“理”的认识。程颢认为,“理者天也”,“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天人无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在他这里,天理并不离开具体的事物而独自存在。因而,明道先生的学术思想以后发展延宕为宋明理学的心学一脉。
而程颐认为,“若论道则万理皆具,更不说感与未感”,“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四海而皆准”。在他眼中,“天理”更偏向于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更接近于希腊哲学中的概念或形式。所以,伊川先生的学术思想以后发展成宋明理学分蘖出的理学一枝。
心学一脉将诞生出以陆象山与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学派,理学一枝将繁衍出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
两位兄弟合其大成,独树一尊,又分别影响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之儒学两大学派,世所罕见!
又何止于此呢?
完全契合了《诗经·;周南·;桃夭》中这首诗所描述的意象:“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程颢、程颐死后,经其弟子倡举,林木繁密,落花遍野,洛学向四面八方挺进,大兴于天下。“洛学之入秦也,以三吕;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谢湜、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刘、许、鲍数君;而其入吴也,以王信伯。”
桃李天下,果实累累。二程兄弟在文化夜空中相对而坐时,会时时相视捋须一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