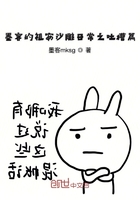“忍人”不是我的杜撰。这一概念早已出现在《左传正义·文公元年(二)》子上论商臣中。子上曰:“蜂目而豺声,忍人也。”蜂目,就是像蜜蜂那样凸出的眼睛;豺声,自然是豺狼之声。中国的相命师不仅喜欢探索面相,还喜欢探索心相。一探索心相就涉及声音。蜂目,属于面相,豺声则属于心相。赵翼《瓯北集》卷七《赠相士彭铁嘴》中说:“古人相法相心曲:豺声忍,鸟喙毒,鸢骨躁,牛腹黩。”这也是讲人发豺声性格就有“忍”的特点。蜂目与豺声都是忍人的标志。
不过,这种标志也不那么确定,例如,我国著名的大忍人秦始皇,他的面相虽也与“蜂”有关,但不是蜂眼睛,而是蜂鼻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也许“蜂准”比“蜂目”更可怕,所以才会干出“焚书坑儒”的坏事。如果秦始皇不是一个忍人,他是不会开创这种屠杀知识分子和屠杀文化的先例的。
我不是相命师,但能理解把“蜂目”和“豺声”视为“忍人”符号的相意。中国人常常喜欢用兽性与畜性的特征来比喻人性恶,譬如,以猪喻蠢,以狐喻猾,以狗喻贱,以猫喻媚,以虎喻猛。当某些人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时候,不是具有兼容万物的襟怀,而是集中了各种兽物畜物之特性。豺之凶残与蜂之恶毒集于一身者,谓之忍人,是很恰当的。聪明的祖先创造语言的天才,至今还让我们这些后人佩服。
不过,我的“忍人”概念,不是从面相与心相概括出来的。因为判断蜂目、蜂准还好一些,而要判断“豺声”却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在中国的今天,森林砍伐得很厉害,豺狼因此也稀少了。我至今没听过豺声,这就难办了。自然,如果要把社会中那些老是讲杀戮、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讲全面专政的喧啸称作豺声,倒也可以,但恐怕又得争论很久,所以还是不把蜂目豺声之人作为忍人的标志为好。
我想到的“忍”,是和“不忍”相对应的。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不忍”是一个重要概念。孟子最先讲不忍之心。他认为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就是“不忍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就是良心,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种特征,即和野兽不同的一种特性。例如,人见到同类被摧残、被杀戮、被迫害,就会产生一种同情心。这种同情心,野兽就未必有。一个正常人,见到妇女小孩掉到河里,总会感到不安。见屠伯砍杀人的手脚、头颅总会感到难受,不忍“目睹”,这是人性世界中某种神秘的东西在起作用,我们的古圣人把这种东西称作“不忍之心”。我想,有这种不忍之心的人,就是正常人,而不是“忍人”。忍人则是掏空这种不忍之心的人,他们对人类的不幸、灾难、残暴,能够做到不动情、不动性、不动心。由于见残忍而不动心,所以他自己还可以充当杀手。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可以干残忍的行为,而且还能毫不动心地欣赏残忍的行为,这种能够制造残忍和欣赏残忍的人,就是忍人。
中国老百姓常骂一种叫做“杀人不眨眼”的人,也就是忍人。如果一个人的内心还有一点与兽相区别的人性,杀了同类,至少会眨一眨眼,也就是动一动心,哪怕是一刹那也好。但世上就有一种连杀人也不眨一眨眼、动一动心的人。中国历史上这种人不少,所以他们才发明“凌迟”、“剥皮”、“油炸”、“五马分尸”及“株连九族”等刑法。能想出这些刑法和执行这些刑法的人,大体上都可以称作忍人。我曾对朋友说,忍人其实是一些未完成人的进化的人,但朋友不同意,他们反驳说,人与动物区别在于人能制造工具,倘若未完成人的进化,他们为什么能制造那么多精致的刑具?想想,觉得朋友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就退一步说,忍人是一些基本上完成了人的进化,但离兽类最近的一些人。
中国的忍人比较著名的都出自宫廷。凡人中自然有很多忍人,但其忍的故事不易流传,身居宫廷和身居高位的人,往往暴戾无忌,而且有史官作记录,因此,他们的残忍反而能遗留后世。中国的忍皇帝、忍皇后的故事很多,早在公元前一两千年,就出现纣王这种很有名的忍人。纣王使用“炮烙之刑”,把朝臣与劳工像烤肉一样地煎烧,将敢于直言的诸侯梅伯斩成肉脯并做成醢肉分给各诸侯王吃,以至把敢于说真话的王子比干杀死挖心,把文王之子伯邑考烹为肉羹,这都是常人难以置信的。纣王的残忍,不仅在于他敢杀戮,而且还在于他能欣赏杀戮,所以挖心之后还要欣赏一番,如《史记》所载:“剖比干,观其心”(《殷本纪》),把残暴行径作为一种和妲己玩乐的游戏,最后,他还把人肉制造成食品,让诸王分享。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把人性中的“不忍之心”刷洗得一干二净。刷洗得如此干净,确实也不容易。
汉代的吕后,也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忍人。汉高祖刘邦死后,她控制朝政,杀害功臣,剿灭仇家,可以说是做到“心狠手辣”的程度,符合我国“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对敌人一点也不能心慈手软”的要求。她杀害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真令人惊心惨目。《史记·吕后本纪》中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吕后这种残忍行为,便是忍人的典型事迹。惠帝虽然是吕后之子,而且身为皇帝,但因为内心还残存不忍之心,便不忍目睹这种残杀戚夫人的惨状。所以,他从此之后便称病而不听政。
身为皇帝而有些杀人的记录,本来并不足怪。因此,能以忍皇帝而闻名后代的,总有一些特别的残忍行为。例如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他所以出名,一是因为他杀人杀得太多,二是因为杀得太狠。他以“靖难”名义打败惠帝之后,竟把抵抗靖难军的前朝高官,一律处以死刑,并灭其三族至九族,一共杀了2500多人。其中杀惠帝的御前侍讲方孝孺和御史大夫景清,更是空前残忍。明成祖入京后,要方孝孺起草登基的诏书,孝孺不仅拒绝,而且写了“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成祖大怒地问方孝孺:“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骂道:“便十族,奈我何!”明成祖果然杀灭了方孝孺的九族加上学生一族,共十族,一举杀了800多人,而方孝孺本人则两边被割杀至耳根后磔于市。景清也被诛杀九族,连远乡亲属也一个不留,真是做到“除恶务尽”。此外,在朱棣起兵时,身为惠帝时山东参政并在济南屡破燕王兵(之后因此升兵部尚书)的铁弦,也遭到朱棣最残忍的处罚。处罚本也可以理解,但已当了永乐皇帝的朱棣却令“割其耳鼻……逐寸磔之……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割切、剁碎、油炸,使人体化做煤炭都极残忍。这种行为对中国人产生过很深的心理影响。在中国政治斗争史上,变节的人较多,与中国具有这种特别凶残的酷刑有关。
说到忍人,人们自然会气愤。所以纣王、吕后总是被后人所诅咒。永乐皇帝登基之后虽文武兼治,表现出一些雄才大略,但他的残忍,却仍然未能被后人所原谅。中国语言中的“容忍”二字,还是有些界限,像吕后如此惨杀戚夫人和朱棣如此残杀政敌,无论如何是人类道义难以容忍的。倘若人类对于这种残忍行为没有良知拒绝的力量,那么,人类就要退回野兽界。但世界上的事非常麻烦,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被做出另一种解释,包括残忍的行为也可以被解释得十分合理甚至神圣化。这种把残忍行为神圣化的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时而是“法治需要”,时而是“礼治需要”,时而是“革命需要”,时而是“改革需要”,于是,认真的学者常常感到头疼。
就以长着“蜂准”的秦始皇来说,他的焚书坑儒,把那个时代本来就很稀少的400多名知识分,硬是活埋,无论如何,这种用最残忍的手段无端杀害知识者的暴行,是绝对不符合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德准则的,但是,历史上为秦始皇辩护的人还是有的。辩护的理由就是法治需要。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类社会已文明得多了,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又再次成为光荣事迹。他被封为“伟大的法家”,成了现代“文化大革命”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先驱。在“批儒评法”运动中,骂秦始皇也变成一种“罪”,必须“斗私批修”,于是,一代年轻人就不知道如何看待“焚书坑儒”的凶残行为了。一种本来最容易分清是非的历史事件,也说不清楚是非了。这么一来,“焚书坑儒”就有理,作为“儒生”的知识分子就活该倒霉,不断地被“坑”下去了。
以法治的名义所做的辩护可怕,以礼治的名义所做的辩护也很可怕。“五四”时期,吴虞《吃人与礼教》一文,以臧洪、张巡杀妾为例,揭露以君臣之礼的名义杀人吃人,是有道理的。安禄山造反时,为唐皇坚守睢阳城的将领张巡,因被围困很久,城中粮尽,处于饥饿之中。张巡为了挽救危局,继续坚守以效忠王朝,便杀了他的爱妾,以飨三军。他对所属军士说:“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张巡杀死了爱妾之后,全军泣下,感动了全城,接着城中百姓便纷纷效法张巡杀妻杀子,竟一共吃掉了二三万人。张巡杀自己的妻子并把妻子的肉分给战士们吃,这种行为是对还是不对,常有争论。张巡被新旧《唐书》写入《忠义传》中,自然是忠义的模范,他的行为虽然残忍,但符合忠诚原则,符合君臣之礼。以忠于领袖的名义,可以把这种大规模的直接的吃人行为变得那么神圣,难怪忍人也可以变成圣人。历史的荒谬被现代人所重复自然就更加荒谬。“五四”运动固然批判了张巡杀妾,但“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将们已不知道张巡为何人,他们在“忠于领袖”的旗帜下,任意打人甚至杀人,把人踩上一万只脚,也觉得是“忠义”的壮烈行为,其道德标准又与张巡相通。到了此时,残忍又变得神圣。以圣人的名义干忍人的事,又成了大时髦。我们面对残忍,如果不说“好得很”,而说“糟得很”,那就有立场问题了。
还有一层麻烦的以革命名义所做的辩护。像张献忠、孙可望这些农民革命领袖,其残忍是很有名的,他们对敌手总是用“剥皮”一类的极端手段,但因为他们是在革命,所以不仅应当原谅,而且应当用“历史长卷”为他们写颂歌。“文化大革命”中,一听到“油炸×××”、“千刀万剐×××”就毛骨悚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的许多时日,我的耳边充满这种声音,心里一直发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听了许多如张志新被割喉管的惨事,总是连日做噩梦。但是,这种残忍的声音和行为,总是被革命的词句所掩盖,他们用的是“造反有理”的指示,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因此割张志新的喉管也是革命,其暴烈行为也是革命的应有之义。至于“油炸”、“千刀万剐”等,自然也是革命逻辑。
大约因为给残忍行为找到的理由愈来愈多而且愈来愈神圣,所以忍人便以“坚定的法家”、“钢铁般的革命战士”等名目在中国迅速繁殖。很奇怪,文明的繁殖很难,而野蛮的繁殖却很快。现代的中国,蜂目不一定增加很多,但豺声确实布满天下。忍人不仅横行无阻,而且显得崇高,而那些具有不忍之心的人自然变得可笑,不仅落后,而且因为残存人道之念而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即历史的“罪人”。不过,这么一来,残忍与崇高,忍人与圣人,罪人与非罪人,就分不清楚了。无数的同胞,再也没有拒绝残忍的良知力量了。这样下去,忍人集团便愈来愈庞大,未来的社会,倘有阶级斗争,恐怕就是非忍人阶级与忍人阶级的斗争,相当于人与兽的斗争。


![[苏]阿莫纳什维利实验教学体系与教育论著选读](https://i.dudushu.com/images/book/2019/09/28/0555130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