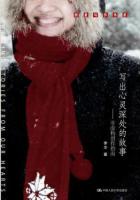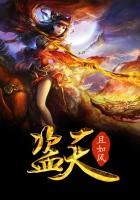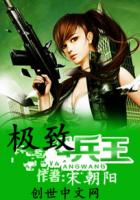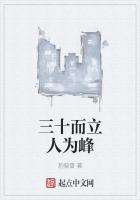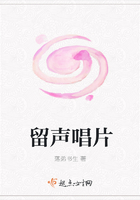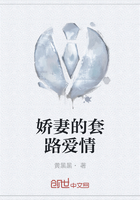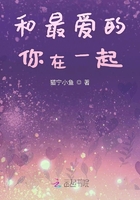王安忆 陈思和
陈:你看过《出道》没有?就是发表在《上海文学》去年第九期上的那篇。作者真写出了一个“文革”时代上海市民社会中的少年阿Q。他的人生开端,适逢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他的许多朦朦胧胧的感受中,都含有悲壮的味道。
王:我看过的,好像这个人物是71届中学生,也有点儿接近69届、70届的那一伙。
陈:差不多。他与你笔下的69届初中生一样,你的人物都偏重于自我心理分析,属于理智型,而《出道》里这个人物则是懵里懵懂的,在行动上比较受外界环境的支配,他的自尊、自豪抑或愚昧在这里还只是表面现象,更主要的是揭示了无知的价值,它多少证明了十年以前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在无知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与俄国民粹运动不一样,没有丝毫的神圣性。志强这个人物更具市民社会的特征,可以说是你所写的69届形象的一个补充。
王:69、70、71届这代人其实都是牺牲品。我们不如老三届。他们在“文革”以前受到的教育已经足以帮助他们树立自己的理想了,不管这种理想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毕竟有一种人生目标。后来的破灭是另外一回事。可69届没有理想。
陈:我记得你有过一篇短文章,对“6”和“9”的颠倒字形作了分析,是很有意思的。69届初中生,就是颠三倒四的一代人,在刚刚渴望求知的时候,文化知识被践踏了,在刚刚踏上社会需要理想的时代,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变得荒谬可笑了。人生的开端正处于人性丑恶大展览的时期,要知识没知识,要理想没理想,要真善美,给你的恰恰是假恶丑,灾星笼罩我们的十年,正好是13岁到23岁,真正的青春年华。
王:即使到了农村,我们这批人也没有老三届那种痛苦的毁灭感,很多都有《出道》中志强那样朦朦胧胧的,甚至带点好奇和兴奋的心态。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朦朦胧胧之中,整个社会就改变了。我们这一代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但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生活观念,所以也是很不幸的。理想的最大敌人根本不是理想的实现所遇到的挫折、障碍,而是非常平庸、琐碎、卑微的日常事务。在那些日常事务中间,理想往往会变得非常可笑,有理想的人反而变得不正常了,甚至是病态的,而庸常之辈才是正常的。
陈:这一代实际上是相当平庸地过来了,作为一个作家能够表现这种平庸本身并加以深入发掘,实在要比虚构出一段光辉的历史更有意义。
王:记得我刚刚写完《69届初中生》时,你说过这样的话:雯雯在前半部分是写我自己,后半部分走到平凡人中去了。这有道理,雯雯当然不是我的全部,我后来当了作家。为什么能当作家?就是因为我比雯雯复杂得多。这也是《69届初中生》简单化的地方。人还是有差别的,我有时候会相信古典主义,喜欢起华丽的辞藻,向往崇高。
陈:那是浪漫主义。其实69届一代人很难有浪漫气。
王:不过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还是有的。境界高的人,有时有点孤独。
陈:其实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体验能力。你能感受的,人家也能感受。只是有的人意识到了,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没有领悟。即使是庸常之辈,也有很复杂的心理。我喜欢看你的小说,就是因为你把普通人写得很丰富。雯雯就是一个丰富的庸常之辈。在你写了《墙基》《流逝》之后,许多评论家都很高兴,赞扬你从雯雯的“小我”走到了“大我”。但我始终认为你更适合于写雯雯这样的人物。问题是一个作品的深刻程度不仅表现在它所展示的场面的大小,还可以表现在人物心理挖掘的深刻程度上。有时很奇怪,一个经历很复杂的人,不一定感受就很深刻,有些人“文革”时期挨过整,受过苦,恢复原职以后反而变得麻木、卑琐,这是为什么?是不是经历过多,更压抑了心灵感受新事物的能力?有些人经历不复杂,可是他对生活体验得深透,心灵的感受能力强,认识事物就深刻。你说歌德的经历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他的作品也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宏伟画面去概括德国整个时代吧,但他就是把人物写得相当深刻,一个维特,一个浮士德,都展现了时代的精神。我觉得也应该从这个标准来要求你。我写了《雯雯的今天和明天》,我不希望雯雯没有明天。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人物写得更深刻。我喜欢这个作品,是因为你写了一个很平庸的人物,没有英雄气,与外国的教育小说不一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特色,作品毫无做作地刻画了这一代人。
王:我们这一代人被捉弄得太厉害。叶辛曾告诉我这样一件真人真事:他在贵州插队时有一个女孩子,在知青回城时,唯独她还留在那儿。后来,村里有一个又丑又穷的无赖打她的主意。那无赖就对她说,你应该结婚,不然就要灾难临头了。不信你将一只电灯泡放在哪个地方,如果三天内打碎了,那就是真的。那女孩子真的这样做了,到第三天,一不小心果然把电灯泡打碎了,她就哭着去找那无赖。无赖说,你再去把一件东西放好,如果三天内又打碎了,你就必须嫁给我,不然你就大难临头了。她便又去把一个灯泡藏在箱子里,心想这下不会再打碎了吧?一天、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恰是好天气,她忽然想去晒晒箱子,结果真的又把灯泡跌碎了。她真信了,就嫁给了那无赖。后来叶辛去看她时,她一句话也不说,抱着孩子,坐在门槛上,就是哭,一个劲地哭。你看,人到这种时候,什么都会相信,一张扑克牌都能决定一个人的终身命运。
陈:可惜的是这些事在知青文学中反映得太少,知青作家始终没有像西方现代青年厌恶战争那样去厌恶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没有对它的反动本质给以充分揭露,实在是使人失望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人口大迁移都是残酷的,或者战争,或者专制性的迫害,但人口的迁移在客观上也促使了文化的横向交流,在惨重的代价下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除了给国家,给一代青年白添了巨大的损失以外,我真不知道促进了多少文化的交流。知青原来在城市多少经过一点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刚刚下乡时也确实抱有天真的想法,可是下乡后遇到了什么?中国落后的农村文化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了他们,吞噬着他们身上萌芽状态的现代文明,经过几年下乡,到底有几个人的素质提高了?恐怕是极个别的吧。但文学作品并没有把这种倒退的历史悲剧写出来,即没有把落后的文化怎样抹杀现代文明萌芽的事实写出来。
王:不过情况不太一样。老三届下乡时,大多是满怀理想的,要他们承认自己的失败是很痛苦的,他们把这种失败也看得很悲壮。
陈: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正视自己的勇气。
王:还有许多人去过边疆,也许他们所接触的民众,还带有原始的先民风味,感受要好一些。但我就不一样,第一是69届初中生没有理想,第二是我插队的江淮流域,那里的农民已经受到较重的商品经济的污染,所以我在农村的两年中,很少有农民对我真心好过,有时表现得对你好,也是从私利出发的,不能说他们很坏,但也决没有那种无私、博大的气质,他们太穷,贫穷实在是件很坏的事,人穷志不穷是少数人的事,多数人是人穷志短。
陈: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值得同情的,它是历史所造成的,这个责任不是由哪一代、哪一些农民能负得了的。但我们在同情他们的人生的同时,不能不认清他们身上的许多弱点。而许多知青文学,包括你的在内,却把农村写得一片纯朴,一片仁义,把城市人原来的各种烦恼、痛苦、厌倦的心情,在农村中予以解脱,一派民粹主义的味道,这显然是片面的。
王:我只插队两年,我总不能用我两年的经历去否定别人的经历。但就我自己来说,我对下乡本来就没抱多大的希望,我那时只觉得上海的生活太无聊了,无聊到病态,就想改变一下环境。但一到农村,马上又后悔了。以后就整天想上调,找出路。我那时跟我妈妈写信说:“你当时阻拦我去,只要花一笔钱,让我先到我姐姐下乡的地方去住几天,我马上就会改变主意的。”真的,下乡以后,我后悔极了。就是后来进了文工团,我还是感到寂寞无聊,早上起床后不知干什么,这是很不好受的。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感到更加惆怅,总感到这么好的天,我干什么才能对得起它呢?
陈:所以,你作品中每写到人物的百无聊赖的情态时,特别传神。
王:是吗?现在就没有这种情绪了。我发觉我的人生似乎是这样的,一个是写小说,一个是谈恋爱,经过一段时期,我小说写得成功了,也结婚了,这两件人生大事是同时完成的,这样,我好像就找到自己的路了。我现在的心境的确很平静。
陈:对了,你在作品中几处写到主人公三十岁以后,有了孩子,就感到人生似乎完成了,这是怎么回事?是否是某种心理暗示的幻觉?我觉得人生在三十岁之后,会面临更多更深的内心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比青春期的幼稚与冲动了,往往是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压抑了。生了孩子以后,在自我价值的辨认上恐怕会更加痛苦。
王:但这对于平凡的人生来说,这一些也就够了,我自己有时也感到这种心态很糟糕,可我也不太愿意打破这种平静,没办法了,生活环境已经把我铸成这个样子了,定型了。
陈:中国过去的女作家,如冰心等,在三十岁之后,都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这是很可惜的事。往往人到了而立之年,社会形象已经确立,作家是作家,学者是学者,一般人都没有勇气打破这种心理平衡了。打破这种平衡,便意味着你以前所营造的一切将全部失去,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但在对自身,对人的认识上是应有不断的更新和深化的。托尔斯泰在这一点上不仅是作家的典范,也是所有人的典范。所以,怎样进一步认识自己,是三十岁以后人生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社会经历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认识自己。对自我认识得越深,在文学上就越有创造。
王:在这一点上我也感受极深。我现在没有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需要,在创作上,过去写作是情绪的宣泄,是一种内心骚动所致,现在感到是在创造,为创造而创造,我可能遇到一种危机了。
陈:也不能说是危机。你有危机感,那说明你还是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当你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自己时,这种意识就明确了。也用不着硬是去寻找需要。主要取决于心理上的变化,倒不是外在生活境遇的人为变化。而这种心理变化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对你能写出《小城之恋》,实在是抱着极大的喜悦。
王:可是我也挨了不少骂。现在人们把我列为“性文学”的作家,我当然无置可否。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理解我。
陈:你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最初想表达、探索些什么?这是我希望得到你的证明的。从我的理解来说:看了《69届初中生》以后我就感到你应该回到你自己。后来看了“三恋”,以为这是对《小鲍庄》的一个突破,你又回到了雯雯的反身收视状态。
王:这个感觉我也有。我曾告诉李陀说,我写“三恋”又回到了写雯雯,李陀不同意。其实我的小说确是回到了写人自身了。
陈:当然不能讳言你写了人所具有的性的欲望。这在新时期小说中有一个发展过程,认识性是与认识人自身同步深化与成熟起来的,一开始从极左思潮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时候,连爱情都只能写成柏拉图式的,后来写了人有爱的欲望,有性的欲望,但仍然是小心翼翼地躲藏在政治社会的盾牌后面。像张贤亮的“性文学”,还不是真正地写“性”,他是写人的“食”“色”,两种人的最大自然欲望,在不正常的政治背景下被可怕地扭曲了。而这一点,恰恰是现在的许多批评家们最欢迎的,他们以为这不是单纯地写“性”,而是通过“性”来反映社会历史文化内容,这比单纯写“性”要有意义得多。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性文学”,说明我们的文学还没有认识到写“性”的意义,进一步说是对人的认识没有进入一个自觉的阶段。这样一些作品,当然有它们自己的贡献和长处,但这种贡献主要还体现在把人当作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评判的工具这一层面上,作品最终表达的还是社会问题,如社会历史环境是如何压抑人的正常生理欲望的,这里的“性”本身,只是被借来用于揭露社会的工具。所以,这种小说可以说是社会小说,但不是真正地对“性”——这种人的生理本能进行探索的小说。把“性”作为“工具”来描写,是“性文学”的庸俗化。
王:他们对这种小说容易理解,也容易评论。
陈:这类小说有很虚伪的地方,即使在审美趣味上也是这样。一方面写性,赤裸裸的,让你得到潜在的满足,另一方面又要罩上“社会意义”的外衣,你明明是对他写性感兴趣,可进入理性评判的时候,却心安理得地大谈其社会意义,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
王:我认为有两类作家在写爱情。三四流作家在写,是鸳鸯蝴蝶类的言情故事:二流作家不写爱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难以跃出言情小说的陷阱,所以干脆不写:一流作家也在写,因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陈:“三恋”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把作品中所有的社会背景都虚化了。按理说,《小城之恋》中两个演员的恋爱婚姻,如果放在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肯定发现它是受社会环境的多种制约的。但你把背景淡化了,从而突出了这两个人。你有意把读者的眼光集中在人自身之上,似乎打出这样的旗号:我的作品就是写人自身。人果然不能离开社会群体,但人本身又有他的独立性。你的作品就是强调后者,强调人的本体的生命力对人行为的支配、生命存在的意义、生命的延续等等。这就好比把人放在手术台上细细地解剖一样。
王:我写“三恋”可以追溯到我最早的创作初衷上去。我的经历、个性、素质,决定了写外部社会不可能是我的第一主题,我的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别人的事我搞不清楚,对自己总是最清楚的。一个人刚创作时,虽然不成熟,但他往往很准确地质朴地表达出一个人为什么而创作。我写《墙基》《本次列车终点》时,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追求什么,是在追求改变自己的创作路子,当时也的确感到走出雯雯世界很好,有很多新鲜的感受。但我在写“三恋”时却并无感受到很强冲击力,也没有执意去追求写性,我觉得很自然。我写的第一个故事是四个人的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一出爱情悲剧,四个人好像在作战。爱情双方既是爱的对手又是作战的对手,应用全部的智力与体力。爱情究竟包含多少对对方的爱呢?我很茫然。往往是对自己理想的一种落实,使自己的某种理想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得到实现。《荒山之恋》中的那个男人很软弱,但他也要实现自己逃避的梦想,而那女孩其实是一种进取型的女子,他们其实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当然爱情还包括许多很隐秘的东西,如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能战胜男人,往往很自卑的女子却能得到男子的爱,这为什么?第二个故事是写两个人的故事,《小城之恋》中的人物行为如不用性去解释,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的谜就始终解不开。这个作品你已经评论过了。第三个故事是一个人的,一个婚外恋的故事,女主人公感到自己已在丈夫面前什么都表现尽了,丈夫对她也熟悉无余了,她有角色更新的欲求不能实现的感觉。其实她并不真爱后来的那个男子,她只爱热恋中的自己,她感到在他的面前自己是全新的,连自己也感到陌生。所以,爱情其实也是一种人性发挥的舞台,人性的很多奥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释。
现在我的处境很尴尬,有人说我写性,这一点我不否认;还有人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我在这里要解释我写“三恋”根本不是以女性为中心,也根本不是对男人有什么失望。其实西方女权主义者对男人的期望过高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女强人(确也只在知识分子中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女人对男人本来没有过高的奢望,这很奇怪。所以,我写“三恋”,根本不是我对男人的失望……
陈:真正严肃地涉及性,实际也就是触及人性本身。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人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确认自身的全部价值,把人看作是纯粹的社会动物,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极端,但这种极端是被传统认可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遗传学开始发展,它使人意识到人性的构成除了社会文化的因素外,还确实存在着某种命定的力量。于是人们开始研究遗传学,强调遗传等生理视角来补充人物的性格缘由。这就出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过去我们往往承认左拉对人的社会性一面的描写,否定他对人的遗传性一面的开掘。其实应该反过来认识,左拉在巴尔扎克之后,他对社会性的描写没有超过巴尔扎克(当然也有个别方面是超过巴尔扎克的,譬如他写了工人斗争),但他对遗传方面的开掘则是新贡献。遗传科学的意义在当时还没有被人充分认识,然而到二十世纪就完全不同了。左拉对遗传的描写是凭才气想象的,没有科学根据,但他对人类认识自身提供了某种想象的基础。我觉得你的近期小说有点左拉味道,当然你的格局要比左拉小,只顾到人的自然主义的一面。
王:我确是感到遗传对人有重要的影响。
陈:关于这一点,我发觉你在《好姆妈、谢家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这个中篇里已经接触到了,“三恋”又有了发展。所以我说这几个作品有意义,写性,在你只是为一种更为宏大的研究人的自我确认的目标服务的。《小城之恋》突出地强调了在文学上被长期忽略的一个角度,就是把人看作一个生命体,揭示它的存在、演变和发展过程。这就必定会涉及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欲望。人之所以有性,是人作为生命体所自有的,而不是一种社会现象。人当然有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面,他的奋斗、交际、欲望等,但“性”却完全是人所“私有的”,而不是社会的。在社会上人们所追求的是公有的——对公众有意义的东西,而性恰恰是私有的、隐秘的。过去从社会角度探讨人的性欲,总是把性欲看得很肮脏。对于性的描写,西方文学史上除了人文主义时期对之有强烈的赞美之外,一般也把性看作丑恶的。即使有性描写,也是因为“有利于揭露资产阶级的生活糜烂、精神空虚的丑恶”而存在的。连左拉似乎也没有摆脱这一点。而你的《小城之恋》则完全是从遗传学角度写性,性不再是一种丑恶的现象,而恰从生命的产生到生命的延续的重要过程,是人体不可缺少的、正常的有时是美好的现象。这样得出的结论与用社会学眼光得出的结论就显出不同,它不是从道德去看“性”,而是从生命本体价值上去肯定“性”。这样,“性”是与整个人类对自身生命体的研究的科学联系在一起了,这才会使“性”在文学中得到公正的评价。从这个角度说,劳伦斯的作品也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如果在他的人物中寻找社会性,其意义是不会太大的,他是把人作为独立的生命现象,他的性描写丝毫没有丑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美好的感受。这是伴随着对人的更深刻的认识而产生的。这种用审美眼光来描写性的方式,在中国文学中几乎是没有的。
王:这可能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文化中没有一套美好的“性语言”。中国人在饮食烹调上可以有无数好听的名词,光面叫“阳春面”,蛋白叫“春白”等等。即使是《红楼梦》,它涉及性的语言也是狎妓性的。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封建文化发展过早,性太早就已经被功利化的缘故,像鲁迅说的,看见一条胳膊就会“三级跳”到私生子,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能用审美的态度对待“性”。
陈:如果光从语言来说,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写性写得漂亮的,《西厢记》里就有。但关键是语言背后是否隐含了健康的文化心理。中国文化传统中当然有写性的语言,只是没有健全的眼光,把性作为人性的淫恶来对待。所以,这样的说法有其合理性:在文学中用审美的眼光来描写性活动,是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的吃倒是审美的,非功利的。而性是为了传宗接代,是功利的。
王:中国人讲究吃也可能是性不自由的转移。中国文学中也有表现性的文字,只是并不直接去表现,而是寻找别的途径去表现性。我记得萧红有一个小说,写一个人每天独自匆忙地吃蛋炒饭,上面放着葱花,他的心理冲动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性冲动,只有用性心理去解释他的冲动,才能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吃有葱花的蛋炒饭。
陈:好像是《马伯乐》。
王:也许是的。我读了以后,再也不吃有葱花的蛋炒饭了。
陈:所以我说关键还在于语言背后的作者的情绪是否饱和,如果有饱和的情绪,情之所至,到时就非这样描写不可,决无猥亵的感觉,读这种文字,也给人以净化之感,而决非挑逗或发泄。
王:阿城曾跟我谈起在陕西观察到的农民对性的看法,他说那里的农民把性看得很崇高,很神圣。我没有去过这种地方,所以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我插队的地方,农民的人口也很多,也需要繁衍,但也许他们已经比较有钱,讨老婆不太难。所以,那里流传的许多关于性的故事以及笑话中,一点儿看不出性的尊严感、神圣感。不知阿城说的现象更有代表性,还是我感受到的更有代表性。
陈:追溯历史,在中国的神话和传统中对性也没有很好的描述,中国人对人体就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正与希腊人相反。中国礼教文化对人体的压迫很深重,总以为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连头发都不能剪削,否则就是不孝。这跟古希腊崇尚健美的风气完全不同。
王:我读《中国娼妓史》,作者追溯娼妓的起源,以为是古代巴比伦的宗教卖淫。巴比伦的少女,一生中必有一次是在一个清晨,跪在Venus的圣堂,第一个丢钱给她的男人,她则与他做爱,而此钱于她则成了一个神圣的东西。作者以此为印证,又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史例,推想出我国娼妓的起源是殷代的巫娼。我却觉得他的推想并无可靠的根据,反而觉得我们大约正是缺少了这一个宗教“行淫”的起源,而使得“性”在我们民族心理中,永远无法美丽、光明和神圣。
陈:古典的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郁达夫等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代赤裸裸地写性的作家,他们是在西方人文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写性的,写得很直率。特别是郁达夫,他毫不掩饰地写性苦闷,写手淫,写窥浴,写歌妓等等,都写得坦然,但语言也很粗俗,表现了内心的痛苦和渴望。他是把性作为人自身的痛苦加以表现的。
王:他的《茫茫夜》所表现的是一种变态性心理,而且还带有中国文人的“士大夫式”的自我压抑感。
陈:对,士大夫的高雅气质是郁达夫意识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的本性又是非常从俗的,行动被从俗的欲求所驱使,高雅的一面马上从理性上对之限制和批判,于是出现了灵与肉的分离。这是郁达夫最痛苦的,而真诚地表现这种痛苦又是他小说中最精彩的地方。
王:有人批评我的小说完全脱离背景。我想现在批判写性的,最好先研究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谈到性总是摆脱不了一种肮脏感?为什么日本人对性有一种犯罪感?为什么西方人对性则习以为常就像吃饭走路一样?这种心态的差别已明显地带有社会性了。所以,社会性与人性是不可分离的,我以为,性既是极其个人的,又不是个人的,它已带有社会性了,我们以前太强调社会对人性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人性对社会的决定作用。
陈:中国文化把性已弄得非常扭曲、非常阴暗了,现在不能再给性添以更多的阴暗了。对人类自身要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至少就不应该口是心非,不应该过分地虚伪。说性不符合民族欣赏的习惯,作为外交辞令是机智的,但要是拿来作为文学创作的规范则无异于赤裸裸地提倡虚伪,这倒不仅仅是对性的不同看法问题,而是一个国民性问题。
王:你看过话剧《马》吗?那个男孩是在追怀人类的童年。他带着人类初民对性的观念,性对他们来说还不是能完全公开的。我们认为,性行为是爱情的最高形式,但西方人却对之如此随便。那么,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爱情的最高形式是什么呢?《马》是重新提出性的羞耻惑,是对西方人对性的过分随便态度的反叛。而这种性的羞耻感已经带有对性的宗教般的神圣感,与中国人对性的肮脏感是两码事,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差距。总之,人性这东西真是太微妙,太丰富了,每当我接触这种主题时总感到它是无穷无尽的。
(宋炳辉整理)
原载《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