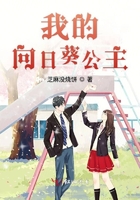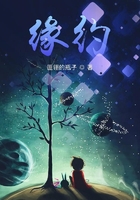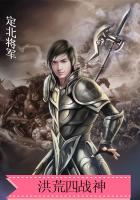汤一介,中国哲学家。
1927年生于天津,湖北黄梅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McMaster)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儒藏》编纂中心主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
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著作行世。
遇到事情你不要逃避它的困难
汤一介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的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
主持人:您父亲汤用彤先生给你起“一介”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这个含义,希望您一生读书做学问?
汤一介:我想是的,他是想让我传承家风。我父亲很少管我,不管我的衣食住行,不管我读书,也不管我做人,他只是埋头做学问。小时候,我喜欢读一点古诗,有一天被他看到了,他就把庾信的《哀江南赋》找来推荐给我,说你既然爱读古典,可以读一读庾信的《哀江南赋》。《哀江南赋》大致讲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父亲让我把这篇文章熟读,大概是想让我知道,我们是读书人家,读书是我们的本分,不要把读书的家风丢掉了。
主持人:您跟您的祖父其实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在您的传记里,您经常提到他。
汤一介:我祖父对我父亲有直接的影响。他曾经跟我父亲讲过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就是说,遇到事情你不要逃避它的困难,这一点在我父亲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我父亲是研究佛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学术上的难关,这个难关,在我父亲以前没有人能突破,是我父亲把它突破了,他做到了事不避难。另一句话“义不逃责”,就是说理应你做的事情,你就不要逃避责任,作为一名教授,我父亲教书兢兢业业,他也从不逃避教书的责任。
主持人:这种“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是否也影响了您?
汤一介: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介”这个名字对我还是比较适合的,我是非常喜欢读书的,现在我的藏书,在北大可以排第二,除了季羡林先生以外,我的藏书大概是最多的,有三四万册。
主持人:据说您小的时候学习并不是太好。
汤一介:严格地讲,我都没有拿到过小学和中学毕业的文凭,甚至大学毕业文凭也是后来补发给我的,因为在大学四年级下学期我就被调出去工作了,后来才补给我一个文凭,算我北京大学毕业。我读小学是在当年的北平(今北京),1939年我读小学六年级的第二学期的时候,此前父亲已到昆明教书,母亲想带我们到昆明跟父亲团聚,这样我们就离开了北京,辗转上海、香港,经过越南,然后才跟我父亲会合,结果我的小学没能念完,小学文凭没拿到。后来我到一所宜良县立中学读初中,在那儿念了一年级,之后转到昆明的西南联大附中,当时我想上二年级,可是一考不行,考不上,只好留了一级。初二下半学期我试图跑到延安去,可是没有去成,又被转到了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我不甘心上初三,跳级到高一,这样初中文凭也没拿到。到了高中,功课跟不上,又留了一级,最后,高中文凭也没有拿到。
主持人:在这个辗转求学的过程当中,您自己的责任好像并不太多,主要是环境的问题,因为当时时局动荡不安。
汤一介:有一些学生很聪明,可以跳级;如果我很聪明的话,也可以跳级。我没有跳级成功,足见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主持人:您觉得聪明是决定一个人最终成就的主要因素吗?
汤一介:那倒不一定。我记得我父亲讲过,第一流聪明的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连第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而第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是可以取得第一流的成绩的。
主持人:您是不是觉得您应该是第二流聪明的人,但是努力了?
汤一介:是努力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第一流成绩的人。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试图去延安,那段历史是怎么样的?
汤一介:初二下半学期,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找到了一本叫做《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延安这个地方,应该挺好玩的,而且也很吸引人,所以就想到那儿去看一看。
主持人:没有更多的政治原因?
汤一介:没有。当年的延安是一个很有朝气的地方,所以我们想去看看。我们五个人,各自偷了家里的一些金子,把它换了钱做路费就上路了,但是刚走到贵阳,就被当地的警备部队抓住了,把我们关在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一个小房子里。当时我们随身带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本书,非常危险,所幸关我们的房子铺着地板,晚上我们就偷偷把《二万五千里长征》撕掉,一页一页地塞到地板缝里面,第二天审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口咬定要去重庆念书,没有说到延安去。这样关了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学校的教务长来了,就把我们接回去了。
那一次,我积极参加了反美游行
20世纪40年代,中国灾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1943年他曾经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这一年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结果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由先修班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
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
汤一介:1943年正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经常批评当时的一些现象。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滴汽油一滴血》,当时达官贵人们常用汽车送孩子上学,可是在抗战困难时期,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东西,看到那些汽车招摇过市,我就痛骂他们是王八蛋,他们就回敬我,叫我汤八蛋。
主持人:您在传记里提到,在1948年也就是您十八九岁之前,您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时事很悲观,常常是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
汤一介: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抗战刚刚结束,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对时局非常失望,因为国共两党仗打得非常厉害,国家的前途完全不知道,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对我有一定的影响。那个时候在西南联大,有一部分教授参加了国民党,有一部分教授做了民主人士,我父亲从来是对这两种态度都不赞同,他觉得作为教授就应该教书,把学生教好,这才是天职。他这种中立的与世事无关的旁观者的态度,对我很有影响。“一二·一”运动时,很多学生都去游行了,我就没去参加,只是站在旁边观看。
主持人: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到政治运动当中去的?
汤一介:应该说是“沈崇事件”之后。沈崇是我们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同学,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班,可是在一起上国文课。1946年12月,沈崇从平安电影院出来,走到东单广场,遭到了美国兵的强奸。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过去受屈辱的感受是间接的,这次的感受却非常直接。那一次,我积极参加了反美游行,我们在东单广场静坐、喊口号,要求美国人滚出中国,我们有一个同学还把美国国歌改编成一首歌,叫做《滚出去洋禽兽》。从那个时候起我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不过,我虽然投身到了政治活动当中,但是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当时我们有一些同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些同学参加了其他进步组织,我都没有参加。我可以说是他们的同路人,就是反对国民党的同路人。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出的壁报,却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国民党学生攻击我们,共产党学生也攻击我们,认为我们是中间派。
主持人:大学时您选择了哲学专业,当时有没有明确自己想当一个哲学家?
汤一介:我非常想当一个哲学家,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哲学问题。当时有个趣事,冯友兰先生有一本书叫《新知言》,我把这本书买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同学跟我开玩笑,就偷偷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院士”两个字,这样就成了“院士汤一介”,他们的意思是说,我将来想做院士。那时候我确实有一定的抱负,甚至有意识地多学一些外语。除了英语之外,在大学我选修了德语课,要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问题,这些外语工具是必须要掌握的。
她说这本书值得一看,我就认真读了
汤一介爱书,有三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主持人:您曾经说对您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的书有三本,是哪三本?
汤一介:第一本书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那是我在高中时读到的。这本书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充满了热情,写得非常深入。钱先生一生热爱中国文化和历史,是深以中国文化和历史为骄傲的一位大学者。通过这本书,我懂得了我们中国有那么长的历史,有那么丰富的文化,同时也为钱先生这种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倾注了巨大热情的学者所感动。第二本实际上是一篇文章,即庾信的《哀江南赋》,这是父亲介绍给我读的。第三本是伏契克的书,叫做《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译本名叫《绞刑架下的报告》。
汤一介:对。那是1950年的时候,乐黛云推荐给我的,她说这本书值得一看,我就认真读了。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它不仅影响到我的行动,也影响到我的思想。读过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过去所谓的爱,只是一种小爱,而人应该有一种大爱。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爱生活,我愿意为它而奋斗——他是要为一个理想的生活而奋斗。通过读这本书,我认识到,一个人应该关怀所有的人,不应该只关心自己,或者自己周围的那个很小的圈子。
主持人:为什么这一本书会使您产生这么大的转变?这种影响,跟当时的时代有没有关系?
汤一介:当然有关系。那是1950年,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包括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是毛主席所讲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切身感受。过去我们经常受外国人的欺辱,比如“沈崇事件”,而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这个问题。解放以后,我们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了,这个变化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之所以积极投身到革命、投身到社会活动中间,跟这种认识大有关系。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您的夫人乐黛云老师,能谈谈您二位认识的经过吗?
汤一介:我是1949年5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好那个时候北京大学文学院要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部,我被选入这个总支部做组织委员,乐黛云是宣传委员。乐黛云是中文系的,我是哲学系的,原来我们并不认识,这样我们在一起工作就认识了。乐黛云是1948年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民青”的,解放前夕一直参加党的地下活动。我一接触她,就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特别。她非常热情,做事情非常投入,而且执著地热爱自己的事业。
主持人:听说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中,乐黛云老师被打成了右派?
汤一介:这是非常突然的事情,因为乐黛云被划成右派,是在1958年初,反右高潮已经过去的时候。当时右派分六类,她是第二类,算很重的,第一类就应该服刑了。那时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按规定,她可以把孩子带到8个月,然后再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孩子长到8个月的时候,她就到门头沟去劳动了。那时候我也被下放到大兴县搞“人民公社化”,所以她下放我并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回来,想看看乐黛云、看看孩子,可是回到家里一看,我的孩子竟然一个人睡在小床上,乐黛云已经下乡去了。当时我把儿子抱起来,满眼泪水,他才只有几个月大啊。当时我就只有一个感觉,觉得人为什么这么残酷,让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失去照顾。
主持人:您当时想没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汤一介:没有想过。因为乐黛云是一个很有激情的青年人,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比我爱得多。所以在她被划成右派的时候,我给他们系党总支打了一个电话,说我觉得乐黛云不可能是右派。但是他们的党总支并没跟我谈,反而给我们哲学系打了一个电话通报情况,哲学系就根据这一条,认为我和乐黛云划不清界限,给了我一个严重警告处分。
主持人:据说在这之后,您给乐老师写信仍写乐黛云同志,这“同志”两个字也给您带来了一些麻烦。
汤一介:我一直都写“同志”。我们每个礼拜通一封信,平常都是我自己去投寄,有一次在乡下不好投寄,我就请一个同学帮我去投寄,他看到“同志”两个字,就汇报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时候,又把这个问题兜出来,还是说我不能划清界限,我就成为当时“反右倾”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
主持人:那您后来写信就不写“同志”了吗?
汤一介:照样写“同志”。
乐黛云:我们觉得这些信非常珍贵,里面谈到的都是我们当时的一些生活,都是我们当时对人生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很怕人家把它抄走,后来我就把它们装进一个塑料口袋,埋在一个葡萄架下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再到那个地方挖,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可能是做的记号不对,也许是别的原因,后来就再也找不到这些信了。
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挨揍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到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文化大革命”十年,汤一介正值“不惑之年”,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迷惑的十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没有了方向。
汤一介:当时,我是坚决反对聂元梓的,但是我并不愿意参加哲学系两派的斗争,我感觉到很难说谁对谁错,我想躲开。1964年底,我就要求下去搞“四清”了。但在1965年,中央书记处开会,邓小平做了报告,邓小平说北京大学虽然有错误,但是还是个好学校,之后北京市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召开整风会议,这样我就被从下面调回来参加整风会议。有一次邓拓找我单独谈话,要我在会上做发言,当时他提出一个思想,就是聂元梓有四个第一。我这个人确实是非常听话的,中央的决定都是听的,觉得中央一定是对的,因此就在会上讲了四个第一。这件事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就不得了,说我针对林彪的“四个第一”,也讲了四个第一。
当时我常常要被批斗,让我举一个写着“黑帮汤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个高台子上。我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牌子非常重,底下都是群众,如果你举不动了,牌子掉下来砸在群众头上,那你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非常不得了。那时候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大人物,红卫兵来了,每天都把他拉来批斗,等于耍着玩一样,让他站在一个凳子上,让我站在边上陪斗,当时我们两家住隔壁。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挨揍,因为红卫兵是没有组织的,你只要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有一个什么动作他们认为不好的话,那你就一定会挨揍。所以我动也不敢动,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一个地方。
主持人:冯友兰先生当时是什么样子呢?
汤一介:冯先生表现得很镇定。“文化大革命”以后我问他:你当时到底害怕不害怕?他说:怕是有点怕,但是我心里只是默念一首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说你们讲这些都没有意义,我心里默念这个东西,使得我的心情能够镇定下来。
乐黛云:当时几乎每天晚上都审他,我又不能进去,可是我觉得很怕。因为那时候突然有的人就会不见了,就给带到了什么地方,关进牛棚里头,或者带到什么地方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很恐怖的,我说要带走他,至少也得让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好去给他送衣服、送一点东西什么的。所以每次审他我都跟着去,在楼外面等着,他当时在哲学楼的二楼交代问题,每天晚上都到11点多,我就坐在哲学楼那个坎儿上等,每天都是这样。那时候人好像都很麻木的,我一滴眼泪都没掉过。
实际上我们跟江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尽管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审查,直到1978年初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主持人:您讲过,在这些运动过程中,您一直想躲避开政治上的纷争,但是始终躲不开,包括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后,您好像还受到一小段时间的审查?
汤一介:那主要是“批林批孔”的事情。当时清华大学编写了一本关于林彪和孔孟之道的材料,毛主席看了以后,觉得清华编得不好,就说是不是请北大的一些教授来一起编写。这样就找了包括冯友兰先生、魏建功先生、周一良先生,还有我,我们这些人。我当时很投入地做这件事情,感觉到既然毛主席非常信任我们,所以我就参加,就很投入地工作。材料出来以后,是用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表的,号召全国学习。因为我在一号文件里头起的作用比较大一些,所以当时在各种范围内做演讲,基本上都是我跟周一良去,我做前一部分的报告,他做后一部分的报告。实际上当时就等于是在受江青他们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组织上要求我们交代跟江青的关系,我们就老老实实地交代了。一直审查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跟江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江青说她传达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不是毛主席的指示。
你的基础不牢固,想建出大厦来就非常困难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但这对当时的汤一介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当他写完《郭象与魏晋玄学》之后,感觉已经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框框了。
主持人:您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您觉得非常遗憾,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可能是一个哲学家了,为什么这么讲呢?
汤一介:大家可能不大了解这段历史:1949年以后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些研究哲学的人,不能叫做哲学家,只能叫做哲学工作者。谁能叫哲学家呢?只有政治上的领袖才能叫哲学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解释这些政治领袖的思想,这才是我们的职责。
主持人:主要是解释毛主席的思想。
汤一介:对,这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创造和毛主席不同的思想,我们只能解释毛泽东的思想,解释得好的就是好的哲学,解释得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哲学。
主持人:所以您当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解释者当了30年。
汤一介: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的想法有了一点变化,我觉得我不应该只是解释别人的思想,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但是这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因为你要真正做成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必须要有深厚的功底才行。我们这一代人的哲学功底,以及其他方面的学问功底都有缺陷。相比我们的老一代,比如我父亲、冯友兰先生他们,有非常大的先天缺陷:他们的国学基础比我们好,他们年轻的时候上过私塾,四书五经都能背,我们没有这样的国学基础;而另一方面,相比他们,我们也没有很好的西学基础,他们都在国外待过较长时间,对当时西方的思潮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的国学基础和西学基础都不如我们的前辈学者。你的基础不牢固,想建出大厦来就非常困难。
主持人:您有没有把您自己和您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作一个对比?
汤一介:我自己感觉到确实有些不同。我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他不多过问政治,也不大关心现实的问题;可是我从1946年以后,就逐渐投入到现实生活、参加到政治活动中间来了,有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我对于现实社会生活,比我父亲关注的多得多。当然我也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总觉得我要超过他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看起来也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主持人:就是因为您刚才说到的他们国学和西学上都有深厚的功底,和他们所处的那种环境条件有关吗?
汤一介:我想是这样,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丧失了最有创造力的三十年。
任何真理都可能是相对的
1949年以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从此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在1947年写的《月亮的颂歌》一文中他曾许下这样的愿:“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1949年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汤一介:1949年以后,我感觉到,共产党非常清廉,比起国民党来,确实大大的不同。1946年夏天我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国民党干的主要是抢房子、抢汽车、抢金条这些事;可是共产党不同,进到北京城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比较清廉。我开始工作,是在北京市委党校,校长是一个老干部,当时大家非常平等,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样的,吃的东西差不多,每人每年发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他大概只比我们多一点点生活津贴。
主持人:所以这个时候您觉得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活,这种生活对您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汤一介:对。我大学没毕业就被分到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当时党和政府准备培养一批组织员,组织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来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我估计他们当时选择我,是考虑到我跟北大的一些老教授们有特殊关系,这样将来培养出来就便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做发展党的工作,大概有这么一个意图。但是我在市委党校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党校的领导感觉到我做这个工作不太合适,倒是做教育比较合适,所以就把我留在党校教书。这段教书生活使我认真读了马、恩、列、斯还有毛泽东的著作。当时大家认为我讲课虽然不敢说是最好的,也算是最好的之一,我常常去市委、区委讲“联共(布)党史”,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是比较熟的,而且我也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因为它使得中国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主持人:那时候您是否怀疑过不应该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存在?
汤一介:那时候我不怀疑,觉得马克思主义就是绝对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其实“文化大革命”没结束以前,我就开始有很多怀疑了。“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当时产生的第一个思想是什么?居然是我今后到底该听谁的?因为以前总是听毛主席的,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话,那一定就是不对的;毛泽东去世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以后我该听谁的呢?但是后来我很快觉悟到,不能听谁的了,只能听自己的。听谁的都可能犯错误,要是听自己的犯错误,那你自己负责;要是听别人的犯了错误,到底应该由谁负责就很难说了。
主持人:等到您想明白这一点,已经是30年过去了。
汤一介:30年过去了。
主持人:在这之后,您的学术思想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汤一介:我开始感觉到,可能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真理都可能是相对的,都可能只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起作用,过了特定的历史阶段,它就不适用了。特别是关于哲学问题,我感觉到原来我们学的哲学,是斯大林的思想比较多,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最基本的教材。这个最基本的教材里最重要的东西,是讲哲学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后来我开始怀疑这个东西:它到底正不正确?符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所以我开始写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叫做《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哲学是人的认识史,它讨论的是概念、范畴发展的历史。人类认识的发展变化,常常表现为一个新的概念、新的范畴的提出。比如孔子时代,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使得中国哲学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原来讲的都是礼乐的思想,而仁、礼、乐到底有什么关系,没有人讲清楚,孔子就讲清楚了。他讲仁者爱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要是不讲仁的话,礼乐是没有用的,只是形式。但孔子并没讲到“仁政”的问题,到孟子就更进了一步,他提出了“仁政”的问题,这样儒家“仁”的概念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所以人的认识是一步一步深入发展下来的,而且常常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交替发展的,并不是什么两者不断斗争着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其实联想到您本身,您的生活经历和您的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认识史。
汤一介: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和他的生活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说我写《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这篇文章,跟我三十多年来的经历有关系。三十多年来我自己都认为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唯物主义一定是正确的,唯心主义一定是错误的。经过这一段历史,我有点觉悟,开始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对立这种僵化的看法。
只有做事才能体会到快乐
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风云激荡、变革频仍的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图强求变的痛苦反思中,经历了从近代向现代的嬗变与转型。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先进的思想家更寄希望于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哲学,改造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以开启民智,启发民力。这段历史,学界称之为“西方哲学东渐史”。在新世纪之初,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改革与建设的未来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由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张岱年先生称这套丛书是“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季羡林先生则称“这套书是知时节的好雨”。
主持人:您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梳理了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思想文化变化的历程,您怎样看待这个过程?
汤一介:我有一个大概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历史上佛教传入中国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佛教附会于中国文化得到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佛教跟中国传统思想的矛盾冲突;第三个阶段是佛教逐渐中国化,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我常常想,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一百多年,如果从利玛窦来中国的时候算起就应该有四百多年了,实际上西方文化真正对中国有影响的也就是近一百多年。经过了这一百多年之后,比附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些中国化的西方哲学派别出现,像中国的现象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解释学学派等。我觉得我们第一步还是要消化西方文化,把它逐渐融化到中国文化中间来,创造一些中国化的学派,最后形成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新文化。当然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主持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儒、道、释三教,其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佛藏》,唯独没有《儒藏》。据说您最近联合十余家高校的力量,准备用16年的时间完成《儒藏》工程。应该说这是一个规模浩大、功在千秋的学术工程。
汤一介:我们把这个工程分成两步:第一步,先编出《儒藏精华》,就是把最主要的儒家经典编在一起,包括500部书,准备花6年时间来完成。我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呢?中国从宋朝开始就有《佛藏》,把佛教的经典编在一起,而且历代都编;有《道藏》,道教的经典编在一起;但是唯独没有《儒藏》。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曾经提出过,要编《儒藏》,特别是乾隆编《四库全书》以前,就有学者提出编《儒藏》,但是大家又都觉得《儒藏》太大、太难,没有编,于是就编了《四库全书》。现在不同了,现在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个非常大的、很好的整理,我觉得是必要的。我非常喜欢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他提出一个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不同的地区,同时出现了几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中东地区也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等。几千年过去了,他们的思想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共同的宝贵财富。雅斯贝尔斯说,文化的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要回顾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回溯到文化源头的那个时期,去找寻力量,把我们的文化根基打好、打牢固。只有文化根基打牢固了,我们吸收外来文化的力量才能更强。这个外来文化当然也不单指西方文化,还有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其他的文化,我们都应该吸收。
主持人:《儒藏》工程规划了6年,但是您今年已经77岁了,您有没有考虑过,可能您这一生,也不会完成这样一项工程了。
汤一介:必须做,除非我根本什么也不能做了。人活一天,就要做事,只有做事才能体会到快乐。你的快乐就是你的生命。你要不做事,你就没有快乐,也就没有生命。
原收入薜继军主编:《大家》,北京,商务印务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