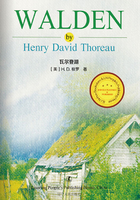在此后多次政治迫害之后,索尔仁尼琴没有消沉,而是越发勇猛。和梭罗的主动寻求隐居不同,“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这次是在时代的冷落中开始了《古拉格群岛》的创作。《古拉格群岛》借助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对一种政治运动及其所产生的政治制度展开了严肃认真的思考:极端残忍的刑讯,荒谬绝伦的司法,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以及毫无人道的株连性流放、集体流放、超强度的死亡劳改,都是人祸的结果。苏联监狱和劳改营的种种内幕,成为小说中纪实性的题材。这本自传兼特写性的长篇小说,以揭露俄国自十月革命以来苏维埃政权下的非人残暴统治为主题,以作者个人为时代的亲见者,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数据集体指向集中营的悲惨,书中描述的一个又一个场景令人发指:“也许它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可怕的。爬满虱子臭虫的看押所,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装置,没有板铺——这里只有肮脏的地面。”“列福托沃的‘心理’监室,如三号,整个漆成黑色,也是昼夜亮着一支二十瓦的灯泡。”“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接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这是索尔仁尼琴式的语言,这是他亲眼所见。与上文我所摘引的梭罗的语言截然相反,这里曾经是人间的地狱。索尔仁尼琴当然被人看作“疯子”。写完了一系列作品之后,似乎是还没有从个人强烈的情感抒发中回过神来,书的主人再次被迫政治驱逐,而这一次,被宣布剥夺苏联国籍的索尔仁尼琴,离开自己的国度长达20年。
在此之前,“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从古拉格囚犯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流亡异域到最后荣归故里,索尔仁尼琴总算是在人生的暮年回归了自己的人生价值。1994年,76岁的大胡子索尔仁尼琴从流亡之乡回到了祖国,这个后苏联时代的先知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作家对于政治权贵似乎很不给“面子”,他深知俄罗斯政治的罪恶。索尔仁尼琴用他的《古拉格群岛》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掀起了政治风波,这位目光犀利而心怀悲悯之心的老人,对于作家的神圣使命进行了最好的阐释。
用幻觉抚慰现实可以疗伤,用现实追赶幻觉肯定很受伤。用上海清口派艺术家周立波的话讲,讲真话有人不高兴,讲假话自己不愿意,所以就干脆讲些笑话。这大概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到底该怎么说话,说些什么话,是摆在我们现实语境的困难。于是,当各种思想在一起出现的时候,常常是听众中没有人开口,集体的失语成为最好的回避。不是怯场,自保下的难言恐怕也让人理解。很显然,索尔仁尼琴没有自保,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在斯大林高度集权的时代,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作堂吉诃德式的斗争。好在最后,他为自己也为时代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2009年俄罗斯政府宣布,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将在俄罗斯出版儿童版,并列入全国中学课程,以加深学生对俄国历史的理解。
一个是在逃离政治的同时又时刻以理性哲学的角度来观照现实世界,在脚踏实地走路的同时不忘仰望人类精神的星空,一个是寸步不离政治而遭受非人待遇的种种折磨,在备受精神折磨的同时甘愿承受时代的痛苦。梭罗和索尔仁尼琴都是相当疲倦的精神辛劳者。一座湖,一座岛,人生际遇无外乎在狭小的空间中演绎得淋漓尽致。洒脱的洒脱入了世人的心间,受难的受难至于非人的境界。看起来温和的梭罗,在温柔的文字背后有坚强的自我表达;倔强好斗的索尔仁尼琴,在激荡的文字中从不掩饰内心的诉求。文学从来没有因为他们个人的痛苦思索而停止向前奔跑的步伐,相反,人类的精神正是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之下继续前进。
作家周国平说,有两种孤独,一是灵魂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这是绝对的、形而上的、哲学性质的孤独。二是灵魂寻找另一颗灵魂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人世间的一个没有旅伴的漂泊者,这是相对的、形而下的、社会性质的孤独。用这样的标准来看,瓦尔登湖中的梭罗属于前一种的孤独,而古拉格群岛中的索尔仁尼琴则当然是后一种了。两种孤独,其实都在阐释同一个哲学命题:人类社会(自然包括个人)该往何处去。
好在一切看起来不公平的事,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看,一切又回归到公平的起点。寻找人类宁静的梭罗寻觅到了湖的宁静,寻求政治话语的索尔仁尼琴看到的是岛的死寂。一百年之后,两个很难被世人遗忘的文人第一次相逢,一个是徘徊在瓦尔登湖,一个是囚禁在古拉格群岛,在各自强大的精神世界中,彼此呼唤着对方。
卑微与崇高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日趋多元,文学也随之众声喧哗:有的作家借用舶来的叙事技巧消解写作的价值取向,有的回到琐屑世俗的生活消解崇高,有的选择玄乎的自言自语,有的开始超实验的文学探索,有的干脆给读者开出一剂虚妄的心灵鸡汤甜蜜着你……最后的结果是,文学的价值判断变得模糊起来。
作家的写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写作意愿,二是作家的责任感。作为文化精神产品创作的作家,终究是靠作品来获得读者认可或者征服读者的,不必高高在上甚至让人仰视。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应该让读者臣服,这样的阅读才多少有点膜拜的意味。
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该得到读者的膜拜,读者也需要这样的文学膜拜。作家不是君临天下的傲然目空一切,读者与作家是平等的,真正接地气的作家与读者更应该是平等的。无论采用何种表现手法,文学作品最终传达出来的终究要与读者的生活相接近,或者说是我们现实平常生活的投影。真善美,假恶丑,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社会缩影,恐怕是作家创作的不二选择。
也许是人生经历的坎坷,也许是作家创作价值选择使然,刚刚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刘醒龙,便是这样接地气的作家。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大潮面前,作家仍然选择自己最熟悉的乡镇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在俯视卑微的同时仰望崇高的社会底层民众。刘醒龙在获奖感言中话道:“作家是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毫无疑问,这是作家对自己写作选择的最佳阐释。
作家选择这样的写作基调,本身就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底层民众是活得很艰难的,他们由于出生的卑微,获得物质上的享受有限,但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精神的崇高,相反,他们骨子里葆有的内在崇高累加起来却足以构成民族精神的脊梁。
对于底层人,刘醒龙有过这样深情的表述:“面对这样辛劳的人,这样诚实的人,我无法举起批判的利器。”然而他又表示:“这样说并不意味自己已放弃了批判的立场,而是恰恰相反,只是我的锋芒不能对着这些在历史的海平线下苦苦潜行的大众。”这些底层的小人物“闪烁着质朴的光辉”:无论是种地的农民还是村里的支书,也无论是民办教师还是乡教育站站长,在道德和人格上他们都承载着他要表现的“高贵”。于是,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是,在他们身上,贫困甚至有时是愚昧不可避免,但道义却是苦苦坚守,无论世事纠结如何大行其道,可是良知从未丧失……一个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卑微人物,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成为一条贯穿作家全部小说的命定线索。
这个时候,卑微与崇高的俯仰,就这样矛盾地纠结于作家的作品中。在最早的小说《村支书》中,当了二十多年的方支书是村里公认的好人,“办事凭良心”,但是仍然无法改变村里落后的面貌,文村长虽然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毛病”,但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一点也不输给方支书,理由是“村长的能力强”。最后的结局是,为了抢修水闸四处奔波求人拨款而如今已进入胃癌晚期的方支书,抱起草棚的棉絮跳入水中堵住水闸的漏洞,不想自身被鲶鱼吃得只剩下白花花的腿骨。方支书最后的死亡就具有了悲壮的意味,这种英雄悲剧般的结尾,既合乎现实生活的情理,也是作家的精心设计。
《威风凛凛》是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赵长子为了报恩,放弃荣华富贵,来到偏远的西河镇创办了第一所私立学校,当了一辈子的民办教师,是乡村传播现代文明的延续者,却成为当地蒙昧野蛮者肆意欺侮的对象。他外表谦卑甚至窝囊,内心却无比强大,他说:“面对别人的侮辱与伤害,不管有多深多重,只要自己能坦然以对,那么他们不但达不到本身想达到的目的,相反地能使自身得到深刻的解悟与锻炼。”同时,他还坚持这样的生活信条:“以知识作为矛,以忍让作为盾,知识不会伤人,忍让可以护身。”
看似平常的内心自白,鲜明而生动地反映了赵长子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样多少富有哲理的话语或者说是自我安慰,立马使得赵老师成为西河镇最威风的人,他的威风不是来自同蛮横粗野力量的以暴制暴,而是来自精神理想的高蹈。怀着“高贵”的“梦想”,拥有超拔的品格与智慧,忍辱负重地承受苦难,坚持对周围人的改造。在赵长子的“高尚”面前,五驼子、金福儿、小曾、大桥等,就显得要野蛮粗俗得多了。文明与愚昧两种“威风”力量始终在较量,尽管赵长子被五驼子肉体上摧残至死,但在精神的高贵面前,孰卑微,孰崇高,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评判。
读刘醒龙的小说,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卑微人物”形象,他们不同的经历、性格、禀赋、品行,通过不同的事件、不同细节的描写和内在心理活动的变化,慢慢地在读者心中延展和定格。譬如,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高天白,《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石望山,《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都是卑微而高尚精神的延续。读着质朴的文字,体味着一个个仿若就在我们身边的卑微人物,如同咀嚼一顿佳肴,让人回味无穷。
“好的小说如同真正的男子汉,没有花言巧语,也不会卖弄风流,甚至还会冷若冰霜地拒人于千里之外,内在却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暗火。”刘醒龙的小说之“真”在于:源于高贵并且懂得去尊重这种高贵,以高贵这“一团熊熊燃烧的暗火”照亮人性中的美丑。
给作者带来盛誉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应该是作家前期小说《凤凰琴》的延展。小说通过几代民办教师的命运悲苦,在不回避乡村矛盾的同时弘扬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这个民办教师群体,虽说是公民意识的最早觉醒者,相互之间也因为转正的一点利益而互相倾轧,互相提防,甚至是明争暗斗。因为受制于乡村权力,声音微弱,自我价值遭到贬抑,根本不可能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国家大的民办教师转正政策上。于是,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明爱芬等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偏僻贫瘠的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虽然只有极其微薄的工资收入,但为了能够让这些身处穷乡僻壤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却凭借良心承担起了教育孩子健康成长的重大使命。即使在他们之间,在“僧多粥少”的转正指标面前,他们同样也避免不了一些蝇营狗苟你蹬我踹的利益冲突,但对待乡村培育孩子神圣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上,他们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故事最大的看点是每次出现转正机会的时候,在转正指标这块试金石面前,几位民办教师的高尚人格,也就熠熠生辉了。三次转正机会,先是张英才主动让出了这个指标,然后,又是大家一致同意把指标留给早已对转正望眼欲穿的明爱芬。多年的愿望终于满足,瘫痪多年的明爱芬在最后一刻离开人世,这唯一的指标最后还是落到了年轻的张英才身上。在张英才面前,始终有三个卑微的英雄存在:教学、照顾瘫妻之余,承担着十几个寄宿家里的学生吃住管理的老好人余校长;节俭、灵活,一切为转正做准备、一丝不苟进行自己人生计划的副校长邓有米;清高、孤傲,与有瘫痪丈夫的王小兰暗中苦恋多年的教导主任孙四海。他们如同界岭中的山一般崇高,有时有如山上的野草一般坚韧。
他们活得平凡甚至卑微,但他们用这种平凡中的崇高感染来过界岭小学的每个人。这种崇高包蕴在日常教学和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里,它可以体现为付出和牺牲,也可以体现为宽容和善良,更可以体现为坚韧和顽强,这是界岭小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最后酿就了“界岭小学之毒”。正因为有过在界岭小学当民办教师的一段工作经历,所以从省教育学院学成归来之后的张英才,历经情感和人生阅历上的选择,最后又回到了界岭小学,因为他特别怀念界岭小学的纯洁与崇高。“纯洁”“崇高”这样的字眼,用在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教师身上毫不为过,他们着实般配这样的“崇高”。最难得的是,作家毫不隐讳他们的卑微,而是在俯视表层的卑微后能够挖掘出他们精神上最为重要的高贵点,继而仰望他们的崇高。
对人的关怀,对人格和生命力度的关注,是作家写作的立脚点。作者谦逊解剖自己:“作家写作有两种,一种用智慧和思想,一种用灵魂和血肉。而我由于智慧的匮乏,思想的浅薄,便只能选择用灵魂和血肉来写文章!唯有如此,我流浪的精神与情感,才能找到那么大小的家园。”家园在何处?曾经作为农耕文化精神家园的乡镇,在时代的发展大潮面前,开始出现了道德价值观念滑落的趋势,再也不是和谐的乐园。坚守道德理想的他们,充满了失落和精神的迷惘。作家只能是深深的理解他们、同情他们。
现实的利益上,一个个的他们有时是利己或者是自私的,但在道德层面,他们脱掉了肮脏的外衣,是道义精神的守护者。尊重高贵或者仰望崇高,都是作家的审美理想。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我的作品是写给大多数人看的。”不回避现实,不回避真实,无论是表现对生活的感动还是沉思,作家都应该是作品中道德审判的法官。自然地,关注社会民间人性的刘醒龙在创作中必然会介入自己的道德情感。尽管现实有时很残酷,以日常人生利益标准和道德选择来评价,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在作家的笔下,人物命运开始展现出不可抗拒的张扬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