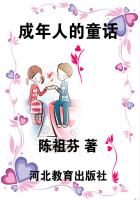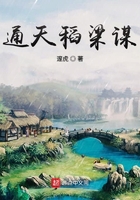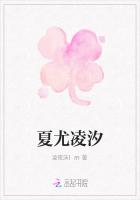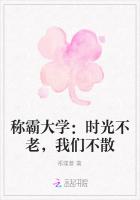第一次亲近尖山, 我就喜欢上了它。
那应该是在1967年12月的中旬, 到八五二农场三分场一队报过到, 匆匆放置好行李, 我们几个伙伴便兴冲冲地跑向了尖山。
我们之所以如此热切地亲近尖山, 一是因为它离我们太近, 生产队驻地就在尖山的北坡上; 再者, 就是它最先向我们展示了北大荒山林的独特风貌!
尖山并不是很高,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它到底海拔多少米。但在四周一片平展展的雪野中, 它那还算有一些坡度的躯体, 确实显得格外突出。
山上分布最广的, 是挂满了枯黄树叶的柞树(这树名当然是后来听老职工介绍的)。天气如此寒冷, 巴掌大的树叶却不落下, 在凛冽的北风中飒飒作响, 让我们这些刚刚从北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 自然感到十分新奇。
当然, 尖山上最使我们着迷的, 还是上上下下布满整个山体的皑皑白雪。
山林间的积雪足有一米来厚, 一脚踩上去, 马上没过膝盖, 直到大腿根儿!
抓起一把雪, 白白净净, 晶莹剔透, 却捏不成团, 随手放开, 撒出去的全是雪粉, 和在北京玩“打雪仗” 的雪团完全不一样。
山坡上满是粗壮的树木, 高高低低, 自然散开, 虽然不成行列, 却各自占据着相当合理的位置, 像是经过精心布置似的, 看上去特别有味道。
映入眼帘的山景, 虽然不是雄奇奥秘的原始山林, 但同样洋溢着一种动人心魄的山野味道。我们倔强地认为, 这应该就是小说和电影中描绘的林海雪原了!
此情此景, 大大激发了我们的热情和好奇心。于是, 我们哥儿几个在树丛中、雪地上, 变换着景物和身形, 拍了不少照片, 打算作为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件有意义的礼物, 寄给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亲友。
北大荒的春天来得迟, 但春天的脚步跑得出奇地快。而最及时地把春天的信息带给我们的, 可能就是尖山了。尖山周边的青草, 突然冒出了嫩芽。鹅黄色的小花, 不知不觉地闪现在尖山隆起的身躯上。说来也怪, 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最先舒展开花瓣的花朵都是黄色的, 散射在绿茵茵的草地上, 分外可爱。此时, 生长在尖山上的植物, 动作最为“凶猛” 的, 不能不说是山上大大小小的树木。仿佛一夜之间, 满山的乔木和灌木同时抽出了绿芽。树叶生长的速度, 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听老职工说, 如果你静静地站在树丛旁边, 能亲眼看到树叶一点一点地长大、变圆。晚上蹲在树下, 还能听见树叶沙沙生长的声响。
倏忽之间, 尖山一片葱绿, 显现出了勃勃生机。
遗憾的是, 我们几乎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近距离欣赏尖山美妙的春色。
春回大地, 我们要紧张地下地耕作, 开始一年之中最为忙碌的季节。我们毕竟是农业工人嘛, 人人都懂得, 一年之计在于春! 这时候, 我们只能远距离地观望尖山, 借以舒缓劳累的双肩。
要说和尖山接触最密切的时节, 是炎热而繁忙的夏季。
前面说过, 我们生产队的驻地在尖山北面的漫坡上, 由于地势倾斜, 不便于修整晒场, 队里的晒场安排在山南面的分场场部。到了麦收季节, 农工们每天都要沿着尖山东边的小路, 翻过一道山坡, 到尖山脚下的晒场上班。
夏日的尖山, 绿树成阴, 成熟而饱满。树丛中不时飞起拖着长长尾巴的山野鸡, 姿势优美地在半空中滑过。据说, 尖山上野兔挺多, 还有狐狸活动, 但那些家伙动作太灵敏, 也太狡诈, 平常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由于乔木连着灌木, 灌木又连着草丛, 交错生长, 山体植被茂密, 上山的道路都被遮盖住了, 绝少有人在这个季节往山上爬。山间道上, 来往最多的可能要数我们一队的农工。清晨,踏着晶莹的露水, 与尖山擦身而过, 看柞树硕大的叶片随风摆动, 听林中不知名的鸟雀鸣啼歌唱; 傍晚时分, 欣赏山上上下被晚霞映照得变色的绿叶, 指点原野上空不时变换的白色云团, 不知不觉地, 一天的劳累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时候, 遇上点儿不愉快的事儿, 心里堵得慌, 我们也喜欢来尖山脚下转一转, 看一看, 迎着山间的清风, 驱散胸中的郁闷。
夏日尖山带给我们的欢乐, 还有很多很多。
麦收时节, 劳动力紧张, 分场场部的不少家属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她们也都是开发北大荒的老员工了, 不但灵巧能干, 而且性情爽快, 给我们的劳动过程增添了相当多的欢快气氛, 通过他们, 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又一个半师半友的好朋友!
具体点儿说吧, 通过胡佩茹大姐, 我们认识了甄科(在另一篇短文中, 我写了老甄); 通过周英大姐, 认识了陈仰能和陶勤存; 通过小霍(对不起, 实在想不出她的名字了) 大姐, 认识了耿永仁, 还有姚启瑞、武汉三等一批住在尖山脚下的老北大荒人。
这些新结识的朋友, 大都比我们年长十岁以上, 有的还要更大一些。说起来, 他们应该算是我们的忘年交、前辈人物。这些人都很有些来历, 基本上都是当年的转业军人, 八五二农场就是他们开发建设出来的。比如甄科, 参加过抗美援朝, 是八五二农场货真价实的元老, 最早探查和确认农场场址的成员之一。陈仰能和陶勤存, 管理着分场的电影放映组, 他们起早贪黑的辛勤劳作, 给我们送来了那么多笑声和欢乐。虽然, 他们的衣着随便, 有的还打着补丁, 言行举止与普通农工并无二致, 但仔细望去, 他们眉目间传达出的神情, 却常常令人惊诧不已。你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 这些人肯定经过严格的训练, 有着非同一般的经历。
说句实话, 当时, 虽然整天念叨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但心里头并不是十分服气, 嘴里动不动还会说出一些不是很恭敬的话来, 惹得领导和贫下中农动怒。然而, 在分场场部的这些转业军官面前, 我们还真提不起半点傲气来, 他们的文化、教养、学识, 很快地征服了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
住在尖山北坡的我们, 借着夏日的阳光, 在尖山南坡觅到了知音和朋友。
陈仰能家低矮的草房, 甄科家热腾腾的土炕, 姚启瑞家临时借住的招待所,成了不少知识青年聚会的场所。
喝一杯热茶, 吃一口和大食堂味道不一样的饭菜, 是一种享受。痛痛快快地聊聊天, 说说天南地北的逸闻铁事, 听听会场(那时候天天都要开会) 之外的家常话, 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而在当时被我们视为最高享受的, 是可以从他们家里寻找到市面上难得一见的书籍和杂志。
最近几年, 看到有些回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文章, 提到当年如何树立理想, 坚持学习, 以待来日报效祖国的经历, 在下确实很是佩服。当年, 我却没有这种伟大的念头, 真的, 一丝一毫都没有。也许, 生活是不允许出现空白的,无论时间还是空间, 都需要实实在在地填满。那时候, 在下只是一门心思地想找书看, 什么书都行, 都想看上几眼。《农村医生手册》看了, 还买了银针, 在自己身上也在伙伴们身上试着寻找穴位。《药性歌括四百味白话解》看了, 还写了不少笔记。李时珍和他父亲合写的《濒湖脉学》看了不止一遍, 翻坏一本, 后来又买了一本。看这些杂书, 并不是想学个什么, 也不是为寻求什么出路, 纯粹是为了填充时间, 愉悦自己的生活。找书看, 真成了知识青年们的莫大期望。为了找到未曾见过的图书, 我们确实是动足了脑筋。
所以, 当从这些朋友家里悄悄地拿到某些还是“禁书” 的书籍时, 心底的欢腾雀跃, 就不用提了! 而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 自然一步步地深入, 共同语言一天天增多, 来往日渐频繁, 如同家人一般!
近年来重读《论语》, 看到孔夫子论学习, 有“为己之学” 与“为人之学”
的区分。前者为的是充实、完善自己, 提升自己的品味和修养; 后者为的是让他人认识与评价, 以求他人的赞赏、肯定。孔老夫子当然是提倡为己之学的。
对照着《论语》, 回顾当年在尖山脚下的学习经历, 的确感到很是欣慰。不管怎么说, 我们是在有意无意中和圣人贴近了一回!
后来, 我们连队(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后, 一队改称二十团三营十六连) 搬迁, 北移了大约三公里。离尖山远了, 但我们和尖山的关系却丝毫没有疏远的感觉。
收获时节, 正在晒场上忙乎, 如若远远看到, 顺着尖山北坡飘来一片淡淡的白雾, 敏感的当值管理员老白一定会大惊失色, 那是瓢泼大雨就要降临了。操着一口山西话的老白, 会马上敲响报警的犁片, 刺耳的声音响遍整个营区。正在连队驻地忙碌的所有人员, 都要立马放下手里的工作, 奔赴晒场, 手忙脚乱地抢收摊晒的粮食。那场面, 那气氛, 和战场上的拼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有时候, 绿莹莹的尖山顶上, 会突然缠上一团白色的云雾, 停在那儿, 一动不动。连里上上下下都知道, 那叫“尖山戴帽”, 预示着三两天之内将要下大雨,那可真是百试不爽, 十分灵验。遇到这种情况, 连队领导肯定会紧急开会, 改变工作日程安排, 顺应气候的临时变化。
农业生产离不开气象气候, 尖山简直就是我们观察气象变化的晴雨表, 也许, 还应该算是我们连队领导班子的特殊顾问或者参谋吧。
天气由热转凉, 北大荒短暂的秋天来了。尖山也在跟着变化, 原本通体绿色的身躯, 忽然间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彩衣, 一片鹅黄、一片绛紫、一片暗红, 数不清的色泽扑上树梢, 扑入我们的眼帘。
尖山秋景的规模, 虽然难以同北京香山的红叶景区相比, 但这里丰富的秋色, 绝对要远远超出香山! 在难得的“大礼拜” (农忙时连队十天一休, 称之为大礼拜), 顺着尖山西侧的沙石路去分场, 我们都愿意在尖山旁多停留一会儿,近距离地观赏层林尽染的秋日景色, 享受秋天带给我们的乐趣。曾经有人嘲笑我们的这种情感表现是“小资情调”,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无论怎么嘲笑、怎么批判, “小资情调” 就是丢不掉、改不了, 奈何?
斗转星移, 转瞬之间, 和尖山分手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间, 我拜望过国内很多名山大川, 西岳华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祁连山、天山、长白山、青城山, 甚至还到过喜马拉雅山区的珠穆朗玛峰,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包括台湾在内的三十四个省、自治区, 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各地的风物景致, 无不优美动人。然而, 细细思量, 在我的记忆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却是在地图上难觅踪迹的尖山!
原因很简单, 名气再大、再雄奇伟岸的山川, 和我只有一面或数面之缘, 顶多算是匆匆过客, 而尖山却与我有着整整十年的关联。
唐代大文学家刘禹锡有言: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尖山不高, 也没有仙,但尖山有情, 十年相依相望, 形成了属于我们北大荒人的特殊情感。
我们的结论和体会: 有情往往比有名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