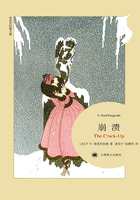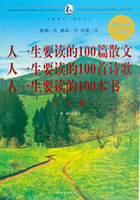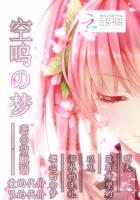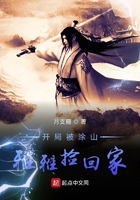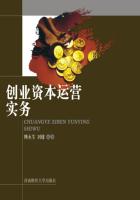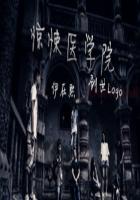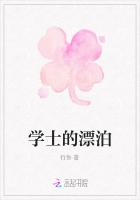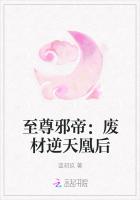梧桐树下飞出一辆自行车,弟弟?!不不,这人完全没有弟弟的气质和风采,只是因为我想老家的亲人们,所以这时只要看到一个英俊、挺拔的男性,我就会以为是弟弟。走到老家楼下了,楼旁走出一位妇女,妈?不不,这哪是妈?仅仅那件蓝上衣,是妈妈也有的,常穿的。这么些年了,好像所有的男人、女人,所有的妈妈、女儿都只穿蓝罩衣。我尤其喜欢穿一身蓝黑色。同学叫我“蓝人”。我儿时,我的青春蓝人时代,都锁在这幢楼里了。
我不敢在老家楼前停留;不敢多看;这太消耗感情:到了女同学家,她的收录机里正播放广告节目:“西丽湖度假村,是你度假明智的选择。”但我此时很高兴自己在远离西丽湖、远离深圳蛇口的上海——已经无家可住偏偏强说有家的上海。女同学极欢喜地安排我吃、睡,我却哭了起来;我要看看我的家,我现在就想去!
我是在蛇口临时决定来上海采访的,所以未带老家的钥匙。我的女同学是有钥匙的。她开着我家的大门:“你先别进去,我先去开窗。”为什么我先别进去?啊哟,屋里一股什么味儿?一股久无人住的屋子的味道。不过我能毫无差错地分辨出这是我家的味道。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味道——搅拌着主人身上的味道和家具、食物的味道。
这一件件落满尘土、蓬头垢面的家具,于我便像故居老人那般亲近。嘿,这个旧得坑坑洼洼的、里边可以放进好几个饼干筒的饼干箱。家里最受惠于它的是我,最受惠于我的是它。我极有兴致地把妈妈买来的饼干装进去,又更有兴致地把饼干取出来。缝纫机上那个大针线盒还在!有一日我穿上一件太肥大的连衫裙,一下变成了一只老母鸡。妈妈不会做衣服。天知道她怎么用这个针线盒、这台缝纫机把连衣裙改出来的!这次我跑各地采访还穿着这件过时而合体的裙子。不过妈妈改这条裙子,实在是一场当时不堪想象、现在又不堪回首的恶战、灾难!
妈妈为什么不在老家?妈妈怎么可以不在老家?家里怎么可以没有妈妈?没有妈妈便没有家的感觉。什么叫家?简而言之,妈妈就是家。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家。
妈妈正在我北京的家里为我披阅信件,接电话。依然咳着,还是那种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跳出来的咳嗽声。依然顾不上去治病,只是承担着母亲的义务——不不,是承受着女儿转嫁到她身上的义务,无尽无休,我才能想去哪儿采访就去哪儿,想来上海就来了上海。
女同学走了。我越发不能忍受这孤单,这寂静。在别处我喜爱独处、索居。在老家我渴望听到亲人的声音。有了,拧紧那只老式座钟的发条,看看还能不能响了?响了!滴答滴答地响了。半小时还“当”的敲一下。总算除了我,还有别的什么存在着。
“归来吧,归来哟……”我下意识地哼了这由费翔唱响了的歌曲。只哼了一句,自己就被自己吓着了——这屋里怎么有人声?
我回到同学家等吃饭。邻居家的女孩小兰兰来了:“我要听费翔!听费翔!”
“侬也知道费翔?”我俯下身来打量这个穿着汗背心、三角裤的五岁顽童。
“我顶喜欢费翔了。”她极开心地笑着,弯弯的嘴占去三分之一的脸,“他面孔好看,衣裳好看。我看见他要亲他一记面孔。”
兰兰把脸扎进被子里,扎猛子似的。
“我要和费翔结婚。”兰兰扎完猛子越发神气了。
“侬晓得什么叫结婚吗?”
“晓得。结婚就是吃一顿饭,擦红红(胭脂、口红),吃桔子水。”
“费翔那么大高个子,侬这么小,人家要笑话的。”
“那么我们晚一点进去吃饭。”
“那侬总是太小。”
“那么等我长到十岁再结婚。长到二十岁!”
“侬长到二十岁,费翔就会长成老伯伯了。”
“那怎么办呢?”
兰兰,父母都是工人,既无海外关系,又和音乐无缘。兰兰比其父辈,接触的世界大,受的约束小,于是生出许多奇想。
先有奇想然后方有突破。不过兰兰的这个奇想,似乎是上海风味的。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上海妈妈对手推车里的两岁娃娃说:“橱窗里的阿姨好看哦?”我便和这个两岁娃娃一起向“橱窗里的阿姨”看去——一个个高鼻子长腿的模特儿,说不上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好看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上海小囡兰兰怎么这样喜欢费翔呢!
如同我的上海老家尽管久无人住,我一跨进去便能闻出老家的味道,我一走到上海的随便这儿那儿,尽管人异物变,总能一下就领略到上海味道。只有上海才是这样的,这样的。“妹妹,妹妹!”菜场上的一位大嫂子喊我。上海街头常常有些个体商贩这么招呼我。好像我从来就是她(他)的妹妹,好像她天天都在这么招呼我,乃至关照我。这不,我刚看了一眼鳝鱼摊一桶滑腻腻扭动着的活鳝,被牙刷柄一条一条地剖开了。一声“妹妹!”就把我和鳝鱼摊的距离拉近了,大嫂的眼神表情又在使劲儿把我往她那摊上拽。我还来得及想明白怎么回事呢,大嫂已经把剖好的鳝鱼塞进我的兜子里。我愣愣地想起话剧《桃花扇》里庆贺李香君新婚的台词:“不知不觉入了洞房,不知不觉上了牙床。”我呢,不知不觉买了鳝鱼。
个体商贩没进过经济学院也会做生意。不过上海的人嘴甜脑勤手脚快,有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各自便悟出许多生意经来。
我家附近的一个小书亭,是组合成我中学时代的一部分。现在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当时我怎么好意思拿起书亭里的书,一看就没个完。大概一看书,就把书以外的世界全忘了,靠着书亭站着,一小时,半天,今天复明天。不过潜意识一直在提醒我,这是人家的书。所以书在我手里不管多久,都和没人翻看过一样崭新。我至今看书还是这个习惯,至今不能容忍我的新书(我的书都永远是新书)借出去变成旧书回来。我经常买书送人而绝不忍心把书借出去,这个固习不能不追溯到这个小书亭,包括看书亭的一位老伯伯。我最高兴他到书亭旁边的公园里去上厕所,那是要走相当一些路的。当此之时,老伯伯便叫我进书亭,坐在他那把惟一的椅子上看管书亭。这样地被信任,这样地充大人,这于十几岁的我,真是大可以满足我的心理需求了。
我印象中,在我看管书亭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什么人来买书。而老伯伯是常常要上厕所的,而我是常常看书亭的。那时候的人还是钱少。现在的书亭,不知为什么叫我老是联想到钱,钱多了。书亭里挤坐着两位像“橱窗里的阿姨”那么洋气的女郎。那衣着是需要一些钱的。从柜台到书亭的顶棚,这么一点空间也堆满了书籍和录音带。岂止空间,连空气也利用了起来,每一平方毫米的空气都在扩散着流行曲,招徕顾客。我是不招也来的。我先向A女郎买了一本第三期的《上海滩》。买完了一看,还有第四期的《上海滩》。便又向B女郎买这本。“你拿了几本?”B女郎的眼神,一下使我惶恐起来。“第三期的钱呢?”B又射来一句,一下把我发射到小偷席。而B和A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审视我。亏得A记得我交了钱的,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是这样想念那位老伯伯啊!当年他不到上厕所就不会打断我的阅读。我和他事实上从没交谈过什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书亭里的老伯伯和书亭外的小姑娘我,相知很深地共处着,乃至依存着——书亭没有老伯伯自然不成,不过书也需要人来读,才能实现书的自我价值。当然,书亭毕竟是商业性的,得有经济效益,得赚钱,都像我那样又想读书、口袋里又没有一分钱还行?那么,B女郎在钱的问题上的绝不心慈手软,正是全社会经济观念增强的一个反映,是一种进步。很好。只是,如果吓得顾客下次不敢再来,那么这账怎么算?
上海再怎么变,我也能用我的眼睛认出你是上海。不过,这一次我认不出来了。我的对面站着一个人,大声在喊住我:“陈祖芬!”可是,你,你是——
他对我笑着,一个酒窝,又一个酒窝。
我冲他愣着,眨一下眼,又眨一下眼。
我就住在你对面楼上么。他漾开了两个酒窝。
哦——哦——我一点一点想了起来了,我都不认得你了。
我是很记得你的。
记在他那深深的酒窝里?自然。我和他结识的那些日子里,只有欢笑。我的上海老家和他家隔着一条不算宽的马路。窗下是法国梧桐,梧桐树上面是我们两家对着的窗口。他是个单薄白净的少年郎,我是一个混不知事的傻丫头。互相在窗口看见了,我们开枪便打。我家姐弟三人,他家兄妹三人。条件均等的双方便在各自的窗口架上玩具枪、橡皮手榴弹和一切可以权充枪炮弹药的东西——包括伸开拇指和食指当枪。总之,梧桐树下的街道是幽静的,梧桐树上的空气是紧张的。我不时把脑袋扎到窗台下面,躲避想象中飞来的流弹。他也是。
现在他开始发胖了,出现了两个我以前没见过的深深的酒窝。事实上,我以前从来没有走近看过他,和他的全部交往就是梧桐树上的战斗。
那时真淘气。他浑厚地笑着。
妈妈为什么不在老家?妈妈怎么可以不在老家?家里怎么可以没有妈妈?没有妈妈便没有家的感觉。什么叫家?简而言之,妈妈就是家。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家。我们老是打仗——我说。我实在觉得那情景太可笑了。
他说他买了我的集子,要我给他签字。呵,给他签字我太愿意了。他在搞医学研究,我不懂得,不过我知道这远远比我的书有价值。他三十八岁,头发竟已灰白了。着一双草绿旧军鞋,背一只旧军用帆布包,这在上海滩是鲜见的了。
我和他,是从少年人一下变成中年人的。好像没有青年时代,没有中间色的过渡。从见面光知道玩打仗的可笑少年,变成除了不知道玩什么都知道了的中年人。青年时代,他插队,我逍遥。后来又都忙着抓住珍贵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没再见过,直到这次。
我觉得他真好,比“橱窗里的阿姨”还令人悦目。我不会再忘记他了。我要记住这些为事业早生华发的人们,这些榨取自身来滋补我们的事业的人们。
对了,他叫什么名字?
有一种幸福叫守候
文/佚名
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上海的中学生插队来到北大荒。
那年他才满17岁,还没有读懂这个世界,就被无情的命运从繁华都市抛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异乡。
他五光十色的生活瞬间被苍凉的大荒湮没,他曾痴痴望着南方,每晚在梦里哭泣,但醒来眼前还是天苍苍、野茫茫。寂寞与思乡让这个还没长大的孩子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就在这时,一个北方女孩走进了他的视线。那个年代的北大荒,爱情这个字眼还没有流行吧,一个不到17岁的小伙子,一个刚刚15岁的姑娘,更不会说“我爱你,你爱我”的,说到底,他们连手都没敢拉过,他们就那样远远地、默默地被彼此懵懂的情愫牵系着。
爱情让他适应了荒原,除了野草,他还看到了美丽的花朵。几年的相恋后,他们准备结婚了,准备死心塌地在那里过一辈子。那些日子,他们沉浸在喜悦与兴奋中,相约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对被时代抛在一起的患难情侣,用汗与泪浇灌的爱情之花终于要绽放了。就在这时,一纸造化弄人的文件把他们从喜悦中惊醒了——所有知青大返城。他的家庭政策被落实了,他可以回上海上大学了。他不知所措,她鼓励他回去,而自己会在北方等着他回来娶她。
分别的前一天晚上,荒原上的月亮特别圆,她说不知道人今后能不能圆。他就发誓,一定会回来娶她。她幸福地笑了。他终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从此,她最幸福的事,就是守候,漫长的守候。每天,她都要看看他临走时没有带走的换洗衣服,回忆他每一句话,每一个笑容。他大学毕业那年,她每天都兴冲冲跑到县城的火车站,直到人群散尽。那些天,车站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她的事了。就劝她,别等了,因为从没见过走了后又回来的,她对此置之一笑,然后回家去等他。
春去春又回,雁去雁又归,她一直守候着他,用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其实,回到了他久违的都市后,他的父母就每天劝他忘记她,忘记北大荒的生活和一切,他说他做不到,母亲就每天看着他,父亲还模仿他的笔迹,向北大荒寄了一封信给她:我不会跟你结婚的,我们分手吧。
收到信,她晴天霹雳一样的感觉,眼睛一黑,一下子靠到门上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村子里的人都来劝她,不要再等他了。趁年龄还不大,嫁了算了。但她无动于衷,她把那些人赶出家门,坐在家里守候,她相信,有一天,他会随候鸟一同飞回来。
她最幸福的事,就是守候,漫长的守候。春去春又回,雁去雁又归,她一直守候着他,用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终于被逼着跟父亲老战友的女儿结了婚,她的影子,在他的印象中渐渐淡了。婚后两口子去了美国,几年后离了婚,他一个人回到上海。就在那一年,与他一起插队的同伴儿回了趟北大荒,那个同伴儿见到了憔悴不堪、一直独身的她。她对那个同伴儿说,不要找他,不要打扰他的生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其实这个同伴儿好几年前就调到青岛工作了,早就跟他失去了联系。可事情就这样凑巧,有一次他去上海出差,临走前去一家商场买东西,他下班回家也碰巧路过这家商场,于是,这两个20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巧遇了。同伴儿问他,你知不知道有个人一直在等着你。他说谁呀,同伴说是她。他差点没摔倒。他丢掉了手里的东西,发疯一般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这个冬天,距离他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整整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