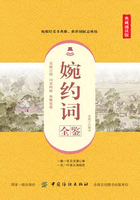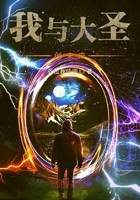陈丹燕是近年来以写上海而闻名的上海女作家,但她的几部畅销书——《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都属于纪实作品,即在采访和调查材料基础上加上一些文学性描写,以满足同时也塑造着追逐时尚的一班年轻读者对于或新或旧的上海的幻想。在她的上述作品中,文学性描写只是辅助手段,主体则是纪实的人与事。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视作者文学描写的功底,或者低估文学性描写在这些纪实作品被读者接受时所起的催化剂作用,而是说,作者很不错的文学描写功底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只是一种辅助工具,而不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解自我的方式(我们也许可以说这就是每一个作家属于自己的具体的哲学)。衡量一部叙事作品文学性因素的标准,并不在于它是纪实还是虚构,关键要看在无论纪实抑或虚构的作品中有没有作者自己的自主而统一的理解世界和理解自我的方式。这个标准,显然不适合用来衡量陈丹燕的上述以上海为题的系列作品,后者更应该在比较成功的时尚写作中确立自己合适的位置。
最近,云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陈丹燕的新书《慢船去中国》,作为该社与《收获》杂志共同策划的“金收获丛书”的一种。《慢》据说是纯虚构作品,全书以一个具有悠久的买办家族史的当代上海家庭数代人的命运为主线结构成首尾一贯的故事情节,主要人物不下十个,场景涉及新疆、上海、美国,时间跨度更大,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90年代末。作者试图以此突破其以往描写上海的几部作品的纪实界限,实现其强烈的文学性追求。
一种“上海文学”的诞生小批判集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看完这部四十三万字的长篇,直觉判断是,它的底子仍然属于纪实,只是加上了更多的自以为属于文学性的描写,而弄得非常尴尬,既不像文学,也不像纪实;作者努力对采访、调查得来的素材进行提升,可惜没有成功,如果我们将作者一笔一画耐心渲染的某种淡淡的忧愁和沉醉(这是典型的属于作者个人的情调)撇开,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相当呆板而缺乏想象力的纪实性故事框架了:小说按部就班地从上海一家人如何送大女儿去美国,依次写到该大女儿如何失败,该家庭如何利用大女儿的失败将二女儿送到美国,一直到二女儿如何处处胜过姐姐而学成归国另创一片天地,这中间除了作者的一些小情调和小摆设之外,叙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使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开掘,故事在叙事的表面匀速滑行,各个段落的长短好像用尺量过一样整齐。
作者为写这一篇故事,也许做了许多调查,但她自己并没有什么切身的体验要表达,只为了讲一个时新应景的上海故事而已。她要为读者提供一个精确的关于上海的公共想象,而不是个体对上海、对时代和世界的体验。这个长篇仍然是一种时尚写作,与直达个体心灵并渴望与当代读者进行对话的文学写作,尚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某显赫一时的上海买办家庭的后代不甘家族的没落,在80年代末出国热中,成功地将大女儿送到美国。这位从小在上海长大,和远在新疆的父母感情疏远的大女儿很不争气,一到美国便就地取材,仅仅因为虚幻的美国梦和拥有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男子做情人的虚荣心,而和室友、一位美国大学生同居,并迅速怀孕。男友不仅不想与她结婚,也不愿承担责任,她只好回国堕胎,结果被父母强迫着返回美国,最终为了要在男友面前维持自尊而在美国堕胎。失望、苦闷和委屈使她身心交瘁,神经错乱。这时候,在早年留学美国、见多识广的爷爷的安排下,父亲以服侍生病的女儿为名到了美国,他不想就此带着发疯的女儿回国,就自己撞车,骗取保险,终于让二女儿来到美国求学。这是小说的上半部。下半部写妹妹如何争气,虽然和姐姐一样,一下飞机就有可爱的美籍华裔男室友等着,但她不为所动,一切以在美国出人头地为目的,终于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而为了获得工作经验,继续攻读美国的MBA,她争取到美国公司驻中国分公司的秘书职位,暂时回到讨厌的上海,埋头工作,连家人也不愿相见,但她的家人正希望她如此绝情,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姐姐的覆辙。可惜她一心为美国老板做事,得罪了思想糟糕的同胞,美国老板非但不支持她,反而认为她没有当好中美合作的桥梁,将她解雇。小说结尾说她在上海又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距离当初的理想已十分遥远。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框架,而每个人物也都值得大书特书,但全书写到最后,仅仅勉强把这个故事框架撑起来而已,读者只要弄清楚情节主干,就一览无余,没有多少值得回味的实质性内容。原因很简单,作者虽有不错的故事原型和框架,但没有写好人物,几乎所有的人物,出场之后就定格了,再没有什么发展,更重要的是,作者与人物之间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交流,因此也无法将自己或有的体验通过人物传达出来。
《慢》中的人物也缺乏起码的性格逻辑,比如作为主角的姐妹俩,有时很聪明,很有自制力,有时又显得很糊涂,很弱智;她们的生活品位,一会儿高雅精致得像公主,一会儿又粗糙恶俗得像瘪三。其他人物,如爷爷、叔公、两个叔叔、父母以及两姐妹各自的美国男友,大多概念化、类型化和脸谱化,似曾相识,——作者缺乏独特的发现。只是那个维尼叔叔的潦倒与超脱,做父母的一切为子女着想的苦心,还算刻画得比较成功,但这并非作者主要用力之点,显然不能弥补全书整体的苍白与空洞。
背景描写,也停留在一般纪实作品的水平。论历史背景,只是一些关于“王家”辉煌往事的不断重复——这是该书最大的特点和主要的叙述内容。作者的态度也于此显得相当暧昧,我们分辨不出她是在讽刺王家后代“祖宗曾经阔过”的阿Q心理,还是跟着王家后代一道来追怀和炫耀。从小说叙述的直接效果来看,恐怕还是以后者居多。
再看现实的描写,80年代上海的“出国热”、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90年代上海合资企业的人员关系,也都没有很好地挖掘和特别出彩之处,至少在众多同类题材作品中,未见多少新意。占全书大部分篇幅的两姐妹在美国的生活,更加表面化,雷同化。虽然两人生活态度不同,但生活内容如出一辙:不是偶尔去拜望孤身隐居在纽约的退休教授婶婆,以及婶婆的好友、专门研究他们家族史的美国学者,和他们聊一些家族的往事,就是与男友逛咖啡店,做饭,或者在大学听课,此外更无他事。
如果读者要问,就这些内容怎么会写出偌大的篇幅,答案也很简单:作者非常善于不看具体情境而信心十足地渲染某种气氛与情调。比如,本来沟通很困难的中西方男女之间的交往,在作者笔下却显得极具抒情和浪漫气味,而其实不过是小资情调的贩卖;本来同样沟通困难的姐妹俩和那个神秘的婶婆之间,到了作者笔下,似乎就有谈不尽的话题,而其实只是关于“王家”往事的一再重复;本来是人物并未融入其中的纽约曼哈顿街区,包括那个走马观花的美术博物馆,却被作者描写得流光溢彩,似乎充分投射着中国女性的丰富情感,其实也不过是对一张旅游图的美声咏叹而已。作者很像一个认真而勤奋的描红高手,先打好基本的故事框架,再一笔笔把颜料描上去,直到所有的空格都被散发着她的气氛和情调的文字填满为止。
为赋新词强说愁,为时尚而时尚,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作者的写作冲动,不是个体积累甚深的人生经验一吐为快,而是要借用一个留学故事演绎一种制度性的时尚想象而已。这个留学故事和以往的留学故事区别在于,以往的留学故事涉及某个梦想中的陌生的他者文化和急欲离去的绝望的现实,而《慢》的留学故事,既不曾触及多少此地的现实,也不曾触及多少彼地的文化,而只是将此地的现实和彼地的文化统统笼罩在作者所接受所演绎的某种关于上海、关于美国、关于当代生活的制度性想象之中。这也是作者为什么那么依赖其善于渲染的文字功夫的原因。《慢》的灵魂,其实既不在作者对于美国有什么切实的了解,也不在于作者对于中国有什么深刻的把握,而只在于她的那一副特别能够制造情调和渲染气氛的笔墨。换句话说,作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写上海,写美国,或者写生活在上海和美国的一些人物,而是为了把自己的某种生活情调渲染出来。
说到“文字功夫”,作者的看家本领,就是无论什么都能写得深情款款,情调十足,而考其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反复使用可操作性极强的同样制度化的拟人手法。
试看她对某种上海情调的渲染:“上海一九九六年暮春的黄昏,熏风阵阵,那是沉重的暖风,又软又重地打在身上,夹着上海那种躁动不宁又暗自感怀的气味,梧桐树上的悬铃子在随风飞舞”。之所以要引这段其实在《慢》中比比皆是的文字,就是想让读者看看现在流行的是怎样的“汉语写作”。写上海,本来是一个困难的工作,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有多少作者的文字搁浅在上海滩了,但《慢》的作者却以拟人手法,轻巧地化困难为平易,化复杂为简单,化生疏为娴熟,任何事物,一旦落到高度拟人化的文字中,就好像已经被她揣摩烂熟的一个老朋友,尽在掌握,任她横写竖写,都无不合适了。比如,本来已是“黄昏”,可巧又赶上“暮春”,唐诗宋词或新文学学生腔小说诗歌里的风味,摇笔即至,而且似乎非此不足以显出文学性;你在“熏风阵阵”中还没回过神,她又吹来了“沉重的暖风”,还“又软又重地打在身上”。想象不出?那就只怪你自己无能且无趣了!写上海,竟然闻到了一种“气味”,可见作者对上海的把握是如何的精微,然而,是怎样的“气味”呢?叫做“躁动不宁”,叫做“暗自感怀”!如果你仍感觉情调不够,还有背后标准上海式的布景:“梧桐树上的悬铃子在随风飞舞”。多么漂亮的文字。什么意思?其实经不起细想,反正这样写出来,显得漂亮就够了。
在当下流行的穷奢极欲的所谓“汉语写作”中,陈丹燕的笔墨算得比较懂点节制,也比较可以见出根底了,——但即使这样,也无法遮掩其骨子里的轻飘、含混、油腻、媚俗和自我膨胀。另外,生造、不通,也所在尽有,比如形容一个人的表情,是“由衷稚气”,描写一家人走进红房子西餐馆,是“各自鱼贯而入”——但这也许并非作者之错,而是编辑之误,至于我这篇文章如此关心这些细枝末节,而非直达那些更加具有文学性和挑战性的问题,大概也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文学批评了。
是上海的文学只配这样的批评呢,还是上海的批评也只配咀嚼这样的文学?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上海的文学,还是上海的批评,一旦乘上这样的“慢船”,恐怕就很难抵达文学的彼岸了。
聪明的作家应该知道,如此沾沾自喜地围绕一个虚构的上海旋转,或围绕一个实有的上海旋转,都不是文学,因为你旋转着,忙碌着,推衍着,渲染着,演绎着,就很容易迷失你自己。抓住了上海,或抓住了别的比上海更加光鲜时尚的所在(比如曼哈顿),却失去了自己,其实是很不合算的。没有你自己,没有你自己的眼光、你自己对这个时代和世界的真切感受,却健笔如飞地写出一大堆时髦的东西来,这除了能够满足时尚追逐者的幻想之外,怎能和更多的人的实际感受对话,获得他们的共鸣?
自从上海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神话之后,以上海为主题的文章应运而生,层出不穷,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至于文学在这种时尚写作中显得异常兴奋,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的文学本来就有一个善于闻风而动的传统,即总能紧跟时代的主旋律,一步不拉。90年代以来,文学本应该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考验中或壮大,或衰微,但一场以上海为中心的新的文学造山运动,使众多一度迷惘的作家不仅免去了考验,还侥幸在另一个意外降临的有利可图的主题下面找到了安全舒适的逃避所,和似乎可以无限开发的市场资源。好在读者已经被彻底驯化了,分辨不出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他们已经成为时尚的俘虏,一旦碰到时尚的参与者、消费者和制造者——以书写上海为时尚的某种上海文学——当然要大声叫好了。在这种读与写的良性循环中,我们的文学依然十分陈旧乃至陈腐,它尽可以在一夜之间占领脆弱而盲从的图书市场,但最终还是不能打动读者的心。即使那些追逐时尚的读者,在占有和消费时尚之后,最终获得的也只能是新的虚空,和对于一度喝彩的时尚作品的遗忘。只不过,对这一种时尚的遗忘,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种新的时尚的警惕,相反,时尚正是借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而使其简单的重复性把戏总能够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
关于陈丹燕的新作就说到这里,还有一点余兴,不妨再说一说某种方兴未艾的“上海文学”的生产机制。
过去我们总认为先有了上海这个地方一定的经济发展,才产生了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这当然是对的,上海文化与文学的空间当然只能在上海,不会在外地,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上海也不断附加和追加了很多未必跟经济对等的观念,特别是对于近年来的上海文学,如果仅仅从经济、政治甚至上海本地的习俗、方言等角度单向度地来研究,就很可能会忽略那些真正催生着一种新的上海文学的制度性因素。
当一个作家的写作涉及上海时,他对上海的历史和现状很可能并没有达到历史研究或现实调查所追求的那种熟悉程度,但他完全有理由从某种制度性想象切入,构筑他们关于上海的想象性叙事。比如,现在流行的一些概念,像“三四十年代的摩登上海”、“国际大都市”、“日常生活”、“欲望”、“时尚”、“消费文化”、“白领”、“小资”、“中西文化交往”、“高速发展”等等,在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叙述上海的作家作品中,显然就一直先验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是这些制度性想象而非上海经济政治的实际变化,使“上海文学”在90年代后半期发生了质变。这以前的上海文学虽然具有不容忽略的“上海特色”,但这种上海特色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上海文学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绝对从属关系;某种整体性的中国文学和与之相对应的关于中国的想象推动着上海文学的发展,也把上海文学牢牢编织进这个整体的中国文学的概念里。90年代中期以后,上述关于上海的制度性想象的介入,不仅改变了上海文学的素材与色彩,也改变了它的地位和性质,使得一种相对独立于整体的中国文学而又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整体的中国文学随它一起发生变革的新的上海文学成为可能。
现在预言这种颠倒的文学景观的终结还为时过早,因为支持这种颠倒的文学景观的关于上海、关于中国的制度性想象已经蔓延全国,在这过程中,并没有遇到足够有力的抵抗。事实上,许多作者已经搭上了这条通往他们心目中的上海和中国的慢船,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同样颠倒的文学旅程。
2003年12月1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