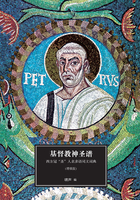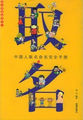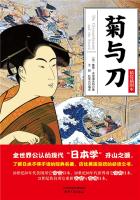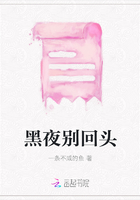自清代康、乾时起,在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同时,中央决定对西域实施大规模屯垦,以作长久之计。屯垦方式有兵屯、民屯、谴屯,还有商屯。兵屯也叫军屯,这是汉代开创的屯戍策略,军队战时打仗,平时耕作,保证粮草基本自给,减轻国家负担,减少给养长途运输的麻烦,也能增加士兵个人收入。因为按清政府规定,屯田军人国发粮饷不减,还可以从农业收入中分得一部分生产所得,为使这些人安心地长期定居,政府鼓励他们携带家眷移居当地,迁移费官给,并分给耕地和牲畜,还赏给一定量的盐菜银,视其官给财产的多少决定纳粮的数量,超纳晋级奖赏,不足按情节处罚。民屯(户屯),单一的兵屯无法满足大规模屯田的需要,又招募河西的贫苦农民来西域安家落户,迁移费用由官方支出。自费移居者六年内不纳税粮,许多人愿意自费移居,到西域每户拨给地三十亩,有能力多耕种者,悉听民便。西域地广人稀,水源充足,自然环境较河西好,容易维持生计,加之政策优惠,河西贫苦农民踊跃西迁。谴屯(犯屯),是将内地囚犯谴往西域屯垦,视其表现可增减服刑年限,刑满后编入民籍,享受民屯待遇。商屯,由富商认购土地,再雇用人员耕种,可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优惠政策吸引中原汉族源源不断地来到西域,作为西域门户的巴里坤是首先接纳内地的屯垦者。所以应募认垦者最早,户数、人口也多。极大地推动了巴里坤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陕甘总督文绶到巴里坤,见当地生产生活状况后在给乾隆皇帝的奏章中是这样写的:“城州嘉禾盈畴,天时、地利、人和,屯田甚广,颇为丰美。该处地广粮贱,谋生甚易,故各地民人相率而来,日益辏集。”
在大批屯民中,有湘川军人、陕甘农民、晋冀商贾,以及多处官吏、流民、囚犯。他们带着不同的语音、生活习俗和文化来到这里,受当地自然环境和原居民文化的影响、制约,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变异,在两百多年中逐渐形成新的固定的区域文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巴里坤文化。
巴里坤汉文化就其主流而言,理所当然的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从它的语言词汇、语音,到生活习俗,民间文化样式,都十分明显地打上中原文化的烙印,以致许多陕甘宁青晋冀鲁豫的人到此,很少或完全没有隔膜,多有回到家乡的亲切感,即使湘川人士,对此文化也会很快找到自己认同的文化的基点。当然,它绝不是内地某一地域文化的翻版,和上述任何一地的文化相比,既有很大的相似性又有大的差异。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它对推崇“中庸”精神的认定,在巴里坤文化中得到了最好最具体的诠释。
§§§第1节大杂居和小聚居的居住格局
从总体情况来看,巴里坤地区始终是多民族杂居的区域。但是,当年屯垦移民之始,大部分屯田人员携妻带子整家迁移,来到巴里坤由政府统一安置,大体的原则是原籍某一地方某一宗族的人安置在某一片地方,逐渐形成村落。比如最早迁到现在的大河镇二三村的多是甘肃兰州、武威人,而这一地方的人中相邻而居的又多是同一家族的。这样的好处是从政府而言便于管理,田亩分配、公差派遣、税收征集以及邻里纠纷等都可以依靠屯民中有威望的人(可以是族长也可以是能力强的)实施管理,这些人在村民中最具发言权,村里的大小事务他们出面就能调节处理得更好更合乎情理。就屯民们本身的利益而言,本土人士相对集中居住,大家推选出的管理者往往能代表大家的利益,自己有与政府打交道的代言人,会照顾自己人的权益;本地方本家族的人集居一处,便于形成合力,万一遇到其他地方其他家族或意外的侵扰伤害,可以集体出手抵御。另一方面是本地本家族住在附近能够相互帮忙,在生产资料的调剂、生产工具的借用,包括日常用具、生活用品的互通有无诸方面都方便得多。俗话说:“谁能背上锅灶出门?”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不可能备足所有需要的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别是一般农民家庭,资金的匮乏生活的拮据更是如此,农人家里需要的东西太多,大到车辆、磨房磨盘,小到顶针麻线,杈把扫帚绳索棍棒水桶榔头马蹄铁泥抹子,样样都需要,一个家庭不可能什么都购置齐备,只能互通有无经常向邻里借用。这样的交往发生在老乡本族之间就比较好相处。所以在安置上和个人意愿方面都愿意这样集居。兰州、武威先来的人占据了大河乡的中间地带,算是老户,叫做“旧户”。后面来的人只能向两边发展,紧靠老户西边的居民村便被称为“新户”。新户西边的人又来得较晚一些,人们按他们的原籍称之为“敦煌户”“玉门县”。安排在现在红山农场地段的是另外三个县的移民,故称“三县户”。而被安置在现在三塘湖的人几乎全是民勤籍农民。本地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习俗相同,自然便于交流。
但是,每个地方移居的人口都是有限的,而且占的地方大,造成了地广人稀的局面,其他地方后来的人逐步被插花安置在原老户中间,打破了原先一地人群居的格局。可能一开始在沟通交流上会有障碍,时间一长,互相了解学习,取长补短倒是相得益彰。一代人之后逐渐忘了原籍,大家都是巴里坤人了,不只是日常生活的交往填平了鸿沟,儿女间的婚嫁也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可事实上这新一代巴里坤人已非原巴里坤人,在语言、习俗、情感文化诸方面都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
内地汉人不断增加,而且占据了巴里坤盆地南北山冲积扇的宜农地区。原先生活在盆地中游牧的蒙古人大部分迁往蒙古草原,少数留居在巴里坤的大都搬迁到盆地西面的丘陵中,那里草场广阔牧草也算肥美,还有一些耕地。段家地、红柳峡一带成为他们的栖息地。但那里春季枯草已经被牲畜啃完而新草还没有长出,属青黄不接季节,一年一度的这个时节他们必须向农区求援。而农区的汉人在庄稼长出之后,牲畜在附近放牧不仅会糟蹋庄稼,还因为田间堤埂和近邻庄稼地的草湖(湿地草场)里的牧草面积数量有限,只能作越冬牧草的储备草场待到秋天打草。所以每到春末夏初,汉人就得将自家的牲畜送到蒙古人那儿请他们代牧。更因为蒙古人数量少,在求医问药、子女读书教育等方面都难以自己解决,一方面是他们经常到农区寻求解决办法,一方面是一些汉族人如江湖郎中、工匠经常到牧区行医、找活,有的干脆就在牧区定居和蒙古人为伍,因为蒙古人生性豪气爽快好打交道,较少斤斤计较。还因为蒙古人少,婚嫁局限在本民族内很难持续,和汉族通婚就势在必行,如此一来,巴里坤的蒙古人后来全都有汉族血统,汉族中不少家族有蒙古血统,生理上的混血与文化上的混血同步进行。1883年起,哈萨克人开始移居巴里坤,并且逐年增加,他们的主要游牧地也在盆地西部、北部丘陵山区。蒙古人由于和哈萨克人在同一区域放牧又有相同相近的生活方式,沟通就更加方便容易,长期的共同生活使他们都能操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同时因上述的原因他们也会说流利的汉语,而他们在本民族内部交流就使用蒙语。这个人数不多但顽强地保留着本民族重要特征和基本习俗的人群,在巴里坤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往往是汉哈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对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融合起到催化作用。
二百多年来,巴里坤地区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小聚居大杂居的居住格局,不仅使这里的汉文化极具多元色彩,也使蒙古文化、哈萨克文化无不具有浓重的农耕文化色彩。
§§§第2节顽强的地方婚姻观念
无论哪种文化,对其他文化样式都具有排异性。其实这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吸收融合是文化发展中的一对离不开的矛盾,或者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能谈融合忽视排斥,谈排斥否定融合。巴里坤汉文化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一方面吸收其他文化的东西,另一方面也顽强地固守母源文化某些东西,譬如婚姻观念和嫁娶习俗等。
“巴里坤的亲,扯扯秧的根。”外地的人这么说是因为巴里坤人自己这么说的。先说什么是扯扯秧,扯扯秧就是野生的牵牛花,取这个比喻不在于它耐旱生命力强,而是它的根在地下穿透能力极强,一株扯扯秧地表的植株并不起眼,可根系十分发达,能延伸几米甚至十几米远,主根与支根毛细根密布,形成一张根系网络覆盖在植株地下。几株几十株相邻的植株下,各植株的根系连成一片,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密密麻麻分不清哪些根是哪棵植株的。巴里坤的亲戚关系正像扯扯秧的根系,所有的巴里坤人如果要拉扯亲戚关系的话,几乎都有血缘或虽非直接血缘但与某血缘亲戚又有血缘关系,如张三与李四没有直接血缘关系,但张三的舅母是李四的姑姑。如此一来,整个巴里坤人相互都是亲戚。
究其原因,客观上,第一是这里总人口数量毕竟有限,乾隆之后最多达五万人,而且汉族只占一半多点,满族官兵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民族人群,而一般时期全县人口维持在三万左右,最少时只有一万多。婚娶的范围就局限在这些人中间。第二是绝大多数家庭生育的子女数目多,七八个子女是常见的,十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屡见不鲜,到下一代,有直系血缘关系的表亲就是几十个。如此繁衍几代之后就造成了绝大多数人都成了隔代亲戚或近缘亲戚,即使无直接血缘关系,也少不了如前所说的舅母的、姑父的、姨父的亲戚连接成自家的亲戚。更何况除此之外还因为有的两家关系密切感情融洽或者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要“认干亲”,即乙方的子女拜认另一方为“干爹(多称为“干大”“干老”)、干妈”。单从亲戚方面说,全县就是一张亲戚的关系网,说它是扯扯秧的根绝不夸张,这样比喻更贴切生动。
比这些客观原因,更起作用的是人们的婚姻观念,做官的有钱的在婚姻方面讲究门当户对,老百姓也不是不如此考虑,只是往往不明确如是说,他们认为此说法只适用于有地位的人家。婚姻大都是利益的交易,所以婚姻的男女双方别说相互了解、有感情以至于爱情,多数连对方的面也没有见过。男女双方的父母长辈根据他们的利益、情感关系决定子女的婚姻,情感最好的莫过于先前的亲戚,所以亲戚之间继续联姻的婚例更多,比如姨表亲之间、姑表亲之间联姻的就比较普遍。不过这里的讲究是舅舅的女儿可以嫁给姑姑的儿子,但姑姑的女儿不可以嫁给舅舅的儿子,否则叫“倒眨毛”。隔代联姻的:爷爷辈、太爷爷辈的表亲之间就更普遍。这叫“亲上加亲”。巴里坤有句俗话“有亲的亲顾呢,没亲的断路呢”,亲戚之间的照顾当然会多而且周到。至于血缘联姻会影响下一代的身体健康和智力发育,很多人不去考虑,可能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
巴里坤人很有点“夜郎自大”的味道,在婚姻方面尤为突出,男子一般不肯娶外地女子,女子同样不愿意嫁给外地男人,无论姑娘小伙如果与外地人结婚,大家会认为是可能有身体、品行、家庭经济状况或家庭大人声誉等方面的毛病。这些人被称为“说不下媳妇的”或“没人要的”,说不下媳妇的或没人要的肯定是劣等的,往往会被人另眼相看,受到歧视。与本地人联姻,一是知根知底比较放心,二是生活习俗语言交流等方便容易,一句带有当地式幽默色彩的话,一个眼神,一种滑稽的鬼脸或动作,当地人大都心领神会,而外地人就莫名其妙或者会产生误解。这种联姻方式,按巴里坤土话叫“内窝子里”倒腾。“内窝子里”倒腾既包括近亲间的联姻,也包括非近亲的当地人间的联姻。
但是,不管如何在“内窝子里”倒腾,“内窝子”终究有限,而且人口结构随着社会变迁快速变化,婚姻取向必然打破“内窝子里倒腾”的格局,不仅常有与“外地人”联姻情况的出现,而且与其他民族特别是蒙古族联姻的更为普遍。在近二三十年中,人们自觉破除“内窝子”联姻习俗,主动寻找“外地人”联姻,对优化人口结构有益,增加了文化的元素。
§§§第3节妙趣横生的地域方言
以巴里坤为典型的新疆人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各操方言,不利于交流。这就需要统一的语言(语音、词汇等)达到便于交流的目的。
而在重新组合的这个人群中,以西北数省即晋陕甘宁人最多,加上与甘肃省地理位置的相近,更主要的是官方极力推广以兰州、银川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这就形成了以兰州银川话为基本语音基础的新疆方言,“文”而言之叫“方言”,”俗”而言之叫“土话”。当代语言学家称之为兰银官话新疆次方言北疆片。它的语音与兰州银川话大体相同。新疆天山两麓尤其是北麓地区的语音都属于这一方言。而以巴里坤最具代表性,并且使用时间最长。在全国大力推行普通话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仍是许多巴里坤人不忍割爱的惯用语言。有人说是巴里坤人食古不化保守封闭由此可见一斑,而巴里坤人却认为非巴里坤话不能准确表情达意。普通话中的许多词汇无法传递乡情的信息,无以表现言外之诙谐幽默的韵味,不能精准地描物述状表情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