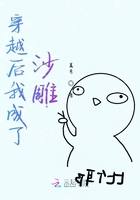(选五)
徐迅
要来的寒流不冷/手捂的伤口不疼/秋天/想起皖河/就有一股
温涌的力量/连绵向上……
——摘自一首诗
油菜花的村庄
如果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那么从油菜花的田野里呢?在春天的五月,我又一次面对油菜花,面前的油菜花与我二十四年前的油菜花没什么两样,大片大片的金黄,黄得炽烈的油菜花丛里,有我熟悉和不熟悉的蝴蝶和蜜蜂。我无法抓住其中的一只,这与我的从前也没什么两样,蜜蜂的叫声嗡嗡嘤嘤的,吵得五月的田野微微发熏,土地已裂开美丽的花纹。
村庄被油菜花包围着,乡亲们的心情被一种喜悦包围着,我的心房被一些往事包围着。村庄与乡亲们闻到那浓浓的菜花香,乡亲们就看到了油亮的菜子。他们都喜欢注重结局,因为结局总意味着丰收,意味着锅里有香喷喷的油水,意味着身强力壮,红光满面。但我不是。在这里我与乡亲们有着一些差别。我只注意过程,油菜花美丽开放的过程,在二十几年前我就是这样。我的这种与乡亲们细微的差别,表明我从来就不曾想过与脚下这块土地认真地贴近,我是这个村庄这块土地的叛逆者,是这块土地上的又一个“叛徒”,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但乡亲们原谅了我,同时也原谅了一只疯狂的菜花狗在油菜花田野横冲直撞、糟蹋庄稼。那一季的油菜花香香地开过一阵,突然就下起了一场春雨。雨打着黄黄的菜花,花儿太柔,太嫩,盛不下那密集的雨脚的蹂躏,凋谢了。许多黄黄的花儿,像死了一地的黄蝴蝶,趴在泥土上飞不动。它的翅膀断了。但香气还在,残存的油菜花的枝秆,结出一粒粒的菜子在风中昂首挺立。那是乡村五月的旗帜。几阵麦黄风吹拂,那上面就会有轻轻的爆裂声响着。阳光里这种声音很悦耳、圆润,如同大地上窃窃的私语,交头接耳着日子。
油坊在远远的镇子上。那原是一座破旧的厂房,屋很大、很黑,却终日弥漫着喷喷的菜籽油香。几个强壮的汉子,脱得精光赤溜的,只穿着一件裤衩,终日在油坊里劳作着。榨油机全都是木头做的,特别坚实的那种木质,粗粗的庞然大物。汉子们将油菜子放在上面碾碎,然后几个人共同推着一根巨大的木棒挤榨着。那酱色的液体汩汩地从木器上流下来,流进盛油的木槽或铁皮桶里,那东西亮晃晃的,能照得进人影。榨油的汉子在旁边乐呵呵的笑,他们在吸烟,光溜溜的身上满是油渍,伸手一摸,像泥鳅一样滑不溜秋。
乡亲们将油菜收割起来,扎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放进用篾编扎的晒筐里。在阳光里暴晒几天,轻轻用手一揉,菜子就落了一筐,堆得厚厚的。母亲是多么地高兴啊!收起油菜后,晒、榨油就是她们的事了。她们从此将日子过得像菜子一样精细、圆润。小小细细、圆圆的菜子在她们的手指缝间细细流淌着,幸福火焰般跳荡在她们胸间。时间在菜子中悄悄流逝,夜晚来到她们的身边,她们浑然不觉。
在乡间春夜寂静的皖河边,油坊里几盏菜油灯亮着。木榨油机“嘭嘭”地响,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河水哗哗地在月光下粼粼地跳跃。这生活中的一种沉重且轻快的旋律,从此伴随着皖河人度过一个短暂而又有些丰收的春天。春天里,乡亲们锅里、碗里的油水都放得很重,灶火烧得嗞嗞直叫。菜油这种来自土地里的东西,叫乡亲们感受到了无比的爱怜,他们亲口尝着,饭也吃得多,干活也更有力气了。春天一过,皖河里开始就泛起桃花汛了,平时清亮的河水夹杂着许多的泥沙,这时候变得尤其浑浊。
就在那个春天里,我打翻了一只菜油桶。喷香的菜油流了满满一地,土地上留下了一滩黑斑,母亲飞快地捞着地上的香油,时而还用手捻着、用嘴舔着。但没有人注意,乡亲们都忙着防汛抗洪去了。
桃花汛的时候
院子里桃花开时,春水漶漫,整个村庄都湿淋淋的。黑色的瓦片在雨中仿佛浸淋得很久了,油黑亮亮的,使村庄的棱角格外地分明。白色的土墙阻挡着田野上漫延过来的花草,池塘边的垂柳枝条点点,招惹得春天里的孩子们,眼睛汪汪地随着它转悠,麻鸭就在那池塘里船队一般游过,蹀蹀地踩着春天的物事。
乡亲们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扛着锄头,这时候总喜欢走动在田野上。他们顺着田埂走,雨水将春天的气息打发得特别充足。这气息也特别诱人。但乡亲们当然不是专门为嗅这气息而来。他们在这条田埂上走走,那条田埂上跑跑,为的是关关这个“田缺”,开开那个“口子”,他们在做大地上的修理工。疏导春水,让桃花汛来临时能顺利地经过村庄,到达它们必须到达的地方。
皖河两岸的高高河堤,长着细细长长的小白杨树,像是春天大地里逸生出来的翅膀,拍打着河水飞快地奔跑。混浊的河水又似一条小蛇,在河堤的指引下动动静静的。只是由于春雨的淤塞,田野都像浸泡着的水草,这时候大地特别肥沃,用手在地上一抓,都是乌黑黑的泥土,肥得流油——喜欢用手扒泥土的是孩子,他们在田沟里翻泥鳅、黄鳝什么的。天气乍暖还寒,孩子们赤着脚,撒野般地奔跑在田野上,春水滋润着双脚,有一种异常熨帖的感觉,脚丫子一踩进泥巴,那更是瓷实得可以。让人更乐观的是田沟里真有不少泥鳅、黄鳝之类的。那些小动物在泥巴里骚乱得不行,一逮一个准。还有人干脆就在小河汊里支起网儿,这往往也不会落空。十有八九都会捞起一网白花花的鲫鱼、胖米,还一种鱼叫鲹子,那种鱼全身都是刺,不好吃,孩子们捞起来也不稀罕。白白胖胖的鲫鱼,大家抓起来就一阵欢呼。晚上在家里拌上葱煮,那鱼汤真是鲜美。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喜欢带我抓鱼。但不知道怎么的,我总是抓不到。连一根泥鳅也逮不住。每次看到伙伴们抓到了鱼,我心里就一阵难堪,但姐姐时而抓起一条鱼,就对我说:“这是我们俩抓的”。她总是这样——后来念书升初中,大队只推荐我们一个,她也让给了我,说:“我们俩念的。”妈妈知道我抓不到鱼,说我穿姐姐的鞋穿多了所以抓不到。我们那里人说穿过女人鞋的男人是抓不着鱼的。
我现在的劳动大都是在晚上。但记得小时候在晚上干活,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就充斥一种犯罪感。桃花汛的时候,河水上涨,池塘里的水也上涨,大人们总喜欢在夜晚,背着网兜在池塘叉鱼。父亲也精通这门手艺。他有一副上乘的叉网,经过一天的劳累后,有时他还带着我到处叉鱼。现在想起来,那时塘都是集体的,这样叉鱼也算不得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我生来胆子就小。父亲在塘边叉鱼,我掌管着手电筒,望着父亲在黑漆漆的水里,用竹竿一下一下地驱赶,捞起来,网里果然就有一层鱼。但我总兴奋不起来,父亲也有点害怕,很快将鱼倒进背后的鱼篓里——也经常碰到同类们,彼此心照不宣地打一声招呼:
“有吗?”
“有。”
“多么?”
“不多。”两个人在夜幕里分手,就匆匆消融在黑暗的春夜里。
桃花汛前后也不过就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季节里,乡亲们脚步匆匆、忙忙碌碌的。土地上许多新奇的事物随着春水开始发酵和泛滥,到处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生机,这使乡亲们的生活也变得生动和有滋有味起来。
但桃花汛过后,急匆匆的,一场洪水真的就过来了。
麦黄风
麦子在四月的皖河两岸,是最为金黄明丽的植物了。这种庄稼使南方的土地和粮食变得异常的生动和丰富多彩。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奇怪,以稻米为主食的皖河两岸,在稻子黄熟的时候,乡亲们对一阵紧似一阵,将稻穗染黄的风儿熟视无睹,偏偏看见散乱在地上并不多见的麦子成熟,叫那刮来的风作“麦黄风”呢?这里,麦子作为南方独特的,点缀庄稼和生活的东西漫延着生长在山坡地,表明了乡亲们一种什么样的成熟的期待?
说也奇怪,在麦子成熟的季节,真的就有那么一阵风刮过来。那风被太阳镀上了一层古铜色,夹杂着皖河水的一丝清凉的气息。株株麦穗整整齐齐地伸展在天空下,如一把把麦帚,将天空打扫得异常的蔚蓝和明亮(不像稻子成熟时稻穗低垂)。在皖河边隐约可见的丘陵上,一块麦田就像一块金黄的烙饼,蒸腾着一种让人口水流涎的味道。乡亲们割完麦子,立即就将麦子在太阳下一粒粒碾下扬净,然后送进磨坊磨成白花花的面粉,用来做粑和扯成挂面,偶尔在吃腻了米饭的间隙,调节调节口味。
磨坊和挂面坊就是皖河岸边最富有激情和意味的风景了。乡亲们大箩小箩地将麦子晒干送进磨坊。磨坊里的磨子一律都是石头做的,很圆、很大。大多时是要两人才能推动它,还要有一个人将麦子一捧一捧地漏进磨眼里。或者就用牛拉磨,牛的眼睛上蒙了块黑布,人在一旁呵斥着,牛就围着磨子一遍又一遍的转圈儿。面粉磨成后,乡亲们很快又将它送进挂面坊里。皖河边的挂面坊有多少?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的印象殊深,那就是一到麦黄季节,所有的挂面坊里都忙得热火朝天。扯面的师傅在晴天丽日里将那扯面的架子端到外面。架子照例是木头做的两根柱子,中间几根杠子上钻了一排排的小孔,白色的、细线般的面条被两根竹棍拉扯得很长。紧绷绷的,远远望着,像是晒着一匹白老布,或像战争年代战地医院洗晒着的绷带——这是那时电影上常出现的场面。当然,在乡亲们的眼里,挂面就是挂面,是用来招待客人的。皖河两岸,招待尊贵客人的最高礼遇,就是“挂面鸡蛋”——这与乡亲们喜欢叫“麦黄风”似乎并无内在的关联。
“挂面”在皖河边不叫“面条”。更不像在北方,还有“大宽、二宽、粗的、细的”之分。这里招待客人的程序是:先端上一碗挂面煮鸡蛋,然后“正餐”还用米饭。大鱼大肉的,还有酒。“挂面”含有一种祝福长寿,长久的意思。由于这个,扯挂面的师傅在这里就特别受人尊重,有点“技”高望重的意思。我有一个姨婆家、还有一位邻居都是扯挂面的,我看他们扯挂面很有讲究:面粉先用水发酵,水要恰到好处,发酵后师傅用手翻着、揉着,揉得满头大汗,汗珠子甚而就掉进面里。但乡亲们并不介意,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说来奇怪,面粉在师傅手里,细软如线,坚韧如针,就那么揉、捶、打、拉、扯几下子,就如一根根丝线了。师傅们将那“线”儿款款摆弄出来,晒在太阳里,同时还晾晒着一份得意和自豪。
我家由于有了上述那层关系,麦子熟的时候,想吃挂面就非常的方便,用钱买或者用麦子换都行。要是人家做新屋,那屋正上梁的时候,乡亲们都会蒸上一点米粑,称上几斤挂面,然后搭块红布送过去。
后来,出现了一种专门磨粉制面的机子。在皖河两岸,要是那机子昼夜不停地响着,磨出白花花的面粉,一定是刮麦黄风的季节。
温暖的花朵
在皖河那纷繁的花朵中,棉花是一种最富于人情的花朵了。仿佛是某种神示,它总是赶在冬天到来之前盛开。那时候当然是皖河的秋天了。一泓秋水浅浅地流淌,如一滩白银泻在雪白的沙滩里,天地一片澄澈。站在皖河的中央四下张望,大片大片白得像雪的棉花远远地开放在皖河两岸。一不小心,你就会当作是谁放牧的一群白羊。更远的,似乎就是一朵朵飘荡的白云,逗得皖河刷刷地竖起了倾听的耳朵。棉花的白云,以它独特的姿态绕过了所有的谛听,在阳光下淋漓地抒情。
棉花似乎是皖河为寒流而准备的礼物。女人们穿着薄薄的秋衫,胳膊挽着竹篮,几乎不约而同地就走进了棉花的田里,她们小心翼翼而又大把大把地摘着棉花,夏天火烤火烤的阳光被如水的秋阳冲淡,但那炙热的光芒并没有远去,它们都躲避在棉花坚硬的壳里。女人们穿梭在棉花丛里,四周攒动的立即全是一张张棉花似的笑脸,不知不觉地,她们浑身也感到一些温暖。冬天就要到来,孩子们正等着御寒的棉袄,家里床上盖旧了的被子需要翻新,而一些老奶奶们呢?额头上深深的纹沟已让棉花擦尽,缺牙掉腮地笑得合不拢嘴。她们焦急地期待着,要将棉花捻成一绽厚厚的线棰,然后在寒冷而漫长的夜晚,摇着古老的纺线车,将那棉棰纺成一根根棉线。纺线是她们最为拿手的活计了。用这棉线,她们差不多就可以织成背带,纺成围巾等各种小玩意儿,然后留给自己的子孙。在活蹦乱跳的孩子们身上,老人看到他们穿着自己织成的小草、小花什么的。孩子胸前编织的“老虎头”在灿烂地微笑。
“弹花匠”因而成为皖河一种古老和最受欢迎的职业。乡亲们将棉花一朵朵摘回来,剥掉那褐色的壳,将棉花糅混在一起,在秋阳里晒干,然后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好鱼好肉、好烟好酒地招待几番。弹花匠喝得醉醺醺的,将弹弓调好,站在面前巨大的雪山上,放肆而欢快地用木棒调拨着。“嘣——锵锵”,“嘣——锵锵”。皖河秋天里的棉花散发出了一种金属的气息,两岸的弹花声弹奏起一种奇妙的音乐。使皖河变得闲适,优雅。河水因此也激动得不停地歌唱着爱情和劳动。尔后又归于一种平静。弹花匠将那弹好的棉絮弄得熨熨帖帖,如一方硕大的豆腐。高兴的时候,弹花匠还会细心地在网住棉絮的时候,用红线头织成“福”、“喜”……和“新婚快乐”的字样——那样的被子,一般都是主人为待嫁的姑娘,或者为待娶的新娘而准备的。
新娘子在洞房花烛夜里,暖暖地捂盖着一床绵软阔大的棉被,除独享着一个男人的体香,同时能清晰地嗅到的就是棉花与阳光混合的气息了。这种人生中最奇妙的气息,搅得她们躺在温柔乡里,幸福的陶醉和快乐着。过不了几天,她就会毫不害羞地将这床棉絮拿到阳光下翻晒——通常这哪里是晒被子,简直就是晾晒着一种幸福和富有。
从棉花的播种到成长,以及制作成棉被、棉袄出来的时间短促。但对于其中的每一件活计,乡亲们都做得非常精心和认真。棉花是最不容易凋谢的一种花了,但它在生长、制作过程中,乡亲们领略到的幸福、愉快和轻松,却是皖河所有庄稼活所无法比拟的。不像种稻子和麦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棉花成熟的季节,一朵朵白云绕山间。皖河到处飞扬着悠扬的歌声和欢快的笑……当然,皖河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栽插水稻和麦子。相反,他们不像完全以棉花为生的棉畈区那样,将所有的土地都种上棉花。像仅仅只是为了欣赏一下自己种的花朵,他们种的棉花最多只管家里床上盖的和身上穿的就够了。棉花大都习惯生长在山地上,而皖河流域大多是水田,土地并不富余。乡亲们觉得,这就是上苍的一种安排。上帝给他们的分工就是种稻,没必要白白浪费大片大片肥沃的水田种棉花。
什么地长什么庄稼,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皖河两岸除了大片大片的白棉花,在秋水茫茫的季节,还有白色的芭茅花和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它们一般都凋落在冬天——只有棉花既干净又利索地在秋天里成熟和结束。冬天真正来临之际,寒风吹彻了皖河每一处村落,那时棉花便穿在他们的身上,温暖在他们的身心了。
谁都清楚,乡亲们感念棉花——是因为真正的白花,雪花就快要降临到皖河了。
有些雪不一定落在河里
昨夜又下了一场小雪,皖河两岸的道路、村庄和屋顶已被白雪静静地覆盖住了。乡亲们没想到雪会下得那么薄,薄得像一层白霜。更没有想到的是河里的水依然深绿深绿的,似乎比平时绿出了好几倍——它的身上居然没有雪。由于饥饿和寒冷,冻死了一条黄狗,还死了一只老鸹,都僵硬硬地躺在河堤上。河里一缕缕水汽袅袅荡漾开来,牛棚里牛冻得哞哞叫唤。
冬雪和春雪是有区别的。一场这样的春雪,皖河靠着自身蕴藏的暖气就迅速地解决了自己的困境。冬雪就不一样了,它奇寒无比,大片大片的雪花凶猛地蚕食着土地上的一切。雪下得很厚,像是一床棉被,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就将皖河两岸紧紧地捂住了。谁家不结实的草屋让雪天雪地压得吱吱直叫,稻场上草堆将自己扮成了一个雪人……皖河像一个自己掀掉身上被子的人,正探头探脑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这时候它也感受到寒冷,冰冻将它的行动弄得十分迟缓。但那水依然流着,冰冻下的河水像一群小蝌蚪在不停地游移着,使人感觉出生命的一种勃动。
但雪落在皖河里肯定就看不见了!有些雪不一定落在河里,它落到了它想要落到的地方。
冬天的皖河,总是荒凉和寒冷得让乡亲们无法忍受。所有的庄稼在秋天早已收拾干净,稻田一片狼藉,光秃秃的树枝、丘陵、平原和一排排村庄,在漫长的冬季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裸露着羞处。呼啸的北风夹带着灰尘,卷起秋天最后的残叶。河水这时候也变得有些懒散——这种气氛似乎也感染了乡亲们,使他们的生活一下子仿佛就陷入了沉闷的境地。老天爷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的疏忽,想努力补偿什么似的,于是用一些虚幻的雪景迅速地遮住了一切,企图让人在冬天里还建立起一些生活的信念——飘飘洒洒的,雪就这样身份可疑地来到了皖河。
雪注定是皖河一个美丽的谎言。
谎言使乡亲们在冬天不断地欺骗着自己,也欺骗着别的生命。他们在大雪封门的日子,常常独自躲在屋里,依偎着红泥小炉,温一壶热酒,编造一些故事和童话,假装成一份若有若无的轻松。大人们在雪地里还用竹箩筐教着孩子欺骗麻雀,捕捉它;与孩子们堆一尊雪人——假人,或者干脆就用雪的子弹互相射击着,然而这一切都透着一个“假”字,子弹的谎言很快就被人的身体击碎,但他们都陶醉在自己用谎言制造出来的欢乐之中。“雪是神的粮食!”乡亲们说。
这当然是乡亲们编造的最大的谎言了。
谁也无心戳穿这个谎言。只是皖河的一些老人们经历了皖河的一切,却再也无法忍受,无法按捺住自己的心情。他们好像不好意思告诉孩子们关于雪的一切,也不容许雪花欺骗一切。就独自选择在冰天雪地里离开人世。于是冬天里,皖河辞别人世的老人就特别特别的多,漫天漫地的白白雪花,转眼就变成了他们身上穿的最大的孝服。在河堤上,冷不丁就出现一支披麻戴孝的送丧队伍,吹着唢呐,敲着锣鼓。喧天的锣鼓恰好冲淡了冬天的沉寂,白白的孝幡又暗合了白雪的皖河。那些活着的乡亲慨叹着人生的无常,赶紧找了一块平地,将老人深深埋葬在那里,那隆起的土堆很快又被雪花深深地遮盖住了。
雪悄悄地落在上面,似乎就落在这个人的生命里了——这时候,你一定清楚雪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但这不是唯一的。雪落的最大理由就是落雪。我常常看见乡亲们站在下过雪的田野,瞅着天空,嘴角流露出一丝赞许和欣赏的微笑。他们说土地太干太燥了,各种害虫就会躲藏在大地下面,雪是庄稼的医生,它是在给大地进行一次消毒。“瑞雪兆丰年”,他们在说这话时,心里依稀就有一种温暖慢慢洇渍开来。这时候你仿佛看见很多害虫、很多的毒菌都被雪毫不留情地杀死了。这就是皖河人喜欢雪的原因。在雪花的美丽和纯洁性上,乡亲们似乎更喜欢雪花的纯洁——尽管这一点与很多人不一样。
或许最平静的还是皖河。它不需要白雪的装扮,当然也就坚决地拒绝雪花给它的外套。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我跟着母亲拿着一个瓦罐在皖河的河边收拾了一回雪花。母亲说,要用冰凉的雪水腌上几只咸鸭蛋——这时,我才发觉一冬的白雪,全都落进母亲那油黑亮亮的瓦罐里去了。
(选自《清明》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