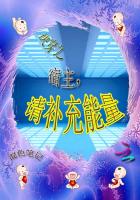防风,又名“铜芸”、“茴芸”、“屏风”、“百枝”,大风,头腔痛恶风,风邪瞳无所见,风行周身,骨节疼痹,烦满。
五加,又名“白刺”、“追风使”、“木骨”,明目,下气,治中风骨节挛急,补五劳七伤……
——《本草纲目》
五加是我哥哥。
我们家是汉朝的医药大家,世代习医,传至我哥哥这代,已是声名狼藉。
五加好赌,每回赌完,都带一身伤回家,面色苍白,呼吸微弱,不喊、不闹、不喝酒、不打人,只是静静地坐在门槛上,数天上的星星。五加说,那颗半亮不亮的星,就是杜仲。他一直在看着我们呢。他就是要败给他看,让他看看他到底生了一个多么没用的儿子,让他死也不得瞑目。说完,他就在月下大笑,不停地笑,笑出了泪都不自知;笑得累了就倚着门框睡了去,睡到第二日日上三竿继续去赌。
杜仲是我爹,五年前沉湖,自杀身亡。
五加有数不尽的赌本,因为他有妹妹杜铜芸。
三年前,我翩然而至,用一味药治好薛家少爷多年目昏的顽疾。自那以后,薛家隔三差五地送来银两。我们杜家子女心脏里都生长着一颗药草,由心脏造出并流淌过全身的血液,本身便可入药。以药材为引,用血熬煮,治疗顽疾有奇效。根据血液的药能,冠人以名。曾经,我放了满满一锅血,煮成了那碗乌黑暗红又黏稠的“防风”,救了薛儒生。外行人自不会知,“防风”便是“铜芸”。
曾曾祖父年代,曾有帝王邀杜家人入朝为御用医师,被断然拒绝。帝王怒,直指杜家罔顾圣意。杜家瞬时处风口浪尖,因四处受压迫,无奈归隐。即使如此,朝廷的人依旧对杜家多方刁难毫不手软。浩浩杜家,时至今日,只剩下我与五加两个。
五加常年厮混在外、日夜颠倒。我时常一天都见不到五加一面,更甚至于大年三十,我只是一个人草草吃一顿饭,再同自己说一声“过年了。”
有时候,五加输光了钱,回来得早些,便能赶上晚饭。吃完饭,我陪着他,指着那颗星,一起骂杜仲这个老匹夫,连血都不敢放。我只不过放了一锅,换来今生的温饱,多划算。骂完再取笑胆小鬼杜仲,连死都不怕了,放血有什么可怖的!
井胡同的尾上,人烟稀少,有成片的空落小院,我与五加就住在那儿。因为晒满了药草,即使是两个人住也没有显得大。站在院中,还能看到隔壁文里巷巷口的薛家大宅中出墙而来的繁茂绿枝。
文里巷与井胡同相邻,却与井胡同是天差地别。那里住着许多学士名儒,进出都是轿子马车。再过去,便是喧闹的街市。
以前,我常常在街口、巷头摆一个悬壶济世的小桌,为他人诊治,因为诊金低廉又颇有疗效,渐渐有了声望。直到薛家请我去治病,一治成名后,时不时就有上门求医的人,我只需在自家的小院中,也不用愁吃穿。久而久之,周围的院落中搬进了一些人,小院也渐渐有了生气。
三月,草长莺飞,郊外溪流中的破冰终于全部消融,混迹于潺潺的泉水中。春日的早阳照在身上,才觉阵阵喜人的暖意。五加难得兴致极好地拉了我,说是要放纸鸢。可是,看着他两手空空,我坐在草坡上细数抽发的嫩芽,不明所以。身旁的五加两手撑着身体,仰头望天,眼中的迷惘与哀恸倾泻而出。
我心中一酸,学他一样看那空中悠悠飘过的白云。浩渺的天空似乎也在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们,更似在嘲笑我们的渺小无知、柔弱无能。
不远处,成群的孩子你追我赶,传来阵阵“咯咯”的笑声。五加却扭头,看向了另一个方向,轻道:“纸鸢来了。”
我朝着他的视线望去,一个编着两只小辫、身穿大红丝制棉袄的小姑娘拽紧了手中的纸鸢,张开双臂在空阔的绿地上胡乱奔跑,两名婢女提着裙摆吊着胆急急跟在身后。我疑惑地将头转向五加。五加粲然一笑,嘴角的弧度僵硬无比。他将我被风吹到肩前的长发拂到脑后,指向两名婢女的更身后。那里,白衫少年轻挪着步伐款款走来,眉间满溢出柔色,眼不曾挪开红衣小女孩半步,舒心而又宠溺地笑着,我却觉得这笑比三伏天的阳光还要刺眼。
身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循声望去,五加起身,眼眸微收,轻拍去身上沾有的草屑,径直大步离去。那一刻的五加,形单影只,好似走向无边的黑暗,孤寂卑怯的背影却异常高大。我心内如绞,正想去追,耳侧响起低唤。
“杜姑娘,你也在这儿,真巧。”
白衣飘飘,落在我的身侧,正是薛儒生。我垂了眼:“薛公子。”
“一个人?”
“嗯,你呢?”
“带舍妹出来耍玩。”
“春日晴方好,很适合出来走一走。”
“是啊。”
初春的风向恍若孩童的脾性般不可捉摸,打乱了五加为我理顺的发,我伸手将遮在眼前的碎发撩到耳后。身旁的视线越发灼热,我看着前方耍玩的人群,不敢侧身。忽的,“哎呦”一声,一个孩子跑得太猛烈,扑倒在坡上。我未及细想,急忙起身上前,查看他的伤势。好在衣服穿得厚,只有掌心磨开了些皮,我细细挑开陷进皮肉中的沙石,掏出随身带着的金创药,为他上药。我正要撕开自己的裙摆,一只温暖又宽大的手掌制住我的手,我抬头看他。薛儒生摇着头,就着自己的衣摆,撕下一根布条,亲自为孩子包扎。他那时眼中的柔软,不知是因为我,还是因为受伤的孩子。孩子的母亲跑来,接过孩子,不断点头道谢。
转身,是薛儒生淡雅的笑脸。
才不过巳时,我已觉疲乏。我向薛儒生浅笑,别过。
扬起的秀发在风中飞舞,迷了谁的眼,乱了谁的心。
料峭的春意如同一只搔首弄姿的鹦鹉,可笑却极尽奢华,浮夸又不知深浅。群芳苦争春,奈何不争;掉落枝头,化万缕香魂,萧瑟成海。
盘踞在冬春之交的恶霸,正悄然游走在我们身边。
近几日风寒肆虐,病倒的人与日俱增。我核对好几个方子,合上账本,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推门而出。门前小院里,五加正蹲着身子,在奋力地拔草。
常日这个时候,五加应该还在酣睡,今日怎的如此勤快。忽的,脑中闪过一道光,我暗道不好,沉了脸跑上前去钳住五加的手。五加的手中还握着一株杂草,愣愣地抬头看我。我却恍然,轻叹一声,松开了他的手。
是五加这些年来太过潦倒,还是因为我已经走得太远渐渐失了自己,我竟忘了杜五加也是懂得药理识得药草辨得药香的!
五加拔起手下的杂草,扔到一旁,将双手往衣上一抹,牵起我的手就往外走。
“诶,等等,去哪?”
“我带你去尝尝云仙楼的芙蓉鸭和桃花酿。”
“钱呢?”
“昨晚赌赢的。”
“你就这样去?”
“又何妨。”
五加的声音合在风声中,令人生出虚无缥缈的感觉,也令我半信半疑。
名食坊云仙楼,招牌芙蓉鸭和桃花酿,一桌千金。桃花还未开放,云仙楼的桃花酿却已经香飘万里,入小楼深巷,穷地海中天。芙蓉鸭脆皮酥香、肉质鲜嫩,配上清甜甘爽的桃花酿,堪称人间极味。云仙楼,顾名思义,足让人如腾云羽化飞仙遨游天际。初初来此,我曾小女孩心性,央五加带我去云仙楼尝鲜,没想五加一直记到现在。
等我回过神来,我们已经坐在云仙楼二楼临窗的桌旁。往窗下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尽是朝向这边的艳羡渴求的目光。
除了芙蓉鸭和桃花酿,五加又点了几样别致的素食。看着眼前色泽诱人、晶莹透亮的菜肴,我不敢下筷,只觉得自己是在梦中。
“怎么了,快吃啊。”
我抬头看五加。真想把五加的手一把拽过来狠狠咬下一口,看看疼不疼,可惜我够不着对面的五加。五加阴恻恻地朝我笑,宛如一只龇牙咧嘴的恶狼。
“再不吃我可要不客气了。”
我心中一紧,快速夹过一只鸭腿塞进嘴里,以眼神挑衅:“哼。”
五加微微一笑,向我轻抬酒杯,将桃花酿一饮而尽。
透着桃色的清酒,闻着已让我垂涎欲滴,入口更觉甘醇。分明类似果酿,我却醉得如坠云里。恍惚中,有人拉开椅子,与我们合桌。我眯起眼,滚烫的双颊熊熊燃烧间,我看见一张模糊虚幻的脸,“噗”得笑了,纤细的手指朝他一指。
“你呀。”
“嗯。”那人接住我指向他的手,在手背落下一吻。
我全全失了表情,血液都往脑中冲上来,晕晕乎乎的。我还没来得及抽出手,眼前一暗,整个头都往桌上栽去,意识不复。
薛儒生轻轻放下裹在掌中的纤手,朝另一侧的杜五加拱手。
“失礼。”
五加摆了摆手,过分悠闲都吃着:“无碍,是小妹贪杯。”
“杜兄,请问令妹可有婚配?”
五加突然沉了脸:“那边在等着你。”
薛儒生侧身,才发现不远处的一桌人正盯着这里,懊恼地起身,向五加告辞。
五加不理他,自顾自吃着,直到肴核皆尽,搀着醉倒的我离开。
我直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过,五加就是不肯告诉我,只说那一顿是薛儒生请的。
怎的平白冒出一个薛儒生?我想不出个所以然,自个儿生闷气。但是,我想,这一定和五加脱不了干系。
我同五加连着三天都未曾说过一句话。我恼他自作主张,他却满不在乎依旧天天不知疲倦地往赌馆里跑。而小院,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我坐在案前,正在研究一本医书上的药方,薛儒生脚步轻盈,落座在我的对面,与其他病人一般,将手伸到桌上。白衫无垢,明眸璀璨,我瞧不出他有任何的病症,迟迟没有搭上他的脉搏。
“这几日觉得胸闷气短,劳杜姑娘帮我看看。”清浅的笑声,如微风拂面。
我替他把脉,微微惊诧,顷刻又了然于心:“薛公子在服药?”
“嗯,补药。”
“有几味药与你的身体相冲,还是尽早停掉的好。”
他正色:“可有伤害?”
“有,是慢性的。”我略一沉吟,“我给你开一副方子,每日一服。”
“麻烦姑娘了。”
“嗯,公子走好。”
五加从门口面无表情地经过,浑身上下带着沉重的戾气。
我将薛儒生送到门口,他却不走,灼灼地盯着我。我一时羞愤,立时掉头折返。走到门口,一阵香味扑鼻而来,案上被摆了满满的一碗面。我不解地上前,挑起一筷,竟是连接不断的面条,面汤上飘着翠绿的葱花,泛起少许的油沫,闪闪发亮。我抿了少许汤汁,虽不算鲜美,却醇厚朴实,有家的味道。
一双大掌抚过我的发间,发被捋起几缕挽成髻,一根“筷子”被插进发间。还未等我反应,眼前横空出现一面铜镜,我用手抓起镜子,侧过脑袋看自己的发间。没有多大的变化,除却无故多出的一支红里透黑的木钗,钗头被细细雕琢成精巧的图案,煞是好看。我猛地回头,看见了五加。
“喜欢吗?”
“喜欢!”我盯着五加的眼,终于找到了些从前的澄澈,“这?”
“铜芸,这是给你的生辰礼物。”
呀!今日是我的生辰,我自己都不曾记起。我只觉得心中满满的都是装不下的欣喜与满足,五加的脸在其中渐渐模糊了起来。五加忙捧起了我的脸,一时间不知所措。
“别哭,快吃面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嗯!”
我埋头吃长寿面,不敢让面条断掉。泪花掉落在碗中,被我一起吞下肚。五加一直坐在一旁看着我吃,见我如此,哭笑不得,揉了揉我的发,叫我“傻姑娘”。
一根面条吃到底,我扬起泪光闪闪的脸,将碗推向五加。
“好吃吗?”
“你自己尝尝,我给你剩了些汤。”
五加磨牙,就着碗喝了一大口汤:“啧啧,真苦。”
我佯装扑过去要打他:“胡说,我的泪是甜的!”
五加惊跳起,大笑着跑开。
阳光在五加的身后铺陈开,而五加,置身于光束的最中央,如天外来客,耀眼夺目。
这是千百个日夜中,我所见过的最欢畅、最自由的杜五加。而这一场冷战,终是与往常一样,悄然不见了踪影。
手旁的杯中,细小的苦丁起起伏伏,带着些微温,浸润在所剩不多的茶水中。我拂去额上沁出的汗水,手下疾书。
屋门大开,可以清楚地看到院中架起的两排砂罐,在腾腾地冒出热气,冲着不远处愁容满面席地坐着的人们叫嚣。春日的风寒愈发严重,轻微的尚且能自己出门寻医,重的已经是卧床不起无法自理。我配了副抵御寒症的药,在院中煎上,免费施药于左邻右舍。邻人纷至沓来,就连住得较远的,也有闻之而来的,一时间,小院竟拥挤了起来。我将有症状的病人安置在内屋,屋舍不大,其余的只得等在院中。五加见我咬牙将担子全全压在自己肩上,不忍我辛劳,留下帮忙。
晌午刚过,我有些晃神。茶水重又添满,我轻抿了一口苦丁茶,丝丝苦意入喉,似忧愁滑进心中,令我清醒了不少。五加进屋来寻药包换药,身后不远跟着一个半大的少年。我记得那少年是跟一位妇人一道来的。他的母亲有轻微的寒症,在内屋歇着,怕将病气过给他,不准他留在身侧。
那小少年凑到我的耳边,声音并不大:“杜姐姐,我刚刚瞧见有人从后院出来。”
我一笑:“保不准是去找茅房的。”
“可是他东张西望的,像个贼。”
“这里都是病人,你是不是看错了?”
“可是那个人一丁点病着的样子也没有……”少年的声音渐渐低了,却清晰无比地传到我的耳中。
我闻言一惊,猛地站起来,头顶一片黑云压下,令我一阵眩晕,身侧的五加忙扶住我。
是了,找茅房哪有去后院的。我们并不富裕,后院除了几捆柴,几只鸡鸭,独独有一口井。是谁?是五加不小心开罪了什么人,还是我在不知不觉中与谁结了怨?我未及细想,只觉得头越来越重,慢慢靠向五加。
五加将我揽住,端起苦丁茶轻嗅,顿时皱起峰眉。鼻下有轻微的血腥味,我无力地睁开眼,看着眼前被咬破了一个小口渗出颗颗血珠的手指,生硬地撇开了头。
“不。”
“就吸一点点,不会有事的。”
“就不。”我用双手环住五加的腰,将头藏与他的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