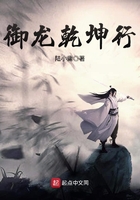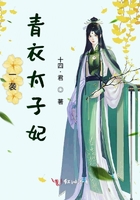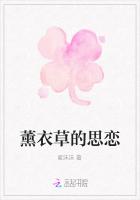第四章 董仲舒
一、略传
董仲舒,广川人。少年时治《春秋》学,在汉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仲舒以贤良对策,说“天人相与之际”,能使武帝动听,遂册问他三次。对毕,武帝叫他去做江都王的相。后来废为中大夫。那时辽东的高庙,长陵的高园殿,都被火烧了。
仲舒在家推说这两次火灾,以为天意烧去“其不当立者”。因说“在外而不正,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
那时有人把这篇说奏上去,武帝召诸儒讨论,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先生的书,说是“大患”。于是武帝把仲舒下在狱里,已定死罪,武帝诏赦之。仲舒本来最喜谈灾异,有求雨止雨的方法;如今吃了谈灾异的苦,从此不敢谈灾异了!后来仲舒起为胶西王的相,不久告病回家,死时享高寿。(《汉书·五十六》、参考二十七上《五行志》。)
董仲舒的书,现存的除《汉书》本传所记《三策》外,有《春秋繁露》八十二篇。这书性质杂乱,像是经后人补凑过的,不见得是他的原书。
董仲舒在中国文明史上要算一个重要人物。西汉朝的儒生大都没有什么哲学的兴趣,他们注意的大都是一些社会政治的问题。只有董仲舒可算是个哲学家,他的主张都可以说是从一个名学的观点出发。他又是一个宗教家,所以他的主张又都带着不少的宗教色彩。
他对策时,请武帝兴太学,重儒术,推明孔氏,罢黜百家,令州郡举茂材孝廉,后来这些主张都见实行,遂使儒术真成一尊的国教。他一方面推崇儒术,一方面讲阴阳灾异之学,遂使儒术变成“道士派的儒家”。
二、公羊春秋学
我讲孔子的哲学,最注重《易经》和《春秋》,以为这两部书是孔子哲学的根本所在。《春秋》的传授,不大可考。《史记》和《汉书》都说汉初始治《春秋》的人,“于齐鲁(《汉书》无“鲁”字)自(《汉书》作则)胡毋生,于赵自(《汉书》作“则”)董仲舒”。
《汉书·儒林传》又说“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己。”我虽不愿加入古文今文的纷争,但我老实说,从哲学史上看来,《春秋》当以《公羊传》为正宗,《榖梁传》还可供参证,《左传》只可当文学书看,没有哲学史料的价值了。
胡毋生当景帝时年已老了,他的影响不很大。《史记》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太史公《自序》极推崇董生,董生的势力能压倒一个主张《榖梁传》的公孙丞相,能使《公羊传》独列于学官。可见他的学说影响真不小。细看董生的学说,所有得力受病之处,都在《春秋》。
《春秋》本来没有什么哲学可说,至多不过是“寓褒贬,别善恶”的正名主义的应用而已。但公羊一派的《春秋》学从这个正名主义的观点上敷演出许多意义来,——或者可说,他们把许多意义读到《春秋》里面去。
无论是他们寻出来的,或是读进去的,他们造成了一种《公羊春秋》的学说,从董仲舒到我们同时的康有为、崔适,影响了不少人的思想。
三、名学
我常说一部《春秋》是孔门的应用名学。孔子的名学只在一个正名主义。一部《春秋》只是这个正名主义的应用。董仲舒的名学也只是一个正名主义。《春秋繁露》(以下省称《繁露》)说:
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
“辨”是分别。“大”就是名学上说的“全称”,也叫做“共相”。他说治天下的起点在于能晓得辨别大小。辨别大小的起点在于深察名号。他接着说: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
“大理”是“大之理”。大小的分别,最先表现于名字上。今且用原篇中的例:
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
“号”是大的类名,“名”是一部分之名。“祭”是类名,大于祠、礿、尝、烝四名。故可说“礿,祭也”,不可说“祭,礿也”。正如人可说“孔子,人也”,不可说“人,孔子也”。所以说,大小的分别最先表现即在于名字。认定名所表示的大小分别,用来观察所名之事,即可辨别是非,即可知道逆顺。故接着说:
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
如上文举的例,“礿,祭也”,是“顺”的,即是“是”的。“祭,礿也”,是“逆”的,即是“非”的。从前的儒家虽主张正名,却还有些人知道“名”的原起不过是一种人造的符号。
所以荀卿那样注重正名,也不能不承认“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董仲舒去古已远,不懂得“名”有心理的和社会的原起,所以竟说“名号之正,取之天地”。这竟把一切名号看作天造地设的,看作天经地义了。他接着说:
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名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天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
这一段说名号的原起。謞、效、号及鸣、命、名,古音大概相同,故董仲舒可以傅会声音。通段的条例,说名号都有神秘的起源;并不是思想的符号,乃是“圣人所发天意”。下文论名号的区别:
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分别离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猎禽兽者号一,曰田。
田之散名:春苗、夏狝、秋蒐、冬狩。无有不皆中天意者。……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以上所引皆见《深察名号篇》)
如此说来,名号竟是沟通“天人之际”的线索。深察名号,可以得圣人所发天意。顺了天意,便可使“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欧洲中古时代的哲学家说“名先于实”的道理,有一派人以为未有“实”时,上帝心中先有了实的法相意象,故说“名先于实”。董仲舒论名号与这一派正相同。
但董仲舒论名,有时又近于“名在于实”一派。如下文所引:
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深察名号篇》)名者,性之实。实者,性之质。(《实性篇》)
又如:《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深察名号篇》)
大概董仲舒论名,以为一物有一物的“真”性。这种真性即含在那物的“名”里。物的“真”性,生于自然,故又说名是表示“天意”的。(古音天、真音相近,“真”读如“填”、“滇”。故真属天然而伪训人为。)
因为名是表示物之“真”,天之意的,故深察名号,可以得知物理天意。得知物理天意,便可以审是非、定曲直。故说:
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於非也,犹绳之审於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矣。(《深察名号篇》)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的正式解说。孔子的“政者正也”,儒家的“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乐者乐也”,都只是用这个方法。独有董仲舒把这种名学说得明白清楚。他说:
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同上)
这两个例,都是用声音相近的字来说明字义。有时他也从形体一方面着想。如《王道通篇》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许慎《说文解字》即引这话说“王”字。可见董仲舒一派的正名论无论如何荒诞,在当时颇能引起学者对于文字训诂上的兴趣。
无论他是从声音假借下手,还是从形体构造下手,总而言之,董仲舒的正名论只是教人深察名号,要从名号里而寻出所名的事物的真意义,寻出了这个真意义,然后拿这真意义去审定那事物的是非得失。这是公羊、榖梁两家《春秋》学的根本学说,这是孔门正名主义最明白的解说。
四、董仲舒《春秋》
董仲舒的《春秋》学,最得力于正名主义。故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賈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鹢之辞是也。
凡是偏重名的名学,其结果一定是一种尊上抑下,尊君抑民,尊全体抑个人的伦理政治学说。这是百试不爽的定理。
董仲舒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又说“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篇》)。名是全称,故尊名的人自然趋向最高最大的全称。
欧洲中古时代,最大的全称,在天上是“上帝”,在人世是“教会”。中国中古时代,最大的全称,在天上是“天”,在地上是“天子”。故董仲舒《对策》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此指《春秋》书春王正月)。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又说: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又说: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志也。(《玉杯篇》)
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的大纲。他一方面要“屈民而伸君”,一方面又要“屈君而伸天”。总而言之,只是要求一个最大的全称,“辞之所谓大”。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切要的。汉初兴时,那许多功臣都是高帝从前的平辈,没有什么君臣名分可言。所以有的“沙中聚语”想谋反,有的在朝廷上“拔剑砍柱,争功妄呼”。
后来虽然杀了韩信、彭越,虽然定了朝仪,终不能使人不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所以汉兴百年之内,有陈豨之反,英布之反,济北王之反,淮南王长之反,吴楚七国之反,淮南衡山王之反。
所以当时的要务在于提倡一种“辨上下,定民志”的学说。叔孙通、董仲舒一般人“屈民而伸君”的学说正是当时所需要。这是尊君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恰与此相反。汉代的****制度当时虽不曾十分完备,却是非常严酷。如《汉书·刑法志》说汉初夷三族之令道:
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孝文二年,……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后元元年)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
法律如此惨酷无人理,君主的威权遂没有限制。所以那时的儒者又不能不想出一个可以限制君主威权的物事。那时的君主又都是迷信鬼神、信方士,妄想长生不死的人。
于是那时的儒者自然想到“天”的观念,要想请出“天”来压倒君主的威权。所以董仲舒一方面要“屈民而伸君”,一方面又要“屈君而伸天”。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苦心。
我们虽不能说那些人先存一个限制君权的观念,但是那些人生在那时代,看着那时势的情形,有意无意之中,遂不能不有这种双方的主张。我们生在二千年后,先怀了二十世纪的成见,对于这种尊君信天的主张,自然不能满意。
但是读史的人,须要有历史的观念,须要能替古人设心处地,方才可以懂得古人学说的真意义。
例如读董仲舒的《对策》,须先看汉武帝策问的题目是什么。武帝问的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
董仲舒借着这个机会便发挥他的《春秋》之学,说“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的道理。一个“畏”字,很写得出他捧出“天”来吓倒那迷信的皇帝的心理。
所以我说这种学说的发生,依历史的眼光看来,是很可原谅的。至于这种学说内容的价值,那另是一个问题,又当别论了。
五、六科十指
董仲舒研究《春秋》,归纳得“六科十指”的义例。“六科”见于《繁露》的《正贯篇》(第十一),但原文的文字太糊涂了,旧注家如凌曙、苏舆都不敢指定六科是些什么。我也分不出来,所以也不敢胡说。“十指”见于《十指篇》(第十二),原文如下: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
(一)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
(二)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
(三)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
(四)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
(五)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
(六)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
(七)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
(八)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
(九)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
(十)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