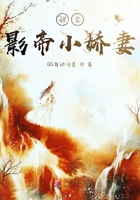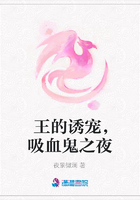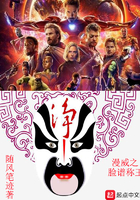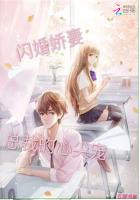问题一:“历史还原”与文学史写作的主体意识
现在我们关于文学史写作的讨论当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强化写作者的主体意识,同时又如何理解同样呼声很高的所谓“历史还原”的问题。显而易见,近20年来,如果说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在“拨乱反正”之中还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么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归功于研究者、写作者的主体意识的复苏、自觉与强化,没有对于自我思想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就不会有“重写文学史”的可能性。迄今为止的几次文学史的新成果的推出都可以归结到一种研究者、写作者的思想观念的跃迁。但是,值得注意的还在于,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学术规范化”思潮的出现,更多的对于历史“还原”的要求也出现了,而且显然这种还原的呼声也是基于对那一段不堪回首的“以论代史”的记忆的反拨,也就是说它同样是富有革命性的一种文学史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样两种追求之间的关系,因为,前者分明在强凋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意义,而后者恰恰要求了我们的客观姿态。
我认为对于文学史的理解就像我们对于历史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一样,需要弄清楚的是可不叮能存在一个绝对的“客观”,我们进入文学史的时候能不能真正排除掉我们先前的知识背景与审美趣味?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不仅我们面对的文学史现象在等待着我们的立于特定立场的清理与批评,就是对于貌似客观的材料的选择与处理当中也无不反映着我们的思想与特定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应当清醒地看到强调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主体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必然的。那么“还原”又当作何理解呢?我认为所谓的“还原”在这个意义上决不意味着那种字面上的绝对的客观,那种不搀杂着研究者、写作者个体思想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我倾向于这样来理解“还原”:这是一种基于特定思想立场的对于客观对象自身完整性的尽可能的包容与呈现——相对于在文学史研究不断发展的“先前”的立场而言,我们新的研究与叙述应当对于更多更丰富的文学史现象加以说明,也就是说,不断出现的新的文学史写作不应当是对于对象的进一步的简化与省略,而是更加完整地显现了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还原”指的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无限发展着的目标与愿望,而且总是于先前的研究与写作的比较的意义上,我们才有资格称自己的努力是在更加的“还原”,同时我们却决不可能宣布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是“已经”彻底地还原了历史。就这样,我们的努力必须得依靠我们自己的新的思想立场,我们不应当在“还原”的需要中放弃了自我,放弃了我们作为研究者与写作者的主体性,我们只能完成这种“主观”中的“客观”;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和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写作者、我们以后时代的人们也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着他们各自的历史“还原”,他们同样拥有这个权力,拥有这个学术的可能性。
这样的“还原”的主观努力当然就与那种“以论代史”的思路绝然有别了——其实“以论代史”的可怕并不在于它有了什么“论”,而在于那个年代当中只容许这样一种“论”,它拒绝了其他“论”的产生!就每一种主观的“还原”而言,它必然是充满了偏执与片面的,是一种并不那么还原的“还原”,但只要我们清醒地承认了这种还原的特定意义,那么无数“还原”的共同存在和彼此抵牾恰恰就造就了一个整体上的历史的“还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应当保持的健康的语境与心态。
问题二:文化反思时代的文体学研究
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文化”的时代,也就是说,从大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的问题显然已经蔚然成风。这一演变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杰姆逊在中国演讲的结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只是在思想启蒙和集中批判“庸俗社会学”理论的当时,这样的“文化理论”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了最显赫的位置,杰姆逊当年的一系列表述也就格外的重要了:“我不是个美国主义者,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我可以说是个文化批评家。我讲的理论方面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文学理论,因为结构主义于五六十年代中出现的时候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从语言学发展而来,并且首先是人类学方面的理论。”中国的后现代论者在20世纪90年代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绝非如有人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文艺思潮。这种看法既不准确,又与后现代发展的事实相悖。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倾向,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由这个高度去看文艺思潮,才会有一种新的文化‘语境’,才会使其内在的精神逻辑呈现出来。”
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几成“显学”到新世纪之交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更加丰富的认知,尽管中国文学研究的灵感源泉多有变化,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也经历了一些自我的演变,但从大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却似乎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这里还不包括我们一些著名的文学研究者已然“越界”而出,在纯粹的文化研究的领域“自由”驰骋。的确,文化的“语境”就是我们近几年来反复读到的一个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人们相信文学在它的自下而上发展的环境中可以获得更好的说明,诸如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学术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学院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社群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等等课题都以其新颖别致的思路大大地开拓了既有的思维空间,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由于中国现代性文学不是单纯的诗学或美学问题,而是涉及更广泛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就需要依托着一个更大的学术框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涉及现代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几乎方方面面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而需要作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考察。”“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然而,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
我以为,这样的新的“文化反思”的思路,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真正展现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的丰富与魅力。众所周知,我们的文学批评曾经长期陷入到所谓的“社会学研究”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在上世纪80年代的“狂飙突进”时候,“社会学批评”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几乎就成了一个贬义词!其实那个时候所谓的“社会学批评”不过就是一些相当固定的政治权威概念的演绎,根本就谈不上有对于“社会文化”内容的真正的发现,批评者面对这样的“理论模式”完全是被动的,没有创造,没有激情,没有个人的体会。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的批评则真正改变了这一模式,它真正成为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学的个人的研究,而不是对某种政治概念的“应用”。可以认为,经过我们近几年来的拨乱反正,文学批评的社会文化学方式将不断展示其独特之处,并在未来获得良好的发展。
然而,今天我想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普遍强调文学的社会文化视野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文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我们的研究究竟要解决的是什么东西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关注文学的种种“背景”,但所有这些观照的实质却最终还要回到文学的本身,也就是回到文学文本的本身,文学研究最后想阐述清楚的毕竟是文学文本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一般社会文化的发展,否则就无所谓文学研究学科的独立性了。综观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态势,我以为在充分看到它的优长的同时又不得不加以认真的检讨:我们的学位论文(尤其是北京、上海一带高校的博士、硕士论文)越来越多地选择着“文学之外”的题目,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文学之外”的分析篇幅加大,而文学之内的阐述却蜻蜓点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温儒敏教授一直潜心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在2001年夏天的南京大学研讨会上,他不无忧虑地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难道我们的文学史正在为思想史所代替?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对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所回应,我们关心的“文体”问题就是一个“文学之内”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对文学的进入十分重要,因为显然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常常表现为一个“文体重建”的过程,可以说,现代文体的重建构成了我们文学的艺术性的重要内容,并且只要看一看新世纪的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诗体重建”之类的话题就可以明白这种文体的思考对于我们有多么的重要了。我们需要的学术回应在于,在今天的丰富的文学之外的知识背景上,我们的文学如何进行“现代性”的文体的重建?也就是说,我们要尝试的是在文化的变迁中认识文体的新变,用文学之外的视野打开我们的思路,但最终我们所关心的还是文学的“文体”本身。
我以为,对于文体问题的探讨这依然是一个并没有真正开展过的研究,其中许多东西应当说都是饶有趣味的,比如中国新文学的缘起与中国作家文体意识的关系、中国新文学启蒙目标与文体追求的协调性与矛盾性、中国新文学政治功利化思潮与文体建设的复杂关系,中国新文学诗体的文体特征何在?作为抒情文学它与散文的区别何在?叙事诗与叙事性散文的区别何在?剧诗的意义在哪里?中国新文学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在哪里?作为叙事性文体,小说与戏剧有何不同?中国新文学文体创造与传统文学文体模式的关系?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我们付出认真的思考。
问题三:现代性问题与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预测未来总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历史的未来并不总是按“过去”与“现在”的经验进行“合目的合规律”的逻辑运动,任何一个历史的细部与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在根本上改变未来的面貌。所以,我以为我们今天所谓的新世纪的猜想其实也仅仅只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但尚未“蔚然成风”的“现实”的描述。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以为最值得注意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需要继续关注的是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于当下的世界性学术思潮的回应,而且更有意义的在于,正是这一概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细致的分析,使得我们曾经有过的一系列模糊、含混的思想之争被置于一个更具统一性的知识背景之上,争论的双方都出现了更多的对话的机会。众所周知,在走向“现代”的文化语境中诞生发展的中国新文学,正是以其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树立自我形象的。在过去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以后随着文学史意识的生长,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维度上来认识“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涵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候,关于“现代性”我们的知识还是相当笼统和模糊的。
应当承认,中国新文学的阐释乃至中国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对于“现代性”知识体系的全面探讨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而饶有意味的又在于,这种全面探讨的契机却来自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的质疑者——中国式后现代论者“重估现代性”的呼声构成了对中国新文学价值体系的挑战。
中国“后学”的唯我独尊的姿态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那里遭到了有力的阻击,新世纪的到来也许会进一步显示这些“后学”论者骨子里的“狂躁”之气的不合时宜,我们将可能以更充分的理由来分析、回应、反驳这些后现代论者的“重估”之声,但这样的分析、回应、反驳却也有可能突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正是中国“后学”的质疑与挑战促成了我们对这一知识体系及这一知识体系观照下的文学发展本质的深入认识。显然,在以往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当“现代性”追求被我们视作中国文学理所当然的目标之时,现代性问题是与“开放”、“进步”、“走向世界”、“全球一体化”等辉煌的概念连在一起的;所谓“先进”的“现代性”的目标往往被作为落后的“民族性”的参照与对立。同样,当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论者将复杂的现代性追求一律视作西方文化东方“殖民”的结果,并以所谓“中华性”的目标对抗所谓话语霸权的“现代性”,这其中仍然体现了十分明显的“民族性”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发展与新文学阐释发展的事实就这样地一再证明着“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复杂纠结。可以这样说,只有在与民族性的复杂联系中,我们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现代性”的缘起、本质及文化根据。
我认为,进一步探询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工作者反思自己的研究对象,反思自己的学术史与工作方式的重要选择,也是我们真正有效地与“后学”的挑战相砥砺、对话的基点。
当然,我们无法简单认同后现代论者关于“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的判断,但也不能满足于长期存在的对于“现代性”的笼统认识,不能同意曾经存在的对于现代化与民族化“相互协调一致”的简单的道德性判断,我们完全可能通过这一课题,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的复杂关系进行全面的梳理。
我们的新研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近现代以来的中外文化冲撞与新文学“现代”意识的诞生
我们力图通过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追踪,展示“现代”意识产生的复杂的文化背景。这一“复杂”在于,我们既“输入”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西方近现代知识体系,同时因军事斗争的失败而从内心深处孕育了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历史事实的复杂告诉我们,不是单纯的西方知识的“输入”而是中外文化的相互冲撞,是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汇构成了新文学的“现代性”,我们对发生史的追踪将有助于更清晰地阐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深厚渊源。
2.民族性与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相互关系
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所谓世俗的现代性及审美的现代性(后者体现为对前者的批判)在中国新文学中均有明显的表现。值得注意的在于,我们中国新文学的审美的现代性往往与民族传统文化有更多的联系,即新文学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不时流露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留恋。民族性与新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值得我们仔细辨析。
3.文学现代性与文学现代主义思潮的相互关系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径。我们的工作是,清晰地说明这一路径,从而剖析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价值取向。
4.“重估现代性”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民族性”要求之关系
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估”之声中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然而,就是这一场几成“显学”的“重估”运动也有着相当复杂的文化背景。从表面上看,它固然是民族性要求上升的结果,但出自于中国后现代论者的这种“反现代”,却依然呈现出了一种“进化论”的思维模式,于是,“民族性”的追求搀和进了世俗“现代性”的因素。重新检讨这一“重估”的缘起及其阐释体系,将加深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理解,也有利于我们对新文学批评话语的认识。
我还认为,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当在保持自己的激情的同时继续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学术规范。这里的“学术规范”不是指那种回避现代人生关注的自我封闭,而是指将丰沛的人生激情潜藏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更充分的展示当中,我们需要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和分析,需要新文学发展的更广阔的“历史主义”的视野。作为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的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历史复杂性的问题,也更需要我们体现出一种“回到历史”的耐心。我想,或许在新世纪里,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进入和解答将会在一个新的基点上巩固和完善自己的学术方式和学术阵地。
自然,我们在新世纪的首要的课题也是一个难题,其难就难在“现代性”追求自身的复杂性。现代性代表着人们的时间意识,但它却又是一个腹地宽广的话语系统,各种概念、取向、观念彼此抵牾的情形时有所见,我们的研究必须对这种复杂性有足够的把握和意识,并要恰到好处地透过这些“复杂”形成的意义间隙探寻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远距离联结。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个语言的、思维的与文化的陷阱。
(以上文章分别载于《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