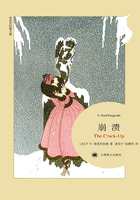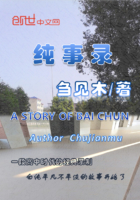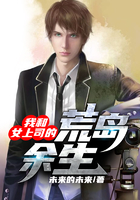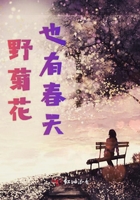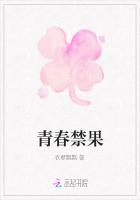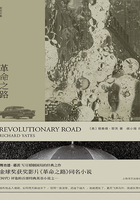中国当代思潮的流行和转移,常常是缘于一些专家学者对西方各种时髦学说的宣扬。与二十多年前无书可读的情形相比,时下的知识多得目不暇接,而且转瞬就已过时,令人感到知识的不能承受之重。知识一旦成为信息,就如同自然山水变成了旅游景点,看到的不再是风景,而是络绎于途的游人和垃圾。因此现在出了一个王小波,沉静地守着某种知识,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信念而不是资本,这使人们趋时的心感到某种清新。
王小波的力量在于他拥有一个常识的立场。
《思维的乐趣》封面渊博的学者指出他的思想来自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这也许是对的,但他的文字更像是表达了某些常识,而不是某种主义。在本质上他不是个诗人而是小说家,这可以从他不唱高调,比如不喜欢崇高或激情之类中发现。他关注的是现实生活本身,对于时下的一些理论和主张,他都把它纳入常识的范畴中来观察,这使得他的随笔具有一种简洁明白的效果。所谓常识,不过就是明白日常事理的能力,顺任自然和习俗,大至民族历史,小至个人经历,都可以拿来作思想的参照。
人类精神的成长,其实是很缓慢的,根本的东西就那么一些,例如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等等。现代人弄出许多博大精深的学说,实质上并没有给人类精神增加什么新的含量。何况先哲的言论原本也都是出自常识,只是后来由于文化的积淀,它们才变成了知识权威。所以面对复杂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学说,往往倒是平常的心智来得可靠。王小波喜欢在书中叙述许多个人故事,就因为倘若离开了寻常经验和常识的描述,任何学说都可能成为谎言。
服从常识往往能使人通情达理,因为它总是直接洞悉事物的真实。鲁迅先生说过:“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常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直接的方式,其精髓在于自然,而一个不能靠常识作出判断的人,通俗的说法是没头脑。在王小波眼里,他的姥姥是个有头脑的人,她在“大跃进”时期不相信一亩地会产三十万斤粮食,因为这不符合常识。尤其她还是一个普通人,面临没有饭吃的问题,因此她的常识中还包含着利害的成分,而懂得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懂得事理,已经没有饭吃还说形势大好,就不是承认事理,而是顺从思想。其实常识正是思想的底子,王小波明白这一点,对于应不应该抢救被洪水冲走的国家财产,他认为首先应问问值不值得,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是通情达理,也是真实不欺。
服从常识还意味着使用简洁明白的话语,让思想的表达举重若轻。朴素的语言也能说出真理,而且说得更好。这方面,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的文章总是明白易晓,与人沟通。如果一个明白的道理,却非要表达得很复杂,做出很有学识很有思想的样子,其结果往往是显得举轻若重。王小波曾谈到一个生产队长,在常识领域中他十分聪明,而且有趣,但他偏想要有思想,说点“文革”时代的时髦话语,结果很闹了些笑话。那个队长恰恰忘记了,一句蕴含着生活经验的话语也许比任何迷人的理论都更有价值。
我们曾生活在一个失去常识的年代,“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就是全民对常识的恢复,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小岗村村民的大包干,其实全都是常识。后代的人将不会明白,这样的言行当初竟然能使全民激动不已,他们更不会明白,为了这些常识中国人曾付出了几十年的苦难代价。我们的社会不缺乏理论,缺乏的是常识,像王小波姥姥那样的常识。在生活中,任何伟大的思想并不比一位老农的看法对人们更有益。如最近的报纸所透露的,50年代末的科学家们还曾奉最高指示,开展“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研课题,要将吃不完的粮食转化成有机化工原料,而当时的状况早已是哀鸿遍野了。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习惯于寻求一个关于世界的普遍性理论,用某种思想或主义来对现实进行解释,而不管生活本身是不是这样。
这里奉行的是格勒定律:如果事实和理论不一致,这事实就必须被抹去。
造成20世纪灾难的这种思维定势今天仍在延续,看不出有多少改变。许多人不明事理,却喜欢高谈思想,谈学说。比如:二十几年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对个人对国家都是悲剧,一代人的读书、工作和婚姻都被耽搁了,如今他们中大多数人又面临着下岗,承受着家庭生活的重负。但有些人却以一种精神被虐狂的心理宣称“青春无悔”。据说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然而,什么时候黄土高原变成了鲜花盛开的原野?无望的生活变成了田园牧歌?辩证的理论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人们痛苦的经历?
对于当前的集体腐败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一面是有人在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资产,一面是让严肃的思考脱离现实的轨道,而无论是理论界提倡给改革引入人文关怀,还是认为腐败是由于过去制度难以为继的体现,其实都是言不及义,因为它们都没有指出权力体制导致腐败的作用。从本质上讲,正是由于造成过去灾难的那种权力关系仍然在起着作用,在权力制约方面并没有质的改变,腐败才得以大量产生,如果要追根溯源,那么,具有当代特征的腐败其实从“文革”后期利用权力关系“走后门”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稍有一点常识和记忆就可以弄明白的。但许多人不能明白,很多事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要让判断停留在常识中就行了,如果不具备真诚与思考的素质,追求理论的结果往往会败坏人们的正常理解力。
思想出于持续的恐惧,这是20世纪人类经验的核心。在王小波的思想背景中总有着过去年代的威胁。他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他对事物的理解,大多也是源于那个年代,告诉人们不要相信什么,而不是像有些人总喜欢叫人们相信什么,所以他的常识是一种“反思的常识”。他所反对的都是过去几十年的东西,以及从过去延续下来的那部分现在。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所反对的物欲横流,他并不特别关注,他关注的是过去年代幽灵的复活,那些试图改造人。
王小波像们思想的倾向,还有信仰的滥用,比如90年代中期的“重建精神家园”、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等等。的确,与过去的“突出政治”、“反帝反修”相比,当代的精神迷恋实难说取得了多少历史进步。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后,仍然有人对全民的一统世界观感兴趣,这恰好说明,只要过去的许多事情没有说清楚,没有得出一个常识性的结论,任何历史就都是当代史。
这似乎是80年代启蒙的主题,其实正是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基本问题,不应该越过这个基本问题去探讨理论,否则就是对着风车挥舞旗帜。非洲饥民、前南地区、高加索当然是人类的悲剧,西方社会物质主义的危机我们也从小就被告知,但这些都不是属于相同社会的同一层次的问题,人们无法对某一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保持恒久的关心,这是人的能力所限。且不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对西方社会的缺乏常识(如认为他们不重视家庭生活)一如西方知识分子曾经对我们的看法缺乏常识一样(如有的西方学者就曾把我们的自我批评看成是一个美好社会纯洁心灵的体现),但西方知识分子毕竟是出于对自身境遇的反抗,可我们则是为了什么?说到底,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才更加迫切,倒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然而,在每天大量制造的文字中,我们却绝口不提那些真正的问题,以及问题的真正原因。这些问题,即使没有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的写作,也早已是人们私下谈论的常识了。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南非作家戈迪默所说的那种“基本姿态”,即真实面对自己生存的境遇,并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将它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终极目的的关怀掩盖不住他们对基本问题的逃避。人们目力所及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文章,操着同一种言说方式,例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及一大堆时髦空洞的词语——荒诞、焦虑、忧患、颠覆、建构、预设等等。90年代以来,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新的报刊文章腔,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些二三流中外教授学者制造的各种理论流派,满心以为那些貌似高深的概念中包含了比千百年的常识更多的真理。这种现象可以称作一种“大词崇拜”,拼命转弄着概念的魔方,可就是不通情达理,与现实相去甚远。读这样的文章,你会觉得它们全都是在举轻若重,就像王小波喜欢引用的那则拉封丹寓言所说,大山临盆,天崩地裂,生出的是一只耗子。把它们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18世纪孟德斯鸠论亚洲的一句话:“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
积久会成习,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方法的学习,好像就只学会了“人类的眼光”,却没有学会多少常识的眼光。而一个民族正是靠着常识生活过来的。鲁迅先生30年代在上海,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当代文化思想界的热闹背后,其实是荒芜,从写身边琐事的散文到谈论各种思想的学术随笔,正是鲁迅所说的“身边”和“天边”的文字。这样的枝头上显然是结不出任何果子的,只有那些注意“两者之间的一圈”的人,才有可能接近真理的地界。
一般来说,常识或经验的东西被认为表现了心灵的局限,不能达到深刻的境界,但几十年来更沉重的教训却是,做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易,而承认眼见的事实,做一个明白人则更难。直接的经验常识往往可以戳穿谎言,照亮被思想蒙蔽的心灵。1975年夏天,我在川东一个县城实习,那时候正在开展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广播里终日宣传着革命的大好形势,对现状我虽不十分认真,但也谈不上怀疑,出于多年来思想培养的潜在影响,我完全可以自我安慰,也许每天看到的现象并不是本质和主流。相比之下,我当时倒是更喜欢跟朋友讨论那些世界大事。我们的政治老师平时是个风趣的人,有天晚上我们去郊外散步,经过一处破败的农舍,看见几个筋骨毕现的老人躺在门板上纳凉,像牲口一样喘息,那个政治老师忽然冒出一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哪!”说完他就沉默了。这句话当时对我的震动是难以形容的,它不过道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改变了我对整个社会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从此学会了常识的立场。
“分子”与人
这些年,不时有人撰文谈到“分子”一词。现代生活中,指称人的“分子”(曾又作“份子”)是一个常用语词。几乎所有作者都曾指出,在意识形态渗透的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思维中,“分子”一词是带有贬义的。这一结论缘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创伤记忆。有人甚至说:“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凄苦的过程。读懂‘人’变‘分子’的过程,就会很容易读懂中国现代社会史。”①这话很深刻。不过,尽管“分子”一词在我们的生活中关系匪小,但对于这个词,仍有许多问题不甚了了,值得我们作一番知识的考古,去发现它在不同历史断层中隐蔽的结构。此无他,目的仍然是为了通过这个话语,真正读懂中国的现代史。
①尘元:《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万象》第1卷第5期,2001年。
“分子”是一个多义词。1999年版《辞海》于“分子”词条下列有五个义项:①分出的子孙。《穀梁传·庄公三十年》:“燕,赵之分子也。”范宁注:“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②亦作“份子”。集资送礼时每人分摊的一份。《牡丹亭·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分子,起了个生祠。”③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如知识分子、积极分子。④物质中能够独立存在并保持该物质一切化学特性的最小微粒。⑤见“分数”。
从组词结构来看,第一义项的“分子”虽然在春秋时就已经出现,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词组,与第三义项即指称人的单词“分子”音义都有别,所以二者应属不同的词语。第二义项产生时代较晚,却也是古已有之,如宋赵彦卫《云麓漫钞》:“随州有后汉修《义井记》,悉列出钱人姓名,云五大夫某郡某钱若干,凡六七十人,下列分子,某郡县若干”,即是一例。这一义项虽与第三义项同音,但二者并不存在词义上的联系,所以也可以说属于不同的词。在“分子”的五个义项中,只有第四义项与第三义项之间存在着引申或假借关系。
“分子”指称人,乃是现代才出现的词义。检索19世纪的中文各类语篇,尚未发现有人如此使用。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近年对19世纪汉语外来词的研究也表明,1900年以前,日译化学名词“分子”尚未被国人所借用,更不用说由此转喻而来的指称人的“分子”一词。见其《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附录二《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年。故从词汇学的角度讲,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新词。最早使用这个新词的大概是梁启超。梁氏于1898年8月避难日本,并于1900年2月20日在《清议报》发表《呵旁观者文》一文,其中写道:“夫我虽愚不肖,然既为人矣,即为人类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国矣,即为国民之一阿屯也(‘阿屯’是英文‘原子’的音译)。我暴弃己之一身,犹可言也,污蔑人类之资格,灭损国民之体面,不可言也。”由此可知,“分子”一词的出现,至早当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
此后梁启超在文章中还曾多次使用此词,如《敬告当道者》(1902):“吾国民一分子也,凡国民皆有监督其公仆之权利,吾不敢放弃此权利”;《新民议·禁早婚议》(1902):“彼实国民一分子,而为一国之将来主人翁也”;《社会主义论序》(1907):“凡员颅方趾以生于今日者,皆以国家一分子之资格,而兼有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者也。惟其有国家一分子之资格,故不可不研求国家之性质,与夫本国之情状,而思对于国家以有所自尽;惟其有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故不可不研求世界之大问题及其大势之所趋向,而思所以应之”;《政闻社宣言书》(1907):“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愿凡为国民之一分子者,咸认此责任而共勉焉”以上梁氏文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