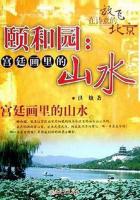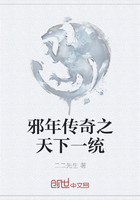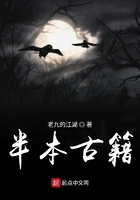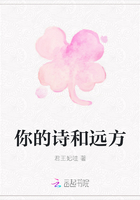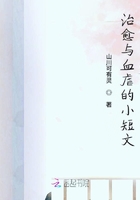1720年,在《感想录》里,鲁滨逊似乎更关心中国人的灵魂,因而集中攻击了中国的迷信。在继续骂遍所有的中国政治、法制、艺术、技术、航海和海军等等之后,还特别谈到了两点,一是孔子的学说;二是中国的宗教。对于前者,谈的不太多,只是说在那里政治、道德和迷信纠缠在一起,既不一贯,也无多少道理。至于宗教,笛福说:“我所注意的,不在乎他们在艺术上的技巧,而在乎他们在宗教事体里所表示的愚蠢和可笑可鄙的冥顽;我竟以为最蒙昧的野人,也比他们略胜一筹了。”这种刻薄的谩骂式批评,在当时欧洲颇不多见,难怪当年林纾先生译到这里,愤怒之极,差一点连译稿带原书一起撕了。
笛福不同意李明神父在《中国现状新志》中提出的中国的自然神教观。笛福的见解是:“然而,如果我们说到中国人,被人们誉为天赋伟大的中国人,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深陷于偶像崇拜的污泥中无法自拔。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狰狞可怕,形态怪诞,面无耳目,既不能行走、站立、飞翔,也不能视听、言说。这些丑陋狰狞的偶像的唯一作用,就是将一大堆乌七八糟,可怕而又可恶的观念装到偶像崇拜者愚蠢的脑子里。”
因此,笛福说,中国的宗教是最野蛮的。中国人在一个怪物的偶像前面弯腰致敬,而那个偶像一点也不可爱,一点也不和善,而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而在这样一个野蛮和未开化的国家传播基督教,势必难以给传教带来什么荣誉。笛福在《漂流记》第二部里就讲到鲁滨逊遇到了三位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为了使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已经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但在鲁滨逊看来,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糟糕,而即使他们使人家改信了,也只不过造就了一些糟糕的基督徒。尽管他们所谓的使中国人改宗基督教一事,同真正使异教徒信仰基督教的要求相去甚远,看来结果充其量也不过是让人家知道了救世主基督之名字,让人家以他们不懂的语言对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祈祷几句,并在胸前划划十字而已。
笛福还有一本题为《魔鬼的政治史》的书里,也谈到了宗教方面的一些问题。他在书中把那些颂扬中国的耶稣会士都看成了魔鬼的同伙,并详细论及了耶稣会士是如何千方百计地企图控制中国和日本的。书中提到了基督教在日本遭到了被魔鬼和枪弹哄赶出境的厄运。耶稣会在日本通过统治阶级所做的努力,一开始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后来天皇于1564年下诏驱逐耶稣会士,1587年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再次命令所有耶稣会士都必须迅速离境。后来为了扼杀基督教及其他原因,日本实行了长达两百年的锁国政策。中国则不同,它没有像日本那样把基督教徒赶出去。
笛福说:“然而,勤恳刻苦的耶稣会教士们似乎比‘中国的魔鬼’智高一筹;由于他们的使命面临失败的危险,他们很可能会像在日本一样被‘中国的魔鬼’和皇帝驱逐出境,所以,他们狡猾地同当地的那些教士妥协,融汇了两种宗教的谋略,使耶稣基督与孔子协调一致,让人觉得中国人与罗马的偶像崇拜似乎能够结合在一起,而且并行不悖,中国人和罗马人最终将成为很好的伙伴。”耶稣会教士的用意在于削弱孔子思想在异教(指儒教)中所占的分量,更多的灌输基督教教义,他们“认为与其抛弃异教,还不如把对基督教的信仰与孔子哲学或教义混合起来,并以宗教的名义正式将它基督教化。这样一来,耶稣会的政治利益就得到了维护,同时撒旦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因为传播福音而失去一寸土地。”
回顾一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可以发现,早期天主教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要“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用西方的上帝来“开导这个半开化的异教国家”,来征讨这个“自古以来被魔鬼占领的在地球上最顽固的堡垒”。但后来才发觉如果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利用儒家经典并作出一些妥协,才能对中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进行突破。于是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主张合儒、补儒,主张调和儒家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甚至主张允许中国信徒祭祖祀孔。这里,笛福的意思是,如果中国人接受的不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大杂烩式的宗教,而是一个宣讲得更好、更为纯正的基督教的话,那么,中国人在他们心灵受到纯化后,就很有可能把心中的魔鬼驱逐出去。
笛福中国文化观的形成
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笛福从未到过中国,为何对中国的评价如此毫不留情,如此极端?陈受颐先生在《鲁滨逊的中国文化观》一文里也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笛福对中国文化的攻击和鄙夷,是他自己的思想和性情的表征,不是受任何人的驱使,或任何人的暗示。第二,笛福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自1705年发刊《凝想录》起至写《漂流记续编》之时,十五年间,未尝变迁;先后言论,也无根本上的矛盾与冲突。第三,他不止参考某一种书籍,而是每种之中,都有选用,都以他的成见为取舍的标准。第四,他对中国表现不满,也并非偶然,这可以从他的宗教信仰、爱国热情、商业兴趣,和报章文体诸方面作些了解。
陈受颐先生的解释和结论应该是颇有道理的,我们由此作为出发点,做些分析阐释。
先说宗教信仰。笛福的父亲是个小屠户和蜡烛商,信奉反对英国国教的长老会。受其家庭出身和宗教信仰的影响,笛福反对英国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更是格格不入,而耶稣会士天主教会的一支。他虽在斯图亚特复辟后英国国教会整肃不同宗教教派的环境里长大,却成为一个典型的反国教会的清教徒作家。有种说法是他曾参加以新教为主体的蒙茅斯公爵的叛乱。英国国教是16世纪上半期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时确立的,后来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和支柱。16世纪60年代,加尔文教传入英国,后称“清教”,很快受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以及下层民众的拥护。清教宣扬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上帝赋予选民的神圣使命,只有那些发财致富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这便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工商业的要求。笛福正是如此。
笛福又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以英国为荣,并攻击外国(尤其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在他的小说里(如《辛格顿船长》)随处可见。《鲁滨孙漂流记续编》也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西班牙人说他遇到的各种人里面,英国人在危难中最为沉着冷静,而他们这个倒霉的民族与葡萄牙人则相反,在同不幸的命运作斗争时,世界上就数他们的表现最差;因为他们一碰上危险,略略作了些挣扎之后,接着便是绝望,便是在绝望中躺下等死,根本就不会振作精神,想出逃脱困境的好办法。
鲁滨逊听到这些好听的话,还谦虚了一番,说他做的事,另一个人在同样情况下也是能够做到的,这倒引得西班牙人继续说到:“先生,在你那处境里,换了我们不争气的西班牙人,那么我们从那船上弄下来的东西绝不会有你弄到的一半;不仅如此,我们根本还不会想办法来扎个筏子把它驾到岸边的;更不要说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我们还能做点什么了!”这一些话,英国人当然会觉得中听。
笛福还是一个商人,因而看待任何事物均完全采取商人的尺度。他之所以崇奉军事力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认为海军、陆军有护商的能力,进而以军队的强弱为评价文化的标准。
我们知道笛福生活的时代正是洛克为私有财产正名,追求财富已躁动于全社会的时代。笛福在这个时代身体力行,渴求富足,投身于当时最赚钱的行业——对外贸易。不仅如此,他更把推崇商业,宣传商业作为毕生的己任,他的《评论报》(1704~1713)、《商业报》(1713~1714)明确地充当商业利益的喉舌。他还写过《贸易通史》、《英国商绅大全》、《英国商业方略》等著作。他对商人的赞扬同样无以复加:“如果说在任何行业中只有勤劳才能得到成功,那么在商业界,恐怕这样说才更确切:比起任何人来,商人更加依靠智慧生活。”他认为商人是“世界上最聪敏的人,因而在迫于无奈不得不另想生活门路的时候也是最能干的人;依照愚见,本书在讨论的题材中所涉及的种种计划都是从这种人中来的。在这种人身上很容易追溯出他们的本行是银行,股票,股票买卖,保险,互助会,彩票等等。”他把不辞艰险在全世界经商、不择手段谋取利润、不惜以殖民手段进行掠夺的远洋商人奉为英雄,而鲁滨逊正是他理想中的典型人物。
总之,笛福是商业时代的鼓吹者。在《续编》中他攻击中国文明,但对中国的一些物产表现出了商人的兴趣。鲁滨逊去南京湾的目的是卖掉船上的货,买进一些中国瓷器、白棉布、生丝、茶叶、丝织品等等,或者到澳门,把自己的鸦片卖到一个满意的价钱,然后用这钱买各种中国货。……当他们要离开中国时,(去了南京)买了九十匹锦缎和二百来匹各种上好的丝绸,其中有些还是绣金的,并把这些货物运回北京;除此以外,还买了数量十分庞大的生丝和其他货物,单是这些货物就值到三千五百镑左右;另外还有茶叶和一些细布,加上三只骆驼驮的肉豆蔻和丁香,总共有十八头骆驼驮的货物,浩浩荡荡,离开北京,然后出关,进入俄罗斯帝国,取道阿尔汉格尔回国。而那些中国香料,一部分就在阿尔汉格尔销售,没有带回英国,只是因为“那里货价要比伦敦高得多。”
笛福认为英国如果“没有商业就不能维持下去,好比教堂没有宗教就不能维持下去一样。”“我们(指英国人)是一个做买卖的民族,我们的事务是经商,我们的目的是赚钱,商业上除了利润而外是没有什么兴趣可言的。我们同土耳其人、信仰邪教的人、信仰偶像的人、不信仰犹太教的人、信仰异教的人以及草昧未开的野蛮人打交道、做生意,只要能达到目的,只要对买卖有利,可以不管他们崇拜什么上帝。商业上崇拜的唯一偶像是赚钱。在商人看来,只要有利可图,不管同什么交易,都能一样的。”
最后,笛福还是个“报章家”,并享有“现代新闻之父”的美誉,明白如何去渲染他的文字,怎样用似是而非的言论,知道故意与人相违反博取注意。1700年,40岁的笛福当上了一名记者,后来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稿件,他又是个绝妙的政治鼓动家,而在讽刺方面,又有拿手好戏。
这样一来,中国既然是不奉新教而又祀天祭祖,虽然名声洋溢,在书卷的记载上几乎要压倒英伦,但从使臣和商人的记载看又无强健的军备,而且商舶从未到过欧洲,那些传闻又少人确见,凡此种种,无不与笛福持有的文化观念方枘难合,这就难怪他对中国无甚好感了。
4.另一类声音难免刺耳——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嘲讽与批评
17至18世纪,随着来华耶稣会士各种报道在欧洲的风行,一个中国文明之邦呈现在西人面前,进而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想的天堂。相对而言,英国的情况有别于欧陆,尽管也有坦普尔、勃顿、韦伯、布朗等人对中国的颂扬,但影响更大的却是那些无处不在的贬抑之词。这方面我们已经领教过笛福的言论,他那种对中国文明不折不扣的批评态度当然也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在此我们又将再次听到这另一类声音,尽管有些刺耳,却无需回避,或许还会发人深省。
简单推论中的中国典章学术?
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一个牧师的声音,他叫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1666~1722)少时以多通外国语和博览群书著名。17世纪末年,英国学术界有一场关于古今作品孰优孰劣的争论。论争的一方是威廉·坦普尔,另一方的代表则是沃顿。本书前面已经提到,坦普尔在这一问题上是坚定地站在古代学术一边的。他于1692年发表文章《讨论古今的学术》,推崇古代作品《伊索寓言》和伯伊尔编注(Charles Boyle,1676~1731)的《法拉利斯书简》(Epistles of Phalaris)——这后一本书系后人伪托,坦普尔当时并不知晓,认为这两本古代作品远非近代作品所能企及。这种看法引起了沃顿等人的批评,他们主张近代学术比古代的优越。沃顿在他的《关于古今学术的感想》(1695)里,深叹欧人不谙中国实情,而徒信传闻。他评论的材料来源主要是耶稣会士卫匡国、柏应理、金尼阁等人的著作,但他对于这些传教士赞叹中国文明的言词显然无法赞同。比如,他根据传教士们关于满洲人入关取代大明王朝的记载,而以为中国的学术文物,都是非常幼稚的。他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满洲人能统治中国,自然是几年之间便已经深晓中国的典章制度,而一国的典章制度,如此简单,则其文化程度,想必也就非常幼稚了。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推论同样不免武断简单。
沃顿以为坦普尔的言论,是根据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us)的《中国史》。于是他在论争过程中就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略,引用卫匡国的一段言词加以批判,并证明中国学术之徒具虚名:“卫匡国曾告诉他的读者,他自己先要认识六万个中国字才能比较容易地读中国书。这不要有什么疑惑——这一定是传扬学术的顶好方法。一个人将一生中最好的八年或十年,花费在‘认字’里头,‘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
汉字难学,费时甚多,对西方人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共识”。利玛窦就说过没有哪一种语言能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精通的,中国语言使用一个确定的符号来表示每一桩个别事物这种书写方式使记忆不堪重负,甚至连现代的英国学者威尔斯也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失去世界领先地位,是因为中国人的头脑被禁锢在一种那么复杂、那么困难的文字和思维成语中,使得这个国家的精神活力大量消耗在语文学习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