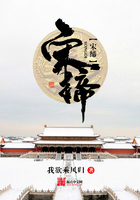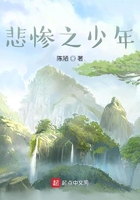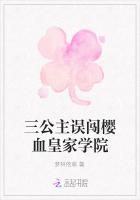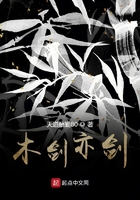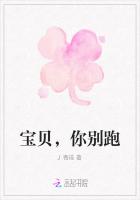万瑞祥
我家住在蓝淀厂“万瑞祥”的那段时间,是很有趣的日子,多年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田园式的生活,总会有一些淡淡惆怅和遥远的往事萦绕在心头。
“万瑞祥”位于蓝淀厂“西岔儿”的西北面。
“万瑞祥”,是过去的一家“銮仪铺”,在蓝淀厂一带属于最有实力的一家。
“万瑞祥”过去又被人叫成“轿子铺”,在旧社会,其经营业务是对外出租婚丧嫁娶的用品,此外,还有一些仿冒官场所用的“銮驾”,在前清衰落以后,出租给一般平民,满足老百姓的虚荣心。
解放后,“万瑞祥”基本上业务瘫痪,只有几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一片巨阔的院产。
原先它的前面是一条“御路”,有一座很大的花岗石桥,通往西边儿的“老营房”。
“老营房”,是相对于火器营而说的,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属于“圆明园护军八旗”,可令人费解的是,这座“老营房”离圆明园并不近。
据老人们讲,那会儿皇上到这一带“巡幸”,前一天就得让老百姓“黄土垫道,清水泼街”。
因此可知,上面所说的“御路”,就是当年玄烨巡幸这一带时走的路线。
四十年前,这一带风景非常清幽,四野有潺潺的清流,古意盎然的老树和广阔的田野,而“万瑞祥”的南面和东面是几泓清碧的池塘,池塘的岸边有依风飘拂的垂柳,夏天很多小孩在池塘里嬉水。
所有的溪流都有碧绿如发的水草,鱼虾随处成阵,水色澄碧,一清见底。
“万瑞祥”就处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中。
“万瑞祥”的前院是一座地形较高的院落,院里有一排砖砌的花坛,里面栽种着各色玫瑰。
进“万瑞祥”的正厅,光线非常之暗,黝暗的空间压抑而沉闷,环顾四周,只见许多仪仗用品密密麻麻的杈在一起,有伞盖、大扇、明角灯、宫灯、大喇嘛号、水火棍、木制兵器……简直是铺天盖地,只给人留了极狭小的行走空间。
大厅里弥漫着一种神秘而令人窒息的老木头味儿,更使人毛骨竦然的是许多画在法器上的老画儿,上面妖魔鬼怪的形象十分恐怖。
有个人称“四老头子”的老者每天看守这个大厅,他瘦小精干,笑不离口,但少言寡语。
另外还有l两位老者,人们分别称他们“二老头子”和“七老头子”。
这三个老者可能是兄弟三人。
“四老头子”一头白发,留一撮稀稀拉拉的小山羊胡,脸上永远凝固着一种不变的笑容,走路时一路小颠,目不斜视,一付城府很深,老谋深算的样子。
他有个不太雅的习惯——时不时的吐口水,精确点说,他是把口水从两片紧缩的嘴唇中“滋”的一下射出去,这使我非常惋惜,因为这个不雅的习惯大大破坏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他似乎精于占卜,时时有些农人来此卜卦。
一次,似乎是想知道考试结果吧,我也来他这儿算过一卦。
他占卜的方法很简单——从一只罐子里摸出一个小黄纸卷,然后按上面的数字查一本发黄了的书。
“不赖不赖,是上上簽,好好。嗯,不赖……”他用尖细的嗓子说着,然后“吱”的一声,突然朝墙角射出一股唾沫。
他住的是东面几间高大的厅堂,有很宽大的方格木窗,阳光从已经陈旧的玻璃上费力的透进来,再加上可能他经常偷偷的烧香,这就使整个屋子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旧时代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所有的玻璃上都被他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毛笔字,也不知道这些字的内容是什么。
通常,他每天的事就是毫无声响的坐在那间屋子里发楞,“吱吱”的吐唾沫,到了饭点,他就带着一种凝固的微笑,颠颠儿的回老营房老宅子里去吃饭,下午亦如此,晚上,就他一人住在这充满神秘的厅堂里,守着那些曾为他们赚了大钱的,可眼下过了时的古怪玩意儿。
我们家看中了万瑞祥的另一座很大的后院而把它租了下来。
这个院子位于火器营营墙的西南角上,面朝东,正对着火器营的老壕沟。
院子分为两进,外院是个杂院,住着三户人家,一家是个姓桂的铁匠,家里有两个孩子和老婆。
桂铁匠整天乒里乓啷的敲锅底壶底,可是人很诙谐,经常对我做怪样,逗我笑。
另一家姓潘,一个老太婆带着三个女儿过日子,她们是江苏人,大女儿潘明华在附近一个小学校教书,养活全家。
听说潘老太的丈夫解放前是国民某党部的官儿,前几年被“镇压”了。
潘老太的一家在附近很惹眼,原因大概是出自她名叫“西华”的二女儿,此女时年十七八岁,无论是身段和长像都很出众,一些青年男人经常借故往她家跑,她正值青春,也很自命不凡,每当外出,必一路香风的招摇过市,引来无数觊觎的目光。
大女二潘明华人称“二百五”,是个女人中的“怯不吝”,平时身着男式衣裤,走路大步量,剪一个小子头,再加上她戴着一付上千度的近视眼镜,所以二十多了,她还是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另两个小女儿年纪尚小,名叫冬华和北华,北华是个很胆怯的小女孩儿,留个娃娃头,老是一付迷迷糊糊的神情,她另有一个小名——小不点。
冬华比她大些,但可能由于家里的不幸,也总是有一种隐约的忧郁神情。
潘老太倒是个乐观的女人。她一口大嗓门儿,唠唠叨叨的说着一口浓重的江北话,很有闲心的谈论着张家长李家短。
或许是因为那动荡的年代罢,人们几乎看不出她家里刚刚发生过的悲剧。
西华常和她妈吵嘴,但我很听不懂她们的江北话,每当吵到最激烈的时候,西华就会一边叫一边跑出去。
“有本事你就别回来!”潘老太蓬着一头白发,在屋檐下用江北话叽哩咕噜的嚷着。
可西华往往是没多长时间又悄悄的蹩回家里来。
“你还会来呀。”潘老太择着菜头也不回的说。
“我不回来你高兴了是不是?狠心老太婆!”西华用很冲的淮南话还嘴,冲我们偷偷的霎眼。
“锅里有饭,炒一炒吃,吃冷的肚子疼哦。”潘老太择着菜头也不回的说。
“疼死了你好开心哦。”西华大口吃着冷饭说。
“疼死了你我烧高香叩头,好了吧,没良心的……”潘老太佯怒的丢了一把菜根过去……
其实她们也并非是天天吵嘴,有时候也老老小小抱在一起打打闹闹,旁若无人。
依我妈看来,这就是典型的“二百五”之家了。
然而,这个“二百五的女儿国”就这样在吵闹中和嘻闹中平淡的生活着。
总的看来,她们没有烦恼。
另一个住户是个人称“李同志”的独身男人,消瘦之极,满脸的斑痕好象是烧伤的,他好像是在蓝淀厂精神病院上班,平日少言寡语,可我怎么看也觉得他自己也有点神经病似的。
“李同志”门窗一向是紧闭的,他在屋里时一点响声也没有,我经常想,他到底吃不吃饭?如果是和我们一样,为什么见不到他做饭呢?
一件突发的事儿使我再也不敢研究他了。
一天,我在他的门外捉蟋蟀,偶然在他门外一小堆废铁里发现了一具好象是枪板机的铁零件,就把它拿给爸爸,想让他帮我做个木手枪。
“哪儿拿来的?!”爸爸看了看,严厉而小声的问我。
“就在‘李同志’的门口啊。”我胆怯的说。
“马上放回去!”爸爸小声说。
我立刻把那危险的玩意儿放回了原处。
今天回忆起来,我无法确定当年这令爸爸忧虑和恐惧的铁玩意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其中肯定隐藏着一些秘密。
后来,那位沉默寡言的“李同志”不见了踪影,几个警察进了他屋,呆了好半天,走了。
……
靠近我们里院大门的那个铁匠叫桂义,也就有二三十岁,是个很“矬”的男人,胳膊、腿都看起来非常短似的。
他穿着很一般,都是那种老式的衣服,可留着一头“******式”的发型。
细说起来,他的这头“******式”发型可能并非是去“剃头棚儿”特意修饰出来的,而是每天用手捋成的。
一张并不太衰老的脸和“五短”身材再加上一头“毛式”的发型使他显得很好笑。
他的住处兼有营业和居住的双重功能,他老婆是一位梳着短发、极善良朴实的女子,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
桂义从早就开始乒乒乓乓的敲打铁皮、换“钢种”*锅底和制修煤球炉子之类,活路还不算少。
*钢种:五十年前北京人对于‘铝’的叫法
他住的屋子很黑,有一股很呛的焊锡味儿。
我经常蹲在旁边看他敲打铁皮,他虽不和我说话,但常常出怪样,对我做很多可笑的动作,比方:他用两片嘴唇做出像水滴在水缸里的声音,还用四个手指像弹琵琶一样在嘴唇上做出一种酷似琴声的效果来。
在我的印象里,他从不说话,就是不停的敲、打,直到天黑。
可一次剧烈的场面使我不敢再去看他了。
一次放学之后,我看见他家的两个孩子缩在墙角发着楞,又听见他家里发出怒吼和女人的哭声,忽然我看见桂义哭着端着一只大绿瓷盆走到屋门口,猛的把它砸向自己的脑门儿,那瓷盆“咣啷”一声碰个粉碎,一大团和好的玉米面撒得满地都是
……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撒腿就跑。
……
以后,有好长时间,我都没到这个打铁屋去。
半年以后。
一次妈妈带我到厂西门小学“老刘老师”家去拜访,我在他家看到一只精巧的小轮船,只要点着上面的一个小油灯,船就可以“咯咯咯”的在水面上走,这使我着了迷,一路上缠着妈妈也要这样一只船,尽管妈妈百般解释,说人家这只船是十几年前的日本货,现在已经买不着了,可我还是要个没完。
几天以后,一次我下学的时候,桂义对我神秘的吹口哨,示意我过去。
我想了想,走了过去。
他笑了笑,从背后拿出一样东西。
一只白铁皮做的小轮船,桅杆船仓都有,连那小小的舵轮都做得唯妙唯肖!
我高兴极了!
“这个我很喜欢,可我没钱哪?贵吗?”我问他。
“不要钱,拿去吧,别让你妈为难了啊。”我终于听到他开口了。
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嗄哑,不太好听。
我高兴极了,抓起小轮船就跑回了家。
妈妈见到了我拿回的小船没说什么,就说了一句“你想着两天就把它弄坏了啊。”
过了会儿,妈妈到外院去了。
远远的我听见妈妈在外院热情的说着什么,还听见桂义用嗄哑的嗓音说“嗨,这有什么呀,就点边角料,您缺什么就言语声儿……”。
后来我才知道,桂义做这只小船用了好几个晚上。
妈妈给他钱,但他死活不接。
我家住里院。
这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子,有七间西房,都是连通的,这就为我增加了乐趣,可以一路呼啸的从第一间跑到第七间房子。
大院里紧西头有一座用巨大青条石砌成的井栏,安装着一具古老的“栌轳把”,可以汲水,但在我的印象里,很少有人用过它,这座古老的石井深不可测,里面长满了墨绿色的青苔和附在井壁上的灌木,妈妈严禁我们到那里去玩儿。
不知怎地,我总想着这个阴沉的井里会潜生着一条巨大的蟒蛇……
院子的西北角有几株梨树,春天,满树娇艳的白梨花非常好看,树下是一片长着各色野花的天然草坪,我和弟弟经常在上面打滚儿。
爸妈对这个大院似乎很满意,觉得可以愉快的过上田园日子了。
他们雇了东冉村一个年青农妇做保姆,为我们做饭。
夏天,由于住的是西房,“西晒”很厉害,妈妈就向一家编席的定做了一批苇帘子,那帘子装配得很讲究,上面还配有一些仿玉的料环子,可以任意拉上拉下,夏日下午当阳光肆虐时,姥爷就把它放下来,屋里顿时阴凉宜人,加上一拉溜的七间房都是连通的,所以屋里凉风习习。
那段光阴好象是我家最快乐的时光。
妈和爸每天开始琢磨各种“美食”,他们烤“面包”、烙果酱馅饼,但似乎都不太成功。
爸爸的“面包”是这样烤的:用一铁皮罐头盒放一团面,但可能是由于他往面里加了白矾的缘故,结果搁炉子上烤了很久后,烤出了一个类似烤白薯的坚硬的糊面团,而且酸的要命。
从此,他再也不烤“面包”了,可又开始了“代用油”的开发。
院子里种了很多“蓖蔴子”,长得非常茂盛,结了很多子儿,爸爸对它动了心思。
我们小孩经常把“蓖蔴子”穿在一串,用火柴一点就“哧哧”的冒起火来,可以点燃很长时间。
“我想这种东西的油一定能用来炸东西吃,”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听见他对妈妈说。
他立即开始动手了。
他把剥出来的蓖蔴子在火上炒,然后砸碎后在水里熬,还真熬出了一大层油,他把这些油收集起来炸油饼儿,结果吃了以后大家的肚子都翻天覆地。
妈妈也不甘示弱,买了几种家畜,一只猪、一只羊、一群小鸭子、一窝鸡雏,好像要大干一场的样子。
我二姥爷——我外公的弟弟,一个老画家,被妈妈从宣武门白纸坊请来放牧那只羊,兼而在我们的“田园”里修身养性。
“我愿意在野地里走走,挺好,人家苏武那么大的官儿还放羊呢……”二老爷是个脾气很好的老人。
二姥爷长的有些象******,当他穿着一件黑呢子大衣在田野里拉着那只羊吃草时,很多小孩都在那儿探头探脑的睁大眼睛说:“瞧嗨,毛主席,毛主席嗨!……”。
而二姥爷却也笑而不答,任其所思,仍就拉着那只小羊幯风沐雨,徜徉于四野之间。
……
我妈养的那只猪享用的伙食标准和人几乎没什么两样,就差和我们共进三餐了,所以长的非常之快。
到年底了,那只猪成了一堆硕大的肉山。
“我跟您说,您这猪该宰了,要不然一过节,就这个长法儿,背不住就成了老母猪了,那肉就跟那柴火似的,怎么吃啊……“女保姆不紧不慢的笑着说。
她是一个壮硕的年青女人,脸颊上老是有两块红晕。
“得宰了?——这么快?”妈妈很奇怪似的。
“那是啊,就您家这伙食,猪比人都吃的都不赖,它能不长膘吗?”女保姆大笑。
“那怎么着呀?这就宰?可谁来宰啊?”妈妈问。
“这些事哪能让您操心哪,有呣哪,明儿一早就能来人。”女保姆满口应允。
那位女保姆毛遂自荐,请来了他丈夫——一个矮壮的农夫,来为我们宰猪。
一应用具均由她家操办,连大锅也运到我家里来了。
一口临时砌的大灶被熊熊燃起,那位“屠夫”也开始磨刀嚯嚯。
我们的院子在一分钟一分钟的向着屠场演变。
那只猪开始有感觉,不吃食且警觉的四顾,最终开始狂躁奔突。
“开刀”在即,妈妈让全家人退避三舍,都离开了院子。
随着一声真的“杀猪也似”的嚎叫,整个紧张的气氛陡然松弛下来,大家都明白,一个无所谓生命就这样在一具铁器下面终结了。
它再也不会用那对混浊的小眼看着人,拼命吃着它眼中的美食,发出满意的哼叫了,代替原来它的,现在只是一具被开水烫得紧绷绷的巨大躯体,着实难看死了。
不过在蓝淀厂人的眼中,这具紧绷绷的巨大躯体却是至上的美味,包括它身上几乎每一个部位,甚至最脏的肠子。
……
约两个小时后,我们藏在妈妈的身后小心的进了院子。
……那只猪已经不存在,它已经变成一大堆红红白白的东西散在一张大台子上,一口大锅在它旁边冒着水汽。
妈妈让“屠夫”拿走了猪头,因为她看着这个猪头很不舒服,还给了她们不少肉。
“您瞧,这猪肝上有几个黑点儿,您要是不格应*的话——”女保姆做出一种恶心痛苦的表情拿着一大块猪肝儿对妈说。
*格应:北京土话厌恶
“是吗?那你赶紧拿走!拿走!”妈妈皱着眉连连摆手……
“那挂肠子……您还要吗?那个洗起来可麻烦透了!弄不好您猜怎么着……”女保姆又激动的说。
“肠子?——别说了!不要不要!你都给拿走!还有那些猪尾巴什么的……”妈妈忙不迭的说。
“哎哎!得嘞……那我就——”女保姆面露喜色,收获去了。
于是,“屠夫”和保姆赶着小驴车满载而归。
……
妈妈又给了桂义家一大块肉,潘老太家也给了些。
星期天是家里最安适的一天。
爸爸妈妈都休息,于是这天的饭菜特别好。
妈妈打开窗子,满眼的绿色顿时袭入眼帘,同时一股大自然的清新气也跑进屋内。
院子里,保姆丈夫帮我们开辟的一垄垄菜畦都长出了绿油的小苗。
阳光明媚,每个人心情都好。
爸爸洗漱完毕后,头梳得倍儿齐,还在额前把头发弄出个小波浪,(妈妈戏称其为‘凤头’)穿上洁白的衬衫,亲手做早点,经常做的有炸馒头片、甜味的鸡蛋摊饼等等,满屋子香气四逸,诱人食欲。
每当此时,我和弟弟都会摩拳擦掌,伸出我俩的‘爪子’,可都会被妈妈呵斥住:“去洗手去!你们这些小脏孩”。
爸爸最拿手的菜是糖醋排骨,先用油把排骨煎黄,再加糖醋酒烹之,简直好吃得没法说。
其次是一道大概来源于自云、贵、川的菜品——五花肉块炖象牙白萝葡,吃的时候蘸酱油,也是味美绝伦,尤其是那慢火靠出的浓浓的白汤。
(这道菜很有可能与先祖们游宦于云贵川的经历有关)
妈妈有时会在星期天带我们进城,她的最大兴趣是逛东安市场。
每次逛东安市场,都要在其内的有名的“五芳斋”饭庄吃顿饭,这是一家淮扬风味饭店,做的菜有滋有味。
她会给我们买我们很爱吃的“奶酪”和“杏仁豆腐”,那可真可称为人间美味!
五十年代的东安市场巨大而破烂,无数小店铺黑洞洞的挤在一起,销售着老北京人所喜爱和熟知的各种商品。
只有门脸那儿才有些许光亮,“小业主”们用并不踏实的表情看着你,脸上带出一种商人的假笑,好象随时准备接受“革命阵营”打击似的。
很多商品可能年代已久,它包括一些美国货和不知有多少年了的各式古怪商品,比如;女人的“玻璃丝”袜,巨大的男式军用皮鞋,一种极厚重而式样洋派的军绿色“皮猴”是青年们的抢手货,有人甚至会凑出七八十元来买。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战后的美国物资。
几种自行车也是那时青年们梦寐以求的,如:英国的“凤头”,“三枪”,荷兰的“菲利普”,这几种车都装有一种令人羡慕的“加快轴”,走的时候,“哒哒”声不绝于耳,当时人们认为,如果你骑着一辆“凤头车”,家里必定很“趁”,找对象都好找。
一些瘦猴子似的“归侨子弟”穿着包屁股的“鸡腿裤”骑着一种“凤头”高把的女式车,竟然成为当时北京青年羡慕和摹仿的样板,其实,这些精瘦的印尼华侨大都是因躲避印尼当时的排华浪潮而“归国”的。
可笑的是当时有些青年人还摹仿“归侨子弟”的大舌头口音讲话。
东安市场里还有一种“估衣铺”,里面挂着很多制做考究的旗袍和西装,这都是一些破落大宅门儿里当年的小姐太太、先生老爷们卖出来的。
民间小吃也是东安市场里到处都有的,妈妈最喜欢吃一种叫做“酪”的冷食,这种“酪”好象是用牛奶制造出来的,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泡在甜水里,论碗儿卖,既凉又香甜,夏日里,妈妈只要见到必买。
还有一种“酸梅汤”和“雪花酪”也都是东安市场里卖的,属于更平民化的一些冷食。
东安市场的北门有一家卖“奶油炸糕”的摊子,生意特别好,买的人络绎不绝,都边走边吃,表情贪婪得很,可见此物之好吃。这种食品外焦里嫩,有一种香甜的奶油味儿,价钱也很便宜。
通常是我们闲逛良久后,妈妈就要带我到东安市场里的一家“五芳斋”饭馆去吃饭,那是个江苏馆子,炒的菜很好吃,也不贵。
离“五芳斋”很近的有一区卖海味的,走到这一带就会闻到强烈的鱼虾味道,里面很暗,有一条极大的鱼标本挂在棚顶,约有七八米长。这里还卖火腿腌肉之类。
妈妈的另一癖好是买瓷器,只要见到中意的必买,尽管家里已经器满为患,所以我俩经常是分提着沉重的大百小包迎着夕阳返回家。
那时的火器营还不通车,只能乘坐冷34路、汽车在“板井”站下车,一直走到蓝淀厂。
在今天,这种黑洞洞、乱糟糟的营业环境或许有点“寒酸”,然而在当时,这种情况却大受人们欢迎,因为它隐藏着一种“便宜”的内涵。
在我的印象里,东安市场的很多小业主穿着“中山服”和“解放装”,说着时髦的革命语言,认为这样就进入了“革命”阵营,可以免遭更惨的下场。但十几年后,他们仍旧受了惨重的打击。
++++++++++++++++++++++++++++++++++++++++++++++++++++++++++++++++++++++++++++++++++++++++++++
爸爸弄了把小提琴回来,经常拉奏。
以今天我的听觉来说,我不敢恭维他的琴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能学一点正规的演奏方法,一定会拉的很棒,因为他的音准很好,在某些片断,他拉的非常好听,很有味道。
爸爸的确是个音乐天才,可惜其命不济,多难多舛!
他在其它方面也是天才,可惜其命不济,多难多舛!
他经常拉的是一些外国名曲,如托塞里的《小夜曲》,圣桑的《天鹅》,巴哈的《G弦咏探调》,还有一首不知谁作的《加佛特》舞曲等等。
夕阳西下时,金色的夕辉从院子西边绿色的菜畦上慢慢的移过来,照在已经相当陈旧了的花窗玻璃上,反射出奇妙的五色斑斓的光亮,爸爸凝神拉着他那把心爱的提琴。
忧郁的旋律廻荡在光线暗黵的屋子里,使我幼小的心里生出莫名的惆怅感。
妈妈和我和弟弟在院子里散着步,看着渐渐暗淡下班去的晚霞……
成群的“马郎”在暮色中盘旋飞舞着,在薄霭中若隐若现。(马郎:满语蜻蜓)
这个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蹲在院子西南角的一片“香蒿子”面前饶有兴味的端详它们,我把这片如烟若云的植物幻想成一大片森林,还用树枝划出小溪、山路,用石头堆出起伏的山峦。
我和弟弟在一起玩,在“大森林”里挖了几个洞,幻想能在土里挖出一些宝贝什么的。
奇迹出现了,有一天,我们终于在第三个洞底挖出一样东西,那是一柄锈迹斑驳的铜勺,一头是像“耳挖勺”的形状,一头有些尖,大概有十几公分长。
这个东西肯定有年代了,它虽然很像“耳挖勺”,但要比今天人们常用的要大几十倍。
我们把“宝物”拿给河边上休憩的老人们看,他们的回答很令人震惊。
“耳挖勺!没跑儿,就是古人的耳挖勺,你想啊,那会儿的人多高多大呀,关云长,关矬子,那还身高一丈多哪,身高一丈多,那脑袋得多老大个啊?不就得用这么大个的耳挖勺吗,好玩意儿!好玩意儿!好好收着吧孩子,背不住……”火器营著名的侃爷“打鼓常”捋着几根稀疏的胡子说。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和弟弟热烈的畅想着:把它卖了以后的钱买什么。
最终,我俩商定买一只足球,再每人连着三天把“炸丸子汤”和“炸三角”吃够了,剩下的钱攒着过年花。
可拿给爸爸看了以后,我们对这个“宝物”顿时没了兴趣。
“这是从前的药勺,盛药面儿用的,比如那些有些毒性的药,为了不致过量。”爸爸说。
“那能值多少钱哪?”我急不可待的问。
“白给我也不要。”爸爸笑着说。
“那怎么人家给埋土里呀?”我又问。
“这还不简单吗,人不在了,家里人看着这东西别扭,又是弄过毒药的,就给扔了呗。”
爸爸懂的真多。
不知时候,爸爸声称要自己亲手做出一把小提琴来,很快,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些木头,又托人打制了一些刀子、铲子,煞有介事的干起来。
没多久,他真的做出了一把小提琴。
令人惊讶的不单单是这些,它的漆也非常漂亮,是一种光彩照人的琥珀色,使人清晰的看到琴板原本的虎皮纹。
爸爸虽然琴技一般,但在他拉奏的时候,仍可听出这把琴饱满有力的音质。
由于他的这突如其来的兴趣,我们家已变成了一个制琴作坊。
到处是木板、木条,很多瓶子泡着带颜色的酒精,废弃的沙纸纱布到处都是。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只大木工台子,在上面锯刨着木材。
由于涂抹颜色和油漆,爸爸的手指都变成了红黄色。
满屋子是酒精和不知道是什么的味道。
大表哥大贝(潘作翰,现在美国拉小提琴。)平时也会拉两下子小提琴,一次,他带来一个叫“皮特”的德国人来家里玩儿。
(皮特德国人我们称其“唐哥哥”原在广州乐团拉琴今下落不详)
“怎么样,我舅舅做的。”表哥拿着一把爸爸做的提琴得意的说。
“你在撒谎,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可能的,我想……中国人是做不出来这个来的。”那个金发蓝眼的“皮特”仔细端详着手里的提琴耸耸肩,用地道的中国话说。
“好,你来看吧。”表哥带皮特进了爸爸的工作间。
“天哪……这是个奇迹!是万能的上帝给了这个中国人智慧!”皮特用白皙的手指在琴弦拨出一段华丽的分解和弦。
很快,家里来了不少人,都是和爸爸探讨提琴的,其中有一个叫“赵世臣”的家伙,来的最勤。
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秃顶中年人,听说没工作,神神叨叨的,可说话挺咬文嚼字儿。
他经常带来一些小东西,似乎想博取爸爸的信任。
事实证明,他很快达到了自己有些不光彩的目的。
一天,天气奇冷,妈妈把门关得严严的,大家坐在炉边烤火。
“咚咚咚”有人轻轻敲门。
开门一瞧,是赵世臣,他推着一辆很旧的老日本大把车,鼻尖冻得通红。
他从车筐里拎起一个小绿瓷罐冲爸爸晃了晃:
“嘿您瞧,给您的,——这可是好东西呀!这是家父做的‘炒红果’,我们旗人管它叫‘榲桲’,干净!择洗了好几遍呢”,“宫里御膳房的秘方啊!——知道您老丈杆子也是旗人,得,给老先生尝尝鲜!”他煞有介事的压低嗓门儿,好象他给我们送来什么稀罕东西似的。
“当年西太后——还是哪个太后来了?……嗨!管哪个太后呢!现在是我们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了!反动派被打倒了……”
他擤了下鼻涕,恶心的用围巾擦着:“哎,对了,我就随便一说呵……听XXX说,您做的提琴还真不赖……我还没跟您说呢,您不知道,这要说起来家父的爷爷早先还是宫里‘升平署’的乐师呢!那也就是说,本人也算是音乐世家子弟了!”
看着爸爸莫名其妙的样子,他现出小市民混混的神情:
“嗨!呸呸!您看我这张嘴,怎么这么掖不住事啊……”他自嘲着,佯装着用手轻轻抽自己的脸。
(升平署:清时颐和园里的戏班子位于牌楼以北这位赵大为家在牌楼以南有可能祖上确是宫里当差的)
他说话是憋着喉咙做出来的“男中音”,能口若悬河的说个不停,弄的你根本插不上嘴。
不知不觉,他已经从家里拿走了好几把琴,说是帮助卖,可一去就渺无音讯,人见不着,钱也没见着。
一次,爸爸终于找到了他。
不料他毫无惧色。
“您是知道的,现在抓得很紧,到处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呢……我不见您为什么?您想想呵?我是为您好哇!……您想想,私制小提琴出卖——这个后果……恐您比我清楚吧?”他做出一付极诚恳但又些恐吓的样子。
“那就给我拿回来吧,我不卖了。”爸爸说。
“可……人家已经交定钱了,这样吧,我把定钱交给您,等下礼拜钱拿回来一块儿算吧。”他煞有介事的掏兜。
爸爸没要他的什么“定金”,只是让他下星期把琴拿回来。
一天晚上,大风呼啸,爸爸没在家,赵世臣风尘仆仆的骑着那辆“叮咣叮咣”响着的破车来了,一进门就把一只破布包递给妈妈。
“嗨,弟妹,这可是好东西,真正的‘澳洲黑’呀,您拿它炖点汤喝,是最好的营养品,大补呵……对了,您跟我兄弟说,那琴的钱我这两天就拿来,得,忙着啊……”还没等妈妈反应过来,他骑上那辆破车“叮咣叮咣”的跑的没影儿了。
那个破提包蠕动着,还发出叽叽咕咕的声音,好象里面有有只动物类的玩意儿。
打开以后,一只苍桑的老母鸡瘸着腿蹦了出来,同时带出了一大股鸡臭味,把我们吓得退了好几步。
这是一只不小的芦花鸡,倒是挺肥,就是外表太古怪了——脖子那儿肿起个奇怪的大包,还只有一条腿。
更怪的是它每天像公鸡一样的“打鸣儿”。
“怪,怪,甭动它,这都说不准的事儿,谁知道这是哪路神祗哪……”姥爷小声跟外婆嘀咕。
由于姥爷每天都毕恭毕敬的给那只瘸鸡“献食”,我们没敢用它来“大补”,一直养着,直到老死。
它下的蛋我们也不敢吃,大倒是大,可没一般鸡蛋的硬皮,只有一层软膜。
从此,赵世臣再没露面。
他没影了,那些爸爸费尽心血做的小提琴当然也就没影了。
几个月以后,爸爸说,有个可靠消息——赵世臣被抓起来了。
每当那只瘸鸡在院子里蹦来蹦去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那个捏着嗓子装男中音的赵世臣。
那只瘸鸡又活了一年多,在我们搬家的前夕,它死了。
我和弟弟把它埋在了我们的寻宝坑里,还用一块“纸壳背儿”立了块“碑”,上面用笔写上“赵世臣之墓”,不料妈妈看到之后,勒令我们立刻把“碑”拆掉,说即便人家有错儿也不能这样。
……
八十年代初,我曾回到这处旧居看过,目光所及,令我失望之至。
原先那些美丽清幽的乡间风光,今日已面目皆非,其上大多已建起恶俗不堪的宅院,人们为自家多一寸土地而大打出手,视若仇敌。
不伦不类的建筑鳞次栉比,人们象老鼠一样在狭窄的巷子里出来进去,斜着眼张着嘴打量着你,一个生人刚转身,他们马上会瞧着他的背影叽叽啾啾的嘀咕着什么。
我们当年住过的美好的大院被改成了一座“孵鸡厂”,老远就有阵阵异味飘来,而且看起来只是一小堆房子。
桂义一家不知何去,潘老太一家听说搬到了西直门,至于那位神秘的“李同志”,谁都不知他后来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