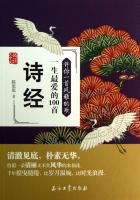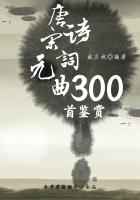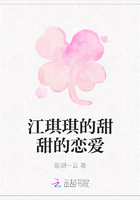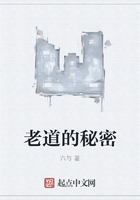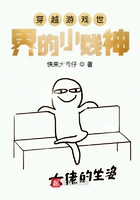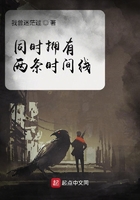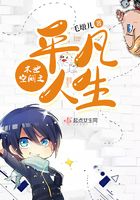文学流向及其危机1983年,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一次演讲中说道:“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为它已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参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第16页。该演讲原题为《塞万提斯的遗产》,随后以《如果小说抛弃我们》为题,发表在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这句话表达了一种绝望的忧虑。就小说的现代命运而言,它确实越来越被边缘化,在这个符号帝国急剧扩张的时代,小说如何去(去哪里)寻求它的安身立命之地呢?它的衰败是必然的。然而,这句话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思,如果说小说“自己的世界”不仅仅指外部的符号帝国,由现代文化工业构成的排斥性力量,更重要的在于小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小说找不到自己“内在的世界”。也就是说,小说不再处在自己的(美学规定的)世界中,它放弃了它的根本的艺术追求,逃离了它应是的存在,这将是它最根本的危机所在。当今中国小说显然正处在这样双重困境之中,一方面,它置身于视觉符号帝国和各种非文学的社会化力量的分化和瓦解的境地;另一方面,它的艺术追求变得越来越模糊,它正在走出自身的世界。
没有先锋性的探索,文学在现今时代就难以找到自身的世界。然而,“先锋派”这个术语现在已经变得陈旧而不合时宜,曾经被称之为“先锋派”的作家们,功成名就后已经难有再探索的热情。当然,从来就没有永远的先锋派,随着一代先锋派创制的艺术经验被广泛认同,先锋派的挑战意义也就终结了。但当今中国的先锋派的历史如此短暂,并且如此迅速地被人们抛弃乃至于遗忘,这不能不说令人惊异。尽管说当代文化语境是如此复杂,个人的选择总是被多重历史力量所决定,但个人总是能确立自己面对文学说话的基本位置和文化目标。“有力量的跟着历史走,没有力量的被历史拖着走”(斯宾格勒语)。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有力量”不幸被理解为“有能力顺应时势潮流”。“永远的先锋派”固然强人所难,但文学却永远需要先锋派。即使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先锋派”这种说法显得非常勉强,但文学共同体总是保持着创新的努力,保持着构筑新的文化乌托邦的冲动,否则人们就注定了生活在一个“文化稗史的新时代”(列奥塔语)。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处于急剧的裂变和转型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复杂、丰富和含混。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以其面对“现在”的直接性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就文学面对“现在”而言,它无疑提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经验,改变了不少由来已久的原命题。但是,先锋性的形式革命很少在表现现实的文学叙事中留存下来,没有形成进一步保持面对“现在”写作的先锋性。一方面,昔日的先锋派逃离“现在”;另一方面,面对现在的写作没有展开有效的先锋性艺术探索。这二者构成的矛盾严重阻碍了当代文学的有序发展。仅仅是(又是)短短的几年,随着历史背景的不断变幻,文学为适应“现在”的潮流进行各种调整,已经耗尽了文学的创新冲动。不管人们从哪方面而言,先锋性的丧失,对“现在”把握无力,不能不说是当前文学创作缺乏深度、高度和力度的危机所在。归根结底,文学共同体缺乏一个深厚有力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体系,就不可能保持先锋性的艺术创新和对“现在”(历史)的深刻把握。因此,重新审视先锋派文学直至九十年代的文学面对“现在”的文学叙事,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进入到历史的实际过程,去找出那些症结性的问题及其可能的出路,这是本文试图做出的努力。
一、先锋性的退化与文学转型的历史语境
当代先锋派文学到底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还是实际的历史?或者如某些论者所言,所谓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不过是1989年以后的特殊意识形态氛围的产物,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持而风行一时参见杨扬文《先锋的遁逸》,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该文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是在1989年以后的特殊意识形态氛围里出现的,“恰好满足了当代意识形态的需要”。这里暂且不去辩解先锋派批评是否是“合谋”的产物,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后期崛起于文坛,这是基本事实。它的崛起既不仰赖南方批评家的慧眼识珠,也不必凭借北方批评家的不遗余力,更重要的在于它乃是文学史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它表达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先锋文学创立的文学经验可以普遍化并且有效建构当代文学的美学典律(canon)。
很显然,先锋文学一直在文学史的对话语境中展开探索,它既与西方现代主义构成一种借鉴关系,同时更重要的是与当代中国既定的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构成对话关系。当文学不再能从意识形态推论实践中获取内在动力,它只能以形式主义实验来寻求从社会领域退却的途径。先锋派文学回避了意识形态话语,但其艺术创新方面的探索无疑使当代文学的格局发生某些根本变化。如果不理解八十年代文学写作的历史前提(历史语境),就无法理解任何文学创新给出的意义。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经典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就面临合法性危机。在文学创新的压力之下,现实主义文学体系既保持着顽强的制度化的支配力量,又难以提出与之应战的开放性策略,未能及时提出一整套的表象体系和表意策略突破旧有的文学规范。这就使得八十年代后期(直至九十年代)文学所做的一些小小的技术性调整和观念的些微变化,都被视为具有变革意义的探索。文学创新的意义显然是被经典现实主义的自我封闭语境放大的。换句话说,如果经典现实主义的制度化力量呈开放性势态,它有可能提出自我创新的表象体系,它有能力接受一切先锋性的挑战,并且把那些反抗和创新吸收为它的表象体系。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使得所有的创新被置放到它的对立面,任何创新都不得不看成是一次背叛,那些细微的变化也成为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超越。
当代中国文学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历史转型,我坚持认为这种转型发生在1987-1988年,持续到九十年代。这种转型是政治/文化/经济多边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某个历史事件起到突发性的杠杆作用。不理解这一点,就不理解当代中国文学所发生的那些变化本身具有的文化逻辑。不管是用“新时期后期”还是“后新时期”来描述它,都是基于文学历史本身的变化和起关联作用的语境来给予定位关于“后新时期”的讨论,1992年10月,在北京大学由谢冕教授主持的“告别新时期”座谈会才为文学界广泛注意。“后新时期”这一提法却有一个发展过程。笔者在1988年以来写的一系列关于当代先锋文学的文章中,“新时期后期”是我理解当代中国文学历史转型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1992年拙文《“新时期的终结”与新的文学课题》(载《文汇报》,1992年7月8日)再次强调“新时期后期”的文学转型:“‘先锋派’的实验性探索无疑最深刻地显示了‘新时期’的终结,而且最尖锐地预示了‘新时期后期’极端的文学流向。”“后新时期”这一概念明确地揭示出新时期转折。尽管当代历史语境是如此复杂,包含过多的变异和重叠,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最主要的历史前提,找到创生的文化与主导文化冲突的基本关系。这些关系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创生力量时,不找到那些对话的阶段性语境,就不能给出它的准确位置。先锋小说在八十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应运而生,这并不表明它是投机取巧或“合谋”的产物,恰恰相反,它的崛起表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少有的对文学说话的纯粹姿态,它那过分的形式主义实验,既是一次无奈,也是一次空前的自觉。毋庸置疑,先锋小说把中国小说叙事推到相当的高度、复杂度和难度。
面对先锋小说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创立的艺术经验和准则,文学界除了保持短时期的麻木和排斥之后,再也无法回避它的存在。进入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叙事语言和叙事方法在潜移默化中被广泛接受。然而,这一切并不表明先锋派完成的叙事革命就取得永久有效的胜利。事实上,先锋派的实验突然而短暂,在九十年代随后几年,先锋派差不多放弃了形式主义实验。除了格非和北村在九十年代初还保持叙述结构和语言方面的探索,先锋派在形式方面已经难以有令人震惊的效果。一方面,先锋派的艺术经验不再显得那么奇异,另一方面艺术的生存策略使得先锋们倾向于向传统现实主义靠拢。故事和人物又重新在先锋小说中复活。苏童的《妻妾成群》(1990)不仅仅是在叙事方法方面回到现实主义的规范之下,而且那种文化品位明显是在表达某种“复古的共同记忆”,只是那种叙事语言和叙事情境的构造还保留着先锋小说的痕迹。这是一种“成熟”,也是一种退避。不管如何,苏童的成功具有示范意义,与传统和现实的调和,使先锋派的写作找到安全而有效的途径。
但是,这种“退避”(或成熟)对于先锋性的写作来说却是退化的开始。先锋派的写作并没有关于历史、现实和人类生活特别独到深刻的认识论基础,他们仅仅是依靠与经典现实主义的文化史语境对话写作,其艺术表现方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当他们的写作从这个对话语境撤退之后,他们迅速要忍受思想方面的贫困。先锋派表达的那些对人类生活境遇的怪异、复杂性和宿命论式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形式方面的探索。那些超乎寻常的对人类、生活境遇的表现,其实是艺术形式的副产品。这点在余华的写作中表达得最为明显。余华那些对生活的怪异性、对人类生活的原罪和暴力倾向的揭示,例如《世事如烟》、《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等,得力于他寻求那种将人物与所处的环境不断剥离的叙述视点,得力于他始终寻求的语言对不可表现之物的倔强表现。格非的小说对生活的劫难,对不可知的命运的复杂表达,得力于他经常使用的叙事“空缺”,通过把故事的某些关键性部位“隐瞒”的方法,格非的小说(如《迷舟》、《青黄》、《褐色鸟群》等等)对生活的那些命定的困境和存在的真相进行了令人震惊的书写。很显然,这是当代中国小说非常特殊的时期,形式主义的书写替代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直接书写,先锋派文学在这里不仅仅提示了崭新的艺术方法论,也表现了对生活世界的异乎寻常的表现。然而,这也正是先锋派的局限,当他们试图从形式实验的高地撤退时,他们要直接面对历史和现实时,哪里又是他们的新的立足之地呢?
事实上,九十年代最初的几年,先锋派没有找到撤退之后的新的起点。那些放弃艺术创新尝试的作品,大多数只是简单回到写实的传统,并且依靠陈旧的思想观念来支撑再现性的叙事。苏童的《妇女乐园》(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收录的小说,无疑对妇女生活作了极为细致的表现,那些情境描写和人物心性的刻画都非常出色,但不能说在对生活、对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把握上有多么独特复杂而深刻的认识。余华的《活着》在表现一个人的命运方面当然相当成功,但他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超出古典人道主义。余华最近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受到多方颂扬,他的自我感觉也十分良好。就常规小说叙事而言,无疑可以从中看出余华的艺术手法已经十分圆熟老到,叙述显得纯净而流畅。但这部小说出自余华之手就不能不说还留有诸多缺憾。这部关于“苦难生活”故事,不过是近几年重写五六十年代苦难兮兮往事的流行主题例如,方方早在1988年就写过《风景》,随后发表《落日》。池莉1991年发表《你是一条河》。这些故事都是对五六十年代的苦难生活的叙述。池莉《你是一条河》讲述的是一个妇女卖血养家糊口的故事。这个主题在九十年代初还有些令人惊异之处,而在1996年则很难说它揭示了什么新的经验。就其叙事而言,这部被称之为长篇小说的作品,过分追求单纯性,流畅明晰的叙述替代了余华过去的有意混淆现实和幻想的叙事方法。其中一些片段通过人物语言来迅速推进叙事,类似电影惯用的叙事手法,虽然在这里恰到好处,但也不过是经典现实主义惯用的手法而已。而余华在叙事中甚至剔除了人物与人物的复杂的关联,以至于人物的内心刻画,人物与环境的交流都没有得到必要的表现,更不用说对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人物真正面对的生存境遇进行强有力的揭示。不能不说显得过于单调平直。单纯性并不是长篇小说追求的艺术特征,正如跳高不是跳远追求的效果一样。余华在当今青年作家中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他当然可以放低形式实验和对生存的复杂性的探索,但他在回到生活现实,回到人们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境遇时,他应该有相当的创造性。然而,1996年余华充其量处在徘徊或重复的状态,如果视之为一次卓有成效的艺术进步或转折,那就不能不说是夸大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