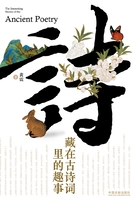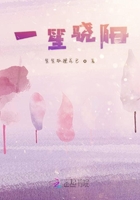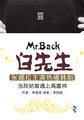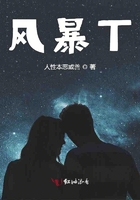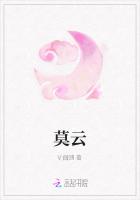“审美反映形态”表明文学形象借助虚构等艺术手段所达到的一种审美高度,在这里,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转换关系,尽管写实类的话语以传达现实生活的“似真性”为目的,但是它的审美价值却是产生于真与不真之间〔即一种审美形态〕,正是由于虚构对“真实性”的构造而完成审美反映形态的建构。“审美反映形态”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极大的突破。尽管这一概念依然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但它打破了现实主义美学的限制性结构。审美反映形态表明了一种多元性的认知方式,在这里“实践一精神”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已经试图把现实(历史)存在的绝对第一性加以创造性的表现。它实际解除了对叙事的权威化的限制,使“叙事性”发生多元性转化成为可能。当然,“审美反映形态”解决了艺术表现的能动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抵御意识形态总体制度推广的思想现实。说到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并不只是来自权力机制的运用,重要的在于几代中国作家自觉认同。通过作家世界观的改造,使作家的立场真正转移到“工农大众”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才能确立,并不断扩展。尽管说在“审美反映形态”中包含了作家自觉的思想感情,但由于世界观的问题,这些思想感情也渗透了权威的意识形态。“世界是第一性”,“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唯物论的表述在其理论范畴内是令人信服的哲学,但问题在于,知识的权力与社会实践权力密切相关。在非多元化的认知语境中,谁能获取对存在的第一性的解释权,谁就给予并占有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话语领导权。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性所赋予的“真实性”原则,为重建历史提供了有效的手段。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占据审美领导权的地位,就因为它为“真实地”建构历史和阐释现实提供了全面的符号象征体系。当代中国文学一直以现实主义美学规范为主导,而现实主义文学依靠一整套的历史观念为基础建构它的审美观念和叙事法则。同样,中国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现代性历史,也依靠现实主义文学建构宏大的历史叙事。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完整地叙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讲述了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运动;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梁信的《红色娘子军》等叙述党如何领导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走上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艳阳天》、《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等,则讲述农村集体化道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历史。直到“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依然是在这种历史观念延续之下重建和修复历史叙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绿化树》等典型的“伤痕文学”,其主题无疑是批判揭露“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人的迫害,但这些最有影响的伤痕文学都隐藏着一个深刻的主题,那就是重建一部反“四人帮”的“真正的”主流历史。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这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不论经受多么严重的精神压迫,都始终不渝坚持革命信念,对党对人民坚贞忠诚。这当然与“文革”后的历史实践相关,经历过“文革”浩劫,百废待兴,重建现实需要信心和信念。但这一历史叙事依然无法完全修复历史的歧义和分裂,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把“文革”的谬误算在“四人帮”头上,但一部完整明确的历史不可避免出现歧义。历史的权威性正如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意识形态要么是全能的,要么是无用的”(丹尼尔·贝尔语)。历史叙事也同样如此,五六十年代建构的历史叙事,现在难以完全延续下去。事实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明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历史已经告一段落。虽然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制在起作用,但表象体系不具有权威性,这使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也不再能起支配作用。
中国的现代性总是以断裂的方式运行,现代性断裂构成中国现代性奇怪的历史过程。这种断裂总是在西方压力之下作出的过激反应的结果。现代性焦虑总是伴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在追赶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愿望中,包含着强烈的反西方情绪;正如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投射,总是隐含着同样强烈的达到发达资本主义水准的渴望。这使中国在多种历史合力作用的关键时刻,总是采取激进的措施,以剧烈革命或变革的形式来促使社会的制度体系和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实现质的变革。急切摆脱传统的束缚,脱离既定的秩序,一直是中国现代性运动的法则,也使中国的现代性总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它永远处在开始和终结的两个极端。在意识形态生产方面,其历史也是采取了断裂的叙事方式。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关于路线斗争史以及阶级斗争史,这些宏大历史都是采取断裂的方式加以表达。它们经历过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总是被重新书写:断然拒绝过去,以崭新的命题和方式重写。历史并不具有直接而完整的延续性,它总是以段落的形式重新开始并被不断改写。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路线,无疑是对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进行的一次断裂。这种断裂并不是在中国现代性历史之外,而是其最内在的表现。阶级斗争的现代性叙事,同样是试图建构一个中国特有的权力与各项资源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式的民族一国家。在冷战时期,中国无法介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不能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取任何资源,它设想通过国家高度集中(垄断)所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动员社会力量,以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建设,并以此来作为与西方资本主义较量的基矗但在这一空前的动员中,手段变成了目的。为了建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经济资源,需要无止境地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需要集中统一全体民众的思想,需要完整严密的国家组织,这就使建立这一手段,或者说通往目的的途径已经足以耗费所有政治经济资源。在整个建国后的政治经济策略中,到底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一国家是理想,还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冷战是目的?这二者既不清晰,也经常相互缠绕。结果,理想与目的,都让位于手段一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最后成为全部历史实践的核心。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在所有的政治文件和文学艺术作品中都被描述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或者说“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种描述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历史在这里发生断裂,历史以跳跃的方式跨过原来的延续性,它的方向和运行规则都发生了根本的(至少也是深刻的)改变。这种改变在社会的总体性制度和组织结构方面是缓慢的,但在人们的直接经验方面和思想意识方面则是剧烈的。意识形态实践虽然可以依靠强大的权力机制延续原来的模式运行,但其表象体系则不可避免出现危机。原有的历史观念支配下的建构历史和阐释现实的活动,则受到质疑并被改写。对于文学艺术来说,经过短暂的修复历史的叙事(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党的忠诚),便随之进入反省历史的叙事,由此生发出“人性论”、“人道主义”、“主体论”、“异化”等一系列命题。很显然,这一思想序列背离了原有的历史轨迹,使原来的宏大历史受到质疑。如果说这还不过是在思想层面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话,那么,随之则不可避免对历史本身进行直接的和观念的质疑。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权威意识形态实践经历过较大幅度的反复,从非常时期的严整到相对宽松。特别是继续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来临,跨国资本和西方高新技术大量输入中国,以及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这些都使意识形态总体性制度不再以强加的方式制约社会的精神生产,使人们有可能重新思考直接的历史。由此出现了一部分小说重新审视革命历史年代的故事。90年代初,李晓的《相会在k市》,讲述一个革命年代的叛徒的故事。主人公到底是叛徒还是烈士?在故事中的一系列难解之谜中很难得出结论。这篇小说与当年方之的《奸细》有着本质意义的不同,方之的“奸细”终于平反,对“奸细”身份的恢复,使一部革命史变得更加完整和完美;而李晓通过对人物身份的反复辨析,结果使革命史陷入疑难重重的领域。类似的作品还有潘军的长篇小说《风》,革命者的身份总是难以辨认,这与经典叙事中出现的革命人物形成强烈反差。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是一部企图重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小说,在这里,历史以偶然性的方式最大可能表现了它的戏剧性特征。个人的卑琐欲望构成了历史的直接动机并产生决定历史变化的结果。刘震云随后的作品《故乡相处流传》则对中国经典历史进行全面解构,通过重复的手法,使历史的神圣性和绝对性解体。陈忠实的《白鹿原》试图叙述他所理解的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历史。在小说的扉页上,他清楚地表明他怀有的历史冲动。实际上,这部小说隐含了一个传统革命二元对立的复杂关系。陈忠实从他的角度写出现代性革命对乡土中国的渗透。
尽管小说在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底蕴的把握方面,以及对乡土欲望的表达方面还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作者重写中国现代史的意识则是有相当力度的。陈加桥的《别动》(《花城》,1999年第2期),是最近一部讲述国共战争的小说,这部看上去实验性很强的作品,不断在叙述与人物意识之间制造冲突与转折关系。人物的偶然意识随时生发出新的可能性,从而用瞬间来给历史重新编码。但更重要的在于,作者有意抹去经典历史的政治视角,他把英雄主义作为历史失忆的一个支点,导向对历史的全面质疑。重写中国现代性历史,并不是对经典历史本身有强烈的批判性意识,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些作者是把经典历史叙事作为一种语境来运用,在把宏大的经典性历史随意加以打碎的叙事中,寻找一种历史与个人、绝对性与可能性之间构成的叙述张力。但不管如何,经典(革命)历史由此被推到一个疑难重重的领域。对直接历史的审视必然导向对历史观念本身的质疑,同样,前者也有可能根源于后者。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先锋派小说,对历史观念就持一种怀疑态度。最典型的作品如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褐色鸟群》的叙事采取重复的方法,使历史的存在显得可疑,对历史的叙述其实就是关于历史的失忆,把没有起源的原初的历史作为叙述的绝对依据。格非的小说总是把那些关键的历史环节掩盖,从而使人们可把握的历史变得可疑。事实上,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就带有很强的否定历史绝对性的思想、历史观念就是一种霸权性的叙述观念,通过破坏性的叙述,同样可以重述另一种历史。刘震云意识到“另类历史”同样可疑,因而他采取了彻底的非历史化的态度。对形而上历史的质疑其实是历史叙事发展到极端的后果,早在80年代中期,朦胧诗出现“史诗”倾向,试图重述中国精神史。杨炼、杨牧、宋渠、宋炜等人的史诗,把远古神话引发的历史想象,作为思考中国现代性命运的背景,表达了80年代中期寻求民族自我更新的现实愿望。但庞大的历史想象令更年轻一代的诗人厌倦。当代中国文学一直被一种求新变异的愿望所驱使,80年代把现代主义作为创新的理想目标,这一目标与当时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共同想象相关,因而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有序的变革过程。90年代,文学已经没有艺术和思想的目标,创新变革的动力仅来自对文学现实的不满。这就使变革只是逃脱厌倦的一种方式,求新只是为了“新”,并且只有“新”才标志进步,标志着方向。90年代初的“新”当然也有抵制“后……”的直接功利性,但求“新”表达了文学界失去方向感的焦虑,一种历史终结之后的恐慌。一时间,“新状态”、“新都市”、“新乡土”、“新市民”、“新生代”等等,充斥了各个刊物的主要版面。正如杰姆逊所说:“一种绝对变化(或者是某种新的追随潮流的浮华意义上的‘永远革命’)的修辞,对后现代而言,并不比由大公司制造的绝对同一性和不变的标准化的语言更令人满意(但也并不更令人不满意)……”杰姆逊用于批评“后现代”的观点,不幸在中国也适用于“反”后现代的那些有组织有行为的人。人们期望在新的名目下,那种旧的时间性不复存在,然而,留下的却是随意变化的一个表象,“而这些变化又只不过是停滞,是历史终结之后的一种混乱”(杰姆逊语)。意识形态权威不再支配实际的文学实践,一部分民间力量开始增长,刊物按市场化效应不断制造各种文学新人。问题与热点都不再激动人心,只有新人才会引起一些阅读兴趣。按年龄代来制造文学群落和热点效应,也是90年代后期文学奇怪的现象。在将“晚生代”和“新生代”迅速以“60年代出生”命名之后,文学界已经失去了从美学上对文学群落和流派进行把握的能力和兴趣,干脆以“70年代出生”来标明文学新人就足够了,因为最新的就是最好的,那么最年轻的当然就是最新鲜的。
1998年,《作家》第7期推出一组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在封二封三配上了这些女作家故作姿态的照片,看上去像是时尚招贴画。这些作家的出现,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代作家杰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97,第20页。
传统作家老成持重的形象,现在被改变为毫不掩饰的矫揉造作,但这种姿态与其说是挑逗性的,不如说更多些挑衅的含义,它表明传统中国作家精英形象的世俗化和消费化的趋势。当然,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作家的作品及表现的生活情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典文学的本质含义。文学的社会性、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观念与法则,都发生了相应的变更。在这里,文学没有难题、没有障碍,也许文学史在她们这里真正发生断裂,朱文韩东们的激烈,表明他们并没有忘怀文学的秩序;而她们则属于另一种文化秩序,另一种符号体系。与其说她们是文学史不贞的传人,不如说她们是当今消费社会天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