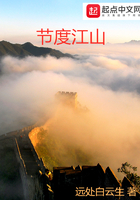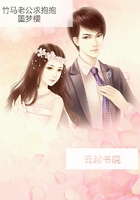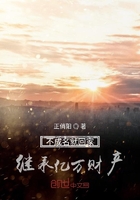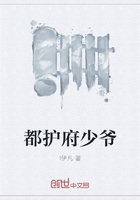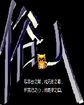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发表后,鲁迅以为文章总算较为清楚地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多少澄清了一点容易引起混乱的思想理论上的问题,对于类似“托派”、“破坏统一战线”等横加于自己的罪名,也都因此一并有了辩诬的机会,应当可以有安静一些的时候了,想不到英雄们不但没有退隐,反倒更为神气,雄赳赳地打上门来。
是徐懋庸的一封信: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朋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全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真是骄横恣肆,达于极点!
信中虽然攻击的是巴金、黄源、胡风几个人,其实是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挑战,不放过任何异己者。写信的虽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后却是一伙。他们何尝维护什么统一战线?白天里讲的冠冕堂皇,暗夜里做的又是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左联的时候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忍耐了这么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写它几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或也可以算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然而,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一直拖了下来。而今,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的了!
就在鲁迅收信的当天,冯雪峰来看他。他余怒未息,一边把信递给冯雪峰,一边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不是挑战是什么呢?过一两天我来答复!”
冯雪峰觉得,这是公开批评周扬和解决两个口号纷争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是非答复不可的;但是,看鲁迅的身体远没有恢复健康,又因为六月间曾以“O。V”笔录的形式,代他草拟过两篇文章,还算符合他的意思,看完信后便说:“还是由我按照先生的意思去起一个稿子吧。”
“不要了,你已经给我替过两次枪了。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
临走时,冯雪峰仍然向鲁迅要了徐懋庸的信,说:“让我带去再看看。”回到住处,当晚就动笔起草了一篇公开信模样的文章,用意是给鲁迅做个参考。如果可用,他想就这么发出去,省得让一个病人再耗费心思,而且也免得拖时间。
鲁迅看了拟稿以后,平静地说:“可以的,但我要重新写过。”隔了一会,又补充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来弄吧。”
过了二三天,冯雪峰再到他家里来时,稿子已经由许广平誊抄出来了。拟稿几乎全被红笔勾画过,还有整整四页,是他用毛笔在白宣纸上加写的。
全文的题目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前面部分基本上是冯雪峰代拟的,说的是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关系。其中说这个口号是鲁迅提的,是冯雪峰有意借鲁迅的威望,以图缓和空气,停止国防文学派的攻击。鲁迅接受了这个要求,关于两个口号的解释,即使有些地方与本人的原意不大切合,鲁迅也没有作什么改动,只要在大的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出入,就无须字斟句酌,尽可以让它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完善。
统一战线问题。文章说: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无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文章对各种不同派别的文艺家表现得相当宽容,但是对动辄加入以“破坏统一战线”罪名的“指导家”,则是十分的严厉。文章说:“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两个口号问题。文章认为,问题不在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为了推动左翼作家奔赴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而提出来的。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的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文中特别驳斥了“标新立异”的说法,说:“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
为了有效地孤立和反击周扬、徐懋庸等人,冯雪峰在拟稿中对茅盾和郭沫若有意做出让步和妥协的姿态。
文中有几处提到郭沫若,并且引用了他的话,其实不是不可以省略的,郭沫若明显地属于国防文学派,但是只要有那么一点意见,或几句说话是可取的,就立即加以利用。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一事曾经同茅盾商计过,算是冯雪峰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为了表明新口号在文艺界中的代表性,同时也为了表明鲁迅一向愿意同茅盾合作的态度,冯雪峰在拟稿之前和茅盾商量,要求同意有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冯雪峰以共产党和他个人的名义要求他,他也就同意了。此外,质问《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也的确是很牵强的。这里以几部名作并提,无非为了提高《子夜》的声价,以换取茅盾的好感,争取他对参加议决新口号一事的确认,和在实际行动中对新口号予以进一步的支持。
如果说拟稿的前面部分在于政策和口号的理论分析,倾向于理性的冷静,那么后面增写的部分则主要从事人格批判,充满着搏战的激情。
增写的部分是从这里开始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从此,在“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之后,又多出了一个新名词:“四条汉子”。
在交代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时,鲁迅更多地说到胡风,从而证明“田汉周起应们”的发昏、说谎、诬陷、造谣,如何的“左得可怕”。其中,“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这样一句近于定评的话,是原稿没有,后来加上去的。他严正声明说:“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友情之于他,其神圣并不亚于信仰。正由于过分地看重友情,所以才不惮于“同人”的背叛,“朋友”的反目,而至于珍爱孤独。
文章几次提到上海的一份小报《社会日报》。它任意诬陷鲁迅和鲁迅的朋友如胡风、巴金、周文等,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鲁迅在年初有信给茅盾说:“我已连看了两个月,未曾发见过对于周扬之流的一句坏话,大约总有‘社会关系’的。”这种关系无非是宗派关系,因宗派性活动而成文中所说的“天罗地网”。
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是十分可怕的。由于领导者的运动,于是才有了大布围剿阵的“群仙”,或是纠集在大纛之下的“群魔”。鲁迅多次在信中作过类似的表示:“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在这篇公开信里,他丝毫也不掩饰对于周扬和徐懋庸的憎恶。所称无论是“文坛皇帝”、“奴隶总管”,或是别的什么名目,都无非说明他们实际上在维持某种旧式威权,不但于革命毫不相干,相反是可以将革命扼杀的。
他的憎恶是有道理的。在原稿的“周起应之类的青年”那里,他多加了一个“轻易诬人”的限制词。最后一段,在说到徐懋庸时,也加重了严厉的语气。“否则”之下,原稿为“只一味的这样卑劣下去,就毫无救药,这样的青年于中国毫无用处的”,终于改定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但是,在批评的同时,也可看出鲁迅为人宽厚的地方。譬如原来“周起应如果肯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仍无妨碍他将来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一句,改成“自然周起应也许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便透露了内心对于青年的希望,虽然两个“也许”的使用,同时也强调了一种不信任感。至于徐懋庸,文中也把他同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行为的“破落文学家”区别开来,说他“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虽然“已经胡涂得可观”。
严厉也好,宽容也好,当鲁迅从事批评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就不只限于目前中国文坛的病象,中国的未来是他所忧患的。青年就是未来。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这样的大题目之下,罗织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者乃至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多年以前说的“阿Q党”,岂非不幸而言中了吗?
最使他无法忍受的就是专制和奴役。他知道,在中国,“朕”即天下的皇权思想是如何的深厚广大,源远流长。所以,他在指出无凭无据,即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这种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的恶劣倾向以后,特别强调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所谓革命,就是人的解放运动。解放别人,也解放自己。如果在革命的队伍中复又产生新的“横暴”,就必须以新的革命手段把他除掉!人不是生而为奴隶的,自然也不是生而为“奴隶总管”的。人应当是,而且也只能是自己的主人!
这篇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问题,也超出了文艺问题。它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统一战线的个人宣言,是对于被诬枉的有为的青年的辩护词,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挑战书。
它一经发表,便被称为“万言长文”,立刻在上海、北平、东京文化界引起强大的反响……
这时,茅盾给郭沫若寄去一封信,希望他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能与鲁迅的步调保持一致,正确地引导青年,使论争早日结束。郭沫若没有回信。他不但没有接受茅盾的意见,反而写了一篇颇长的文章,明确地把矛头从胡风那里引向鲁迅。
文章在9月10日《文学界》1卷4号刊登了出来,题为《苗的检阅》。全文充满反语,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称作调遣大家作“现代的模拟战”,“把自己人认成为假想敌”,是有意挑起“文艺家的内战”。文中假借某些“朋友”对公开信的所谓“家丑外扬”、“使仇者称快”的评语,表明影响的严重性,从而要求撤回新口号!
郭沫若一再表示说,新口号的提出在手续上不完备,在意识上欠明确,是不大妥当而且没有必要的,不仅是“标新立异”而已。它的出现,使文学界起了一种类似离析战线的纠纷。他认为,鲁迅对两个口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不大妥当”的,因而“青出于蓝”的茅盾从那儿出发,为安置两个口号的苦心也是空费了的。两个口号的对立之所以使人们感到棘手,都因为鲁迅的存在。因此,为了消除这种对立状态,只好由鲁迅主动撤回一法。这就是文中所说的问题的“明朗化”。他引用鲁迅公开信中的“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等语,进逼一步,说:“我据这些语句来推想鲁迅先生的意思,大约是在这场纠纷上,要叫胡风诸君委曲一下,让‘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继续着它的顺当的进展,而从此愈加‘实做’起来。假使我这个揣测是不错,我是极端赞成的,我想茅盾先生也不会有甚么不同意。”又说:“以那样见解,态度鲜明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决不会一意孤行到底,以不正确不正当的口号来强迫青年来奉行的。”又说:“像这样明达事理时常为大局着想的我们的鲁迅茅盾两先生岂肯在大家得到了明白的解决之后,一定要为争执一个口号使纠纷纠纷到底吗?……”
此外,文中还曲解了鲁迅关于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无条件联合的观点,以及茅盾关于“创作自由”的口号的阐释,不指名地攻击他们当人们“焦头烂额地从事着救亡的时候”,为佳人才子和鸳鸯蝴蝶派文学争“特权”,使之产生消极作用和负面效果。对公开信中提到的悔过转向的问题,也都有着别有意义的申说。他反对“把敌人的武器当成武器”。
这样的文字,是只有郭沫若能写的。直至现在,应当说,他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原来的“才子”气和“流氓”性。9月下旬,《今代文艺》以醒目的标题登出他的《戏论鲁迅茅盾联》:“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更为明显地反映了他的认识和心态。
茅盾不敢正视郭沫若的挑战,反而认为:“郭沫若先生的《苗的检阅》是‘澄清’空气的一大助力。”在《谈最近的文坛现象》一文中,他居然把郭沫若文内的称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一类反语当作正面的论点加以引证,虽然在文章的结尾,仍然坚持了他后来的意见,即两个口号并存说。
冯雪峰对茅盾的争取工作是有一定成效的,茅盾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立场的偏移,多少增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影响力。然而,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他在文学界中的尴尬地位。他本来是“文艺家协会”的中心人物,而周扬们的系列行动,在鲁迅、巴金等人看来是意在向协会以外的人们挑战的。因此,他势必要失去原来的大批簇拥在周围的人们。而当他倾向于新口号之后,又与胡风等不相融洽。处在宗派主义阴沟四布的地带,这个一贯精明而谨慎的人,便不能不考虑人际关系的平衡,以防失足落水。
但是,在东京,一个统一的团体开始分化了。
“龟裂”的现象不是产生在新口号提出之后,而是在郭沫若建议撤消的时候,这也是颇带戏剧性的。东京支盟分成两派,魏猛克、陈辛人等表示赞成新口号。就是这个魏猛克,曾经撰文嘲笑鲁迅从“坟”里爬出来欢迎萧伯纳,还曾画过一张《鲁迅与高尔基》的漫画,把高尔基画得很高大,鲁迅画得很矮小,意在讽刺关于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不过,后来总算彼此消除了隔膜。鲁迅的人格是具有感召力的。
随着形势的变化,文学队伍的变化,随着《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以及后来的鲁迅逝世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也就渐渐地自行消失了。
徐懋庸在乡下看到朋友寄来的载有鲁迅长文的《作家》,心里很不服气。回到上海以后,又遭到周扬、夏衍和从前左联常委会的几个人的批评,陷入了里外夹击的境地。
周扬他们认为徐懋庸给鲁迅写信惹了大祸,于是批评说是“个人行动”、“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等等。使徐懋庸不满的是,他们自己却毫无检讨之意。况且,说是“个人行动”也不全是事实,信里的基本内容,还是批评者经常议论到的,只是由他捅了出去而已。对于左联的解散,他原来是不同意的,然而既然解散了,又还有什么“组织”和“纪律”可言呢?说起同鲁迅的“团结”,还好意思说出口吗?这几年与鲁迅方面的联系工作,还不是靠他去做的吗?还有,鲁迅在文章里所揭露的事情,绝大部分是他们所干而他竟不知道的,现在居然要他一个人负起责任来了!
徐懋庸极力争辩,但是没有结果。
他既感委屈,又不免愠怒。过了些时候,他又开始采取“个人行动”,把一封已经写好的公开信,叫《还答鲁迅先生》,交《今代文艺》发表。
在信中,他指责鲁迅不应公布私信,说藉此引起多人的恶感相威胁,是一种“恶劣的拳经”。鲁迅因替胡风辩护而尽情暴露左联内部的人事,形迹近于“告密”;尤“糊涂得可观”者,是对于周扬等人的公开批评,“株连”,“诬及”他以外的“他们”,是有违极通常的情理的。他在信中坚持了对胡风、巴金、黄源等人的看法,还称胡风为“鲁府的‘奴隶总管’”,继续进行攻击。此外,还引了鲁迅的话打击鲁迅,说所谓“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者,正是鲁迅自己的行为,鲁迅是企图通过他而打击大批的青年的。最后,他以反语写道:“为鲁迅先生的‘威严’计,我是宁愿发现一切真是如他所说的那样的。不过如果真是那样,则足见两间之正气,一贯的真理,实为鲁迅先生独占得太多,而青年们分有的太少,这在鲁迅先生,当然是光荣的,但对于中国,恐怕也是‘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罢!”
发表前,徐懋庸曾经给周扬等人看过,他们不让发表,怕惹出更大的乱子。但是,他毫不理会这个“集体”的意见。他豁出去了。
自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周扬在文艺界中的地位大不如前,要像先前一样开展工作并非易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组织上人事上的变动。7月底,共产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这时,冯雪峰可以名正言顺地管文艺界的事情。他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改组或撤消原来的文委,停止周扬对文艺界的领导工作。虽然,计划没有最后实行,但是其中的矛盾和压力,周扬不会感受不到的。9月20日,《作家》就曾发表过冯雪峰化名吕克玉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对周扬等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理论上的机械论观点,给予了原则上的批评。其中,称周扬等为亭子间里的“土皇帝”,希望他革除动不动称对手为“反革命”,为“汉奸”,为什么派的恶习,“虚心点,不再胡闹”,都是很严厉的警告。
鲁迅逝世后,文艺界曾经成立过一个临时核心组织,周扬没有参加。卢沟桥事变后,他便从上海到南京,经南京办事处到延安去了。
郭沫若在《苗的检阅》里,指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违反了“对内的纪律”。原来“国防文学”派的人,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徐派”,也有认为鲁迅在公开信中是用了对敌人的讥笑怒骂的态度,对待自己同一战线的人的。于是,《社会日报》闹哄哄地接连发表《鲁老头子笔尖儿横扫五千人,但可惜还不能自圆其说》、《读鲁迅先生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应向徐懋庸先生辩白的几句话》、《梅雨以大义责鲁迅》之类的文章,对鲁迅施以攻击。显然,这是称鲁迅为“托派”、“破坏联合战线”等流言的一脉余波。
鲁迅憎恶那些动辄以维护“联合战线”,捍卫“民族利益”的名义,绞杀个人正当权利的行为,正如当年憎恶那些麇集在“正义”、“公理”的旗子底下,参与镇压学生运动的正人君子者流一样。他甚至把这种纯然从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出发,任意诬陷和打杀民族精英的作法,称为近于“内奸”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社会正义的存在。他所否认的,只是非正义的正义形式而已。而他本人,正是一个独立不羁、无所畏惧的正义者,所以才敢于在所有人都宣称“一致对外”的时候,发动这场“内战”。在他看来,惟有“内战”,才能除去迷幻的毒饵和专事破坏的蚁冢的。这个观点,早在左联时代他就强调过。何况这次“内战”,严格说来并非出于他的发动;只是从他那无法阻挡的凌厉的攻势,以及论战的彻底性来判断,反而显得是挑战的一方。
挑战就挑战。其实,他一点也不在乎名分上的这种纠缠。他习惯了。如今,写下“万言长文”,犹觉意兴未尽呢。文界败象,公开信只不过公开了很少的那么一点罢了。他几次写信告诉朋友说,拟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载过后,再作一文,使徐懋庸辈的嘴脸暴露更加清楚而有趣。
其中,致王冶秋云: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可是,等不到文章写成,他就一病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