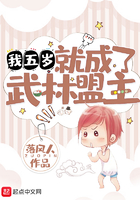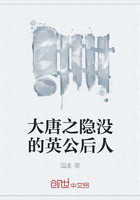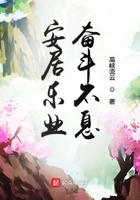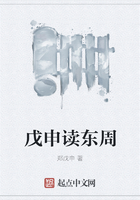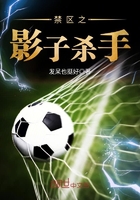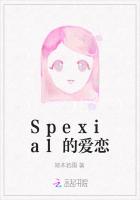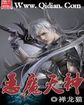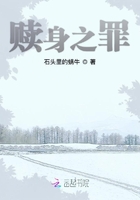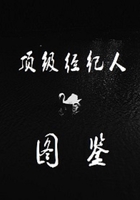鲁迅变得越来越孤独。
他简直不愿意接触任何陌生的客人,尤其是青年。他存在戒心。几年来,与他缠斗不已的,不是几乎全是青年吗?然而,就在他深居简出的时候,又有两个青年人前来纠缠他了。他命中注定要同青年厮混在一起,无论是好是坏。因为,对于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青年是惟一的生机。
这是一对青年男女:一个叫萧军,一个萧红。
萧红,原名张乃莹,出生在中国最东最北部的呼兰河畔。那是白雪的故乡。她一生下来,就被家人当作不祥的种子而加以歧视。父亲是家里的暴君。九岁时,母亲因病故去,她便随同慈爱的祖父一起生活。老人常常抚摩着她的头发,祝福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长大以后,不料境遇反而更坏。二十岁时,残暴的父亲逼她中辍女中的学业,嫁给一个官僚地主的儿子。因为逃婚,她成了哈尔滨街头的流浪者。后来,由于别人的资助,她来到北平读书,但结果,还是被骗回到婚姻的笼子里。在哈市的一家旅馆,那位少爷纵情玩乐,过了一段的日子,突然逃之夭夭,留下她只身作为抵押房租的人质。当此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投稿《国际协报》求援。萧军、舒群查明地址,先后看望了她。借着哈市发大水的机会,萧军偷偷地从旅馆接出萧红,从此作为人生的伴侣,开始了长长的艰难的跋涉。
沿着温暖和爱的方向,萧红继续着她的追求。她的文学和绘画的天分都很高,做学生的时候,就画过电影广告,写过诗和散文。1933年5月开始小说创作,她以特有的抒情气质,写失业青年、佃农、惨苦的妇女,写革命者,写自由之魂。10月,她同萧军合印了第一个小说散文集《跋涉》,署名悄吟。然而,集子问世之初,却立即遭了禁止的厄运!实在太难了!活在这样的中国,要做成一件事情实在太难了!
但接着,两人连立足之地也将要失去,于是不得不像众多的东北流亡青年一样,漂流到关内来。
青岛是第一个停泊点。在这里,萧军任一家报社的副刊编辑,萧红则在家承担所有为家庭妇女所应承担的繁琐而沉重的工作:买菜,劈柴,烧饭,烙葱油饼,甚至变卖家具……在依然艰难的生活中,他们创作不辍,并且开始向长篇掘进。萧军写的是《八月的乡村》,萧红写的是《生死场》,虽然个人气质以及在作风上的反映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一样深切地眷恋着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一样有热血的灌注,一样有不屈服的奴隶的心。他们具备了作为作家的最可珍贵的素质,对于命运的痛苦的皈依。但于创作的前途,却缺乏足够的自信:这样的题材是合适的吗?所表现的主题是否有积极的意义?是否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恰好萧军从当地荒岛书店经理那里得到鲁迅的通讯地址,便鼓足了勇气,以个人名义给倾慕已久的导师发出第一封信。
鲁迅在收信的当天作了回复。针对信中提及的两个问题,他说: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恍如一只孤舟,在茫茫夜海上寻见了灯塔的光芒!两个青年贪婪地读着来信,一遍又一遍,显得那么兴奋。信并不长,但是在他们的眼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都隐藏着深刻的意义,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萧军写了信,并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跋涉》,一起给鲁迅寄出。
就在这时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报社的所有工作即将结束,个别人员也及时作了转移。萧军闻讯,马上给鲁迅发了一封信,然后同萧红一起搭乘一条日本轮船来到上海。
刚刚安顿下来,他们就迫切地想望见到鲁迅。这里固然有着一种感情的牵系,也有着关于文稿的悬挂,但同严峻的生活本身是不无关系的。除了支付拉都路亭子间的房租,买一袋面粉,一只炭炉,一些木炭、砂锅和碗筷油盐之类,临行前从报社领取的四十元路费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样,在大上海,将怎样生存下去呢?……茫然之际,惟觉鲁迅是惟一的依靠,但是,要是不能解决呢?他们想,只要能见上先生一面而被迫离开上海,也当心满意足了……
萧军直接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但是,收到的复信却使他们陷于深深的困惑。“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这种拖延,会不会是委婉的拒绝?
又过了两天,来信重提了见面的事,说:“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就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在这举目无亲的冰原般的世界,现在,他们可以取暖了。信里还提醒说:“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只是这种用心,他们暂时还不可能理解。青年毕竟是单纯而傲岸的。
这回多出了一条内容,就是问候“吟女士”。萧红领头抗议了。
鲁迅的回答很风趣:“中国的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不过因为用滥了,意义变成含糊,所以也就这么敷衍过去。不错,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如这么认真,则即使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现在也有不用称呼的,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式,所以我不用。”这里,他再次说明了一贯主张“硬译”和“重译”的根据,即中国人思维和语言的单一性和含糊性。老拳斗师轻轻一击,两个青年拳击者就伏倒在地了。
在接连的几次通信中,他们知道,鲁迅是深爱着稚气而不安定的青年的。但是,对于他们流露的稚气,他又很不放心。他一再告诉他们: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容易上当、受害。上海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看成虎狼,但也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有一封信,还特别通告说:要警惕白俄。其中,以告密为生的人很不少的。因此万不能跟白俄说俄国话,否则疑心是留学生就将惹出麻烦来……
充满长者的温情的信,常常使萧红想起故去的老祖父。她的心头,乃一次又一次浮起一张有着幽默的微笑的、慈和而又充满战斗激情的面影……
一个月后,渴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两个东北青年急急地来到内山书店。这时,柜台里面,有一个瘦小的老人正在检点着摊放在桌子上的信件和书刊,同两个日本人模样的人谈说着什么……
“你是刘先生吗?”老人瞥见萧军他们,立刻走了出来,问。
“是。”萧军点了点头,低声答道。
“那么我们走吧——”老人说了一声,走进内室,把桌面的东西快速地装进一幅紫地白花的包袱皮里,挟在腋下就往外走,谁也不打招呼。
这就是鲁迅先生吗?这就是鲁迅先生!……
萧军和萧红默默地跟在后面。寒风里,没有帽子,没有围巾;袍子,裤子,网球鞋,几乎全作深黑色。望着老人瘦削的背影,两个人的眼里都涨满了泪水,萧红差点要哭了出来……
鲁迅走路很快。不一会,他们便来到了一家咖啡馆里。
整个厅堂里几乎没有几个客人,其中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鲁迅拣了靠近门边的座位,招呼两个青年坐下,介绍说,这咖啡馆主要靠后面的舞场赚钱,白天这里很僻静,所以他常常把这里当成和陌生人接头的地方。
过了一会,许广平和海婴也来了。
“这是刘先生,张先生……这是密司许……”
鲁迅介绍过后,许广平立即把手伸了过来。萧红一面微笑着,一面握着手,眼前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她太激动了。
席间,萧军说了他们从哈尔滨辗转到上海的原因和经过,还讲述了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底下挣扎和反抗的情形。鲁迅简略地介绍了上海左翼文坛面临高压的现状,以及左翼内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希望他们以后多加注意。
“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他说这句话时,特别缓慢,沉重而有力,如同喑哑的钟声在青年的心头震响……
最后,他把一个信封交给了萧军,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
萧军知道,这是所要借的二十元钱。即使如此,由于回去的坐车的零钱也没有,他还是直白地说了。
鲁迅听罢,笑了笑,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些银角子和铜板,放在桌子上……
把《八月的乡村》的抄稿交给许广平以后,萧军便同萧红一起告辞走了。走时,许广平向萧红说:“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呵!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再见?”萧红没有话,只有默默地扬着手。
走进车厢,他们发现:远处,鲁迅直直地站着往这边凝望,许广平招扬着手帕,小海婴的一只小手也在不停地挥舞,庄重一如远别。
其实,他们很快又在一起聚面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二萧突然接到鲁迅请吃饭的信。地点是梁园豫菜馆。这意外的邀约,使两个青年人同时呆住了。两颗在漂泊生涯中磨砺得近于僵硬了的灵魂,因了伟大的热情的浸润,而变得从未有过的温柔。一封短简,由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然后又转递回来,两只手一起把它平展开来。手在颤抖。字迹模糊。读着,读着,萧红的眼泪就簌簌地落下来了……
赴鲁迅安排的宴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萧军立即抄出一份上海的市街地图,查抄菜馆的位置;萧红跟着出门为萧军买了一块绒布料,日夜赶制新“礼服”。她不能让他像平时那样穿着破罩衫去见鲁迅的朋友们。
除去鲁迅夫妇和小海婴,赴宴的客人有茅盾、叶紫、聂绀弩和夫人周颖,连同萧军、萧红一共九人。此外,还有两个座位空着。
那是留给胡风和梅志夫妇的。按照鲁迅的解释,宴会本为他们的儿子做满月而设,至于缺席,他猜想当是没有接到信的缘故。
酒菜上来后,许广平到门外转了一会,看看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回来向鲁迅耳边说了几句,鲁迅便以主人的身份开始介绍客人。介绍到二萧,特别说明道:“他们是新从东北来的。”席间的谈话常常使用隐语,颇类土匪的暗话,其实他们全是熟识的,只有二萧是“闯入者”。然而,萧军并不客气,他见到聂绀弩尽是不停地给夫人挟菜,也就学他的样子,向萧红的碗里夹取她不易夹到的,或不愿把手臂伸长才能挟到的菜。这样,弄得萧红很不好意思,只好暗暗用手在桌下制止他……
总之,这一顿吃得很好,谈话也很愉快。在归去的路上,他们高兴得彼此挽着胳膊,飘飘然地小跑起来……
鲁迅这次宴客的目的,究其实,还是为了慰抚两位远来青年的寂寞,平日格外给他们多写信,也是这个意思。在通信中,萧军常常感叹在上海没有朋友。除茅盾外,其余包括胡风在内的几个人,此后的确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们都十分珍惜由鲁迅亲自培种的友谊。
其中,叶紫是鲁迅选定作为二萧的向导和“监护人”的。对于萧军的恃强蛮闯,鲁迅一直不大放心,认为必须有人从中加以诱导和制约。宴会结束时,独有叶紫,主动把地址开给萧军,这就和鲁迅的特别介绍很有关系。
叶紫是可信赖的:热情,善良,正直,坦诚,萧军几乎从见面的时候起就喜欢了他。而且,他一样有着曲折的经历。早在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姐姐和叔父都因为参加革命而惨遭杀害,于是开始逃亡。到了上海以后,先后做过教师、编辑,还曾为西林寺和尚抄写经文度日,生活一直非常困顿。目下,他正在同聂绀弩一起编《动向》,有时便带了萧军到几个编辑部之类的地方走走,见见“世面”,或者也可以算作是改造“土匪”吧。
有一次,叶紫告诉萧军:“人们说你浑身有一股‘大兵’的劲儿,又像‘土匪’!”后来,黄源也曾经开玩笑说他“野气太重”。这些评语,颇使萧军感到屈辱,为此先后征询过鲁迅的意见。鲁迅回答说:“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不两样。”因此,他主张不要故意改掉身上的“匪气”或“野气”。由于环境的关系,一个人的习气总会多少有些变化的。但是,他又不得不一再告诉这位单纯的青年,说:“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这样教青年学会沉重,却常常要使鲁迅感到无奈与悲哀。
萧军能够领会鲁迅消解的话,由是,他更加深爱自己的灵魂。奴隶的灵魂。
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正在印刷中,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已经脱稿了。一天,叶紫对萧军说:“我们的书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也应当像点‘公书’的样子,譬如有个社名,有个发行的店之类,这样外面看起来就很有声势,于买书和卖书都方便,而且书官方也不致马上禁售,这是‘私盐官售’的战法……”萧军欣然同意,当即起了个社名,就叫“奴隶社”。至于乌有书店的名称,叶紫管它叫“容光书局”。计划最先出版的十种书籍,相应地,自然也就成了“奴隶丛书”。
他们把关于“奴隶丛书”的总体设想向鲁迅说了。鲁迅十分赞同,说,“奴隶社”的名目是很好的,奴隶和奴才不同,奴隶造反,奴才是不会造反的。在他的支持下,叶紫和萧军以“奴隶社”的名义共同起草了一个《小启》:“我们陷在‘奴隶’和‘准奴隶’这样地位,最低我们也应该作点奴隶的呼喊,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忍耐。”可以说,《小启》是几个不甘做奴隶者面对社会和文坛发出的公开宣言。
《丰收》出版后,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一,《八月的乡村》列为“奴隶丛书”之二,萧红的《生死场》原打算由生活书店公开出版,被检查老爷压了半年多,结果是不许可,只好自费印刷,列为“奴隶丛书”之三。
丛书三种的序文,都是鲁迅的手笔。因为是奴隶写的书,所以自有不同于“为艺术的艺术”的战斗的标准,正是从这里出发高度赞誉了小说的成就。
对于《丰收》,他指出,这个由六个短篇构成的集子,与活在现中国的读者有着大关系。作者虽然是一个青年,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对于压迫者的斗争中,是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的。回顾封建专制的历史,他指出,中国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著作,文学作品更不必说。然而,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实,《八月的乡村》却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他几次引用胡适“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话,然后说,这书是于“心的征服”有碍的。一方面是奴隶,一方面是奴才;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序文以黑白分明的比较,显示着小说的主题: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生死场》同样是一部不能见容于中华民国,大背“训政”之道的作品。他十分欣赏作者以女性的笔触而能越出常轨,富于力度,它是能给奴隶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
丛书从写稿到出版和发行,耗费了鲁迅的大量心血。《八月的乡村》是萧红用很薄的日本美浓纸抄写的,字又小,几乎每页都要衬上一张白纸才能看清楚。为《丰收》代寻木刻家插图,也颇费周折,最后还是自己拿出五元钱,买了木板,交给黄新波刻制。即使短序一篇,也都颇费苦心,如《生死场》刻画人物的缺点,到了鲁迅这里,评介就转换成了另一种肯定的方式:“叙述写景,胜于描写人物”,显然意在袒护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难怪官方的走狗报纸对“奴隶丛书”的狂吠,总是处处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
——这个老奴隶!
总之,鲁迅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推举年轻奴隶。在此前后,他曾经向美国记者斯诺和伊罗生介绍了大批左翼作家的小说;在自己编选的中国小说集中,也都是侧重于后起的一代的。
斯诺是通过宋庆龄认识鲁迅的。他同情中国革命,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感受鲁迅的伟大,认识到鲁迅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启蒙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心灵的相通未必依赖神圣的血缘关系。不同的国度存在着同一度思想空间。鲁迅一直认为,有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热爱,是远在于同胞之上的,因此他愿意聆听他们对中国的诅咒,而不能接受炎黄子孙在祖先祭坛上的喃喃颂辞。从接触中,他觉得斯诺是明白的、可信任的。因此,对斯诺和他的助手姚克共同编译的小说集《活跃的中国》,始终给予热情的支持。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有一次,鲁迅向斯诺说道:“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奴隶的命运,在他的思想中,一直是缠绕不散的基本主题。
“既然国民党已经进行了第二次革命,难道你还会认为阿Q跟从前一样多吗?”斯诺问。
“更坏。”他大笑道,“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那么,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
“我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读过很多关于俄国革命前的东西,知道同中国很有些相似之处,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当然也可以学习美国,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还应当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当然,他所谓向民族的历史学习,是旨在寻求现代化改革的现实根据,而不是对专制主义传统的眷顾或回归。在这里,他展示了中国改革道路的多种可能性,他反对任何国家不变的模式,而倾向于批判的综合,主体的选择。
《活跃的中国》的编译工作,最先在上海进行,后来斯诺移居北平,便通过姚克同鲁迅保持直接的联系,持续几年,终于在1935年完成。正是接受了鲁迅的建议,他们才在专译鲁迅的原定计划的基础上,选择了柔石、张天翼、萧军、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斯诺在介绍《活跃的中国》时,特别指出它的思想价值,说:“作为艺术,这本小书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是中国文学中抗争和同情的现代精神日益增长的重要表征,是要求最广泛规模的社会公平的重要表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第一次确认‘普通人’的重要性。”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人民性、战斗性,是主要通过“现在新出台的作家”去表现的。
伊罗生选编的《草鞋脚》,是与《活跃的中国》属于同样性质的中国小说集。
鲁迅同茅盾一起,应伊罗生的要求,完成本书的初选工作。为了介绍新人,他们努力推荐哪怕是幼稚、脆弱的作品。“草鞋脚”一词,来源于鲁迅的演讲,书的序文也是鲁迅作的。在序文中,他指出,这“新的小说”,是战斗的产物,是“文学革命”时代的关于“人性的解放”这个文学基本要求的又一发展。为了文学事业的进步,许多青年在黑暗中以生命殉了他的工作。
如果说《活跃的中国》和《草鞋脚》是一个横切面,所显示的是中国小说的现实状况,那么手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则是一个纵剖面,呈示着新小说的创始阶段的全历程。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出版的大型文学选本,时间跨度很大,包括从1917年至1927年间的理论和作品,可以看做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总结。小说共分三集,第二集即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其他文学团体和作家部分,计划由鲁迅负责编选。当编辑赵家璧找他具体商议的时候,他就考虑到了检查官的问题。鉴于书报审查制度的严密,又要确保选本的客观性和完整性,鲁迅认为以他这样被政府通缉的“堕落文人”身份是不大相宜的。赵家璧答应愿意在通过审查方面作出努力,他便把事情答应下来了。果然,官方要将鲁迅的名字从编选者中除掉,另换别人。良友公司方面只好走后门,收买检查官,以保证鲁迅的选本和序文不受损害。
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这时候,鲁迅突然通知说“决计不干这事”了。
原来,他所写的《病后杂谈》发表时,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使他大为愤懑。他不想中检查官的诡计,把自己为《大系》所写的序文重新送交断头台,并声明,要用硬功对付他们。这件事弄得赵家璧相当紧张,再度约见鲁迅,把《大系》的整个进程说了,恳求收回成命。书店方面因此而白折费用,自然也在他的考虑之中。在赵家璧答允争取做到保持选本导言的本来面目的情况下,他犹豫良久,才决定着手编选。
他也不是不知道赵家璧的难处的。所以,临别时说,将来序文和选稿送审后如有删改之处,可由书店方面代为决定。
在这部艰难编就的小说集中,对于与他彻底决裂的“狂飚”的一群,虽然有所批评,却并未遮掩他们曾经有过的光耀。他不但收入了这些青年的作品,还在导言中摘录了高长虹、向培良等的大段引文,展示他们的特色和成就。
他喜欢他们的讥刺、暴露、搏击,喜欢他们内心的热烈,且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奴隶的。集内还收编了为他一度讽刺过的陈源夫人凌叔华的作品,而且做出肯定性的评述,指出:她以谨慎的文风,创造了与众不同的人物,从而显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重要的是不要忘却“世态”。一些“才子”所以为他所憎厌,都因为连这么一点俯视人世的真诚也没有。而做人的真诚不是容易具备的。
萧军写信给他说,高尔基对人民的爱是近于母性的,容易流于姑息。他回信说,在他自己,大约也是属于“姑息”一面的。其实,战斗者并非与“宽容”相敌对。不懂“宽容”为何物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斗者,自然,也惟有战斗者的宽容,才是卓具成效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