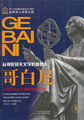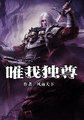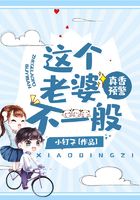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证上帝和清楚明白的关系上笛卡尔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我们还记得,他在论证上帝存在时,是以清楚明白为根据的。基本的步骤是这样的:我心里上帝的观念是如此的清楚明白,所以上帝的观念就是真观念;而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不可能是我有限的理智所能创造的,他一定是由某种原因刻印到我的心里,根据原因一定包含着结果的原则,那就一定有一个外在于我的上帝存在。可是当笛卡尔再转回头论证内心里的“清楚明白”时,他在第五个沉思里却说:“当我认识到有一个上帝之后,同时我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取决于他,而他并不是骗子,从而我断定凡是我领会得清楚、分明的事物都是真的”,“一切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取决于对于真实的上帝这个惟一的认识,因而在我认识上帝以前,我是不能完满知道其他任何事物的”。由此我们看出,当笛卡尔论证上帝时,是以“清楚明白”为根据的,而当他论证“清楚明白”时又是以上帝的存在和被认识为根据的,这就是一种循环论证,这个论证被阿尔诺称为“笛卡尔圆圈”,即:如果笛卡尔的纲领的确是一种激进的“摧毁一切,完全从基础重新开始,那么,假定他完全抛弃了先前的信念,他在重建的第一步就不用必须去预先假设他并没有赖以建立的结果了吗?1648年,笛卡尔会见德国年轻的学者博曼时,两人曾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笛卡尔回答道:“当我实际上正在关注一个完全清楚明显的命题时,并不需要神的保佑;一个清楚明显的命题并不具有超出我当下感知的额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可能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的怀疑论纲领,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极端的。”
第五,针对信仰、理智和真理问题,反驳者指出:笛卡尔认为意志只有在正确理智的指导下才能达到目的,反之则失败。那么你把信仰又放在什么位置呢?如果按照笛卡尔的推论,对一个不信基督的野蛮人,当他不信基督的时候不能成功,即便他信仰了基督,如果没有正确的理智指导仍然不能成功。这个问题的本意就是要问笛卡尔,在追求真理的问题上,信仰和理智哪个更根本。这其实也是17世纪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笛卡尔对这个问题有些吃惊,他本以为这几乎应该是个自明的问题,可竟被这些有学问的人们提了出来,“我奇怪你们会怀疑当意志按照理智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行事,就有达不到目的的危险;因为,假如它所按照其行事的东西不是被清楚认识的,谁能使它靠得住呢?有谁(不管是哲学家也好,神学家也好,或者仅仅是运用理性的人也好)不承认,在给予同意之前领会的越清楚的东西上,我们所面临的达不到目的的危险就越小,而那些对于原因还不认识就贸然下什么判断的人就会失败?”
关于信仰问题,笛卡尔在此做了一个调和,他说,有人认为“信仰是对付模糊不清的东西,可是我们之所以信仰那些东西的理由却不是模糊不清的,而是比自然的光明更清楚、分明的”。
笛卡尔在这里很巧妙地把信仰分为形式和材料两方面,笛卡尔认为,我们之所以要信仰,是因为我们相信那种东西是真的,这正是推动我们去信仰的动力,不断地追求这种真正的东西就是推动我们信仰的动力。“我们的意志由之而能够激发起来去相信的那种清楚性、分明性有两种:一种来自自然的光明,另一种来自上帝的恩宠。”至于说我们所信仰的材料,“从来没有人否认它可以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它就是模糊不清本身”。
从笛卡尔的上述言语中不难看出,他所谓的信仰,早已不是中世纪的信仰,在他的信仰中孕育着新时代的种子。笛卡尔明确指出,信仰追求的目的和动力都是为了“更清晰分明的东西”,来自信仰的动力不仅仅只是“上帝的恩宠”,还有“来自自然的光明”,在这里,他无形中就用理性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削弱了上帝的力量,也许笛卡尔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作用,他的本意只是为了协调信仰、理性和真理三者的关系,可他的这个协调作用本身就是对上帝的地位和作用的动摇和削弱。难怪宗教界人士对他提出这样和那样的非难,他们所维护的是宗教原来的势力,他们似乎已感觉到笛卡尔柔弱、中允的背后所蕴含的革命和叛逆。
至于反驳所谓异教徒的事,笛卡尔是这样回答他们的:“我敢说,一个不信基督教的人,他被排除于任何超自然的圣宠之外”,但是这些异教徒们“由于受到某些错误推论的引导,他也会信仰和我们所信仰的同样的那些东西”,尽管这种信仰是自发的,他们也有可能获得某些成功。,他们的失败并不是来自于上帝的惩罚,“他之所以犯罪是由于他没有很好地使用理性”。在笛卡尔的宗教观里,包含着宗教的宽容和自由,人与理性在人的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的错误和罪过是由于没有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人为自己承担了失败的责任。
笛卡尔还把探讨真理的活动与日常生活加以区分。他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等到事事都弄得清楚明白才去行动,“我主张甚至用不着总是等待会有可能的事物,而有时必须在许多完全不认识和不可靠的事物中选择一个并且决定下来”。至于探求真理的认识活动,笛卡尔认为,那就应该遵循他所发现的认识规则。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区分开来是有一定的好处了,他既可以划清界限、澄清是非,也避免了人们的误解和保守势力的反对。比如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有明确的使用界限的,它仅仅用在探求真理前的排除阶段,作为方法论,它要求人们对未经理性思考的东西不能无条件地加以接受,但他并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地怀疑一切,倘若如此,那就由于违背生活规则而成为世人的笑柄。笛卡尔不会使他的理论重蹈怀疑主义的覆辙,在这方面,笛卡尔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
第六,反驳者提出,笛卡尔一方面认为上帝的本质和存在是统一的,另一方面“我”是不完满的,既然不完满,就不可能认识完满的上帝的本质,那你怎么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呢?“你自己也承认你不过是不完满地懂得无限……既然凡是在上帝里边的东西都是完全无限的,那么什么精神能够非常完满地懂得上帝里边一点点东西?你怎么能够足够清楚、分明地观察了上帝是什么呢?”笛卡尔首先指出反驳者在这个问题上三段论式的错误,然后指出上帝的本质和存在是统一的,因为上帝本身的无限、永恒、完满决定了他存在的必然性,如果我们否认了上帝的本质,那么,“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将既无丝毫理由,又无任何根据而被完全推翻”。笛卡尔认为,虽然“我”不完满,但依我们所拥有的理智“足以认识上帝的本性是可能的”,至于我们在认识上帝的本质和存在时所产生矛盾,其实并不是上帝的矛盾,而是我们自己思维中的矛盾,“一切矛盾性仅仅在于我们的概念或思想里因为它不能把互相矛盾着的观念结合到一起,并不在于在理智之外的任何东西里”。笛卡尔还从逻辑上反驳了对方的一些错误。
第七,反驳者提出笛卡尔关于灵魂不死的论证不充分,而且提醒笛卡尔,仅仅从灵魂和肉体的区别中并不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他们希望笛卡尔能用几何学方法来论证上帝的有关问题。
笛卡尔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认为,关于灵魂不死主要“取决于上帝的纯粹意志”,远不是人类的理智力量所能规定得了的。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方法,认为只有把灵魂和肉体区别开来,才能看到它们的性质,肉体和灵魂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笛卡尔认为,目前还没有什么事例和根据让我们相信灵魂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至于有人提出上帝可以使灵魂随着肉体而消亡,笛卡尔不屑一顾地说:“这只有由上帝自己来回答。”看来,对灵魂不死等问题,笛卡尔宁愿把这类问题交给宗教界解决,而不愿在此做更多的论证和结论,更不愿陷入宗教界的争论之中。
“在你们向我提出的东西里,我看不出有什么是我以前在我的沉思里没有解释过的。”看来,笛卡尔对神学家和学者们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并不是很满意,不过他还是接受了他们的一些建议,对自己的写作风格做了解释,还特地按照几何学方法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及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笛卡尔认为,自己叙述的次序是,“提出的东西应该是用不着后面的东西的帮助就能认识,后面的东西应该是这样地处理,即必须只能被前面的东西所证明”,笛卡尔的方法实际上遵循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笛卡尔认为,自己的证明方式是“分析法或决定法”,所谓分析法,按笛卡尔的理解:就是“指出一条一件事物由之而被有条不紊地发现出来的真正道理,同时也指明结果如何取决于原因”。他认为古代几何学运用的是综合法,是自结果中检查原因。但他们并不是不用分析法。笛卡尔认为分析法“是最真实、最好的教学方法”。他希望在沉思中运用分析法“清楚、分明地领会第一概念”。为认识和发现真理寻找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规则,这正是他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
笛卡尔附在本答辩后面的《按几何学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区别的理由》一文也是非常值得一读,他不但对思维、观念、客观地、形式地和卓越地等概念做了精确的定义,而且为了便于与读者的理解与沟通,他还对读者提出了7条要求,最后又论证了一些公理和命题。
2.群英会战与霍布斯的直接辩论
当笛卡尔把他的书稿转给在巴黎的好友麦尔塞纳时,霍布斯当时也恰巧正在巴黎。他当时正因自己的著作《利维坦》而在法国避难,他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曾当过弗兰西斯·培根的秘书。这个大笛卡尔8岁的哲学家,也是个“赞赏数学方法的人,不仅赞赏数学中的数学方法,而且赞赏数学应用中的数学方法”,他的性格和笛卡尔正相反,率直、果断,“不耐烦做精微细腻的事情,太偏向快刀斩乱麻……比较善抡巨斧,不擅长挥舞细剑”。这两个思想观点和性格迥异的人在进行辩论,一定很有意思。
笛卡尔大概也了解这位重量级对手,他对霍布斯的重视还源于他对唯物主义者的根深蒂固的成见。所以,他一上阵就摆出了一副好斗的架式,在对方每一个反驳之后展开反“反驳”。但由于两人基本的哲学观点不同,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说话,所以一开始双方思想的交锋并不激烈,倒是情绪化的东西多了些。后来辩到上帝、人的精神等敏感问题时,霍布斯拿出了他的杀手锏,连连出招,咄咄逼人,非要笛卡尔把这些问题说个清楚,而笛卡尔则步步后退、忙于招架,有时显得不自信、不耐烦,在争论中并不占什么便宜。也许,笛卡尔适合当帐中的谋士,而不适合当战场上的斗士。一个人在家静静的思考,或许适合他的特长和爱好。
好了,我们这些观众甭唠叨了,还是请我们的辩手出场吧。
第一个反驳
霍布斯真是快人快语,说:笛卡尔怀疑这怀疑那,这也不可靠那也靠不住,感觉与想像、梦与醒都给我们提供不了什么可靠的东西。这一套并没有什么新意,柏拉图和那个时代的怀疑主义者早就提出来了,想不到,一位优秀的思想家竟然提了这些老掉牙的问题。
霍布斯可能委屈了笛卡尔,他大概并不了解笛卡尔怀疑的本意,这么贸然地数落人家,笛卡尔当然不高兴了,再加上本来就有的成见,所以就申辩到:“我讲这些怀疑理由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荣誉”,看来,你霍布斯对怀疑主义的理解还是有局限的,“我之所以使用了怀疑理由”,一方面是为了“把理智的东西和物I体的东西分别出来”,以便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发现真理。使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有个坚实的基础,不至于被各种形形色色的怀疑主义理论所动摇。就好像医生看病,必须先把各种病症描述出来。
第一次交手就闹了个不愉快,笛卡尔尤其看不惯霍布斯居高l临下的样子,心想,连我的意图还搞不清,就板起面孔教训人。不过,笛卡尔毕竟还有绅士风度,给霍布斯解释了自己怀疑的真正用意。
第二个反驳
双方的第二次争论主要围绕“人的精神本性”来展开。霍布斯对这个主题的反驳是通过他的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反驳来完成的。
霍布斯并不反对笛卡尔的“我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但他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推论上有毛病,“因为我认为:说我是在思维的,因而我是一个思维,或者说,我是不理智的,因而我是一个理智,这样的推理是不正确的”。霍布斯认为,笛卡尔的错误就在于把体和用、实体和功能混淆起来了。把有理智的东西和理智本身、在思维的东西和思维、跳跃者和跳跃混淆起来了。霍布斯指出:“笛卡尔把有理智的东西和理智(它的前者是行为(用))当作一回事了;或者至少他说在理解的东西和理智(它是一个有明智的东西的一种能力或功能)是一个东西。可是所有的哲学家都把主体<体>跟它的功能和行为(用>,也就是说,跟它的特性和本质分别开来。因为这跟东西本身的存在和它的本质不是一回事。”霍布斯说,既然笛卡尔能推出“我思故我在”,那么,“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推理说:我是在散步,所以我是一个散步”。
霍布斯并不满足于这个类比,他要进一步追问:“我认识到了我存在,现在我追问,我认识了我存在这个我究竟是什么?”“没有主体<体),我们就不能领会任何行为(用),就像没有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就不能领会思维,没有一个在知道的东西就不能领会知道,没有一个散步的东西就不能领会散步一样。”“我们不能把思维跟一个在思维的物质分开,我们似乎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是物质的,而不是非物质的。”
由于双方是书面交流,霍布斯反驳在前,笛卡尔答辩在后。所以,霍布斯没有机会听听笛卡尔的意见,由于对笛卡尔整体思路的误解,霍布斯还在沿着自己的思路提问。笛卡尔似乎意识到他们两人的分歧所在,他在答辩中一连纠正了霍布斯的几个误解,然后,无不感叹地说:“我坦率地承认,为了说明一个东西或一个实体,我是要把凡是不属于它的东西都从他身上剥掉起见,我尽可能使用了简单、抽象的词句;而相反,这位哲学家为了说明同一个实体,却使用了另外的一些非常具体、非常复杂的词句,比如主体、物质以及物体,以便尽可能地不让把思维和物体(或身体)分别开来。”看清两个人不是一条道的车,笛卡尔似乎也明白了为什么在辩论中各说各的话。他摆出一副叫阵的姿态说:“但是不要再多说空话了,还是让我们看看问题的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