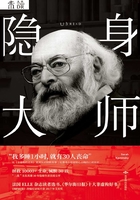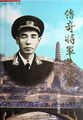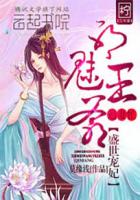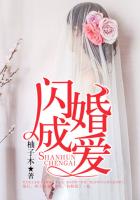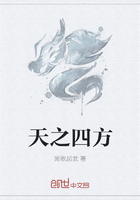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面临着治水的难题。在张居正当政时期的明朝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明朝治水不仅有着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的考虑,而且还有着特殊的政治、军事考虑,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考虑,使得张居正这个并非水利专家的政治家煞费苦心!
积重难返的水利难题
治水的问题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面临的大事,明代也不例外,张居正身处的时代,南北的粮食运输主要依赖运河,而运河又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官员提出了修筑新河的想法,最终却因为不切实际,被张居正否定了。在否定这个提议的过程中,张居正同样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可是北方并不是当时的产粮地区,其他经济也不发达。
明朝真正的经济中心在南方,尤其是在苏杭二州,这里是当时的产粮大区,有着“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由于这个原因,北京政府所需的各种物资,包括每年所需的四百万石粮食,都是从南方调济过来的。要调济物资,自然就需要做好交通运输工作。然而,当时从南方到北方的物资运输路线,就只有一条大运河。
有人会觉得,有了这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还需要为运输物资发愁吗?这样的想法其实是缺乏对大运河情况的仔细了解的,大运河实际上并不像书本上或者传说中说的那样便利和畅通无阻。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运河到洪泽湖时,就会遇到从安徽流来的淮河,这条河会在运河的清口与黄河交汇。这里是第一道难关,因为一旦遇到黄河涨水,就会堵塞河道,运河就无法运输;再接着往上走,当运河到达徐州的茶城时,接替运河工作的就是黄河,也就是黄河的这一段便是运河,这里是第二道难关,也是最危险的关口。因为黄河做运河,遇到涨水时水量太大,会使南方的粮船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而遇到枯水季节水量又太小,粮船便要搁浅在河中,无法顺利到达北京。
大家想想看,这样一条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运河,怎么能够担当起为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运送物资的重任。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北京事实上处在国防第一线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南方的物资一旦不能顺利运到北京来,不仅关系到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温饱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大明朝的国防安全。
可是,就是这样一条至关紧要的运河却老是发生问题,这怎能不让人为此发愁?
张居正就是为了这条很成问题的运河煞费苦心!他也知道,将整个国家、北京的安全和温饱完全交给一条根本无法捉摸和控制的运河,是很危险的事情。不出事则罢,一旦出事就肯定小不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尽快想办法治水。张居正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就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黄河在邳州决口了。这样一来就使得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的黄河水很快变浅,正好将前往北方的粮船搁浅在黄河里,一概不能北上,情况异常紧急。可是,又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治水呢?
在张居正当政之前,曾经提出过两种解决运河问题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不一定非要依靠运河,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海运来解决南方物资的北调问题。提出这种办法的人还设计了一条海运的路线:从太仓、嘉定沿东海航行,就可以到达天津;到天津后无论陆运还是河运就非常方便了。
路线虽好,却不能保证运粮船在海上不会出问题,因为那时的航海技术毕竟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当使用这个办法出现事故之后,明朝政府就没有再利用海运进行南粮北调了。第二种办法就是修胶莱新河。正是在对是否应修这条河的争论中,张居正第一次碰到了治水的难题。那么,胶莱新河是怎样一条河呢?张居正对开通胶莱新河持什么态度呢?
胶莱河是发源于山东高密县的一条人海河,有两条支流,一条在北边,一条在南边。由于南边的支流在胶州的麻湾口人海,因此被称为胶河,而北边的支流则在山东掖县的海仓入海,所以被称为莱河。两条支流之间隔着一个高大的分水岭。那么,什么是修胶莱新河的计划呢?胶莱新河其实就是将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从中凿开,开通一条水道。可是,开凿胶莱新河能解决运河的问题吗?
在提出这个办法的人看来,胶莱新河可以替代一段异常危险的海运路线,进而将原来的海运路线变成如下情况:从南方出发的运输船先走海路,到达胶州麻湾口时,逆流而进入胶河;在胶河航行一段之后,就往北进入新开凿的胶莱河,一直航行进入北边的莱河。只要运输船能够顺利到达莱河,剩下到北京的航运就是从莱河的海仓口再度入海,再往北航行一段海路就可到达天津。
这个主意看起来的确不错,因此它一被提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隆庆四年黄河再次决口之后,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给事中李贵和就上疏请求修胶莱新河,内阁大学士高拱同样极力赞同修胶莱新河。不仅是他们俩,朝中的大臣几乎都赞成这样做。可以说,当时的明朝政界,几乎都在为这个近乎天才的创见摇旗呐喊!
那么,张居正对于修胶莱新河的主张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跟高拱一样,张居正同样出于为国为民之心,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妥善的办法能够解决运河的问题。开通胶莱新河的主张一提出,张居正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思考。他在思考什么呢?
其实,他是在从现实的角度思考开凿胶莱新河到底行不行得通。的确,作为一个手握重权的内阁大臣,不能跟那些手下一样,听风便是雨,一见到理论上可行的解决运河的办法,就兴奋得忘乎所以,根本不计较事实情况了。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示了他作为成熟政治家的稳重和审慎。
让张居正首先就觉得为难的问题是:水源如何解决?什么意思?前面已经说过,在胶河和莱河之间的分水岭是个高大的山岭,暂且不计算把它开凿通了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先思考一下即便是开通了河道,那么河里的水从哪里来?
有人会问:不是在沟通两条河吗?何愁没水呢?这样想的人就有些不顾实际情况了。仔细想想,这个河道不是在平原上,更不是在低洼的盆地,而是在丘陵和高山地区,这样的地势,就算开凿出了连通胶河和莱河的河道,这两条河里的水也进不来!如此说来,胶莱新河还是有问题!
对于这些需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的问题,谨慎的张居正都一一考虑到了,在他的心中已经拿定主意不赞同开凿胶莱新河。然而,这个时候的朝廷上下似乎已经对开凿新河呼声一片。对于大多数大臣,张居正倒不用顾忌,让他顾忌的是高拱。
前面我们讲过,高拱虽没跟张居正有过直接和正面的冲突,但是两人同为内阁大学士,一为首辅,一为次辅,而且都很有才干,自然不能相容了。因此,当自己的意见与高拱出现不合时,张居正就觉得千万不要因为治水而得罪了高拱。
可是,胶莱新河是决计不能开的。又该怎样说服高拱和一帮不理性的大臣呢?张居正想到了这样一个好办法:他让给事中胡槚前往山东进行实地勘察。
为何要选这个人呢?原来,胡梗是高拱的亲信,而且最重要的是胡槚是一个有主见、看重实际调查研究的人。张居正也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个身份和性格,于是来了个一石二鸟之计。至于高拱,见到张居正派自己的亲信前去勘察,自然是一百个同意。就这样,胡槚去了山东。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果然证明张居正的考虑没有错——开凿胶莱新河有太多的现实困难,胡槚也主张不开胶莱新河了。
由于张居正的明智,他既没有得罪自己的政敌,也阻止了肯定会没有成效的胶莱新河的开凿。
在得知胡槚从山东传回来不能开凿新河的消息后,张居正在给胡槚的一封信里说起了自己的心思:
“始虑新河水泉难济,臆度之见,不意偶中。辱别揭所云,剀切洞达,深切事理……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张文忠公全集·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由于是给胡槚的书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张居正是在胡槚面前极力褒奖高拱。张居正首先谦虚地说自己已经料到修新河是不行的。他知道,高拱本来是赞同开凿新河的。可是经张居正一说,竟然变成了“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
张居正甚至为高拱辩护:“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这样说来,高拱的确没有什么错了,连领导的判断失误也被张居正说成是由于忧心国家久远之计所致。张居正的政治素养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进退两难的治河窘境
水利始终是明王朝的一大问题,水患导致的运输危机使得张居正寝食难安。为此,他咨询下属,详细研讨各种方案,最终,提出的数种方案都是无疾而终,张居正的治水努力宣告失败。
尽管如此,运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张居正只好继续苦心思索。万历头两年,那条问题成堆的运河总算让张居正和朝廷上下缓了口气——竟然没有出问题。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和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运输四百万石粮食的船都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张居正兴奋地给河槽总督王敬所去信:
“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无任忻慰。闻度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可以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漕王敬所》)
在这封信里,张居正显得正满怀着信心和希望。他一面在为运粮船的顺利到达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甚至都在准备着国库充实之后的国家计划了。或许,这时的张居正认为,运河可能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吧?这两年都这么顺!可是,第二年,也就是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一场大水,又让他费尽了心思。万历三年,黄河暴涨,水量特别大,在砀山决口了。肆意的黄河到处流淌,很大一部分由淮安进入运河,甚至直接流到了长江。如此一来,江淮和扬州一带就面临着发生水灾的危险。这场大水让张居正寝食难安,他既担心百姓的身家性命安危,更担心这年南方物资的北调。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明朝政府之前解决黄河水患的主要办法就是修筑堤岸,也就是用堤岸拦挡暴涨的河水。有人可能会问:明朝人为什么非筑堤不可呢?这里的原因在于明朝人治河,必须遵守如下的几条原则:
第一,黄河到徐州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南流,因为黄河向南流的话就会破坏掉明朝皇帝祖墓的风水。
第二,黄河到开封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北流,因为黄河向北流就不能向南回流,这样就会使得淮、徐一线的漕运发生问题。
第三,即使没有过徐州的黄河也不允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很容易便会出现浅滩,肯定会阻碍一边运粮船向北,另一边空船回南的路线。
正是由于有这几个原则,所以即使在黄河肆意成灾,洪水漫流的情况之下,明朝人也不会想办法改河道,只是沿岸筑起高堤抵御洪水的侵袭。可是,肆意的黄河水哪是抵御得了的?万历三年的黄河决口,就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刚听见黄河决口的消息,张居正还不怎么了解实情,因此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妥善的解决方案。无奈之下,他只好给河道总督傅希挚写信:
“近闻淮、扬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横决四溢,今不治,则河且决而入于江,维扬巨浸矣。又有言前议筑遥堤为不便者。其说皆信否?从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归,望公熟计其便,裁教。幸甚。”(《张文忠公全集·与河道傅后川》)
看来,张居正对当时的情况的确不怎么熟悉,他不知道到底是由黄河人海口淤堵导致黄河决口,还是筑堤岸的原因,因此希望傅希挚说清楚点儿。
傅希挚回了一封信《治河议》,但是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张居正于是再次写信给他询问情况以及傅希挚的解决办法:
“辱示《治河议》,一一领悉,但据公所言,皆为未定之论。海口既不可开;遥堤又不必筑;开洳口,则恐工巨之难;疏草湾,又虑安东之贻患。然则,必如何而后为便乎?愿闻至当归一之论,人告于上而行之。”(《答傅后川议河道》)
从这封信我们看得出来,张居正的确很着急,他急着想要找到一个“至当归一之论”,也就是确定一个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情况紧急呀!张居正怎能不急?
在张居正的催促之下,傅希挚想到了曾经有人提出过的开通洳河的办法:首先,由于洳河有两个水源,一个在峄县,一个在费县,因此被人们称为东、西二洳河;因此接下来就将北边的微山湖、赤山湖和中间的东、西洳河以及南边的沂水、宿迁骆马湖用水道连接在一起,最后则把这条水道引入黄河。在仔细思索之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二月,傅希挚向明神宗上疏,将开通洳河的计划提了出来。在他看来,与其花费大量费用在其他一些没有多少实际效用的水利工程上,还不如一次多花点儿用于开通洳河上。这种思想是可取的,但是对于一向看重实效和希望节省财政开支的张居正来说,还是觉得不甚妥当。于是,当傅希挚上疏以后,张居正就在户、工二部正在商议以及在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的请求下召开廷臣会议的时候,给傅希挚写了一封信:
“开河之策,议在必行,但以事体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费度七、八百万乃足者,岂其然乎!故请差科臣会勘,徒以息呶(音同“挠”)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大之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道总督傅希挚》。)
张居正的意思是:“现在说要修河,很有可能是要修的,但是事关重大,甚至有人说要花七八百万的钱,因此需要仔细斟酌。因而,派来了人亲自考察。这件事情,以前也有大臣提起,知道它的便利之处,只是由于任务太重,没有人敢担当。现在你既然要担当,你就要坚持己见,仔细办理。”
自然,这封信表达了张居正的忧心,然而他仍然寄希望于傅希挚,希望他能够“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然而,这个傅希挚恰恰就没有把“其中事体”详慎思考。在经过侯于赵的亲自勘察之后,勘察大臣认为要开通洳河,是不太可能的。原因在于,如果开通这条河,就一定要经过良城,那便意味着需要开凿和搬运走这里的五百五十丈石地,工程太过庞大,所需经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商议之后的户部官员认为,“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洳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洳为缓。”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只能用来解决今年的水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万历三年的六月,明神宗下旨不再开通洳河。
大臣们一个人一个意见,自然惹得神宗不开心了。在神宗看来,正是要这帮子人干实事的时候,却“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根本没有人愿意“视国如家,忠谋远虑”。但是,他这样说,也不是怪罪傅希挚,只是将怒火发泄到了河道的其他官员身上。傅希挚接到圣旨后也没有办法,只好停止了开通洳河的计划,专心去做治河的工作去了。而张居正也只好再次认栽:谁让自己不是水利专家呢?遇到水利问题就只好请教属臣,可是一直以来又没有真正遇到治水的人才。真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在明神宗的那个圣旨中,流露出了愤恨和着急,其实那也是张居正的心理状况。
然而,无可奈何也罢,心急也罢,愤恨也罢,总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物资运输的问题呀!现在不能开洳河了,北京需要的四百万石粮食又不能依靠正在肆意泛滥的黄河,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这次真是快愁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万历三年的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和右侍郎徐栻上疏再次请求开通胶莱新河。主张开新河的两人都是和张居正同年考上进士的,因此关系一直不错。尤其是刘应节,这个人是山东潍县人,他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应该还记得,上次大臣们提议开胶莱新河的时候,张居正曾经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胶莱新河的水源难找。但是,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黄河到处决口,开通洳河的计划又落空,目前看来也只有走一下开凿胶莱新河的路子了!张居正为什么这次比较有把握呢?一方面,计划是刘应节提出来的,张居正对他非常信任;第二方面,从那次提议开凿新河到现在,经过几年的财政整治,国库变得充实起来,因此有财力应付工程所需。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毅然决然地对开凿新河的计划表示支持。他派了徐栻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一起开凿新河。在他给刘应节的信中,大家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决心:
“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读大疏具见忘私徇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凤竹公肯身任之,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张文忠公全集·答刘百川言开胶河》)
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批评了那些认为不能修胶河人,说他们其实是出于私心。接着,他对刘应节“忘私徇国”的忠诚表示欣赏。他同时还称赞了徐栻担当重任的精神,希望他们能倾力合作。
不仅张居正,明神宗也是大力支持,君臣上下似乎这次都下定了决心,神宗更是在上谕中严厉地说:“朝廷屡议开河,止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
大家都对刘应节和徐栻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开辟出一条新的水道,进而解决南方物资北调的老问题。
可是,就在上下齐心,准备打一场水利攻坚战时,问题又出现了!首先是山东民间的舆论对于开凿新河不利。在民间看来,一旦运河的河道改变,就会使原来沿河道的商业经济受到损害,对于山东西部的发展十分不利。这自然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但是,撇开这一点不提,山东民间对于开凿运河还是不支持的声音占上风。为什么呢?原来,开凿新河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劳役,很显然这些劳役就是从山东本地而来,因此就给百姓带来不小的麻烦。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山东的舆论大都反对开凿新河。这样一来,山东巡抚李世达坐不住了。随着事态的严重,就连徐栻也心生动摇和犹豫。对于这个情况,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他立即给徐枝去信,以安定他的心:
“仆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明主方励精图治,询事考成,岂宜以未定之议,尝试朝廷哉?神禹大智,犹必亲乘四载,遍历九土,至于手足胼胝,而后能成功。方其凿龙门之时,民皆拾瓦砾以击之。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愿公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滞顾忌,调停人情之说,一切勿怀之于中,又亲历工所,揆虑相度,分任责成。若惮劳不亲细事,徒寄耳目于人,则纷纷之议,将日闻于耳,虽勉强图之,亦具文而已,决不能济也,幸公熟图之。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此国之大事,不敢不尽其愚,幸惟鉴有。”(《张文忠公全集·答徐风竹》)
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说,做事太过就不能把事情做好,他援引了大禹治水时期遭遇民间反对的典故,通过分析民间的心态,敦促徐栻“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意思就是要徐械能够做事果敢,不要轻易听信他人,不然勉强做事,必不能做好。但是,在这样说时,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此他才说“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这一方面是在为徐栻想办法开脱责任,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张居正自己心中已经出现了些许动摇!
事情继续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到了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正月,徐栻上疏说凿开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然后引水进新河,再筑堤建闸,估计需要花去九十余万两银子的工钱。对于年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在三百万两银子的明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数目。看到这个上疏,张居正气急败坏,他认定了这是徐栻“故设难词,欲以阻坏成事”,于是就将已经当上戎政尚书的刘应节调到了山东,会同徐栻一起开凿新河。
张居正的这个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张居正又犯了一次用人不当的错误:刘应节到山东后,和徐械在水源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刘应节主张利用海水,徐栻则主张引用山泉。他们相互攻击,都认为对方的主张不切实际。
在徐栻看来,刘应节利用海水的办法只会导致海沙进入新河,因此又要花费不少钱建闸挡沙。山东巡抚李世达也认为刘应节的办法会使得海沙和海水俱来。而且在他看来,除非海风很大,不然就不能将海水灌进新河。可是在刘应节的眼中,徐栻引用山泉做水源的办法也是行不通的,正如李世达所说,山泉到了“十月以后,日渐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细,适值粮运涌到之时,虽置柜设闸,以时启闭,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滔滔不竭也。”引用山泉存在着水源不足的问题。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奉命勘察分水岭的山东巡按御史商为正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说要想开凿分水岭,“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以了此”。
这个结论让张居正差点儿没有吓晕过去。一时间,张居正真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这个费心的工程了。他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花了二百余万金的钱开凿了分水岭,修好了新河,可要是海水进不了河道,或者山泉不充足,那这条河就等于没用。
如此一来,二百余万金不是等于白费了?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
让张居正头疼的事情还没有完!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审慎的考虑:之所以要开凿胶莱新河,本来是为了代替这一段的危险海运;然而,在进入胶莱新河以前,运输物资的船还是要走很长一段的内流河,也就是淮安以下的运河。要是这段运河也出问题,后面的路程再安全也是没用的。这个考虑不是不切实际,因为万历三年的时候,淮安以下的运河到了高邮就被黄河涨水冲得决口了。
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这种意见。他彻底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工部商议是否还要继续这个工程。经过讨论,工部尚书郭朝宾得出结论:“事体委多窒碍,相应停罢以省劳费。”于是,这个一度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工程于万历四年的六月停工了!张居正面临着第二次的治水失败。
人才:治河第一方略
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张居正治水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偶然地发现了治水人才之后,张居正大胆任用,最终扭转了治水屡遭失败的局面,极大地缓解了明王朝的水患问题。
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张居正不会没有思考过原因。他肯定会首先责怪自己不懂得治水的知识,要是自己懂的话,便能够形成自己的判断,再加上自己的政治力量,也就不会总失败了!可是,张居正可能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原因: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得力的治水人才。虽然他既有政治力量,也有坚强的意志,但是治水毕竟不是搞政治,这是需要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一门科学。只有将科学和政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成就治水伟业。然而,可惜的是,张居正并没有让一些人才充分地发挥其才能。
比如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时,工科给事中徐贞明曾经上疏建议在河北和山东一带都可以兴修水利,这样就可以灌溉北方的农田,以产出更多的粮食供给军用。如此,还可以减少每年南方物资北调的成本和风险。如果采取了他的这个主意,实际上是变相地解决了运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当所有人,包括张居正在内都在运河问题上钻牛角尖时,只有徐贞明跳出来想,不愧是真正的水利专家。可是,就是这样的人才,也没有引起张居正太多的关注。结果,徐贞明的建议在交给工部尚书郭朝宾审查后,得到了“水田劳民,请俟异日”的回复,真是让人为他觉得委屈!倘若当初张居正能够重用徐贞明,全力支持他在北方搞水利建设,那么说不定就不用为运河的问题费尽心思了!
然而,张居正就是张居正,他很快意识到治水要有专门人才的重要性,并且大力支持这些人才的工作,终于取得了治水的一次胜利!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他慧眼识珠看中了漕运总督吴桂芳。正是在使用了这个治水人才之后,张居正才成功地解决了黄河下游淮、扬地区的水患问题。
有人会问:张居正是怎样发现这个人才的呢?原来,就在万历四年的二月,吴桂芳上了一个奏疏。在这个奏疏里,他提出了多开黄河人海口的建议:
“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湮,入海止恃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复可收拾矣。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为水利同知,令其审度地宜,讲求捷径,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很显然,吴桂芳的用意是要解决黄河下游的水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的确是个为民的好官。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有治水经验的官员。因为在他看来,之所以黄河总是在下游造成水患,原因就在于黄河的人海口只有云梯关一个地方。人海口少了,就会导致肆意的黄河水不能及时得到排泄,最终造成冲垮堤岸,形成洪水蔓延的结果。鉴于此,吴桂芳主张多开几个黄河的人海口。只要黄河水一走,淮水也会随同出海,这样高邮、宝应的水患就会减轻。
张居正看到这个上疏后,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虽然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解决黄河水患的暂时之计,但是在当时能想出这个办法,足以说明吴桂芳是个治水人才。于是,张居正采用了吴桂芳的建议,给予了他政治上的支持。在一封写给吴桂芳的信中,张居正如此说道:
“淮、扬之民,岁苦昏垫,朝廷未尝一日忘,顾莫有任其事者。兹读大疏,明白洞彻,底绩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来但讲治水,不求治海,虽费何益?但海口之淤,当必有因,似宜视水必趋之路,决其淤,疏其窒,虽弃地勿惜,碍众勿顾,庶几有成也。设官及留饷诸事,一一如教,属所司复允,惟公坚定而力图之。”(《张文忠公全集·答吴自湖》)
张居正的意思是:以前朝廷不是不顾及淮、扬一带的百姓生死,而是苦于找不到优秀的治水人才。现在看见你的上疏,觉得问题一下就解决了。的确,要解决水患问题,必须疏导下泄,因此就需要治海口。海口只要通了,水就可以流走了。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
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让黄河水都流走,运河岂不是又要没水了,那运输物资又应该怎么办?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张居正管不了那么多了,救水如救人呐!情势已经刻不容缓了,张居正顶住压力,再次给了吴桂芳支持:
“淮、扬之民,方苦昏垫,被发缨冠而救之,犹恐不及,岂能豫忧运道之难处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从容讲求平江遗迹,为国家经久之图。今内外储积,幸已渐裕,法纪渐张,根本渐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贤者任之,公毋虑也。”(《张文忠公全集·答吴公桂芳》)
张居正的意思很明显,现在顾不得运河的问题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因此现在只能先救一方百姓。
在张居正的支持之下,吴桂芳大胆地开始了疏浚草湾的工作。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七月,草湾疏浚成功。八月,工部向明神宗复奏。神宗大喜,赏赐了吴桂芳银币。张居正也非常开心,在给吴桂芳的信中,愉悦之情跃然纸上:
“海口疏通,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从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谁之力与?以此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人存政举’,非虚语也。比者暂行薄赉,侯元圭既告之日,仍当有殊锡焉。”(《张文忠公全集·答吴自湖言蠲积逋疏海口》)
张居正自然是高兴的,他甚至觉得从此以后,百姓就可以平地而安居,无须担心水患了。他因此认为,政事的关键就在人为,只要用对人才,就能解决问题。
这一次治理黄河和淮河的经历,让张居正更加明白了治水专门人才的重要性。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注意发现和利用治水人才。这些人才之中,就包括万历六年出任河槽总督的潘季驯。关于黄河和淮河的水利问题,潘季驯于万历六年提出了他的学说:
“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一听到潘季驯这番话,张居正就知道,水利专家让自己给找到了。于是,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将治水的重任几乎完全交给了潘季驯,最终又取得了治水的胜利。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九月,张居正解决了河漕机构合并的问题。接着,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二月,张居正起用潘季驯总理河、漕。潘季驯接到任命后,起初不肯接受,还在四月上疏请求辞去河槽总督一职。但是,在张居正的坚持下,明神宗没有放走这个人才。没有办法,潘季驯当上了这个苦差事。六月,他上疏条陈了六件关于治水的事情:
“一曰塞决口以挽正河,二曰筑堤防以杜溃决,三曰复闸坝以防外河,四曰创滚水坝以固堤岸,五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费,六曰寝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他的这个上疏让张居正高兴异常,因此在替神宗拟的圣旨中,张居正将治水之事全权委托了潘季驯:
“治河事宜,既经河、漕诸臣会议停当,著他实行。各该经委分任官员,如有玩偈推诿、虚费财力者,不时拿问参治。”(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有了这样的保障,潘季驯开始放手干了。经过大力治理,在免去了有些无才的官员之后,潘季驯于万历七年秋后顺利地完成了河工。这自然离不开张居正在他背后的大力支持。在治水问题上,张居正几乎一切都听从潘季驯的主张。有人说他偏爱,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偏爱,明朝的水患或许还要更加严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