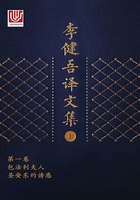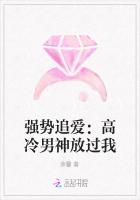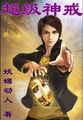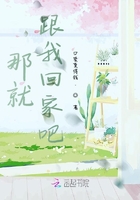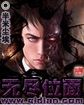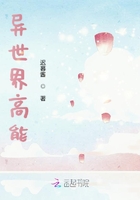关键词的翻译,是《文心雕龙》英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心雕龙》中不少关键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中产生的,其含义往往复杂多元,即使是国内学者也多有争议,翻译者更容易产生误解。但有趣的是,一些明显的误译经过在目标语境中长时间的接受过程,却可能产生新的内涵,丰富目标语的词汇,从而成为经典的“误译”。“风骨”一词的翻译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从“风骨”一词的翻译中,我们不但能看到学者在翻译时对语言、文化等层面所作的考虑,还能看到翻译特有的重塑作用。
1959年,施友忠首先翻译了《文心雕龙》,该英译本一出版,就引来了汉学家和文学家的种种评论,其中一些学者就曾对他关于“风骨”一词的翻译表示质疑。施友忠将篇名风骨直译成“Wind and Bone”,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就提出,尽管风骨一词的译法从字面上来看无可挑剔,但是“如果不能在英语中找到更好的对应词,留下中文总比用……可笑的翻译好”。言下之意,他显然对wind and bone这样的翻译是不满意的,特别是施友忠在文中还有一些不彻底的翻译,比如将“深乎风者,述情必显”翻译成“he who is deep of wind will always be versed in rhetoric”,仍然用表示自然现象的“wind”来翻译风。正如霍克斯所说的,刘勰的语言模糊而难以把握,要用逻辑性很清楚的英语来翻译确实有难度。
施友忠的翻译受到了批评,那么后来的翻译者怎么处理“风骨”一词呢?1962年,杨宪益在《中国文学》期刊上发表了《文心雕龙》译文五篇,将风骨的篇名译成,即情感与结构。他对风骨的理解是风即文章的情感,骨即文章的结构。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我们此处不细究。有趣的是,此后各种译本中或多或少都沿用了施友忠的译法。比如宇文所安的Wind and Bone, Fengku,杨国斌的“Wind”and “Bone”,都直接用了wind和 bone。黄兆杰略有不同,他的译名The Affective Air and the Literary Bones中分别在两个中心词前面分别加上Affective(情感方面的)和Literary(文学上的)两个限定词,试图为“风骨”划一定的范围,但是Air(空气、气)是风的变体,bone(骨)有所保留,仍然不出施友忠译法的窠臼。吉布斯虽然在《释“风”》一文中将“风”解释为“suasive force”(感化力),而将“骨”解释为“bone structure”(骨格),但在指称《风骨》这一篇章时仍然用“Wind and Bone”,可见他也无奈地承认这一翻译的合法性。
Wind and Bone的译法不仅遭到海外英语学者的批驳,也受到不少国内学者的质疑。曹顺庆和支宇等学者就曾指出,尽管施友忠在前言中提到风骨应该理解为“organic unity”,也即有机的整体,但是翻译中他仍然采用了The Wind and The Bone的直译,“……‘风骨’英语翻译的尴尬状态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表面的差异,而且更是深层话语体系的异质性差异。其中所涉及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异质话语的对话问题”。既然wind and bone这一翻译不断遭到非议,为什么这么多学者还要前仆后继地使用该译法呢?笔者认为,这和中西文论话语不可调和的异质性以及翻译的创造性是相关的。
西方文论话语中的范畴多具有抽象性、概括性,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现代性”、“结构主义”、“文学性”等。这些抽象的范畴往往在长时间的历史积累中逐渐形成较为科学的定义。要想真正了解这些范畴的含义,需要对这些范畴的产生、历史有深刻的认识,一篇两篇文章难以说明这些范畴的含义。相较之下,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许多范畴的表现形式则是形象的、具体的,比如“气”、“味”、“色”,包括这里讨论的“风骨”,都是具体有形的东西,但是这些表现为有形的范畴,其含义却是无形的,如羚羊挂角,踪迹难求。因此,中国古人擅长于用形象思维来表述抽象内容,比如用寓言、故事等表示某一种状态,甚至境界,却并不擅长于定义的阐释。在一番形象的描述之后,留下思考余地让读者自去体会,美其名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却苦了需要精确定义的西人。正是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上的这些差异,翻译过程中经常涉及抽象词与具体词之间的转换。特别是一些中文中一些具体词在翻译成英文时通常必须转换成抽象词。比如汉语中我们用“桃李满天下”比喻一个老师处处都有学生,桃树和李树在这里表示优秀的人才,在翻译成英语是就不能说Plums and peaches everywhere,而要用更能概括这一含义的表述方式,比如have disciples all over the world。又如我们用“锦衣玉食”来形容奢华的生活,指华美的衣饰和精美的食品,如果我们翻译成being dressed in brocade and eating jade food,就会显得古怪。brocade尚可以借指绫罗绸缎等一切华美的服饰,jade food就会让英语读者不知所云了。
“风骨”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具体实则非常抽象的概念。从传统的翻译实践来看,这个词的翻译也应该注意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转换。一些译者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试图用抽象词来表述“风骨”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前面提到的杨宪益、吉布斯等。但是,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另一个特点是模糊性。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所谓的“模糊”思维并不是东方人独有的,伍铁平曾指出:“科学意义上的模糊性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特点, 而不是什么区别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特点。”伍铁平《〈模糊语言学〉自序》,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的范畴比西方文论中的话语范畴更多模糊性的表述。“风骨”一词也是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其模糊性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虽然“风骨”一词在人物品评、书画论、文论中多次出现,但是学者从未对它进行过精确的定义。其次,风骨一词的结构组成很不稳定。第三,具体到《文心雕龙》中对风骨的叙述来看,刘勰的解释其实是纠结缠绕、模棱两可的。与此相对应的,西方文论的术语更精确。因此,真正用抽象词来翻译“风骨”时,反而显得生硬、不全面。如杨宪益将“风骨”定义为sentiment and structure,就将风的含义局限于情,骨的含义局限于结构。然而,《风骨》篇中的风、骨含义并不能如此简单视之。刘勰说:“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由此看来,风骨似乎确实可以看作情感与结构的关系。然而,接下来他又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义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似乎骨又与文辞相关。再如篇首论及“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便是有意将风之“触动、感化”之意融合其中。从整篇来看,刘勰论风骨,又着重谈文气,正如范文澜所注的“风情气意,其实一也”,风骨辗转于虚实之间。这样一个虚实相生的词,不宜简单归之于情感和结构。相较之下,倒不如沿用汉语中原来的词,在翻译中赋予其新的含义。
文学作品要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相关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往往来自于作品本身的不确定性。文学作品允许读者对原作的内容和思想进行推测,这种开放性使读者与作品,甚至作者之间产生更紧密的联系。翻译的目的,就是要使目标语读者通过对译本的阅读和源语文本及原作者之间建立类似的联系。翻译者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原文怎样理解”,而是“我怎样理解原文”,不是“作者的意图是什么”,而是“我如何建构想象中的作者的意图”。翻译者不可能完全复制作者的意识,作为独立的个体,他只能给出自己的理解,但是,成功的翻译者能够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能够让读者通过译本接触作者的意识,从而实现自己对原文的阐释。因此,翻译的目的不是向读者呈现原文本的替代品,而是让读者去感觉原作,感觉作者。
风骨的翻译者们经过种种考虑,发现英语中并无这一范畴的对等词,不论用什么词来翻译风骨,都会丧失一些意义。两种语言或文化之间的不对等性(incommensurability)让翻译者面临多种可能,然而,正是这种困惑和复杂性使翻译活动不仅止于译者的选择活动。这种不对等迫使译者通过一定的创造性来弥补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沟壑。因此,翻译者借用原词,通过“风骨”的直译赋予英文“wind and bone”新的含义,这也可以说是翻译的一种创造性。
这种方法在翻译中并非没有先例,译者采用完全直译的方式,让源语词的陌生含义逐渐被目标语读者所了解,从而赋予该词以新的内容。“桥牌”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桥牌英语原文是“bridge ”,常见的含义是“桥”,即架于河流、陆地、沟壑等之上连接两点的建筑物,也可引申为各种类似于桥的事物,或者具有连接作用,或者形状如桥拱等。但是,作为游戏的“bridge”和建筑物“桥”其实并不相关,词源也不同。词源专家对bridge的词源尚无定论,一种说法认为桥牌最早源于俄国游戏,bridge的名称是俄语词birich的变体,表示呼叫、宣布,也正是桥牌游戏中最基本的叫牌规则;另一种说法认为bridge可能源自位于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人(Levantine)的古老游戏;还有人认为bridge源自土耳其语bir-ü,表示一和三,因为桥牌游戏中一人的牌公开,另三人的牌是遮盖起来的。不管各种说法是否可信,有一点可以确定——桥牌和桥并无关系。但是当翻译者接触这一源于异国的牌类游戏时,在进入汉语无法找到现有的对应词,或者因为误认为桥牌和“桥”(bridge)有关,或者出于无奈,把这种游戏翻译为“桥牌”。慢慢的,“桥牌”这一词语在汉语中逐渐站住脚,“桥”作为游戏名称的新含义便产生了。当然,桥牌的翻译和风骨的翻译情况还不尽相同。
反过来,汉语词的英译中也有类似现象。儒家思想中几个核心概念的翻译,就遭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礼”通常被翻译成rituals。英语中ritual表示宗教或其他礼仪活动中所确立的仪式、准则等固定程序,从表面上看,与儒家的“礼”是相对应的。但是,礼在儒家学说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并不是简单的仪式可以概括的。它既包括种种礼节、礼仪、社会行为准则,又是治国、治政的依据,更是一切人生的需要。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因此,国学大师钱穆曾说:“则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惟‘礼’而已。”可见,礼不仅仅是固定的仪式、制度,更有着丰富、抽象的内涵,是整个儒家思想的基石之一。但是,随着海外汉学的发展,英语rituals在指称儒家的“礼”时所包含的意义逐渐通过种种文献深入研究者的意识。不仅了解中国思想史的汉学家们会把rituals和儒家的“礼”联系起来,更多的普通读者也逐渐了解到“礼”的特定含义。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就曾在一次谈话中说过,这些新词的翻译,将逐渐把某一文化中的特定含义带到原有语境中去。或许有一天儒家思想中“礼”的概念将会写进字典中ritual的含义里。
杜先生这种推测并非没有根据,一些汉语词汇由于翻译的困难,以拼音的形式进入其他语境,并已逐渐得到认可。比如“阴阳”在英语中为yin and yang,不但为汉学家常用,现在已经是街头巷尾常听到的词。为什么这些术语能够以特别的翻译方式进入新的语境?这与汉文化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汉语热有关,即和话语秩序的建立和演变有关。
近几年来,翻译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期间伴随着种种理论方法的产生。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在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等学者的倡导下,翻译研究经历了所谓的“文化转向”。社会文化变迁、翻译者和翻译的地位、翻译与改写等文化命题被提到翻译研究的最前沿。这些命题带来学者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等问题的思考,随之而来的是泰莫克佐(Maria Tymockzo)和根茨勒(Edwin Gentzler)所提出的“权力转向”。到了21世纪,学者开始将目光放到翻译的边界,讨论如何以“创造性”的目光从书写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和定义翻译活动,人们关注的不再仅仅是文化属性,更有认知和意识问题,不仅仅是文本本身,还有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开始进入“创造转向”的时代。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化,更涉及意义的创新和重塑以及话语秩序的建立、风骨的翻译,就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1959年,当施友忠出于无奈以wind and bone来翻译“风骨”时,英语是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因此,即使是汉学家也以归化的眼光来审视施氏的翻译,认为wind and bone太浮于表面,无法让英语读者获得足够的信息。当时《文心雕龙》的英译本一出,尽管有纰漏,仍促进了欧美的《文心雕龙》研究。要之,英语研究对《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发展史确实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21世纪,随着中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汉语及汉文化产生兴趣,不少人更是为了增加求职的筹码而积极学习汉语。过去,由于华人人口众多,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现在,汉语不但在华人区域使用者众多,在非华区域也真正得到关注。在这种环境下,外国学生、学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亲近汉语和汉文化。此时,英语读者在看到wind and bone时,试图以异化的眼光来发现汉语词“风骨”背后所承载的种种内涵,更多的人逐渐了解这两个意象所富含的多元含义,同时看到以归化方式翻译“风骨”的种种局限,因此慢慢接受这一最初显得“别扭”的翻译。当然,wind and bone的翻译方式始终未能涵盖“风骨”的所有层面,但是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的翻译。英语世界对这一翻译的反应从侧面上反映了话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平衡关系,以及其对话语秩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