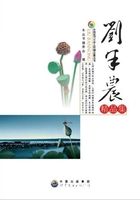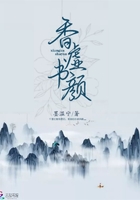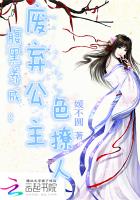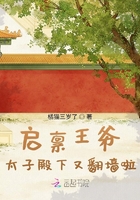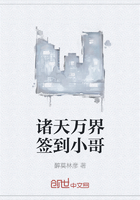而抽屉却对我说:这是唯一的接纳与憩居之地,除了此处,等待你的是铜墙铁壁,你撞破了头也不会有一声凛冽的回音。
为抽屉而写作是我自己的选择。
命运选择了我,我选择了写作的方式。
为抽屉而写作,意味着一块砖头从金字塔浩大的工程中剥离出来,尽管这块砖头的反抗对金字塔本身毫无影响,但砖头却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为抽屉而写作,必然自绝于外界的肯定。
如果说戏剧上演的目的是呼应着绵延的掌声,那么我的写作仅仅是一只小蜜蜂为自己酿蜜。
难以忍受孤独和使我筋疲力尽的方块字,昭示着写作的艰难。
在那些身心交瘁的日子,年纪轻轻的我窥见了窗口死神宁静而恬美的笑容。
我想抽身而去,可是笔拉住我,要我填满雪白的方格。
我自己宣判:“你终身苦役!”在抽屉之外的写作,是我无法认同的写作——它们让人们服从于身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和面包之前低下头颅。
文学已然堕落为枷锁和断头台的颂歌,是朦胧的月光,为黑暗横行张目。
那些肯定性的写作,为什么也肯定不了,唯一的效果是肯定了自身的可耻和无价值。
因此,我坚持否定性的写作,诚如加缪所说:“即使是否定的作品也仍然肯定了某些东西,并且对于我们悲悯而高尚的生活表达了敬意。”我的本科时代,过着清教徒式的刻苦谨严的生活,居然没有谈过恋爱,真有些辜负了未名湖的一池春水。
我为被冷落的命运而感到幸福。
“早无能事谐流辈,只有伤心胜古人”,我在旁人指认的“愚昧”中寻觅一种动人的诗意。
这种诗意与那些吓人的真理无关,它仅仅是一些混浊不明的声音,它在沙漠的深处不抱任何乐观的情绪地呼唤着水源。
它在我快要放弃的紧要关头匆匆赶来支援我。
那道闸门还在。
鲁迅说:“肩住那道黑暗的闸门,放孩子跑到光明宽敞的地方去。”我所做的,不仅没有比先生前进几步,反倒退却了几步——我必须肩住那道黑暗的闸门,却无须放孩子们跑到光明宽敞的地方去。
不是我不愿意放,而是孩子们并不愿意跑。
孩子们说,哪里都一样快乐。
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见证》中曾形象地描述“鸡的心理”——鸡在啄食的时候只看见眼前的那粒谷子,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它啄了一粒又一粒,直到农夫扭断它的脖子。
对鲁迅而言,肩住闸门既是行动也是目的。
我要做的,仅仅是肩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我无暇考虑。
角落里,鲁四老爷假洋鬼子手挽着手,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在说我的坏话的时候,这两个势不两立的家伙才会显得如此亲热。
我的学长孔庆东在送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肩住了闸门,你干什么?
’她说:‘挠你的肋骨。
’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
后来我明白,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
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明白学长幽默背后的讥讽,可我不能像禅宗所说的那样“背不动,就放下”。
作品能够走出狭小的抽屉,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我仍将坚持为抽屉而写作的方式,这一写作方式由三只鼎立之足来支撑: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和边缘的姿态。
为抽屉而写作,也就在极度的不自由中为自由而写作。
自由是人类投身写作行为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
写作及生活的目的只能是增加每个人身上和整个地球上都可能发现的自由和责任的总量。
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在结尾给每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了某种内在的自由。
这样做,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当我整理完这本书稿的时候,我真切地听见我的牙齿啃我的骨头的声音。
冠盖满京华,思人独憔悴。
自诩为思人的我,为抽屉而写作的我,走我自己的路。
有朋友愿意同行,我不拒绝。
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鲁迅的中国。
鲁迅逝世的时候,告诉妻子和孩子、朋友和学生,“忘了我,好好生活”。
然而,我们依然无法忘记他,我们依然难以“好好生活”。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还在不断地谈论着鲁迅,似乎在前辈中只有鲁迅可以如此长久地被我们所谈论。
我们之所以要谈论鲁迅,根本原因还是他的对立面变得更加强大了。
我相信,被后人谈论并不是鲁迅的骄傲,而是鲁迅最大的悲哀。
鲁迅为我们在铁屋子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他还来不及做更多的事情就劳累而死。
开一扇窗户就会耗尽一个人一生的能量,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国情”。
我们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的文化太丰富了,我们的土地太宽广了,我们的人口太繁密了。
所以,我们是“无所不有”的“天朝大国”。
铁屋子的墙壁上开了一扇窗户,窗外阳光灿烂,油菜花也一样灿烂,浓郁的花香还飘了进来。
然而,让鲁迅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行为恰恰成为他招致攻击原因。
那些喜爱或者适应呆在黑暗里的人,开始疯狂地咒骂他。
同胞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同胞们的心灵已经习惯了奴役。
绝大多数人依靠梦境而生活,至于血淋淋的现实,他们可以用鸵鸟埋头入沙、屁股高翘的方式来对付。
因此,最厌恶鲁迅的并不是统治者,而是那些将脖子伸得像鸭子一样长的观看杀人场面的大众。
那位一度权势滔天的林副统帅,虽然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却最害怕光和风。
瘦骨嶙峋的元帅躲在一年四季恒温的房间里,并拉上厚厚的窗帘。
他说,要“绝对”的黑暗;他想,要是整个中国就是这样一间密不透风的屋子该有多好。
而我,愿意透过那扇鲁迅亲手打开的、小小的窗户眺望远方。
正如学者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中所说,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争、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
鲁迅对黑暗主题的揭示特别重要,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种昏暗时刻究竟多久才能结束。
就算是在表面上结束了,在人的心灵中也还是没有结束。
千年的铁门槛,千年的铁屋子。
与鲁迅的那个时代相比,在我们这个所谓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里,真正的智慧其实并没有丝毫的增长。
相反,愚昧却像爬山虎一样肆无忌惮地巩固着这所本来就已经很坚固的铁屋子。
在这间铁屋子里,穿着印有格瓦纳头像的体恤的“新左派”们与穿着印有大元宝的唐装的“新儒家”们,手拉手跳起了草裙舞。
他们太“新”了,以至于发出墓穴里腐尸的气味。
有时候,我很羡慕美国人,羡慕他们脸上的阳光,羡慕他们嘴角的微笑,羡慕他们没有历史,羡慕他们没有皇帝。
倘若传统的存在仅仅是增添我们的痛苦,这种传统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地方的呢?
鲁迅说过:“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我理解鲁迅为什么要劝说给青年人“不读中国书”——虽然他本人读了那么多的中国书,但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这些书籍跟墙壁里的砖头其实是一样,正是砖头和书籍共同建构了这座坚不可摧的铁屋子。
他从“仁”、“义”这些美好的字眼中读出了“吃人”两个字来。
一九九三的秋天,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忍受了一年所谓的“军政训练”之后,我第一次踏进了北大的校园。
在那被延宕的一年时间里,北大的湖光塔影每天都出现在梦中。
然而,真正到了北大以后,新鲜感在几天之内就消失了,我很快就陷入一种没有边际的失望之中:原来,北大也是一间铁屋子。
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就像是一个失血太多的伤员,连走路也摇摇晃晃的,更不用说奔跑了。
伤筋动骨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又被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得阵脚大乱。
未名湖开始“翻修”了,湖水都被排光。
水底只有恶臭的淤泥,而没有白衣飘飘的诗人。
当两岸的乱石都被平整的水泥板所取代的时候,北大正在凯歌高进地走向清华。
学生们都涌进了“新东方”的课堂和党组织的怀抱。
没有青春的“青春”,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过于聪明了”。
那么,对这两种选择都没有兴趣的我,是不是太傻了呢?
面对被挖去眼睛的未名湖,我忽然想起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的一首名为《恐怖》的诗:他们让人渐渐地变得驯顺,他们给一切都盖上了印。
哪儿应该沉默——就让你叫喊,哪儿应该呐喊——就叫你沉默。
不,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
我重新阅读鲁迅的书。
这次的阅读与中学课本的教育截然不同。
在不同的背景下,阅读同一本书,居然会获得如此不一样的、甚至完全对立的感受,这个结果让我惊讶了好久。
我与五位室友住在三十八楼一楼一间向北的宿舍里,很少有阳光,走廊里一年四季都挂满湿漉漉的刚洗过的衣服。
在潮湿与晦暗的宿舍里,我读完了《鲁迅全集》,也开始写自己的文字。
鲁迅说:“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寄希望于孩子,他知道作为“中间物”的自己将在呐喊中与黑暗一起灭亡。
然而,现实总是比人们的估计更加悲观。
夏济安写道:“鲁迅是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个人敏锐的感受性并未被他中国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所充分赏识。
他们作为后一辈反抗者也许真的认为他们所享受的阳光,都得归功于鲁迅以他巨人般的威力肩住了闸门。”我不同意夏济安的看法,孩子们真的享受到阳光了吗?
没有。
鲁迅所赏识的青年们没有一个得以善终。
萧红孤独地在香港的滚滚红尘中告别人世,萧军屡次被当作批判对象而遭到漫长的流放,胡风成为“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入狱二十年后精神失常,冯雪峰则经受了残酷的辱骂和殴打而惨死狱中。
鲁迅几度漂泊逃亡,他毕竟还有一个“且介亭”可以容身,而那些企图跑到光明里去的孩子们却跑进了沼泽地。
后有追兵,前有山大王,如何是好?
思考着鲁迅的命运和孩子们的命运,比较着铁屋子的巨大和窗户的狭小,我寂寞地度过了自己的本科时代。
与《火与冰》一样,《铁屋中呐喊》真实地记载了我那段青春岁月的心路历程。
那时,我常常想,我是不是能够撬动铁屋子里的一块砖头,使得窗户变得稍微大一点呢?
这些年来,也颇经历了一些人世的沧桑,但我的努力依然没有停止。
我向来是“不悔少作”的,尽管我也愿意像梁启超那样“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