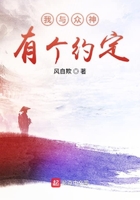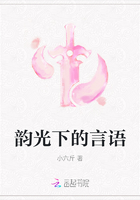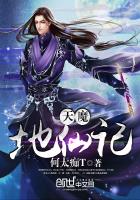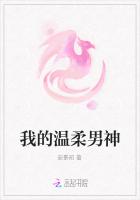《儒林外史》一开卷写了一个名叫王冕的人物。吴敬梓叙述道:他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季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
王冕,就是一个逸人。也是作家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王冕所以是理想的,在吴敬梓看来,是因为他与当时士林中的浊流不同,他不像他们,热衷功名,庸俗媚俗。他把这一切都视为身外之物,不予追求。他把自己与外界的关系简化为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自得其乐,同时又进行艺术创造。他逃避政治,逃避争夺,完全拒绝外界的诱惑,把生命蛰居于乡野自然之中。
倘若要对《儒林外史》进行文学批评,我觉得,王冕并不是一个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他只是为了和士林中的浊流人物形成对照才设立的。有这个人物作为镜子,吴敬梓就有了清浊之分,正邪之别。因此王冕在小说中只是起了一种工具的作用,而本身性格却不丰富,完全是一个抽象的精神符号。所以,从艺术上说,我并不喜欢这个形象。在现实层面上,我也不会像吴敬梓那样,把他作为理想人物。但是,我要为这种逸人辩护,而且觉得,社会应当给逸人有存身之所,尊重逸人。
这种逸人,也可以称作隐士,所以逸人也称作隐逸之人。这种隐逸之人,有的是全隐全逸的,那就是决心隔断尘缘,遁入佛门;有的是半隐半逸的,如《红楼梦》中的妙玉,她虽然在栊翠庵为尼,超然脱俗,但还是“带发修行”,既是“带发”,自然就和尘缘还有许多联系。她称自己为“槛外人”,与槛内人确有不同,因此仍然属于逸人。还有一些逸人,就生活在槛内的世俗世界中,但又能超越世俗世界,并自己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他们也许隐居于山林之中,也许隐居在茅屋草舍之中,也许就隐居于自己的生命之中和自己的作品之中。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妙玉比王冕丰富得多。妙玉虽是一个吃斋念佛的“槛外人”,但又是身居金陵十二钗“正册”的一位重要人物。她天性孤僻,但才华出众,在为林黛玉和史湘云的长篇联句作续时,她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一十三韵瞬息即出,令林、史二人惊叹为“诗仙”。她的气质,更是非凡卓绝。在她面前,连最清高、最美丽的林黛玉和薛宝钗都自觉得不安,妙玉也不客气地(虽属玩笑)称她们为“大俗人”。妙玉这种“槛外人”,社会允许不允许存在?这种人有没有存身之所?《红楼梦》告知读者,这种人必定是“世难容”——“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果真是这样,妙玉的结局非常悲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一个最脱俗最干净的人被最污浊的盗匪所凌辱、强奸。肮脏的比干净的更有力量,这有什么办法呢?
妙玉生活在数百年前,曹雪芹就为她的“世难容”而不平。其实,在中国古代,逸人还是有存身之所的。一个选择隐逸存在方式的士人,并不会受到社会的集体谴责,所以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成为逸人的不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都想做这种逸人。他们一方面看到现实社会的肮脏和黑暗,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去抹掉这种比自己强大的肮脏和污浊,只好选择一条路,就是洁身自好、回避污浊之路,也可以说是自我完善的路。现实社会既无高洁心灵的避难之地,那么,就在远离现实社会的山林田园之中找一存身之所,这种要求,其实是很低也很合情合理的。陶渊明也是一个逸人,但开始并非逸人。当他成为逸人时,便有“实迷途其未远”,“知来者之可追”的想法。也就是说,他觉得昨天在仕途上忙碌奔走,和他的生命本性极不相宜,纯粹是浪费自己的才华。所以他决定远离尘嚣,过清贫而干净,充实而富足的精神生活。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的“封建社会”年代,还有隐逸的自由,也就是说,“世”还是可以“容”下他的选择的。隐逸之前他做过州祭酒,镇军将军刘裕和建威将军刘敬宜的参军小官,之后,又做彭泽县县令。其实,他的县令仅当了80多天就受不了。萧统的《陶渊明传》中说:“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当然,不想见邮督只是个借口,陶渊明实际上早已和政治现实格格不入,只是借此选择人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陶渊明这种对时官的蔑视和愤然而返归山水的选择,倘若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是要备受非议和批判的。其罪名至少有三:一曰对现实不满;二曰企图逃避时代逃避政治;三曰企图钻入象牙之塔。可见,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还是有其宽容的一面,令今人羡慕。
其实,在中国,不能容忍隐逸的社会氛围在上半世纪就形成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再也没有“隐逸”的自由。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之初,他们大部分都想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的道路,但是,他们从外国深造回来之后,才发现社会并没有提供他们施展才能的职业空间,因此,他们一直徘徊于社会的门槛之外,这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不得不去寻找“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即革命的道路,于是,他们便纷纷成了战士。成了战士自然是好,但有些人确实是书呆,只会读书做学问,见到剑与火与血就害怕,自然当不了战士。于是,这些人就想当“隐士”,也就是当“逸人”。但是,这个时代已不允许他们当隐士。倘若他们想“隐”,那些当战士的知识者就指责他们:社会正在大变动,中国人这么苦,你还想当隐士,你的良心何在?于是,当逸人的梦也就纷纷破碎。积极参与“五四”革命运动的周作人,后来就想开辟“自己的园地”,自己创造一个精神的避难之所,当谈龙说虎的逸人。然而,他被指责,连他的哥哥鲁迅也指责他。鲁迅在1935年1月25日以长庚的笔名在上海《太白》杂志发表了《隐士》一文,对隐士做了强烈的抨击。他认为隐逸乃是一种招牌和手段,“登仕,是瞰饭之道,归隐,也是瞰饭之道”。谋隐和谋官其实是相通的。而且,鲁迅还认为,“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糊涂”(《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鲁迅对隐士的批评有其历史具体性和针对性,而且古来隐士中也确有以“隐逸”为手段而抬高自己的身价,或身在山林、心在魏阙的人。但是,鲁迅没有给一些确实希望逃避政治、逃避官场的作家诗人留下自由选择的空间,这就太激进了。做隐逸选择的人与强烈介入政治热衷官场的人确实有区别,而逸者的逃避现实纷争又确实有利于文学艺术的生长。就以陶渊明来说,如果他在41岁时不是选择隐逸的道路,而是继续走仕途的道路,那么中国诗史上就不会有一个名字叫做“陶渊明”的重要诗人了。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成就,的确得益于他的隐逸。隐逸不仅使他赢得时间,赢得写作的从容心情,而且使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和道家那种乐天安命相通,也寻求解脱,但又不同于道家的逍遥无为,他依然执著于日常的现实生活,也就是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守住自己理想、情操和心灵自由的精神世界。这种境界与平凡的生活相连,又超越平凡的生活;它不像玄学佛学的境界那么虚幻,又完全不同于世俗生活的琐碎与平庸。这种境界使它创造出“平淡”的独到的诗歌风格,给文学史留下千古难灭的永恒诗味。在中国诗史上,陶诗真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它似乎“无声无味”,其实却韵味无穷。他面对的是平常的山野田园,闪射的则是“生与死”思索的形而上光辉。很难想象,如果陶渊明继续在官场胡混,还会有这种诗作出现。所以,那个时代能容纳陶渊明隐逸的存在方式,真是诗家的大幸。
我并不是说,作家诗人都必须隐逸,只是说,应当尊重作家隐逸的选择。能当战士并能放声歌唱自然好,而不能当战土,只能感受自然人生,也无不可。不应把逸人当做反对政治的敌人,也不必把逸人当做“革命意志衰退”的罪人。偌大的社会天地和艺术天地应当容下隐逸这种方式。
人们到处都在生活。世界上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应当尊重人们自己的选择,只要这种选择不是在损害他人和破坏世界正常的生活。我想,逸人并不违反这种原则。为什么一定要用一种生活方式统一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呢?真正的战士是值得尊重的,但如果世人都成为战土,这个世界一定会充满火药味和战斗气。隐士虽在某些方面不及战士,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常常强于战士,例如,他们为把世上的功名看得淡漠,因此常常能够进入深远的精神生活,于艺术于哲学常有战士们难以企及的贡献。例如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其实都是逸人或在某一人生阶段是逸人,但他们的诗书画,都很有成就。何况,人生并非是一个凝固体,一个人时而当当战士,时而当当隐士也无妨。弘一大师和苏曼殊,就既当过战士也当过隐士,因为有两种不同的人生体验,他们的艺术才多彩多姿。像李白、苏东坡这样的大诗人,其实也是时而当战士,时而当逸人,所以他们的作品才不会落入单一的战士模式,这与我们的一些只会“放声歌唱”的诗人大不相同,这里确实有丰富与贫乏之别。
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决不会像吴敬梓那样把王冕当理想人物来讴歌,自然也不会把陶潜等当做权威来崇拜,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我们自己愿意或者有朋友愿意生活得超脱一些,离现实社会远一些,离政治斗争远一些,也就是离所谓“时代潮流”远一些,也未尝不可。这些朋友不一定放情于山水田园,但他们能自己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一个属于自己的净土,在净土中,就为艺术而艺术,为玄学而玄学,也未尝不可,恐不能再谴责他们是“企图躲进象牙塔”。其实,20世纪中国的问题,是能躲进象牙之塔潜心于学术、艺术的知识者太少,所以社会至今充满火药味。如果有条件,有些朋友愿意像印象画派大师莫奈,在远离巴黎的一个村庄里建立自己的艺术庙堂也很好;当年,他建造一个象牙之塔,而今天,却变成了世人“朝圣”和享受艺术的地方。所以,逸人表面上是回避世人,实际上常常是为世人服务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