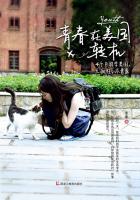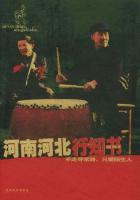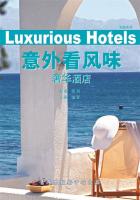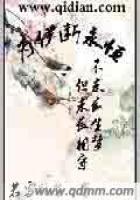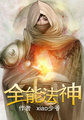1991年,我在美国新奥尔良生活过一段时间,住在滨海大道的一家公寓里,紧挨着著名的法国区,这里时不时会有一些英国游客因为拒绝交出手中的摄像机而被附近嗑了药的抢劫犯杀掉。我却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当然我也买不起摄像机),尽管我无时无刻不在四处晃荡。
我和女友在从纽约到洛杉矶的路上经过了新奥尔良,我决定去这个城市看看。那次我们正替人递送汽车,跨州的话,通常要求走最短的直路,最多可以超出几百里,但是我们的车没有原始里程数的记录,我们就在州与州之间绕来绕去,超出了正常里程数几千里,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在这次狂乱的旅程中,我们只在新奥尔良住了一夜,但是它(我指的是法国区,而不是整座城市)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我发誓等下次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我一定会回来。我一向喜欢发这种誓,却总是食言,但这一次不同,路过新奥尔良一年以后,我又回到这个城市,在此地待了三个月。
找到出租的公寓之前,我先在皇家街客栈住了几晚。我本希望能在法国区中心找到一个带阳台、有摇椅和风铃的屋子,在它的阳台和摇椅上俯瞰其他屋子。最终我却在法国区危险的外围住了下来,那是一处带有小阳台的屋子,俯瞰一片空地,我晚上走回家时,这片空地总是隐约藏匿着某种威胁。
我在新奥尔良唯一认识的人是詹姆斯和伊恩,一对五十多岁的恋人,是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位女友的熟人的朋友。他们对我很热情,两人比我年长不少,又都感染了艾滋病,喜欢过安静的生活,我也就迅速地习惯了一个人日常的工作和孤独。在电影里,某人搬到一个新城镇——即使因为谋杀妻子而蹲过很久的监狱——也很快会在当地超市的收银处或是吃第一顿早餐时遇见一个女人。我三十多岁时经常四处游荡,搬到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城镇,可我在超市从未遇见过一个女人,我在新奥尔良Croissantd'Or[1]吃第一顿早餐时,也不曾遇见。即便我在取名贴切的Croissantd'Or里连女侍者也没有遇见,我仍然每天都在那里吃早餐,他们的杏仁牛角面包实在是我吃过的最棒的牛角面包。有时候一连下好些天的雨,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雨(当然后来还见过更大的),雨下得再猛烈,我也不会错过在Croissantd'Or的早餐,一是因为这里有非常好吃的牛角包和咖啡,更主要的是,它已经成为我每天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了。
晚上我去街边的“停靠港”酒吧,我曾试图在收看CNN[2]的海湾战争报道时和一位女招待搭讪,没有得逞。巴格达的第一次空袭之夜,这家酒吧充满了兴奋和预言,喧闹不止。滨海大道的很多树上挂着黄丝带,每天我都经过那里去Croissantd'Or,我喜欢一边吃我的杏仁面包,一边看来自海湾的最新报道,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当地报纸,名字是——路易斯安那什么的?——我忘记了。早餐后我走路回家,工作很久很久,然后在法国区散散步,似乎是被家家户户垂挂的风铃的声音所引诱了。那是一月份,但气候温和,我经常坐在密西西比河边阅读关于新奥尔良及其历史的书籍。这座城市坐落在密西西比河河口,地基在淤泥中,它的房子每年都会向下沉陷,再加上阳光的曝晒和雨水的侵蚀,法国区的许多房子都明显地倾斜了。这种垂直的偏离却被水平的漂移抵消了。密西西比河的南口冲积了如此巨量的砂砾,将河流淤塞得不得不改道,以至于整个城市都在移动。每年,街道都会相对河流的位置移动一点点,微妙地改变了城镇的地貌。詹姆斯和伊恩所住的迪凯特街和十九世纪地图上标示的位置相比,就偏差了一些。
一天下午,我坐在密西西比河边,背后的铁轨传来货车驶过的隆隆声,非常缓慢。我总是想跳上一列货车,我跃起,鼓起勇气想要跳上车。火车的长度和蜗牛的速度意味着我有很长的时间(太长了)去周密考虑跳车这件事,我害怕有麻烦或弄伤自己,我足足站了五分钟,注视着车厢一节节咣当咣当地过去,直到整个列车驶过。我注视着它蜿蜒消失,充满了紫丁香般的幽怨,就像是你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你们的目光相遇了片刻,你没有开口说话,她走了。那一天你都在想,假如你和她说话,她不会感到被冒犯,反而很高兴,也许你们会爱上彼此。你好奇她叫什么名字,也许叫安吉拉。我没有跳上货车,我回到了滨海大道的公寓,让我小说里的人物跳上去了。
你孤独的时候,写作可以给你做伴。它是一种自我补偿,一种对事物的弥补——而不是对事物的虚构——这种事并不怎么发生。
平淡无奇的几周过去了,天气越来越温暖和潮湿,狂欢节就要到了。我可以在狂欢节的时候搬出来,把我的公寓出租,价格会是平时的四五倍。幸好詹姆斯和伊恩要外出,他们答应我搬到他们在迪凯特街的住所,那里离密西西比河不像过去那么近了。一开始很有趣。狂欢节。我喜欢抓东西的运动——塑料杯、珠子,其他小饰物,其实都是些垃圾,它们是从拥挤的街道上缓缓移动的疯狂彩车上抛下来的。这种运动像是篮球,又像是站在一群难民中疯抢士兵发放的食物供给。我个子很高,伸手够得比大多数人都高,尽管在路易斯安那也有一些高个子,他们主要是黑人,而多数白人比较矮,我很容易比他们跳得高。一天晚上,我和一群人正沿着壁垒街打闹,跳着去抢杯子和珠子,这时枪声响起。大家全都尖叫起来,惊慌地四处乱跑。不知何故,我的一只膝盖发软,这种事以前从没发生过,我蹒跚着撞到了前面的一个人,为了不至于摔倒,我一把抓住了他。这引发了另一阵恐慌,每个人都停下了脚步,处处都是警笛声和警察,一切都回到了狂欢节如常的骚动。
嘉年华的日子越来越令人不快,简直成了一件无聊的事。法国区挤满了大学生,丢满了百威啤酒罐和破塑料杯,街上散发着酸馊的啤酒和新鲜呕吐物的臭味。另有轻佻的一面,是由各种群体主办的奢华舞会。伊恩把他收到的一封宴会请柬给了我,在那里我遇到了安吉拉,一位年轻的黑人姑娘,她正在一家法学院读财富积累专业。舞会的第二天,她身穿新洗过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红色衬衫来到詹姆斯和伊恩的公寓。她用一根红色缎带把头发扎在脑后。我们肩并肩站在阳台上,喝着白葡萄酒,那酒杯如此纤细,让你不忍一握。我们的手搭在阳台栏杆上,近在咫尺。我的手向她的手移动,几乎要碰到她的,接着它抚摸她的,她没有抽出手,我开始爱抚她的胳膊。
“这感觉很好。”她说,目光仍向街上望去。我们接吻,各自握着一只精细的酒杯,放在对方的背后。接完吻后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就又接了些吻。
狂欢节后不久,法国区恢复了它安静而空荡的常态,多纳利,一个与我同样年纪和身高的家伙搬到了我的隔壁。他的头发有点儿长,身着T恤和棒球鞋,可没有我那时候穿得时髦。我们在楼道遇到过几次,比较了一下彼此的公寓——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去“停靠港”吃了一次汉堡,后来就经常在一起厮混了。大概四年以前——“1987年的愚人节。”他说——多纳利得知自己得了皮肤癌。医生说他只有三成的希望能活下来,他经历了一系列手术,仍然精力充沛,我们相遇前的五个月他还有力气闹自杀。那以后他住进了洛杉矶的一家精神病院,现在正在图兰大学医院“接受”进一步的癌症治疗。(在多纳利的简历中,医院扮演的角色就像我的简历中大学扮演的角色一样。)
多纳利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网球打得很好。下午我们经常随便打上一个小时(他觉得记分没有意义)。他的水平高出我许多,但我喜爱扣杀每一个球,而且我有强烈的求胜心(尽管我们没有记分),我们就算是球逢对手了。打完第一场后,他脱掉湿透了的T恤,他的背部和胸部让我震惊:一具伤痕累累的躯体。晚上,我们在酒吧里喝得醉醺醺的,或者随便闲荡,通常是在“停靠港”,有时候也去别的地方。他总是喜欢谈论他经历过的“癌症和其他臭狗屎”。第一次检查结果发现是阳性时,他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在卫生间里刮胡子。我妈妈打开信封,走进来,拥抱我。我是这样说的:‘妈妈,我在刮胡子。’”
“你从来没有感到难过?”
“我的生活毁了,但我没有难过。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接受’外科手术,‘接受’化疗。真让我心烦。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只是在过我的日子。我不是在‘接受’它。”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空地上孩子们在玩耍。天黑得很快。
“你为什么要自杀?”我问道。
“不是因为我抑郁或是别的什么。我甚至不是特别想死。我只是不再想活了。”那一晚上他都在吸可卡因,他说。然后他坐在车里喝啤酒,听音乐,感到很幸福,而排气管将车内灌满了一氧化碳。
天黑了,还是温暖的。我们看不见玩耍的孩子了,不过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
“你的朋友怎么看?”我说。
“我想他们会想,这才是多纳利吧。”
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我一样好奇。他们见过很多自杀未遂的案例,却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他们寻找线索,询问他“有没可能是酗酒的原因”。
“我真希望如此,”他说,“这么久以来我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和时间。”
对他来说,一切都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什么也不在意,却有很强的交友能力。他很体贴大方(他没有工作,却一直手头宽裕),从不强人所难,而每当我建议去喝一杯或吃点什么时,他又总是积极响应。我敲他的门时,他永远是躺在床上喝啤酒或是看电视。他从不读书——连报纸也不读——他从不觉得无聊。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做他自己,做一个美国人,做一个叫多纳利的人。
一个周末,多纳利的家人来访,我和安吉拉则驾着她的车去了密西西比。之前她离开了一段时间,和她的朋友们去了东海岸,所以我们有好几周没有见过面了。我们时常相拥而吻,却不曾真正睡过。我希望在我称之为“自由之旅”的途中,我们能有过一次。安吉拉不知道我的意图。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回首往事我屡屡感到惊讶,人们竟然有那么多不知道的事。这就是旅行的一个特别之处,你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相当无知的,而这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沿着路易斯安那的平原行驶,经过了沃克·埃文斯[3]镜头下的风景以及一排排贫民窟,越靠近密西西比,那些房子越是破败。我们开得很慢的时候,人们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即使是什么也不做),望着我们开过去。天色阴沉又潮湿,积云滚滚。我隐隐约约地期待我们会成为种族暴力的牺牲品,戴着棒球帽的白人乡下佬会漫不经心地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主要是加油站的服务生——他们太疲倦而且又太有礼貌,除了汽车的牌子,他们什么也不曾注意到。
我们住进了杰克逊的一家汽车旅馆,在一家霓虹闪烁的汽车餐厅吃了晚餐,他们供应分量很足的家常饭。晚饭后我们回到了汽车旅馆。我忘记把在新奥尔良买的避孕套带来了,箭在弦上,我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你要是有艾滋的话,我就杀了你。”安吉拉说着,一边引导我进入她。“不要进入我。”她又说。
我们的性事结束之后——我很自然地趴在她身上——躺在密西西比的黑暗之中,车灯扫过天花板,我们听着从隔壁屋里传来的电视声。
“你以前和黑女孩做过吗?”
“是的。”
“多少?”她说道,听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
“两个。你知道可笑之处在哪里吗?”
“她们都问我,我以前是不是和黑女孩做过。”
我们事先从一家酒类专卖店买来了啤酒,余下的整个晚上都在房间里喝酒,好像我们才抢劫过一个加油站,正在逃亡的路上。
回到新奥尔良后,我和多纳利也出门远足,进入过沼泽地——水面上漂浮着的像木头一样的东西,已经漂流了几千年,竟然是短吻鳄——我们会环绕新奥尔良驾车兜风,一边听摇滚乐。一天晚上,我们在城市公园东边的菲尔莫街上行驶,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雨刷模糊了车窗外的红灯,霓虹投射成车窗上绿色的小水坑。一辆等着变灯的车就在前面,我们的车滑向了它。我们速度不快,但是金属的碰撞声很大,玻璃碎屑散落如雨。两个小伙——两个黑人小伙——从车里出来,朝我们走了过来。多纳利把手放在仪表板的杂物箱上。这两个小伙检查了一下他们被撞的客货两用车,想看看有没有撞坏的地方——没有,至少是没有新的剐蹭,他们看来没有放在心上。多纳利关上了杂物箱,摇下车窗。其中一个小伙走过来和他交谈。他闻到了我们车里的烟草味儿,笑了起来,多纳利把他刚才抽的大麻递给他。两个黑人小伙坐回到他们的车里,我们两个白人小伙也继续上路了。有一刻我紧张极了。在美国,你对种族会非常敏感,在英国你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黑人区,你想,糟糕,我在黑人区,也许我不应该来这里。多纳利说,他们下车时,他也有一点儿不安。
“所以我要带上这个,”他说着,一边打开杂物箱,把手伸进里面。他递给我一支枪。我以前从未摸过枪。它看起来很小、很重,乌黑、危险。我把枪还给多纳利,他又把它放进杂物箱,合上盖子。
“麻烦的是,我只剩下两颗子弹。打个比方,要是三个小伙要强奸我,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也来自英国,一样对枪的用法不熟悉。
“两颗子弹。”多纳利说道,摇了摇头。
“也许你应该多买些子弹。”我说。
“你说得对,哥们儿。我要多买些子弹。”
“两颗子弹……”
“他妈的,两颗子弹和没有一样。”
“只有两颗子弹的枪有什么用呢?”我说。我渐渐掌握了枪支谈话的诀窍,并且十分享受。
“一支枪需要六颗子弹。”多纳利说。
“比如六发式左轮手枪。”
“我最少还需要四颗。”
“你的潜能只用了百分之三十三。”
“六减四等于二。”
“还缺四颗。”
“一个枪里只有两颗子弹的家伙就是傻子。”
“我可不想这么说,”我说,“我怕让你不爽。”
“你就算是没说出来,我也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是你,我明天就去枪支店。一大早。”
“你说我到那之后会做什么?”
“你会买四颗子弹。”
“我可能会买六颗。”
“好主意。”
“我就会有两颗备用的了。”
“没错,两颗备用。”
我们把车停在公寓楼外。雨下大了,我们快步走向“停靠港”。海湾战争结束了,酒吧比以前还要喧闹。我们坐在酒吧里。多纳利和那个我曾试图搭讪的女招待睡过了,她给我们免了酒水费。我很饿,点了一个汉堡;多纳利吃过晚饭了,但也点了一个。我们曾在这里喝得醉醺醺;喝了这些酒,我们开始胡言乱语。他和我讲起他入伍的日子。他的部队在柏林驻扎,他和另一个家伙定期向苏联人卖情报。结果他们挣了一大票,使劲花也花不完。周末他们会飞到巴黎,为了和美丽的法国妓女睡上一夜而一掷千金。他在洛杉矶染上的可卡因瘾也越发不可收拾了。
“你会为此内疚吗?”
“什么?把钱都花在可卡因和妓女身上?”
“不是。把秘密卖给军情五处——我是指克格勃。”
“只是觉得钱唾手可得。”
“我觉得是背叛。”
“哦它是的,哥们儿。”
多纳利总和我说这些事,关于他是多么不值得信任的那些事——背信弃义到如此程度——但我从来没想过不要信任他,从来没想过不要相信他对我说的那些事。不仅仅是如此,他以他的方式让我感觉到,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值得信任的人,一个我能托付的人(不是说我有什么事情要托付),我丝毫不担心他会背叛我。我觉得,这一切意味着他是我的朋友。像我这样生活的人,住过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我已经习惯于在别人不再交新朋友的年纪结交新朋友,而他们就是靠十九、二十岁时在大学时积累下的日渐减少的朋友储备为生。这是我的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了,也许我讲这个故事——这个真实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我想把这个简单的事实记录下来,那就是在新奥尔良这个我们几乎谁也不认识的城市,我和多纳利成为了朋友。
“你知道,我还在想着子弹的事。”吃完汉堡,我们又点了些啤酒后,他说道。
“我知道,”我说,“我能猜到。”
“我可以买十颗:四颗装和六颗装的。”
“两套六颗装的。”
“我不需要那么多。”
“那就六颗吧。我的意思是,买六颗装的。”
“二加四。”
“等于六。”
“加上你原有的两颗。”“答对了!”
我在新奥尔良的日子到了尾声。我要去圣克鲁兹,我转租了一位朋友的公寓,他要出门几个月。我才在新奥尔良找到了生活的感觉,却又到了离别的时刻。离愁别绪往往化身为购物的强烈冲动。那个阶段的我不喜欢穿凉鞋,但是在多纳利的坚持下,我买了一双Teva[4]运动凉鞋,就像是脚上穿了一只手套,一只脚各穿了一只——我是想说,穿在脚上的感觉像袜子。我还买了一副近视太阳镜,让我见到了以前从未见到的世界,闪闪发光的清澈世界,玫瑰红色的明亮世界。
多纳利也想去西部,但不想去太远的西部。假如他又到了洛杉矶,他肯定会自杀的。他想去拉斯维加斯,在“新奥尔良的西部,又不像洛杉矶那么西面”。
“好啊,”我说,“正是如此。”他在那儿有朋友,在拉斯维加斯。我们时常谈起合写一部关于他的生活的书稿。“所有那些垃圾间谍内容”都让这本书显得很有商业价值,但我却视它为一种寓言,一种不带任何说教或寓意的寓言,一种无法从中学到任何东西或得出任何结论的寓言。我对写这本书有极大的热情,他也是。
从我们的自由之旅回来后,我和安吉拉又睡过几次,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发生。我们见面的次数如此稀少,从见面到不见面的过渡几乎是无法察觉的。也许我传染上了多纳利对事物的冷漠态度。我怀疑这也并非是我唯一传染上的。我感觉身体不太对劲:我撒尿时有轻微的灼痛感,非常轻微。
走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多纳利醉醺醺地坐在密西西比河边(据说天黑后待在这里不是明智之举)。几乎是一轮满月了。严格地说它不算是满月,但也非常圆了。我告诉多纳利我幻想跳上那节火车的事。
“你真应该这么做,哥们儿。”他说。
“我知道。我在书里这么做了。”
“那天晚上我想自杀,可是几乎要放弃了。我很少会自寻烦恼。我又想,操,随便哪个晚上你都可以这样坐在你的车里喝酒啊。来吧,让我们继续吧。”
“这是怎样的意志力!”
水面有油轮驶过,向着目的地坚定而缓慢地前进,河对岸是阿尔及尔吊车,河的这边是我们。那天没有雾,我记忆中的画面却有雾角声。圆月时不时被涌向海岸线的乌云所遮挡。大河不像是威武的棕色大神[5];它仅仅是一条巨流河,太苍老,太沉重,早就对奔向墨西哥湾或别处失去了兴趣。不过是难以平息的惯性在推动着它向前。
第二天早晨,多纳利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先飞到旧金山,接着坐汽车去圣克鲁兹。我撒尿时的灼痛感已经不容忽视,我去了诊所,医生给我开了些治疗衣原体病菌的抗生素。
我和多纳利有时候会在电话里聊聊,我们合作书的计划却搁浅了:我正在创作的小说所花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完成它。渐渐地,我们失去了联系。
最近我听说詹姆斯和伊恩都死了。我最后一次听到多纳利的消息,是他还住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几年前我给他打过电话,但那个号码打不通了。我没有他的备用地址——那是电邮之前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他会在哪里。离开新奥尔良之后我又搬过很多次家,我不知道多纳利是不是找过我。有时候我想要把他找到,又不知道从何找起。他可能在洛杉矶,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很可能,他已经一枪崩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