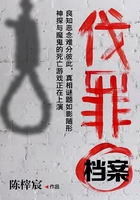“今天府上有客,得把这疯婆娘看紧了,别让她像昨晚那样跑出去闹事儿,不然你我吃不了兜着走,听见没有!!!”
白凝秀是被摔门的响声吵醒的,睁眼时率先入眼的是一方漏出星点阳光的屋顶,屋外方才高声命令的人已经走远,周围一时间静了下来。
“嘶!!!”
她拖着不听使唤的肢体坐起身,头昏眼花地看着这陌生的环境跟满地狼藉。
怎么回事?这是哪里?她怎么会在这里?她不是……死在溪山天坑了吗?
带着重重困惑愣了须弥,白凝秀才伸手捡起被摔倒她脚边的一面铜镜,镜中人瘦骨如柴面色憔悴,右眼眉梢往下至眼下卧蚕位置长了块褐色斑块,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半点看不出昔日风姿飒爽的痕迹。
“这是什么鬼!”
没“死”之前,白凝秀可是京城世家小姐榜上有名的貌美,排名仅次于江府大小姐江雨柔。臭美如她,有点没办法接受自己一醒来就变成这副鬼样子,拧着眉嫌弃地扔开铜镜,抬手扯开了衣襟领口侧头看向藏于衣下的左肩,在看到那一道狰狞的疤痕后表情复杂。
既然不是什么鬼怪作祟重生怪谈,那会是谁在她“死后”将她安置在这儿的?
白凝秀想着想着,心中又阵阵不服。明明她求死之心如此真切,是谁不问本人意愿将人救活的?
“真是太过分了,你问过本人意见么?”
她不满地锤地,双臂却传来痛感,垂首撩开那看似几百年没洗过的宽袖举手查看,两腕有着数道利器划过的狰狞伤痕交错着,不是新伤,血已经止住结痂,但伤痕却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好的处理而变得不堪入目,难以言说。
此时此刻,白凝秀用脚指头想,也知道自己身上这大大小小的伤是谁的杰作,她想骂人,双唇张张合合,却终是只愤愤道了声:“真是……太过分了!!!”
勉强地扶着墙站起身,看向这间空荡简陋的屋子,没有床,地上只铺了张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霉味儿的薄被,但很奇怪的是,屋里没有床,却有张木板钉成的矮几,看样子应该是平日里用来放置镜子、书本等物的,现在矮几被踢翻,铜镜与老旧的书本落在了地上各处,乱七八糟地躺着。
这……过的是什么鬼日子?
白凝秀太阳穴隐隐泛疼,捡起起离自己最近的一本书,拍了拍书本上的灰尘后翻开,发现这是大启开国名臣写的一本游记,精彩之处还点了墨写着标注。
她的指腹抚过标注的墨痕,字迹秀娟,落笔干净,标注内容简洁明了,下笔之人看样子是读了些书的,只是这墨痕陈旧,应该是多年前写的了。
她翻着翻着,不经意间从夹页之中掉出了张泛黄老旧却折叠整齐的纸张。弯身捡起展开一看,上头字迹歪歪扭扭、内容有些颠三倒四,有些地方甚至读不通,书写此页的人应该不是这身份的本尊。
最终,白凝秀连蒙带猜,才大致看懂了些许,这竟是这身份本尊的母亲留给她的一丝念想。
原来,她霸占着这身份名叫戴云萝,出生于明成四年冬季,是菁州县令戴全的庶出女儿。
戴全还不是县令时,看上了一名烟花巷的姑娘,便背着正妻与其来往,不久便让那烟花女子怀了身孕。奈何戴全正妻朱氏是个刁钻悍妇,即便是怀有身孕,戴全也不敢将人往府上领,赎身后藏在了一处小偏院养着,就这么一直偷偷藏了十年。
只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即便戴全再有本事,也瞒不了一辈子。戴云萝母女没过几年好日子,就被正室找上了门羞辱,但羞辱归羞辱,孩子总还是姓戴,为了免人口舌,朱氏还是假装宽厚,将她母女二人容入了戴府。
书尽于此,再无下文,可白凝秀却明白了,入了戴府的大门,便是戴云萝与母亲的噩梦开端。
昨晚哪位嚣张跋扈的大小姐,该就是戴全的嫡亲女,瞧着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戴云萝母女还能有好日子过?
菁州戴全?
好吧,即便她“死”之前耳听八方,却也从未听过菁州还有这号人物。难道是因为她“死”了太久,与世隔绝了?
“真的是对不住!”她无奈又抱歉,不过,她究竟是怎么被弄到这儿的?
白凝秀摸摸下巴思索着,可还未想出个所以然,便听腹中传来异响。为了避免刚醒来就被饿死,她不得不头昏眼花地拖着了无力气的身体出去觅食,可她推了推那不怎么牢靠的门,发现门是被人从外边闩住的。
“还真看得紧啊!”
她弯腰,透过门缝看到门外老远的树下盘腿坐了正在打盹的人,正要张口喊人,就见院里来了个拎个竹篮的小辫姑娘。
以她以往的经验,白凝秀笃定那竹篮里肯定有吃的!话本里一般给犯人送食,都是类似如此,虽说她还未经历牢狱就“死”了。
她心中大喜过望,谢天谢地总算有吃的送来了!!!
可心中还未感激完,那小辫姑娘瞥了眼那打盹的家仆,嘲讽地翻了翻白眼,才扭着身段走到这门前。
正当白凝秀以为她会开门将饭菜送进来,却听脚边“咔嗤”一声,开了个堪比狗洞的口子,从外塞进来一只缺了角的破碗,碗里有些糙饭,饭上盖着个白胖胖的馒头。
“快点儿吃,吃完赶紧给我把碗筷递出来,别又害得我挨训。”
白凝秀眨眨眼,盯着那碗白花花连根咸菜都没舍得放的米饭跟馒头,浑身的气焰都在高歌着要起义,但最终还是被气得没了脾气,忍了下来。
想她白凝秀从前无肉不欢,哪里吃过这样清淡得没一滴油水的饭,真是世态炎凉啊!
她一边嫌弃地只拿了馒头啃一边感伤,那边树下打瞌睡的家仆已经听到动静小跑过来,朝那小辫姑娘笑得憨笨。
“春儿,又来送饭呢!”
“是了,”小辫姑娘圆脸露出嫌弃,没点耐心地说:“不是送饭,谁乐意来这儿,一见了她能不晦气?”
白凝秀背靠着墙,边吃边听着他们说话。
“虽说晦气了点儿,总比去外头走动好,最近菁州不太平,出了多少起命案,老爷多久没回府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尤其是像你这样如花似玉年轻貌美的姑娘,出门可太不安全了。”
已经将馒头啃了一半的白凝秀顿住,皱了皱眉。
那圆脸小辫姑娘被他的花言巧语逗笑,娇嗔着拍他一下,“就你嘴甜。”
那家仆似乎在挤眉弄眼,“春儿,说真的,你真要出门,可得把我叫上,我来保护你,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两个我收拾一双!”
春儿道:“就你?得了吧,还保护我!别我还没怎么样呢,你就已经成了人家刀下亡魂了!”
她嘲笑一番,弯下身伸手进口子里把碗拿了出去,见白凝秀没动过的白米饭拧了拧眉,但许是心情不错,并未说什么,继续跟那家仆插科打诨:“老爷不在城里,听说是京城来了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破案,老爷不得好生陪着?夫人请了几次,只请来了位小公子,这会儿正在前堂喝茶呢。我刚特意去看了看,唉哟早就听说京城的水土会养人,还真的是器宇不凡。没空跟你多说,姐妹们都在争奇斗艳地想搏得待会儿给小公子倒茶的机会,万一他是个多情人,说不定我们姐妹之中还能出个人物。”
说着,她将破碗收入篮中,扭着腰越过了那名家仆离开了。
京城来的?别是来了个老相识!
白凝秀正凝神思索,眼前的门扇就被那家仆拍得“哐哐”作响。
“老实待着去,也不看看自个儿长得什么磕碜样儿,想着飞上枝头变凤凰呢?乌鸦就是乌鸦,飞上了枝头也还是乌鸦!!!”
门外,家仆指桑骂槐骂骂咧咧,对着那晃晃荡荡的门板又拍又踢,哪怕是对待罪恶深重的人或是乞丐,也没有比这更难听的了。
白凝秀掏了掏耳朵,吃了东西恢复些许体力,抬腿一脚踹向已经老旧不已的门扇,“哐”一声搭着门闩的一头裂开了。随即她抬腿又是一脚,门扇立刻向里面弹开,吓坏了门外的家仆,喊叫出声。
白凝秀瞥他一眼,在他惊魂未定之际抬手横劈在他颈侧,仆人立刻瘫软滑坐在地,没了意识。
白凝秀收回手,抬腿轻轻晃了晃家仆侧倒在地的身体,见没反应,撇撇嘴,“没劲!”
她站起身伸伸懒腰,在还尚未热烈的阳光下闭目片刻,犹豫着要不要去前堂凑个热闹,毕竟如今她这副鬼样子,即便是以前打过交道的旧识都未必认得出,看看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可……她如今是不想再跟京城那边有什么牵连。
但以她的脾气,这种情况,走了肯定是不甘心了!
白凝秀一咬牙,顺着传来杂乱声音的前堂走去。穿过弯弯绕绕廊里廊外,才看见前堂外围也围着不少家仆丫鬟。
这究竟是来了谁啊?这么多人围观!
她大喜过望,平生最喜欢往人堆里扎,推开了挡在身前的人窜进人群去,不过,她还没挣扎到最前面,耳边就传来一听便知是做作假装娴淑的女声在说话。
“魏公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作为,长得又俊,府门门槛都要被踏破了吧?公子要是娶了妻,得多少姑娘哭晕在护城河!有时候啊,容貌太过亦是一种罪过,就像小女,因为太过貌美从小不知受过多少罪……”
脸儿真大!
好不容易挤进去的白凝秀,见堂上坐着个保养得当的中年妇人,应该是这府宅的女主人,而坐在她对面的,是个她没见过但却觉得有些熟悉感的少年。
少年唇红齿白肤色白皙,看着不过是十七模样,一身窄袖黑衣衬得腰窄腿长,衣襟领口绣着双焰纹,白凝秀认得,那是大理寺的特有的图案标记。
这图案是太傅温知礼亲自设计,寓意自我约束,她少年时曾在温知礼手下求学,绝不会认错。
白凝秀挑挑眉,思绪有些许恍惚,但很快就被她强行拉了回来。
“夫人过奖。”
那少年倒像是见过些场面的人,这种天花乱坠的夸奖下还能镇定自若地喝了口茶,眼神都没分一个给戴夫人。
倒是戴夫人见他脸色不喜不怒,便觉得还有机会,顺势又追问:“魏公子还未见过小女吧?”
那少年愣了愣,须弥微乎其微地皱了皱眉,将那一闪而过的不愉快迅速敛下,“未曾。”
“她前不久才跟我家老爷说要到京城去游玩,如今魏公子来了菁州,案子结束后可否带小女一起回京城?小女与公子年纪相仿,途中一定很多话说,互相解闷也是可以的……”
白凝秀迫不及待要打断戴夫人那自作主张地牵线搭桥了,不等她说完,便窜了进去笑嘻嘻地扑到桌前,也不管戴夫人脸色有多难看,觍着脸朝那少年笑道:“公子你看我美若天仙,我跟你回京城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