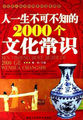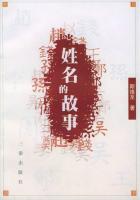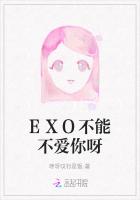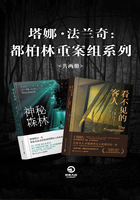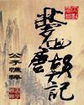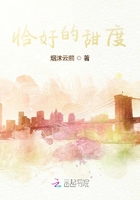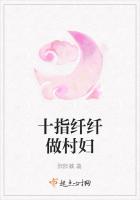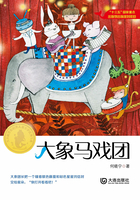李怡:今年,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位五四老人——巴金逝世四周年。想到2005年巴金逝世之时的种种社会反响,真是令人感慨!
毛迅:巴金与五四,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由巴金逝世当年的诸多议论足以见出当代国人的“五四”观念。
李怡:我记得,在当时纪念巴金的文章中出现了一种声音,即巴金之死与一个巨大的时代的结束联系在一起。有不少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巴金之死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终结,意味着“五四”传统的终结;巴金带走了一个时代。
毛迅:这样的观点,确实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巴金是中国文学20世纪最后的一个大师,随着最后一个大师的谢幕,随着他和他那时代的整个文学消逝在我们的视野中,这仿佛意味着五四所开创的文学传统的终结,从我们的价值舞台上应该得到一种重新的评判。但冷静地看,这样的结论最多只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巴金的离去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物质形态上的某种终结。从五四时期完整走过现代文学史的这样一些大师,巴金是最后一个,他的离去意味着某种物质形态的消失。但是,自五四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传统,它一直延伸到当下,并且还在走向未来,它不仅不能用终结一词来表述,而且意味着现代文学原有的方方面面的精神形态在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生长空间。
李怡:就是我们这种“终结论”当中,更包含一种潜在的、不易为人察觉的危险。在匆忙宣布巴金和五四传统终结的背后,折射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动不息的质疑和拒绝五四的文化思潮。按照这种思潮的逻辑,中国20世纪发生的很多不幸,包括文化上的和社会上的,包括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很多不幸,都可以溯源到五四那一批知识分子的那种文化姿态上,整个中国20世纪的灾难在很大的程度上似乎都应该让五四文化的开拓者来承担。巴金的逝世也似乎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终于可以宣告五四传统的终结了!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的话,那巴金和中国的五四传统就简单得不堪一击了。
毛迅: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究竟怎样与历史告别,怎样慎重地对待“历史的终结”。无论怎样,我们都没有理由站在漠视历史事实的平台上来与巴金告别,进而与五四文学传统告别。这样一种思路恰恰同样犯了目前为一些人指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端粗暴”之病,以简单下判断的方式来面对自己民族过去的遗产。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可能是出于某种策略、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需要,似乎站到了全盘否定传统的立场上,而且说出了较多的偏激之言,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不能因为现代文学中有这样一些偏激的言论,就把现代文学这棵丰繁大树上生长的其他美丽的枝条全部砍掉,甚至把这棵大树彻底挖掉。中国文学发展到现在,新文学在五四选择现在这样一个走向,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几个文化人的即兴之作,它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种样态。因此,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否定的告别观,实际上是对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否定。在今天来看,我们既要看到现代文学中早期的一些粗糙偏激的理论思考,更要看到包括巴金创作在内的中国新文学的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例如巴金式的严厉无情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对历史和民族充分负责与担当的精神,这都是五四传统中非常宝贵的资源,也是巴金留存给我们的一笔遗产。
李怡:谈到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我们也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今天在对巴金的介绍和评述当中,特别是到了新时期以后,一般都比较回避对巴金文学作品具体的评价,在这里面,就留下了许多让我们可以展开的话题,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巴金的很多文学作品都给人留下了一种所谓“不够深刻”的印象。一般都认为巴金的创作激情有余,但深刻不足;不仅与鲁迅无法相比,就是与其他一些四川作家相比,其耐人寻味的东西似乎都有所不足;而且巴金的作品,仅提供给青年一代阅读,对于中老年读者来说,让人咀嚼回味的东西就不多了。这样一种观点,对巴金是否公平,值得探讨。
毛迅:我们都曾经历过对巴金作品的迷恋,当我们回首这样一个时期的时候会发现:这种迷恋的的确确是在我们的青春时代发生的,因此我们就很容易被一种观念所引导,认为巴金的文学仅仅是青春激情的一种宣泄,一种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相对简单和简略的文学形态。但问题在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能够不断地在巴金的作品中找到共鸣,找到眼泪,找到欢笑,找到他们的某种信念。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跟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对话,而且被他们所接受,产生共鸣,这个所谓的“简单”“不够深刻”的判断反倒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立场上作出的,因此是可疑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没有真正理解到文学本身也有一种需要,文学本身也需要一种直抒胸臆的青春激情。文学需要原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可以是悲剧的,也可以是喜剧的;可以是哲思的,也可以是感念的;可以是地域文化的,也可以是民间立场的;可以是精英的,也可以是大众的,包括金庸这样的书写方式,等等。各种各样的形态丰富多彩的文学为什么不能拥有青春这样的独特样态呢?针对这种形态,一些“老”读者或者是未“老”先衰的读者,用现成的某些哲学思想资源,站在青春之外的立场上强行地进行一种价值评判,在这种时候,极可能会发生“工具误用”的问题。一旦使用的评判工具错了,就像你硬要用男性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女人的价值,或者硬要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文化的价值,这里面就有个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实际上,一种有生命力的不断地在影响一代代年轻读者的文学,它本身就体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深刻性。
李怡:的确如此。我们通常一方面宣传着这样一个观点,即文学是多样的;但事实上在关于文学的判断当中,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着一元化的思维,得出一个方向的结论。文学的多元如果放在一个共识性的层面当中,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体现出对不同风格的宽容?这就如同是一个人的生命发展史,从它的幼年、童年、青年、中年到老年,它每一个时期的生命都有自身特殊的形态和光彩,都有属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精神品质和这种精神的合理性。就像我们今天无法否认儿童的游戏和他的天真是一种让人神往的境界一样,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一个青年时代充满激情的较少思虑状态下作出的行动和生命的一种努力的合理性,同样的,我们也会肯定一个老年时期的这样一种理性和冷静。其实,人在生命的不同的历程当中,他在每一个阶段的表现都有它的合理性,我们不能用一个老年的理智来代替儿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儿童,却有老年般的冷静和理性的话,这个世界将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同样,我们也不能用老年的理性来代替青年的激情,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巴金是不深刻的,这里面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青春时代的人们都还在享受着、幻想着生命,所以青春期最能与巴金共鸣的那些人(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在那个时候还不拥有文学上的发言权,那个时候被巴金所煽动,为巴金所陶醉,但却不能用更深刻的理论、更丰富的理论来为巴金证明价值,而当我们有了权利,有了资格为巴金说话的时候,已经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境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我们用一种已经变化了的心境来阐释巴金、判断巴金的时候,这实质上与我们先前的生命状态已经发生了错位和偏离,而人们又往往会有一种假定,而这种假定在现在看来很可能是充满谬误的:人的生命的发展越往后似乎才是进入了更高的境界。这种假设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看来,本来就是充满谬误的呢?因为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过程,并不是结果。我们不能说,一个老人最后达到的境界才是一个人生命应该有的状态,反过来说,当一个人进入老年,其实也是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会对人的生命在不同过程当中的一种样态怀有一种真正的宽容,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种宽容,再重新来看待巴金,那就会真正地理解巴金。
毛迅:在文学的阅读中,一种是我称之为训练有素的“后修养阅读”,一种则是本真的即原生状态的“前修养阅读”。“后修养阅读”指已经受到各种文化训练或各种社会经验熏陶之后养成的阅读习惯,它可能有很多经验层面的丰富性,但也有可能恰好丢失了生命本真的一些信息。而一种文学能在一个读者被各种文化系统建构之先的“前修养阅读”中直叩心灵,打动一代又一代的“前修养”读者,那么,恰好说明这一种文学具有更强烈、更真实的生命力和活力,更具有充满人类发展可能性的某种深刻性。借用海德格尔的一种思路看,被现存文化建构了的阅读也就是“后修养阅读”属于“世界”的状态,而“前修养阅读”则属于一种“大地”的状态,也就是未被人类文化命名建构之前的natural world(原真自然)的状态。“大地”与“世界”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进行交流的时候,各自处在不同的层次,你不能拿“世界”的眼光来评判“大地”,当然也不能用“大地”的眼光来否定“世界”,这是各不相同的存在样态。这样来看,对善于与“大地”亲近的巴金作“世界”性的“不够深刻”的判断显然有失公允。而且,即使是以“后修养”的状态来阅读,也不能简单地说巴金的作品就没有深度,你只能说他的某一些作品可能停留在青春文学的层面上。而且,当我们面对《寒夜》这样的作品时,如果还坚持说巴金不够深刻的话,那我们就会怀疑这个读者修养后的素质是不是出了问题。
李怡:因为巴金的《家》给人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当很多的文学读物提到巴金的代表作品的时候,不假思索会涉及到《家》,实际在巴金的自身文学发展历程中,除了《家》之外,他还有抗战后期的一个成熟期,这个成熟期就包括他的《家》《憩园》在内的一系列的作品,这个时候与他前期的形态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仅仅以《家》的存在形态简单地当作巴金的代表,当然就是不全面的。
毛迅:这不是一种发展的观点。巴金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他既有前修养状态的文学样式,也有后修养状态的文学样式。当我们面对《憩园》《寒夜》《第四病室》这些作品时,我们真的没有理由再来说他的作品没有深度或不够深刻。
李怡:以上谈的是巴金思想内容层面。此外,批评界还有一个思维定势是从文学性的角度切入的,认为他的作品浅露、直白,觉得他在文学技巧的层面、文学性诉求的层面,不够丰富,比较简单,甚至才智不足。巴金自己曾提到过,他比较欣赏曹禺、徐志摩等,有人就认为巴金提到这些人说明他与这些人的才华横溢是有差距的。
毛迅:从“多元的文学性”立场来看,巴金与特别偏重表达技巧的作家相比,他可能显得手法“简单”。但这种“简单”是和他简单而深刻的内质相通的。他对青春激情的这样一种“简单”释放如果用非常复杂非常中年化甚至老年化的技巧组合,那么在“架构”和“肌质”的意义上讲,显然是不协调的。他在很多时候选择的这样一种看似很直白、比较浅显易懂的话语方式,是一种有意味的选择,这种选择使他走到了质式合一的境界。进入到《寒夜》时期后,他的整个技法技巧方式又有了明显不同,这与他中年化了的人生体验和人生理解又是质式相匹配的。即使回到他的青春文学样式上,他仍然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话语方式,这就是那种把心掏给读者的倾诉性的话语方式,看上去浅显直白,却平实动人,朴素无华。这样一种倾述方式本身具有一种很强的诱导性、感染性,以及一种与人顺利沟通的能量和价值,这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追求的交往理性中比较有效的交流和对话方式。
李怡:过去我们对巴金的从思想和他所谓的技巧也就是他的文学性方面所下的种种判断,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直接的述说意味着简单,复杂的形式上的设计才意味着一种深刻和高超。其实,对于文学而言,不论从它思想的表述或者技术的设置上都有它一个自身的有机形态。只有结合特殊的意义的运用,我们才能作出判断,并没有一个超越于具体表现形态和表现内容的绝对的低和高的“标准”存在。巴金后期的创作与前期的相比,他显然不能再用“不够深刻”来加以判断,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在这个时候,巴金也和一些专门从事哲理性思考的作家有所不一样。到后期,巴金对人生意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了更自觉的感知,他是用自己感性的方式,来呈现人生的复杂性和暧昧性。在《憩园》《寒夜》中都能看出,他不再像早期那样进行一种简单的单向判断。而是通过仍然富有激情的对人生对生命的诉说,包含了人生的种种方面的意义。在这个时候,当读者读到他的作品时,仍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情绪和感性的冲动,这种感性的冲动和情绪仍然是巴金留给我们的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他跟他的前期仍然是有一致性的。这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他不是对哲理的一种直接的表达和探索,但这其中包含了引发我们诸多思考的可能性。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样一种“把心掏给读者”的一种状态,类似哈贝马斯说的那种交流和对话的状态,实际上也对应着他的一种情绪抒发和情绪抒发当中自然包含的人生复杂意味的创作目的,巴金的哲理和深刻不是直接体现在对思想和哲理的探索上,而是体现在对人生的感性场景的体验和感悟的一种承受和尽可能的原生态的呈现上,这里就不能不说,巴金从他的思想内涵到他的艺术设置都有非常独特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叫做追求一种思想到艺术非常自然化的表现形态,这种形态往往会因为它过于自然而为我们所忽略。
毛迅:正如我们经常谈论的诗艺,诗歌可以直接抒情,也可以间接抒情。直接抒情是喜怒哀乐的直接表达,但有很多诗人愿意选择间接抒情,他不想把自己的人生体悟简单明白、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而是让意象这样的“客观关联物”去承载他的思想和情感体验的丰富性。这样一种传统更像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也就是含蓄、委婉,而像巴金这样一种原生态的具体呈现,通过呈现出的故事、人物、场景、细节等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哲学等所谓具有深刻性的资源的因子,留下了很大的思想延展和品味感悟的空间,这些都是“后修养”读者可以有所作为的“空白”。这样一种书写方式,就我个人来看,反而是一种更具有文学性的方式,把所思所想所感全部藏于现实或者具象的层面之中,自己不做简单的判断和结论,这表明巴金既有思想层面的成熟,具有某种深刻性,也有表达方式上的成熟:给阅读预留了更大的审美空间。因此,他的这样一种选择在文学性意义上确实是一种独特的追求。
李怡:我们经常称道的所谓深刻,其实也可能进入另外的误区,当这个深刻离开了人的自然感受,人为地进行一种直接的呈现和追求的时候,其效果也未必好。例如四川作家李劫人,他是我们都很推崇的一个作家,但李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他的《大波三部曲》进行了改写,特别是在对第三部的改写中,为了体现其中深刻的历史演变的内容,他改变了初版中对成都人情社会很自然很原生态的表述,加入了很多关于反映辛亥革命中保路运动大段落的历史探讨的内容。当然,《大波三部曲》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如果把改编本与初本相比较,就知道改编本为了人为地突出历史演变规律的深刻性,忽略了当时在他最早创作《大波》时所感受到的真正的生活自然性,这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教训。
毛迅:在人生的前行过程中,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都在不断地生长,人们对世界、对人的理解也会不断地奉献出个性化的思考,但这些财富都是人类智慧在特定时期的产物。一种思想能成为一种主流或主导性的思潮,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殊语境所选择的。但就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说,这样的一些思想的合理性不能无限地放大。在人类或个人的成长历程中,人的思想总是流动不居、变化多端的。世界上原本没有一种真正可以被证明为永恒的绝对真理,也没有这样的认证标准,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明的作家不把他某些“特定人生时段”的思考限定在某种思想结论上,而让生活本身的丰富性来蕴含可能被发现的某种新的思想,留足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和空白,这样的做法,反而是对人本身能力、对人本身与自然相处的一种特殊状态的更深刻理解和把握。
李怡:尤其是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纷繁复杂的表象当中,并不容易总结出我们所谓的深刻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加修辞的追求自然的状态,往往有一种很大的包容性和合理性,在今天的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学当中,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现象,今天当代文学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了,普遍都有这样一种感受:今天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生的丰富性已经超过了今天很多精英文学作品可以呈现的丰富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现实比我们的文学更富有现象力,更具有文学性,所以今天进入了一个写实的文学时代,今天写实的文学留下的价值比虚构的文学更具有意义。因为今天虚构的想象已远远赶不上现实所发生的一切,如此光怪陆离的匪夷所思的社会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今天这个时代和社会意义上,我们来回地想巴金包括他的文学作品,从他的思想形态和艺术形态都是意味深长的。
毛迅:这样谈论巴金,其实也是谈论了五四。在所谓的文学技巧已经发达和成熟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指摘五四文学的简单和直白,感叹我们新文学的起点的种种问题,仿佛我们早已经超越了它,可以对它指手画脚,任意评论了。其实,就是在五四文学的简单里,包含了中国文学难得的青春气象,包含了追求“大地”之美的质朴和自然,也许它们的白话形式还不够完善,也许它们的技巧还不尽圆熟,但是青春的五四就是一切创造的起点,大地的质朴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
李怡:就是这样。巴金代表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真实的一面,它或许不是我们今天所期待的那种深刻,但是却成为了一切深刻的起点,不能理解中国五四传统的这样一种质朴的特点,也就无法从内心尊重五四,就会用各种方式挑剔和苛求五四,当然,对于巴金这样一个五四的象征符号,也就多少是不屑的,也会在匆忙中宣布它的终结。但是,一个匆忙终结了自己生命“青春”与“大地”质朴的族群,很可能也就丧失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