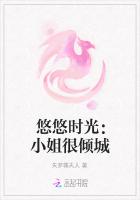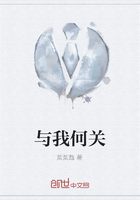说到中国近现代美术,人们常常喜欢把中国不同的地域分成不同的流派,从大的区域而言,像金陵画派、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等,至于西南画派和长安画派的形成基本是1949年以后的事。所谓的“北派”就是其中一个。民国时期的北派也可以叫作京津画派,也就是指北京天津地区的画家群体。但是北派画家不一定都是北方人,也有很多是南方人。谈到民国时期的北派,一定要提到创建于1919年的一个绘画组织——湖社。
直追宋元的湖社
湖社最早的主持人是金城,字拱北,号北楼,当时住在北京东城的钱粮胡同。房子很大,由几所院落组成,后门在马大人胡同。那时一提到金北楼,一提到钱粮胡同金家,旧北京几乎尽人皆知。金北楼早年学戴熙,画风颇有古意。他在民国初年做过国务秘书、国会议员。在1910年就利用部分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了中国画研究会,而湖社正是在中国画研究会的基础上创办的。湖社于1919年正式成立,得到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金北楼被推举为会长,周肇祥为副会长。当时湖社基本上是由两大部分人构成的,一部分是当时精于书画的官僚士大夫,一部分是专业画家。
我们今天一提到当时在北京的画家,肯定会提到齐白石,实际上在1935年之前,齐白石还没有真正登上北京的画坛。当时北京画坛地位很高的画家有这样一些人,首先是金北楼,可以说是彼时画界的领袖,可惜他在1926年就病逝了,只活了四十八岁。金北楼是浙江吴兴人,也是王世襄的舅舅,他的妹妹叫金章,也就是王世襄先生的母亲,画金鱼特别有名。王世襄的另外两个舅舅是搞竹刻的,一个即金东溪,一个叫金西厓,不但擅长竹刻,也精于书画。湖社成员中,官僚士大夫的代表人物有叶恭绰和周肇祥等人,周肇祥号养庵,人称“周大胡子”;叶恭绰号誉虎,在民国时期做过交通总长。此外还有一些重要人物,如陈半丁、萧谦中、胡佩衡、吴镜汀、汪慎生、徐燕孙及金北楼的弟子陈少梅、祁井西等。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与陈半丁很熟,至今我还有几幅陈半丁的画作,都是他送给我祖父和外祖父的,包括我母亲结婚时陈半丁题款的“景南小姐于归之喜”,画作是一幅荷花,题为“同心多子图”。当时名气很大的还有吴镜汀、胡佩衡、萧谦中、汪慎生等,都是北派中的代表人物,此外天津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画家如颜伯龙,稍晚一点的秦仲文、画工笔人物的徐燕孙等,都属于北派画家。
湖社最大一个艺术特点是什么?他们主张以清代“四王”入手,直追宋元,这是他们的宗旨,因此,后来就被南派的画家和一些新派的画家奚落为泥古不化。其实在我看来,元代无疑是中国绘画的一个转折点,明末清初“四王”在此基础上发挥了元人的笔墨气韵意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实际上“四王”并不是很好学的,“四王”的东西也并不是说完全泥古,所以说“四王”在中国画的一些基本功和笔墨的运用方面是影响了有清一代人的。以“四王”入手并没有错,北派画家对此的继承应该说是功不可没,但是他们确实也有比较呆板的一面,比如重皴擦而少渲染,缺乏一定的活力等。而近现代南派画家的风格也是借鉴了前人的技法,从徐渭到吴昌硕对他们都有较大的影响。
我母亲十二岁就开始学习国画,当时家里给她请的老师就是徐北汀先生,也算是北派画家。她的画后来跟吴祖光等“非专业画家”一起在福建展览过,我现在还保存着她的一些绘画,很能看出绝对是受到这样的影响。母亲一辈子也没想要成为画家,绘画对她来说,只是作为一种陶冶身心的修养而已。
怡情消闲的松风画会
比湖社晚一些的是1925年成立的松风画会。松风画会是清代宗室间形成的一个以书画相切磋的松散组织,不像湖社,应该说是属于自娱自乐的性质,怡情消闲的文人雅集形式。发起人是溥雪斋。溥雪斋名溥伒,字南石,号雪斋,别号松风主人,松风画会就是以溥雪斋的号为社名。除了溥伒,早期还有在上海的红豆馆主溥侗,后来被尊为“南张北溥”的溥心畬。这两人虽为松风画会的会员,但因远在上海,又早逝或因其他因素,与松风画会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成员还有像溥僩(毅斋),溥佺(松窗)和惠孝同、祁井西、叶仰曦、关和镛等。因为是宗室子弟发起,因此许多晚清耆旧也参入其中,如陈宝琛、罗振玉、宝熙、袁励准等。松风画会的主张和风格与湖社差不多,也是学习“四王”,师法宋元笔意。
再晚一点的还包括了溥佐和启功先生,当时都很年轻。他们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松字,例如溥雪斋叫松风,溥佺叫松窗,恩棣叫松房、叶仰曦叫松阴,启功叫松壑,我有一把当时松风画会几个人合作的山水成扇,启功补“桥柯远岫”,当时启先生才十九岁。松风画会和湖社之间的人员有穿插,有的人既是湖社的会员,也是松风画会的会员。当时很重要的北派画家还有于非闇、王梦白等,王梦白的画作很好,诗词也佳,这些人都是北派的代表人物。
湖社在金北楼去世后一直延续着,直到今天,还有湖社的名称,但是与原来的湖社已经完全不是一种性质了。松风画会于1925年成立,一直活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始终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雅集形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活动的地点就在北海的画舫斋,这些人我都见过。
民国时期的绘画远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有很好的市场。可以说,从民国初年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中国画是没有太大市场的,尤其是北派画家的作品,更是卖不上价钱。例如松风画会中较晚的溥佐,号庸斋,是道光一系的宗室子孙,还是赵家比较远的女婿。他有八九个子女,没有正式工作,靠卖画根本不可能养家,因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活还十分艰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天津美院工作,才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的收藏热,就是吴镜汀、陈半丁这样的画家,一张画也卖不了十几块钱。
齐白石在北京成名
在北京的画家中,齐白石可谓异军突起。齐白石第一次到北京来是在1907年,陪着湖南夏寿田一起来的,停留时间很短,1917年再度到北京才正式居停。到京后,齐白石得到樊樊山和郭葆生等人的帮助,又结识了陈师曾、姚茫父、陈半丁等人,诸人名气当时都远在齐白石之上。陈师曾是使齐白石得到赏识和提携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他后来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齐到北京以后,画风也在逐渐变化。后来经陈师曾介绍,他的画在日本展览,得到日本画界的极力推崇,在北京也名气日隆。齐白石真正在北京得到认可,实际上是在1935年前后,那时张大千也来到北京,认识了齐白石,他们都在中山公园的水榭办过展览,后来被称为“南张北齐”,奠定了齐白石在北京画坛上的地位。
那时候画家都有润格和笔单,也就是画作每一尺多少钱,齐白石润格最低的是花鸟,花鸟以上是人物,人物以上是山水,但是在写意的花卉或果实上加一只工笔的草虫,价格就要加高许多。因为草虫画得很细,是工笔,什么蝈蝈、蚂蚱之类的,每加一只草虫加几块钱,所以说有草虫的那种册页或者条幅价钱会很贵。不久前,我在浙江桐乡的钱君匋艺术馆保管部看到过一本钱君匋所藏极为精美的二十四开齐白石册页,内中一幅画有数十只草虫,并夹有一份齐白石当时的笔单,明确写着各种作品的价格。齐白石刚到北京的润格差不多两块大洋一尺,但是到1935年以后就十几块钱一尺了。齐白石虽然住在北京,但是不能算是北派画家,只能说是独成一派。1919年,齐白石纳了胡宝珠为侧室,就是如夫人。后来他的原配妻子死了,就把胡宝珠扶正,为此还举行了扶正的仪式,这也是在他最得意之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半丁的画作价钱远在齐白石之上,可是后来齐白石就逐渐超过陈半丁了。1949年以后北京有几个画店,像琉璃厂的荣宝斋,王府井的北京画店、和平画店,买一幅齐白石的小品,一般在十五块钱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十块钱,条幅裱好也不过二三十块钱。
北派画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一直处于低潮,像胡佩衡、吴镜汀,都不太被认可,相对来说金陵、海上画派风头更健,像傅抱石、钱松喦、唐云、谢稚柳,境况都比他们要强。
湖社和松风画会的很多成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到了北京画院,开始叫中国画院,后来周恩来将其改称为北京画院,第一任院长是叶恭绰,以后是王雪涛主持,所以湖社和松风画会的成员都是后来北京画院的骨干力量,这些人活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都有。
这批画家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京津画派的代表,可惜的是有的人很年轻就去世了,像很有才华的陈少梅。他的东西很清雅,但是和金陵、海上相比,泥古的东西比较多,创造性的笔法相对来说少一点儿。尽管如此,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抹杀他们的艺术成就,尤其是民国时期他们在继承传统和传统技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像吴镜汀、胡佩衡、陈半丁、王梦白等都有很高造诣。黄宾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来到北京,为北京的艺术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很多篆刻艺术家都到北京,像王福厂、陈汉第、高心泉、童大年等也都对北京的篆刻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民国的北京画坛是很包容的。
扬南抑北的五六十年代
1949年之后,买画的人很少,解放区来的一批干部,如康生、陈伯达、田家英、邓拓等,他们不大买当代人的画,所谓当代就是指民国时代的画家。他们也去追古人的东西,但是不太推崇“四王”和文人绘画,喜欢的是扬州八怪这类的风格。田家英比较有文化底蕴,趣味较高。我看过他的小莽苍苍斋在“文革”后举行的一次展览,买的东西都是价格不贵的小品或是文人画,在那时也就几块钱、十几块钱,一些明清人的东西名头不算太大,但都是精品。
1949年以后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一些传统中国绘画甚至西洋油画并不符合那时简约的生活方式,买画的人很少了,所以即使像徐悲鸿这样比较红的画家,画作也不是卖得很好。一般人谈不到收藏,即使买也只为装饰。不过相比之下,金陵、海上和岭南画派要稍好一些,尤其是在全国美术展览中,南派画家都显得十分突出。像岭南的关山月、金陵的傅抱石、西安的石鲁、赵望云等,都是那个时代比较突出的画家。艺术评论也是抨击北派画家的风格。过去艺术流通不是那么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和平画店、北京画店,一个星期能卖出几张画就不错了,所以在北京中国画的价钱都不太高。有些老派画家比较惨,尤其是后来在1957年打成右派的一些画家,如陈半丁、吴镜汀等。陈半丁有一张作品是给政府机关的,画的是荷花,有白的有红的,上面题了一首诗:“红白莲花开满堂,两般颜色一般香,犹如汉殿三千女,半是浓妆半淡妆。”据说当时有人看到了,就说诗的内容很反动,红的、白的两种颜色一个样,就是寓意国民党、共产党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给他扣的帽子很多,一直到1970年去世他都很不得意,他的作品当然也就更是不行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画市场,实际上可以说是扬南抑北。当时欣赏的是大写意的作品,另外一些新的笔法更生面别开,如石鲁、赵望云、潘天寿、李可染、傅抱石等。人们喜欢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意,喜欢奔放、新派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受到人们重视,那种遵循传统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市场。我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人向我的祖母借了四百块钱,后来无力偿还,就给了她四十张约三尺的没有装裱的王雪涛花卉抵债,折合十块钱一张,于此可见当时王雪涛作品是什么价格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祖父主要收藏绘画,但他很保守,根本不要当代人的东西,南派北派都不要,怎么着也得要清人的作品,而且像扬州八怪这类的也是不会收藏的。实际上这也是错误的,当代人的东西何尝没有好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这也可见当时某些藏家的一种心态。前些时候在网上偶见一幅陈少梅的山水,居然有我祖父的鉴赏印,实在令我不解。
其实,用“南派”“北派”来区分民国时期的画家并不科学,所谓的北派画家多数也是南方人,只是当时寓居北京,受到更为传统画风的影响而已。而很多南派的画家在北京也有居住和教学的历史,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交融。如张大千到北京,他的一些工笔仕女,临摹敦煌壁画的画稿,还有山水什么的,在中山公园水榭展出,也令北京画坛耳目一新,于是才有后来的所谓“南张北齐”之称。但这个说法在旧北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一般来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北京画坛已经是异彩纷呈了。非常可惜的就是陈师曾,他是在民国绘画教育等各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一个人,可惜去世太早,以至于在今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陈师曾也在日本举行过多次画展。在中日绘画的交流方面,陈师曾和周肇祥应该说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周肇祥这人一直有争议,因为他在人品上有一些欠缺,再有就是他在敌伪时期做过伪华北方面政务委员会的伪职,做过一些中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事,因此,对周肇祥历来有一些不同的评价。但是周肇祥在最早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以及1918年艺专的创办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也是事实。
陈师曾作品主要是花鸟,实际上他也打破了传统,受到吴昌硕很多的影响。再远了说,像徐渭、扬州八怪对他来说都有一些影响,可见陈师曾也是兼收并蓄的人。他学画较晚,但是非常聪明,笔墨确实好。中国绘画实际上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陈师曾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陈三立的儿子,史学家陈寅恪的哥哥,家学渊源,他的绘画和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