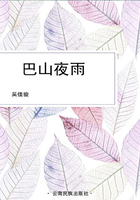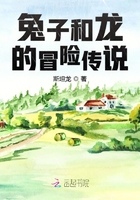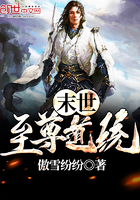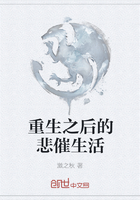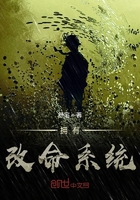中国山水诗所成就的形色清晖空明、襟抱消融心灵安放、自然与性情互融互通的艺术乌托邦境界,在吸引国人的审美注意力、涵养国人艺术性情和精神境界的同时,也召唤着古往今来众多论者探寻其中美的奥妙,破译其中的艺术密码。与以往论者研究山水诗锁定以山水诗作品及其所形成的流衍轨迹——山水诗诗史为研究中心视阈求解不同,本研究尝试另辟蹊径,以“前史”的视野对山水诗进行溯源性的探索与考察。如果说既有的大量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山水诗“去脉”——山水诗诞生以后的作家、作品与历代风格流变轨迹关注的话,那么,我们在本研究中则致力于探究山水诗的“来龙”——对山水诗诞生或者说山水诗诞生前诗类流变中的审美经验进行集中清理。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认为,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准确的还原和把握的过程中,“来龙”与“去脉”二者不可偏废,它们也许是无限逼近研究对象真实样态的两条同样重要的路径,尤其是对于研究业已以历史形态封存的山水诗。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山水诗“来龙”的清理是一件更具前提性、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否则很多研究或论断就会成为不尊重历史事实的、一相情愿的主观臆想。
一
在对山水诗前史的耙梳和董理中,我们的问题意识或者说学术视野是以诗歌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基本感性关系——审美经验为主线。在逼近研究对象的文本细读过程中,我们清理出《古诗十九首》、行旅诗、公宴诗、游览诗、招隐诗、游仙诗、玄言诗等七个诗类作为山水诗前史演进所经历过的标志性阶段。因为在这些诗类中,审美经验表现出大的跃迁与新变。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这几个诗类称谓中的审美经验的变迁并不完全表现为均衡的、平稳的、渐进的演进关系,只是为了研究过程中称引方便而已。在昭明太子主持编选的《文选》中,按题材分类的22个诗类条目中有行旅、公宴、招隐和游仙等,而在后世诗歌发展中具有重要诗史地位的《古诗十九首》当时只是《文选》第二十九卷诗己“杂诗上”中排在第一的一组无名氏诗作的统称。在该选本诗歌分类中并没有出现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玄言诗、山水诗两大重要诗类。山水诗首次获名出自相传为盛唐诗人王昌龄(698—757)著的《诗格》中:“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艳者,神之于心,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玄言诗获名则要晚得多,它是现代学者在研究六朝文学中对“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一类诗歌作品所使用的诗类概念。后世公认的标举为玄言诗和山水诗的诗类,在《文选》中是窜杂在行旅、游仙、祖饯等诗类中的诗作游离分子。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诗体未分的杂合状况,另一方面表明了山水诗、玄言诗与这些诗类在源头上的密切关系。但是,遗憾的是,历代研究者对山水诗起源的清理没有充分注意到这种客观真实的历史情境,根据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诗歌经验,或者根据某一诗论名家的断语,或者根据现代诗歌观念,直接推断得出山水诗起源于某一单独诗类的简单结论。这是一种简单的、单维的直线思维方式,无法见出山水诗审美经验的复杂、多元、曲折的来源。
因此,本研究所做的正面努力是通过对山水诗前史中诗类审美经验的清理,以见出这些诗类在朝向山水诗演进进程中所经历的流变之迹和贡献的美学质素,从本源上揭橥山水诗的审美经验与美学品格及其渊源所自。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正本清源地对山水诗审美经验以多面向的观照。
二
我们对山水诗前史的基本考量质素是审美经验,即人与包括自然在内的客观世界的感性契合关系。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以孤立、静止的原则看待这些诗类,而注重树立和秉持一种动态、运动的视野看待审美经验的变迁,也就是诗歌运动的观念。借鉴杜夫海纳对审美经验的分析策略,本研究在山水诗前史研究中从视野上将审美经验董理为两个维度,即客体维度的审美对象——客观世界(自然山水)和主体维度的审美主体——抒情主体及其情感意志表现。对山水诗前史的诗类审美经验之客体维度的考察,本研究尝试从关注对象、场景氛围(场域)和审美时空的转换三个并列序列结构展开。对审美经验之主体维度的考察,我们则是从主体应对外物的抒情方式和记录方式两个方面进行。
在山水诗前史中,诗类关注对象是由社会人事经由池苑园林渐次转到自然山水的“选择性积累”的诗歌作品。《古诗十九首》和行旅诗中的关注对象是以日常生活的社会人事为主。不管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还是曹操《苦寒行》、《秋胡行》、王粲《从军诗五首》等行旅诗都以社会人事为视点。因为,此期的创作主体往往为求仕、征战或赴任等事功目的而奔走于名利与兵戎之途。行旅诗就是对这种社会人事变迁的写照。此期,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和潘岳的系列诗歌的关注对象,已经出现较纯粹的自然物象并形成景句。公宴诗和游览诗的关注对象主要是在西园(建安)、竹林(正始)、华林园(西晋)和金谷(西晋)等当时著名的池苑墅园中的物象。招隐诗和游仙诗则由想象的自然转到方外仙境再转化为仙境山林化。到玄言诗,其抒情主体以自然山水为“道”的现实体现物,于是自然山水成为关注对象。
审美经验客体维度之关注对象的变迁,实际上就暗含了场景氛围的转换,后者为前者提供场域与背景。这种转换在山水诗前史的演进中是由社会周边人事转向远离人寰的自然山水的。《古诗十九首》、行旅诗、公宴诗和游览诗中的审美经验场域是世俗的周边人事,招隐诗和游仙诗中的审美客体开始与社会周边人事间距化,由自然而方外再至仙境山林化,在玄言诗中走进远离人寰的自然山水。
山水诗前史的《古诗十九首》、行旅诗、公宴诗、游览诗、招隐诗、游仙诗、玄言诗七个诗类审美经验的变迁,还包含了审美时空的转换问题。在《古诗十九首》和行旅诗中的审美经验是以时间驾驭空间,因为抒情主体重在抒发一种生命迁逝的悲怀,体验时间—生命—运命的不可把握。到公宴诗和游览诗中,这种基于时间的感慨相对淡化,因为主体在园林空间内找到了通过观景享乐来排遣基于时光流失所导致的内心悲怆的平台。招隐诗中的山林空间虽然是基于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却使诗歌朝向空间方位的自然山水拓展。游仙诗中的空间已经延伸至仙境进而沟通方内与方外(仙境山林化),以空间沟通时间,表现出对生命无限的美好渴望,但其起点是基于时间之维。在玄言诗中,抒情主体是以自然山水作为体悟形而上之道的媒介,由于玄学追求“独化于玄冥之境”,时间被切分为独立的小段而不对空间产生重构作用,由此自然山水的空间之维得以独立展现。
下面我们来归纳山水诗前史审美经验之主体维度中的主体应对和记录外物的方式。山水诗前史中诗类的主体应对外物的抒情方式大体渐次经历了比兴象征、感物缘情和观物遣理三个阶段。《古诗十九首》以空间物象的物是人非来兴起主体内心生命迁逝的时间感受,行旅诗的主旨也是兴发一种生命情怀,比兴象征是它们基本的、主导的抒情方式。此后虽然抒情方式的显性形态更迭,但是在寓目直观山水前,作为一种类比思维类型的比兴象征一直还是重要的、基本的诗思方式,只不过比兴产生新变,衍化出新的、更为具体的抒情模式。从诗思本质来看,感物缘情和观物遣理也属于比兴类比思维的范畴。随着生命迁逝感的消淡,审美时空由时间主导维度向空间维度转换,公宴诗、游览诗、招隐诗和游仙诗的基本抒情方式是感物缘情。无疑,观物遣理是玄言诗的主导抒情方式。在玄言诗中,其文本结构中的抒情过程一般表现为由“观物”到“遣理”的迁移,而实际构思程式却是主体为某一固有的玄理在自然山水中直观、演绎其对应物或其投射对象,也就是先“理”后“物”。情感在诗歌中第一次被消解。山水诗对自然的观法正是接踵玄言诗之直观传统而实现纯粹的寓目直观,即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里所谓的“物沿耳目”。同时,山水诗前史的审美经验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记录方式在技术上也经历了由叙述到描写的适应性调整。在《古诗十九首》和行旅诗中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基本记录方式是叙述,就是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当作“事件”或“情节”(event or scenario)来记叙。对一个具有发生、发展历程的事件或情节的叙述,就是对一个过程的记叙或再现,而过程表现为一定时间段的持续或延续。因此,《古诗十九首》和行旅诗中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叙述,是和这两个诗类中时间居于主导的时空美学观相适应的。从行旅诗的后期历经公宴诗、游览诗、招隐诗和游仙诗的演变来看,自然物象在客观对象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审美时空组合中空间逐步居于主导,主体记录自然物逐渐以描写为主。为了呈现对象的物色、物态之鲜活生动,主体以园林和仙境中的自然物象为空间之“景”进行多维描写。到玄言诗中,主体置身自然界直观山水,精致地描绘山水之形构和声色以取媚形上之道。真正山水诗的兴起就是以直观山水,即事见景,即物见色的审美观照为起点。
三
结语行文至此,或许有读者心生疑虑:本研究在对山水诗前史的追溯和清理过程中,还有一类重要的外来文明——佛教对山水诗前史之自然审美经验的影响与作用并没有充分展开,在论述中似乎有被忽略或刻意回避的倾向。
这是因为我们基于如下考虑:佛教在两汉间东渐来华、晋宋间被中国的士林中人普遍受容,是通过本土化新道学——玄学的接引,即佛教玄学化的方式,也就是佛教是通过与玄学融合而被两晋士人所普遍接受,遂大兴于中国。大乘概念如“智”或“明”、“空”、“寂”和“方便”,自然微妙地与玄学中“圣”(saintliness)、“虚”(emptiness)、“无”(non-being)、“静”(tranquility)、“无为”(non-activity)、“自然”(spontaneity)和“感应”(stimulus-and-response)相对应。因此,佛教似乎就与中国思想吻合,强调恒常不变的天道是万有存在的原动力,实际上也赋予万有以自然属性。更为生动而具体的案例我们不难从《世说新语》中那些亦玄亦佛的谈锋及宗炳、支道林等人玄佛兼修的双重身份中得到验证。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时著名的玄言诗人孙绰在《游天台山赋(并序)》中所言:“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因此,我们所说的玄言诗在不经意间既表达玄悟,也体现佛理。如饶宗颐先生早已指出东晋前期玄言诗人庾阐诗中所受到的佛教影响。陈允吉先生有专文对玄言诗援佛入诗做了全面的论断:“厥类诗作(引者按,即玄言诗)之所以在此际大量出现,除了受曹魏、西晋以来士人清谈习尚之直接影响外,还同佛法自东晋开始深入本土文化结构这个大背景有关。当时翻译过来的众多天竺说理佛偈,业已具备了对本地诗歌潜移默化的能力,完全可以充当许询、孙绰、支遁等人创撰‘理过其辞’篇章的蓝本。这种诗体上的参照和借鉴,就是催促玄言诗成熟分娩具有关键意义的直接动因。”可见,在玄言诗中,佛教已经以玄言为中介浸淫入诗歌了,而且前贤时俊已经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探索,业已形成学界公论。只不过,今人概以玄言诗之名指称这些浸润着佛教审美经验的作品而已。而更为纯粹的、本然的佛教对诗歌的浸染或者说援佛入诗所成就的审美经验,在谢灵运山水诗中我们可见出早期标本。
如果不受诗类演进的题旨限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进路董理出山水审美经验的生成之迹。从寓目或者观的方法论养成而言,作为中国美学发源地的“人物品藻”在山水诗形成过程中所奉献的审美经验也是不能抹杀的。《世说新语》中记录的对人物的“一见奇之”、“见而异之”、“一见改观”等“见貌”“即形”而“征神”的品鉴和评赏案例,都表现出对亲见身观的倚重,即着力表达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感官的所见。
宗白华先生认为,晋人秉持“人格唯美主义”。这种人格唯美主义以“自然界的美来形容人物品格的美,……这两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可见,宗先生认为,“自然美”与“人格美”是在魏晋时期同时被发现的。在表现形态上确实印证了宗先生的判断,因为魏晋人往往以“自然界的美来形容人物品格的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晋以前(含东晋)包括诗、画、乐等在内的艺术门类中,自然山水并不是它们的主位对象,而只是作为一种“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感物兴情(吟志)的比兴意象。也就是说,晋人的主导倾向是人伦的人格品藻,不过在人物品藻中表现出自然取向,可见自然物象的观察和感应是为兴发人格美之目的。因此,从抒情流向来看,应该是晋人在表现人格美的过程中逐渐转移到对自然山水美感的发现中来,“人格的唯美主义”在山水美感成为自为对象后,其作用和地位式微或至于成为山水的衬托和点缀或至于无了。台湾学者郑毓瑜就认为山水诗的形成是在六朝由人伦品鉴到山水寓目直观的迁移过程中完型的。
《世说新语·巧艺》记载晋顾恺之(348—409)对人物形神的刻画“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描绘人物细节特征、表现其神情特质则是“画裴楷像,颊上添三毫,顿觉神采焕发”。对人物画有着独喻之微的顾恺之认为,“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这反映的是魏晋时期绘画艺术的一般美学观,即在绘画中人物画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高于山水画,山水往往是人物的背景和衬托,而不是主位对象。此时,也就是在晋宋间中国山水画处于形成期,它与人物画尚未截然分离。但是作为人物的背景和活动空间,山川景物已经大比重出现。因此,唐代画家兼画论家张彦远在对绘画中的山水与人物关系的对比中发现,“魏晋已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今天,我们从顾恺之留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画作可以为张氏上述论断找到论据支持。
以“画绝”闻名并对人物画有着深刻见解的顾恺之还留下了“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等精警的写景名句,生动地描写了江南的秀丽景色,诗中的画境如在眼前。他在为云台山这篇画作所作的题记,即《画云台山记》中就表现了上述诗作中的山水审美旨趣,尽管该画属于人物画:“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而吐于东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暎日。西去山别详其远近,发迹东基,转上未半,作紫石如坚云者五六枚夹冈乘其间而上,使势蜿蜒如龙,下作积冈,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从这段话来看,在顾恺之所处的东晋时期,尽管是人物画,但是作为背景的山冈、流水、岩石、桃树、孤松等自然山水物象已经成为艺术家注意捕捉的对象,既有山势的高峻、岩石的棱嶒、水流的隐现、山峰与深涧的对比等表现的空间展延,也能捕捉基于时间维度的光影变化对物象成像的影响,这是早期山水画所标示的绘画高度。《画云台山记》还提到人物画中人物与山水的关系:“凡画人,坐时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鲜微,此正盖山高而人远耳。”值得注意的是,此期人物画对山与植物同人的关系,已经清楚地作了说明。“山高人远”的远近与视觉成像原则表明了山与人的比例对比不再是“人高山远”,可见《画云台山记》提出的“山高人远”的绘画原则自然已经背离了传统人物画中“人大于山”的美学法则了。因此,被认为开启山水画论帷幕的《画云台山记》具体而微地反映的是这样一个节点:人物画向山水画过渡进程中继往开来、这两个画科融合胶着的情形,而人物画中的着墨比重、着力表现的重点已经山水大于人物了。
南朝宋代画家宗炳(375—443)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山水透视法则:“竖画三寸,当千刃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与宗氏同时代、同样纵情丘壑的王微在《叙画》中提出了“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怡情说和“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的尺幅千里说。可见,时至晋宋,中国山水画远取其百里之势、近取其灵趣之质的美学观已确立其逻辑起点,而空间视觉原则的树立体现了山水画的深化和延展。宗炳的《画山水序》被视为具有开山水画论之先河的地位,王微也在绘画中发现自然山水之审美意蕴,看似巧合的是,山水诗大家谢灵运也正生活在此期,而且宗、谢二人还有交谊。也就是说,山水意识汇为时代审美思潮后,几乎同时沾溉了山水诗和山水画这两个艺术门类。当然从文学地理观来看,山水诗和山水画巧合般地在晋宋间诞生,也得益于“江山之助”,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之感。以清丽秀美的江南山水风物来冲销山河沦丧、偏居一隅的现实不堪与精神失落,是南迁士人寻求到的行之有效的精神疗治和心灵解脱之途,于是,士林中人流连徜徉于自然山水,写山水诗、作山水画便相因成习,在士林汇总致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