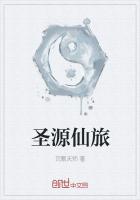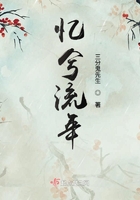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兵也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帮助袁世凯训练骑兵的挪威人曼德就在提供给日本、英国外交官和记者们的一份报告中说,他认为15年后袁世凯将成为中国第一任总统,并且“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名”。1898年,一个来自英国《泰晤士》报的年轻记者莫理循也注意到了同样年轻的袁世凯;1902年,莫理循采访了袁世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但已经被袁世凯所表现出来的卓越能力所吸引。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也是一个澳大利亚人,生于1862年——这个西方记者后来深入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为著名的洋人顾问,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以致北京最著名的王府井大街曾被命名为“莫理循大街”。
在复杂的政治丛林中,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沦为猎物。袁世凯的迅速崛起自然也引来众多猜忌,尤其是他手中掌握着大清帝国最精锐的一支新军,在晚清的乱世时代,手中握有兵权既是实力的象征,但也是众矢之的。当时,维新派已经在酝酿变革,维新人物四处活动,袁世凯这样重要的实力派角色自然是各方都极力争取的对象,朝廷中针对袁世凯的诽谤和各种谣言也此起彼伏,诸如说他企图发动政变、支持维新派改革等等。
正所谓三人成虎,兵部尚书荣禄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关于袁世凯要谋反之类的消息,这让他如坐针毡,于是决定亲自去天津小站看一看。自然,他此行绝非是简单地看一看,而是有备而来,即如果发现袁世凯果真有谋反迹象,那就当场拿下,甚至可以就地毙杀。袁世凯虽然并不清楚荣禄是带着杀机而来,但也对荣禄此行一探虚实的目的心知肚明。
但当荣禄到达小站检阅新兵的时候却不由地暗中惊叹——袁世凯果然是治兵的难得将才,荣禄虽然戎马几十年却从未见过这么整肃的军队,武器装备、战斗素养等皆是一流。这次检阅完全改变了荣禄对袁世凯的看法,不但消除了对袁世凯的怀疑,而且还引为心腹,更加器重。袁世凯自然投桃报李,在朝中有荣禄作为保护伞当然是件好事。
当然,袁世凯很清楚,投桃报李和誓死效忠完全是两回事,尤其在政治上,他现在手中握有一支新军,在风云变幻的晚清政治中,如何进行政治投机就是他目前最费心的了。大清帝国早已向一个熟透了的苹果,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从树上掉下来,这已经是尽人皆知,但满清贵族毕竟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经营了近300年,而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南方的革命党都还显得有些稚嫩,任何一派都无力单独推翻这个老大帝国。不过,帝国正在衰老,维新派和革命派却在迅速壮大,因此袁世凯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存在让他不敢轻举妄动,这个老女人如同当年的孝庄皇后,是稳定这个老大帝国的定海神针,只要有她在,任何谋反都可能归于失败。
袁世凯这时采取的办法也就是脚踩两只船,他暗中与维新党人秘密来往,并且为强学会提供了大笔资金,但一方面也时刻保持警惕,如形势一旦不利则准备立即出卖维新党人。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袁世凯表现的较为积极,甚至与光绪皇帝达成了密约,然而,当光绪皇帝真正需要他举兵启事的时候,他却认识到维新派除了他这一支新军外再无任何其它力量对抗慈禧太后等保守派,而凭他手中的这支新军还不足以翻盘,因此,他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向荣禄坦白了谭嗣同夜访之事,最终导致了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皇帝也被软禁。
袁世凯这次赌对了,他的选择博得了慈禧太后的赏识,1899年,袁世凯奉调出任山东巡抚,率领武卫右军前往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但在这次行动中,袁世凯又采取了既能扩大实力、又能圆滑处理矛盾的方式,这使得他不但扩大了军队,而且还博得了山东民众和外国势力的称赞。他的具体做法就是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将原有的山东旧军20营扩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这样一来,既根除了山东赖以对抗洋人的军事基础,也扩大了他的军事实力。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运动原本是因政府与民众的矛盾激化,但清政府巧妙地将运动的矛头引向了列强,因而这场运动成了中国民众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也十分关注。
第一个报道义和团与外国军队作战的外国人是意大利《晚邮报》的随军记者巴尔奇尼,1900年6月2日,他在天津火车站看到了一大群携带者大刀和红缨枪的农民,这时候,义和团已经和天津周围的外国军队开始了交战。巴尔奇尼亲眼目睹了俄国的一个哥萨克骑兵连与两千义和团战士交战的场景:“我们离他们大约三百码。他们的头上裹着红布条,让人联想起一个行进中的法国士兵团。他们的红腰带在阳光下闪耀。大刀在头上挥舞,红缨枪在飞动。突然,那些打头的,接下来是其他人,再接下来是所有的人,一齐跪下来作祈祷……”,然而,战况却是以义和团的惨败收场:“他挥舞着两把马刀,一只手一把,就像一个玩杂耍的人。接着,一枪打得他脸朝地倒下了,但是,他马上用膝盖支撑着身体,挥舞着马刀。又是一枪打来,他再次倒下,然而他用肘顶起自己,还在挥动那件武器,直到最后一枪使他永远倒在尘土中”(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在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外交使团驻地的时候,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当时是《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如果说巴尔奇尼是第一个报道哥萨克骑兵与义和团大战的记者的话,那么莫理循就是第一个报道外国使团遭到义和团围攻的西方记者——正是他发出了独家新闻,让欧洲了解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危机。1900年6月18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了来自北京的电讯,报道了外交使馆遭到围攻,但文章没有署名,这片报道就是出自莫理循之手。当时,北京使馆区的电报线路已经被切断,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电报线路也中断了,莫理循这片报道写于6月13日,14日,他雇到了一个信使,托他把这份电报稿送到了天津,他在日记中记载道,他为此花费了二十两银子。16日,伦敦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讯,随即刊登在《泰晤士报》上:“一次严重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昨晚在这里爆发。城里东部一些最好的建筑被焚烧,数以千计的当地基督徒,以及由外国人聘用的佣人,就在距皇宫两里范围内遭到屠杀。对所有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他们汇集在一起,由外国卫队保护。拳民焚烧天主教堂的东堂,这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如果外国卫队的援军今天仍不能到达,可以预料骚乱将进一步恶化。据可信消息尚无英国人受伤。”
在发出这篇电讯之后,半个多月里没有再发出任何信息,当时美国记者克里尔曼也在想办法向外界传递消息,莫理循也在想尽办法。7月6日,他再次写了一篇电讯。这次,他把电讯稿写在一张只有5英寸的纸上,然后用油浸泡了一下,用以防水,再把这张纸片藏在一碗稀粥里交给了一个中国教民。这个教民从墙头翻了出去,装成乞丐,想混出包围圈,但没能成功。无奈,莫理循只好把这篇电讯稿取出来,贴在了日记本上保留了下来,成为一份历史资料。
来自北京的消息中断了,英国的一些报纸就开始刊登来自上海的消息,7月17日,英国《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描绘北京惨烈场面的报道:“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在弹药尚足之时,他们冒着中国人的枪炮火力,一次又一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当他们最后一梭子弹打出去之后,他们的最后时刻也便来到了。但他们都视死如归。他们坚守在残破不堪的阵地上继续抵挡中国人的冲击,直到在数量上完全被敌人压垮,最终牺牲在阵地上。他们死得其所,没有给我们丢脸,他们为那些将在他们的尸首上被杀戮的、毫无自卫之力的妇女儿童战斗到最后一刻……至于夫人们,不消说,她们在这可怕的时刻是无愧于她们的丈夫的,她们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长时间、残酷的痛苦,都尽节而亡”。《泰晤士报》以为莫理循也“进节而亡”了,因此还特意表示哀悼,这也让西方人记住了莫理循这个名字,报道说:“在牺牲于清朝京城的人当中有一位应得到我们特别的敬意,他就是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医生。在他的充满惊险经历的三十八年生活中,莫理循医生多次死里逃生,每当紧急时刻,他总是有无尽的智谋。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希望。他很有可能已经在最后的屠杀中,趁着混乱脱身逃走……”,最后评论说:“任何一家渴望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其他报纸都不曾得到一位比莫理循医生更忠诚、更无畏和更能干的雇员”。莫理循的家乡澳大利亚吉隆甚至为此降半旗致哀。
当后来莫理循“活着”走出来后,他从信箱中拿出了一份刊有他讣告的《泰晤士报》,他看完后就问当时在场的另一位澳大利亚战地记者阿瑟·阿丹斯:“你怎么看?”阿丹斯说:“我看,既然《泰晤士报》发了这篇文章,对你赞誉有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你涨一倍的薪水。”
看到了这些报道,莫理循觉得那位上海记者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了,在1900年10月20日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道:“我看《泰晤士报》是在替《每日邮报》掩饰,担保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才发表来自上海的那份不光彩的电讯的。这份电讯使多少家庭悲痛啊。据我了解,发这一电讯的人叫萨特利……他一直以萨特利的名字住在上海礼查饭店充当《每日邮报》信赖的特约记者……那份谈及我们遭屠杀细节的臭名昭著的电讯是化名西尔威斯特的萨特利炮制的,你就会看出《每日邮报》选用这位记者是不明智的。”
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区的最后结果是北京遭到了八国联军的血腥报复,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外国记者们也描绘了遭到血洗的北京城,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记录了联军士兵攻入北京城这天的情形:“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十二个小时……无云的天空,好像因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轰鸣声而震撼和搅动,忧郁得使自己明朗的蔚蓝色变得暗淡无光,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铅色乌云……”;两个月之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罗蒂看到的北京城内是这样的情景:“几个褴褛的乞丐,战栗在蓝色的破衣之下;几条瘦狗,食着死尸,如我们在路上领教过的一样……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一切皆颓坍了,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各处墙上。”当他来到天坛,他看到的是:“这个往昔庄严肃穆的地方,现在任由野蛮人的马队驰骋。英国人派来的攻打中国的上万名印度兵,在那里扎营。他们的马,蹂躏着一切。草地上全是马粪。一个大理石的香炉,往昔是祭神时烧香用的,现在被英国人当做烧瘟牛之处……”
莫理循也在联军士兵攻入北京城后对士兵们的奸淫烧杀通过《泰晤士报》作了报道,8月17日,他报道说:“西什库教堂昨天被解救,北京目前完全由外国势力控制。抢劫正在有组织地进行。法国和俄国的旗帜,飘扬在故宫最好的地段,据信那里埋有皇宫财宝。日本人占据了一个宝库,据说里面藏有五十万两银子(约合62500英镑)。慈禧太后、皇帝、端王等高官均逃亡到山西的太原府,然后从那里前往西安府(西安)。《北京公报》已于13日停刊。此地已无政府”;9月24日,他再次报道:“由俄国人实施的对颐和园的有组织的洗劫已经结束。每件值钱的东西都被装走”,“德国人继续到北京周边地区骚扰,其主要目的就是抢劫”;11月24日,他又报道说:“类似抢劫,被德国军方掩饰地解释为重要的军事行动”;11月27日,他又写道:“有组织地洗劫那些早在德军抵达中国之前就已经投降了的人”。在这期间,莫理循撰写了长达3万字的纪实文章,详细记录了使馆区被围期间的事实,《泰晤士报》在10月14日和15日做了连续报道。
莫理循的报道产生了很大影响,就连一些英国政要也连日阅读他的文章,12月7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布雷克的夫人在给莫理循的信中说:“我正以极大兴趣拜读你的被围纪实。克林德男爵既然在德国使馆杀义和团,并且让使馆警卫向正在北京城区念咒作法的义和团开枪(克林德男爵是在墙头上看到他们的行径的),那么,难道你不认为他对于自己的被杀负有很大责任吗?据我的理解,克林德男爵的所作所为都在使馆被围之前。”美国媒体也注意到了莫理循报道产生的影响,1900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伦敦发来的电讯:“在一封12月28日发自北京的电报中,莫理循博士给《泰晤士报》发来了一段对德国人粗暴行为的长长的抗议书。他说,德国人的这种行为不是在制止混乱而是在制造混乱。他谴责德国人为了支付自己的军费而通过罚款手段对大清国进行掠夺,并不分青红皂白对有罪之人和无辜之人统统进行处罚,为他们自己能够满怀敌意地继续占领清国领土寻找借口。”
对于莫理循的连续揭露八国联军丑行、尤其是描写德国士兵的恶劣作为的报道,联军统帅、德国将军瓦德西大为不满,他在1901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才从报纸中得知,我一直受到英、美、俄三国报纸的激烈攻击,其中,尤以造谣总汇之《泰晤士报》为最。该报的报道都是莫里森先生所写。此人像那些英国记者一样,喜欢夸大其词,我应当特别对他注意……我对报界的攻击毫不介意,正像我对狗叫毫不介意一样。但使我惊奇的是,《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竟然一直容忍自己的人这样糟糕地工作。这里的英国人因为自己的这位同胞感到害臊,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打发走。”
北京遭到报复之后,1901年9月7日,北洋重臣李鸿章和西方签订了另一个屈辱条约《辛丑条约》。不久,李鸿章就背负着沉重的骂名死去。他在死前向朝廷举荐了袁世凯,这已经说明袁世凯已经是北洋派系的中流砥柱,是李鸿章的接班人。果然,向来倚重北洋派系的朝廷很快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派系从李鸿章时代正式过渡到了袁世凯时代,这时他刚刚4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