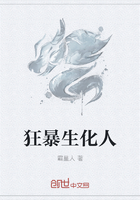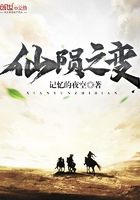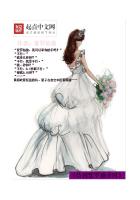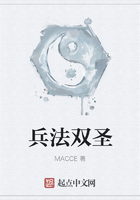香港恐怕是全世界生产“才女”最多的地方。我们的钟晓阳却是这众多“才女”以外的一个,一个真正称得上天才的女孩子。
说我们的钟晓阳,这是就香港来说的。她的小传上这么写着:“钟晓阳,原籍广东梅县,父亲印尼华侨,母亲东北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生于广州,在香港长大……”我们当然知道这不是说她母亲出生于一九六二年,只是别人替她写的小传文字上有一点小小的毛病。也有人说她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的。这区别不大,从十二月很容易一步就跨进另一个年头。可以注意的是,钟晓阳一点也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讳言自已的年龄,因此使我们很容易就了解到,此刻她正是廿九尚不足,廿八略有余的好年华。
还是五个月大的婴孩时,她母亲就把她抱到香港。除了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读书那几年,她是一直住在香港的。就香港来说,当然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钟晓阳”。
还只是一个“书院女”(香港英文中学女学生)的时候,她就开始写作了。有人说开始于十三四岁,也有人说十五岁,这区别也不大。重要的是十七八岁,她的成名之作《停车暂借问》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一九八一年开始发表,就一举震惊了文坛。
说来惭愧,这文坛主要是台湾的文坛,而不是香港,尽管她在香港的文坛上也已经露了头角,而且一再露头角。
一九七九年,她得了香港第六届青年文学奖散文和小说初级组优异奖;一九八〇年,她得了第七届青年文学奖新诗和小说组第二名;一九八一年,她既得了第八届青年文学奖散文高级组第一名,又得了香港第二届中文文学奖散文高级组第一名——前一个第一靠《明月何皎皎》,后一个第一靠《贩夫风景》。
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年,香港的《大拇指》月刊、台湾的《三三集刊》和《自由日报》同时刊载了她的《妾住长城外》——长篇《赵宁静传奇》的第一部。就是这个长篇使她震惊文坛,一举成名。
这个《传奇》的第二部是《停车暂借问》,第三部是《却遗忱函泪》,都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停车暂借问》还同时在《香港时报》连载。最后定下来的总名字是《停车暂借问》,《赵宁静传奇》成了副名。
这部不过十三万字的小说一出来就使台湾一些年长的作家刮目相看,惊异叫好。司马中原说,“它的文字的感应力和描绘力都是第一流的”,“它用特殊创意的文字”,“是一种创造”。还说,“写爱情悲剧写到这种程度,三十年来在写爱情的作品中,还没有读到”。他甚至说,“三十多年前我读过《围城》,我觉得很多象征性超过《围城》”。我却认为,《围城》和《停车暂借问》是两种不同的笔墨境界,不必拿来相比,也不能比。但由此可见,台湾老作家对这位素不相识的香港少女的才情是何等倾心,倾心得不怕把她宠坏。六七年后,他还是“和晓阳从未谋面”,看到她的新作还是赞不绝口,表示了“对晓阳的天赋由衷的赞服”,而称她为“这位民族的才人”。
老作家朱西宁把“天纵”、“天骄”加在他女儿的这位好朋友身上;他女儿朱天心也是作家,更率直地称钟晓阳为“天才”,“才华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日丽天”,使她总是惊动、惊喜。
一个“惊”字,是的,完全用得上。
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直生活在十里洋场的香港,自己又从来没有过什么爱情故事(至少当时没有听说过),怎么能把一个哀感缠绵的爱情故事从日本少年写到中国青年;从东北写到上海,又写到香港;从四十年代一直写到六十年代,从少男少女一直写到老大成为中年男女?
有个东北姑娘做母亲真好!使她可以利用整个暑假,从广州、上海、北京直到东北,去接触沈阳、抚顺的亲戚朋友和风土人情。看得到的就看,看不到的就问,“一路看就一路缠母亲讲当年的事。她是细细地盘问,有些细节连钟妈妈都不记得了;说不出来的时候,晓阳就生她的气,蛮不讲理的撒赖,要妈妈再想想,再想想呀!”“从母亲那里问不到的事,她就去缠母亲家的老人家,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在哪里。这个晓阳!”
真是个有心人,别看她这样小小的年纪!
这总算大体可以解决人在香港而写东北的问题,七十年代而写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小小年纪而写成人爱情的问题,尽管她写的是青少年时候多而中年时候少。
我似乎曾经问过她,而她似乎说不出什么道理,或者是不愿作答。那是十年前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已颇为模糊了。总之是没有解开这个疑团。
那是一九八一年,她在香港一连得了两个奖。台湾《联合报》似乎也给了她一个中篇小说奖,这样就是一年之中,连中三元了。正是“唯有杏花真得意”的年代。我读了《停车暂借问》和她得奖的散文,十分“惊才”,很想见识,解开疑团,就托朋友约她见面,见了面又使我有了一分惊异,因为她本人并不像她的文章那样生得“绝艳”。
面孔有些圆,个子不太高,上边一件普通的T恤,下边一条平常的牛仔裤,这就是钟晓阳!身边还有一位护花人,本身也是花——一个比她年纪大一些的女孩子,张乐乐。后来读了她写的《钟晓阳的世界》这才使我比较多些知道钟晓阳,知道她们原来是“死党”。两人而不是一个人来,一来恐怕是女孩子怯生,二来也可能是怯左,当时我还是左派阵营的一员,而她,既读英文书院,又在右边以至台湾的报纸发表作品,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已经有过长途旅行,“远征”白山黑水,在右派人士看来可能是靠拢左边的壮举呢。
读过《停车暂借问》的人,恐怕很容易想到:作者既然是个女孩子,一定是林黛玉型的吧。然而,眼前的钟晓阳并没有使人产生如此的联想,相反的,只是打破了这样的想像,尽管她斯斯文文,轻言细语,问一句才答一句,不像衣衫给她的包装所表现的随时可以横冲直闯。事后自己心里暗笑:你怎么能期待一个现代的“书院女”有着古代的“闺阁秀气,委委弱弱”呢?
钟晓阳其实是秀气的。几年后从报上看到她的照片,就感到更加灵气。秀气逼人。真是女大十八变!也许不是她变了,而是当时我对于面对面的人不是那么善辨,没有看真切。
我们见面似乎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要不,她怎么会带了她的诗词给我看呢?应该是初次相见时我提了这个要求,第二次她就带来了。我的记忆真是要命!
记得的是对那些诗词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不如她的小说、她的散文。十年后看到她的散文《可怜身是眼中人》有一段提到她的一些诗词断句,如咏牛郎织女的,“直道人间相聚少,那知天上一般难”,“世人只道年年会,不晓年年惆怅还”;又如“春光尽后鸟分投,莫怜天上月,泪滴松枝头”。都是颇有情致的。重读《停车暂借问》时,又发现宁静送给爽然那首不知什么调子的词,也还有它的一片缠绵可读:“片片梨花轻着露,舞尽春日姿势。无情怎被多情系,好花谁为主,常作簪花计。人间多少闺门闭,门前落花堆砌。隔窗花影空摇曳,近来伤心事,摧得纤腰细。”
这些是古典的,还有现代的,如“回想出事那天/三级的地震微微/当你以灾难的双眉/审视我失火的眼睛/燃毁的平原不可以里计”。
她说自己常是有句无篇,除了那一首词,上面引述的都是未完成之作。
司马中原却说,她“更写过非常缠绵的古体诗,‘爱’进骨缝的现代诗”。可惜我们一律都看不到,既看不到发表,也看不到出书。
但我还是认为诗词非其所长,还是小说最好,散文其次。我不知道朱天心为什么要说,“小羊除小说散文,诗词更才是她的本命文章”。
哦,晓阳原来是小羊!这名字不坏,也许是小名,也许是她们这些女孩子之间的昵称,不过,我们又何妨叫她一声,“小羊!”
当年见到小羊时,似乎还对她提了一个意见,那是一个主要的意见:希望不要落进张爱玲的圈套,要走出自己的路。张爱玲再好,也是张爱玲,不应该只是学她,更需要建立自己,钟晓阳就是钟晓阳!话可能没有说得这样透明,反正是这个意思,有这份期望。
初读《停车暂借问》,如遇张爱玲,才有这样的进言。现在重读《停车》,这样的感受又不如当时的强烈了。是当时的错觉,还是现在对张爱玲作品的记忆的逐渐模糊了?
但钟晓阳的发展却是使人高兴的,她的作品是更多钟晓阳,更少他人眉样。
十年来,她写了《停车暂借问》(长篇)、《春在绿芜中》(散文)、《流年》、《爱妻》和《哀歌》(都是中短篇)。此外,还有些没有辑成集子的作品。
数量上不算多,质量上是很有可以称赏的。题材更宽广了,生活气息更浓了,语言文字更精练了。她不断成长,更趋纯熟。
如果在一九八一年她去美国读书时划一条线,《停车暂借问》属于前期作品,《春在绿芜中》和《流年》有前期有后期,都是学生时代的创作,《爱妻》是后期大学毕业留美时所作,《哀歌》是后期回香港后的作品。她似乎在大学读了三年,一九八四年在密西根大学电影系毕业后,又在旧金山逗留了一年多,一九八六年才回到香港。一眨眼,又快五年了。
初试啼声,一鸣惊人的《停车暂借问》,只看那下分三部的篇名,就使人感到浓烈的古典味:《妾住长城外》、《停车暂借问》、《却遗忱函泪》。用古典味的篇名写现代事,似乎是钟晓阳的爱好。如《春在绿芜中》、《春花亭亭立》、《明月何皎皎》、《水远山长愁煞人》、《可怜身是眼中人》、《卢家少妇》、《拾钗盟》、《唤真真》、《忆良人》都是。这里不谈散文,只说小说,《卢家少妇》的故事背景在旧金山,《拾钗盟》从香港写到美国又写回香港,《唤真真》是香港贫家少女的堕落和死亡,《忆良人》是一个不寻常的三角故事,发生在今天的香港。它们一点都不古。
有一篇《爱妻》,篇名虽不古,文字却夹杂着不少浅近的古文,一开头就是:“我的妻子原姓霍,名剑玉,广东中山县人士……幼清贫,年十二即工编织,十五随父学制饼……性沉静,端庄质朴,恬适温和,蛾眉婉转,女心绵绵,一种柔情,思之令人惘然。”后来有一些文字也是这样,尽管不全是。写得精彩的地方,使人想到《浮生六记》;写得平庸的地方,使人想到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的一类小说。我猜想,这一篇大约是她的试验品;这样的东西也要试一下。
她最大的试验可能更在文字的运用上。她爱用叠字做形容词,爱创造许多新的叠字的形容词。这里顺便举出一些——
“阳光跳跳盼盼”。跳跳用足,盼盼用眼,阳光跳盼是怎么一回事?
“清清哀哀,回回怨怨的一支曲子”。清、哀、怨,好懂,回呢?是清怨或哀怨的曲子在低回?
“都有一种青春历历之感”。青春如何历历呢?
“两个人生,殷殷频频,纷纷繁繁”。纷繁可以意会,殷频就难了。
“让他理昭昭雄辩一番”,“慧眼昭昭”。昭昭是明,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的雄辩吧?是一双明亮而最能看透事物的眼睛吧?
看到这些,首先使人有新鲜感,这作者的文字不同一般。再一想,就觉得又有些太过自我作古,作出了古人没有运用过的用法,不妥吧?继续想下去,却又感到不少是可以意会的,未尝不可这样创新一下。更往下想,也还是有一些不怎么恰当的……
我是个同意文字要规范化的人,却也能接受一些新的用法,认为这可以增加文章的一种新趣。像钟晓阳的这些,不是好的和不太好的都并存么?可以欣赏的和大可议论的同在么?这恐怕得由语言文字专家如吕叔湘先生他们来发言,我就不多说了。
这样的文字在钟晓阳前期的作品里比较多,后期的作品里逐渐少。不知道她自己试验的心得如何?
我看到她的最新的短篇,是一九八八年发表在《台北评论》上的《姑娘》。那是写一个设在香港中下层居民区里的一家私人诊所中三个“姑娘”的故事。“姑娘”,在香港(广东也是吧)是对女护士的称呼。它通过这家诊所和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反映了香港中下层社会的形形色色,深刻细致,生活味很浓,现实感很强,是一篇可喜的作品。司马中原认为从它“略略看得出她风格转变的迹象”。
这转变其实也不是突如其来的。从她前期的作品《二段琴》、《荔枝熟》和后期的《爱妻》、《唤真真》中,都可看到她对现实社会的注视,对中下层小人物的关情。《姑娘》是顺着这条线出来的,只是更成熟了。
《姑娘》的文字也很朴实,没有那些创新的花巧。当然,那些创新未必都不好。
我欢喜《姑娘》。这以前,曾经为《卢家少妇》吸引过,那出人意料的结局使我在心中涌起了一阵惘然。《哀歌》是我很喜欢的,那一段欲恋还休的爱情使人低回无限。那些渔村风景和捕鱼人生活的细致的描写,包括那许多海上打鱼的知识,显见得费过钟晓阳的不少精力去一一搜寻、了解、熟悉,要不然就写不出那么深刻生动。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她千里万里东北行去体验生活。
为了写作,她是不惜“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这也许就是一些人爱说的诚意吧。
有才固然难,有才而又有诚意,更难。
在这里,又不禁想起了西西。西西在香港为严肃文学努力不懈,却是台湾把应有的荣誉首先给她。她是个不断勇猛精进的人,不断在作各种新的写作尝试。她对大陆上的文学工作者所作的支持协助,无私得使人感动。这又使人想起了小思。
而钟晓阳,在首先扬名于台湾这上面和西西很相似。
听说她最近在写流行小说,后来看了一些,也不怎么“流行”。但愿这只是一种新的尝试,而浅尝辄止。不是写流行小说不好,已经有好多人在写了,已经有写得很好的在流行了,用不着去凑这个热闹。流行是需要的,严肃更需要,从深远来说;而从事它的人又这么少。
我们的钟晓阳!
钟晓阳写了这许多爱情故事,写得荡气回肠,多以悲剧告终。《良宵》是例外,写的是新婚之夜,新娘头罩红巾,等候新郎用扇子来挑开,彼此深情一视,这短暂时间里的心潮起伏。
没有人写过钟晓阳自己的爱情故事。相信她不会没有,而不知道到底如何。
也不知道,也没听说,学过几年电影的她,到底作过电影方面的什么尝试没有?
她爱好音乐,学过笛子,为了上笛子课,她可以不去参加典礼,亲自领取颁给她的文学奖。
好一个钟晓阳!
一九九一年一月
《海光文艺》和《文艺世纪》——兼谈夏果、张千帆和唐泽霖一
《海光文艺》只有一年零一个月的生命(一九六六年加一九六七年一月),但在香港的文艺刊物中,它不算很短命的。像今年的《作家》月刊,只出了两期;像七十年代的《四季》和《七艺》,也只是各出了一期或几期;而同在六六年出版的《文艺伴侣》,只出了四期。比起它们来,十三期的《海光文艺》简直可以算得有些长命了。
它是生不逢辰的。一九六六,是“文化大革命”惊天动地而来的一年,虽说五月天才正式开始,但在大陆上,早一年甚至早两年,已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文艺界有些人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当我们在筹备出《海光文艺》时,《海瑞罢官》已处于被批判的逆境。虽说香港不属于“文革区”,但在那样的时候我们却办《海光》这样的刊物,也实在是不识时务的。因为,那时我们是左派!
我们,是黄蒙田和我。黄蒙田以前主编过《新中华》画报,以后一直到现在,还在主编《美术家》杂志;曾经是画家,后来成了散文作家和美术评论家,不再画画,这和他的好朋友叶灵凤颇为相似。由于他有过编画报的丰富经验,他的一位出版家朋友有意创办一个文艺刊物时,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请他出马。我是编过文艺副刊的人,虽然长期干新闻工作,对文艺始终保持着很大的兴趣,因此也就被邀助他一臂之力,帮他这个主编组织一部分稿件。对我来说,这正是投其所好的邀请。
从四十年代末期直到六十年代中期,香港文化界一直是红白对立,壁垒分明的。我们的设想是要来一个突破,红红白白、左左右右,大家都在一个调子不高,色彩不浓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兼容并包,百花齐放。这样的文艺刊物在今天的香港是已经有了,但在二十年前,那还是一个较有新意的设想。
如果我们是信息灵通的,当时就不会这样想了。这和当时北京的气候是很不适应的。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裴多菲俱乐部”,都已经逐渐受到批判,而我们却似乎对这些都很为无知,因此才敢想、敢干。
为什么叫《海光文艺》呢?图现成的方便。当时有个《海光》杂志,是综合性、知识性的,不准备办下去了,这就接过它的登记证,加上“文艺”两个字,办一个新的刊物。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刊物灰色些,像是原来的《海光》文艺化,看起来不红。
平日常在左派报刊上写东西的作者,发表作品时也多用了笔名,如何达,尽管他为《海光文艺》写了不少诗,却从来没有一次出现过何达这名字。甚至像曹聚仁,用的也是丁秀这笔名,而叶灵凤,是任诃、秦静闻。
不是说要不分左右、红白混杂的么?怎么又不让左和红的出现?因为红白对立,壁垒分明惯了,当左的、红的出现时,就可能使得右的甚至中间的望而却步,因此,就不得不委屈那些被认为左或接近左的知名作者,换一个陌生一些的笔名了。
在筹备的过程中,就曾经因为背景是红的,一些和《中国学生周报》有关系的朋友,尽管愿意写文章,终于因为上边不点头而没有动笔。但在刊物出版后,却颇有台湾的作者寄来稿件,登了出来的;也有在美国的侯榕生寄来的稿件。
老作家姚克、刘以鬯、李辉英、侣伦……中青年作家舒巷城、依达、孟君、张君默、梁荔玲……画家陈福善、萧铜,音乐家周文珊……都成了《海光文艺》的作者,而李英豪和亦舒写得更多。亦舒那时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却是“崭然露头角”,很受人注意的青年作家,她在《海光》上发表的《满院落花帘不卷》,二十年后被《博益月刊》推为当年佳载,陆离说“每次重读,都有泪意”,有迷人的缠绵,还说:“《满院落花帘不卷》时期的亦舒尽管含苞未放,但是一阵清新的香气,已经散发开来了。”
曹聚仁用丁秀的笔名写的《文坛感旧录》,是一个很有内容的专栏,可惜只写了九篇,连载了三期,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现在回忆,大约是他得了病,进了医院,进入了那一段“浮过生命海”的时期,无法再写。但后来病好了,还活了六、七年,却一直没有重新写,真是可惜!这一场大病,使他写出了《浮过生命海》这本书,二十年后,叶特生又用了同样的名字来写自己的病中小品。
应该一提的是,侣伦以林下风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发表了他的香港文坛感旧录——《香港新文化滋时期琐忆》,也是连载了三期,后来收进了《向水屋笔语》中,成为十几篇香港《文坛忆语》的第一篇,为研究香港文学提供了很可贵的早期资料。
此外,还应该提一提的是,《海光文艺》先后刊出了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以及金庸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梁羽生的《著书半为稻粱谋》这三篇谈论武侠小说的文章。佟硕之的文章很长,也是分三期才登完。当时都以为这篇东西是我写的,我也“认”了。事实上,它出于梁羽生的手笔。梁羽生因为既写自己,又论金庸,不免有些为难,禁不住我坚决约稿,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却提出了要我冒名顶替承认是文章作者的先决条件,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早就认为,新派武侠小说不应该被排除于文艺之外;同样也认为,流行小说也不应该被排除,登载依达、孟君、郑慧的作品就是证明。当然,我们还认为,文学有严肃和通俗之分。这样的分类也是从俗,通俗的作品未必就不严肃。
我当时只是做了一部分组稿的工作。编辑工作主要是黄蒙田做的。由于他是画家出身,每期封面都选用名家油画,颇有特色。至于《海光文艺》这四个字,那是余雪曼的手笔。
在组稿工作中,我交了好些原来陌生的朋友,有些人当时不便写稿,也还是成了朋友。到了后来,形势变了,写稿无碍,也就彼此交换写稿了。戴天、胡菊人、罗卡、陆离……就是那时认识的,在以文会友之外,这可以算是以刊物会友吧。
在香港,由于受了台湾宣传的影响,曾经有人一听到“统战”,就要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其实,统战无非就是尽可能广泛地交朋结友而已,何怕之有呢?事易时移,现在仍抱有这样心态的人恐怕是少而又少的了。
说句玩笑的话,《海光文艺》是个不祥的十三,只出了十三期,在“文革”高潮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出了最后一期就不声不响地结束了。拖这么一个月,多少说明,它并不想死;不声不响,也多少表示了不甘心。但这时“文革”风烈,澳门又有过“十二月风暴”,山雨欲来,不久,香港更有了强烈的“五月风暴”,像《海光文艺》这样灰而不红,调子很低的刊物,又怎么还可以拖得下去呢?
十三期《海光文艺》,每期大三十二开,一百页,不过十万多一点字,合起来一共一百三十万字还不到。它在香港新文学运动的进程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过,作为当事人,我们还是很怀念它。
二
谈到《海光文艺》,我们是不能不怀念那位推动其事的出版家朋友的。特别是此刻,回忆就更加深切,而使人黯然,因为这位朋友刚刚在十多天以前离我们而长逝。
他是唐泽霖,以出版事业终其一生。不过,最后的十多年他是被迫离开了出版工作了。
他是安徽人,四十年代在上海、重庆工作过,和三联书店或三联中的某一家书店有关。一九四九年以后到了北京,负责过新华印刷厂,六十年代到了香港,主持相当繁重的出版工作。“文革”当中,可能是一九七〇年前后,他突然奉命赤手只身回广州,接受“批斗”。后来没有事,工作却丢了,从此就再没有走上任何工作岗位,加上疾病缠身,就只有进医院,出医院,出医院、进医院的份儿,直到今年八月中在广州离开人世。尽管活到了七十一岁的高龄,这样的晚景总不能说是“夕阳无限好”的。
他为人诚挚而又耿直,工作勤恳负责。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就想到了要出一个可以兼容并包,无妨百花齐放的文艺刊物,就这样,想到了黄蒙田和我。就这样,诞生了《海光文艺》。他是刊物的实际负责人,我们是负责编辑工作的。在这上面,他从来不加干预,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充分的尊重。
由于共同对书画的爱好,我们原来就是朋友,这一来,就更加熟起来了。一次,他见我有一个齐白石篆书的横额,“片石居”,就一定要和我交换。我简直是义不容辞地就同意了,因为他又有爱石癖,专门收藏并不名贵的各种各样的石头,“片石居”这三个字对我并不怎么,对他就很有意义了。他是用两个字来换三个字的,弘一法师写的“无上”。他知道我喜欢弘一的字。但后来经过“文革”中的那一折腾,他原有的收藏几乎都荡然无存,包括那许多石头和那一幅横额。
爱石的他,有一句赞石的话:“石头碎了也还是石头。”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应该用这句话来赞美他,他这人就有石头的硬,也有着“碎了也还是石头”的坚韧的风度。
他也欢喜石湾陶瓷,有时不怕十斤八斤重,把大件的“石湾公仔”从广州提回香港。他一定要亲自提,怕假手于人会打破。我有过一件大的旧石湾铁拐李,就是从他那里得到的。那是我少数几件新旧石湾中的重器。
但我们之间(加上黄蒙田成为“三个臭皮匠”),最使人回忆的还是《海光文艺》,尽管分量轻,它还是我们的重器,因为我们是花了一些力气去制造它的,并非轻而易举。
三
说到香港新文学运动中的重器,就不能不使人想起坚持了十二年之久的《文艺世纪》和它的主编夏果。
说到《文艺世纪》,就不能不使人首先想起推动它问世的张千帆。
既然谈到了唐泽霖,就先人后刊,先谈张千帆,再谈《文艺世纪》吧。
和唐泽霖一样,张千帆也是从北京到香港来的;和唐泽霖不一样,他不是“上海人”,原来就是香港人,从广东大埔移民到香港的客家人。
张千帆是笔名,他原名张建南,又名章欣潮。他现在北京做记者的儿子就是姓章而不姓张的。章是他的本姓。
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在香港也是一名记者,工作所在是《华侨日报》。热血男儿的他后来北上抗日,辗转到了延安。更后来到过山东,参加过《大众日报》的工作。抗战胜利前后到了东北,在长春、沈阳都办过报纸,负责过宣传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到了北京,进了侨委。
他是五十年代初期到香港来的,具体的时间大约在一九五三。他主要是去开展中国新闻社的业务。在他的推动下,李林风(侣伦)办起了对海外发稿的釆风通讯社,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事。侣伦在一九八五年釆风社三十周年纪念时写文章说,当年“几个曾经在新闻界站过岗的朋友,对新闻事业具有共同兴趣。在机缘凑合的情形下聚拢一起,决心继续为新闻工作致力,试行组织一个新闻机构”,这就是侣伦主持的釆风社!这几个站过岗的朋友当中,就有张千帆,他而且还是最主要的“发烧友”!
他的热不仅在新闻,而且在文艺。两年后的一九五七,又被他“烧”出了一个《文艺世纪》来。诗人夏果担任了主编。本来是可以由侣伦主编的,他这个香港新文坛的拓荒人挑这担子也许更合适,可能因为肩头已经压上了釆风社,就不想换担挑了。
张千帆的热还不止这些。他还推动吴其敏先后办了《新语》和《乡土》这两个刊物,综合性而又多少侧重于文艺,是以反映新中国这海外华人故乡的乡情为主的。《新语》是什么时候问世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乡土》却是一九五七年一开始就诞生了,是个半月刊,它比五月间创刊的《文艺世纪》还早了几个月。刊物以外,还出了一些书,周作人的《过去的工作》就是,尽管用的名义是新地出版社。
这以外,张千帆还推动出了丛刊式的《五十人集》(一九六一)和《五十又集》(一九六二)这样的书。每一集都集中了五十位作者,每人一篇散文。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是当时已有八十七岁的徐翁(包天笑),他是以九十九岁的高龄于一九七三年病逝的,不等我们替他祝贺长命百岁就撒手而去了。
丛刊式的书以外,他又推动出了《新雨集》(一九六二)、《新绿集》(一九六二)和《南星集》(一九六三)三本书。它们和两个《五十》不同的是,每一集都是六位作者,每一个人都是一辑文章或诗。文章有散文,也有小说。
在《新绿集》中,有张千帆的一辑散文《绿窗小扎》;在《南星集》中,有他的一辑散文《山居散记》。
在这以前的一九六〇年,他还出了一本散文《劲草集》。这可能是他唯一留传下来的个人的集子,是他四十年代末期以至五十年代在内地的作品。
他就是这样对文艺、对写作、对出版有很大兴趣的人,对香港的文艺工作作出了贡献的人。
他对书画的欣赏也很有兴趣,收藏过一些齐白石、黄宾虹的精品。他也欢喜和朋友交换藏品,我有一幅叶浅予画的刘三姐,由叶灵凤题笺,就是他要交换我的一幅黄宾虹而得到的。
但他的藏品后来也都荡然无存了。后来,是“文革”当中,有些是被“抄家”拿走了,不再回归;有些是贫而无以为生,卖去换米买菜。这时他已经从香港又回到了北京。
他是“文革”前就回北京的。“文革”中难逃一“斗”,是势所必至的事。只靠一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费当然不能养家活口。就不能不在书上面和书画上面打主意,为稻粱谋。他也爱藏书,专搜集签名本。这时就不管签名或不签名,一扎一扎的,交给小儿子上街去卖,他自己只是跟在后面,等待交易成功后,和儿子一起去买些食物或简单的日用品,偶然忍不住嘴馋,就带了儿子到东安市场去吃一顿涮羊肉。这当然是辛酸的故事,不过,比起另一些知识分子所受的遭遇来,却又算不得什么了。
他后来也到过江西,进过“五七干校”,得了重病,又得到许可回北京治病,几个月后就不治而与世长辞,大约是一九七一年春末夏初的事。
“沉舟侧畔千帆过”,他就是这样过去了,永远过去了。这样一位为香港的文艺工作默默地尽过力,有过热,发过光的人。
我们应该记得他。可惜我所能记得的实在不多,暂时就只能说这些了。
四
这就要再谈谈《文艺世纪》。
《文艺世纪》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创刊的,一九六九年结束,前后经历了十二个半春秋,出了一百五十一期。在香港的文艺期刊中,是寿命最长的一个。《诗风》也出了十二个年头,(一九七二——一九八四),一百一十六期。但和《文艺世纪》的十六开本、五十页相比,形式上它就显得小了一些(初时是单张,后来是三十二开一本)。而比起另一些篇幅更多的刊物来,如后来的《海洋文艺》三十二开本,一百四十四页,《文艺世纪》时间上却更长久,《海洋文艺》只存在了八个年头(一九七二——一一九八〇)。因此,要说香港文艺刊物的重器,就只能是《文艺世纪》居于首位了。
《文艺世纪》是纯文艺的。侣伦说:“它是同时期的一些以‘文艺’标榜而实际是综合性杂志的刊物中较突出的一本。它的内容纯粹是文艺性质的,而且也是较有分量的……在此之前,香港还不曾有过像《文艺世纪》那样风格的文艺刊物。”
它不仅有“较有分量”的东西,也有较为轻量级,适合年轻人的内容,每一期还增刊《青年文艺专页》,为港澳和海外的青年写作者提供了发表创作的园地,并且还配合评介的文字。
在青年性以外,它还有海外性,经常发表海外各地作者的作品,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它是在许多方面都能使爱好文艺的读者感到满意的。曹聚仁甚至说,如果他只够订一份杂志的钱,他就只有订《文艺世纪》了。
叶灵凤说,《文艺世纪》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能存在十年之久,真是一个奇迹。事实上,它比奇迹更奇迹地多活了两年。
这十二年是并不简单的。它创刊之年,内地掀起了反右浪潮,席卷了几十万知识分子。不过,这浪潮并没有卷到香港来,要不然,它的诞生就要成为不可能了。
它的晚年,又碰上了“文革”,和反右不同,“文革”对香港是有了很大的冲击的,最大的冲击就是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风暴”。左派报纸上的新闻说得夸张些就只剩下两条:要闻是“文化大革命”,港闻是“反英抗暴”。副刊好些都被砍掉了,幸存的也力排“封资修”,许多东西都上不了版面,版面上“干净”得很。《文艺世纪》能够大体上保持一贯的风貌而没有变脸,真是不容易的,那一种艰苦也就不问可知。
当然,它也并不是十分完美。“文革”未起以前,就感到它有最大的薄弱之处:不能使站在比较右边的作者替它写稿。正是这样,我们一些人才有了办一个打破红白界线,不那么壁垒分明的《海光文艺》的设想。《海光》只出了十三期,而《文艺世纪》却坚持了几乎十三年!虽说离世纪还远得很,只不过一个世代多一点,却已经要使人对它不能不肃然起敬了。
这敬意首先当然要奉献于作了四千五百天辛勤耕耘的夏果。
夏果,原名源克平,诗人而兼画家。和黄蒙田一样,当我认识他时,他早已放下画笔了,以至于在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作为画家的过去式。
虽说后来已经是很熟的朋友,我对他的过去式还是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夫妇合做了一点小生意,卖点小首饰和纪念品,这当然是为稻粱谋。
他的诗笔却一直没有放下,他没有自我放逐于“文艺族”。因此,当张千帆回到香港,推动办文艺刊物时,他就成了伯乐看中的千里马了。如果只是日行百里的话,这匹千里马也就跑了几乎半百万——四、五十万里。
他既编又写。编《文艺世纪》之余,就写诗、写散文。十分可惜的是:他只是替别人编文章,却从来没有替自己编集子。除了散见于报纸杂志的诗篇和文章外,就只有在《新雨集》中看到他自编的一辑十三首诗。
这些诗的最后一篇是《萧红的墓志》,写于一九五七年。那一年,是《文艺世纪》创刊之年,也是香港的作家们送走萧红骨灰安葬于广州银河公墓之年。重温一下这首诗吧:
“在那黑色的日子,/灾难的日子,/虽则是一阵清爽的海风,/吹来也像刀刺一样苦痛的日子。/那个时候——/你草草地离开‘人间’,/是的,你是静静地离开了地狱的。
“一株小树,一块木碑,/是代表萧红的墓志。/伴你长眠的是贝壳,是死叶,/人说撮土为香,/但能为你供奉的,是乱石,/是沙子,/是呻吟的海语。
“虽有一个诗人,/‘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他说‘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海涛闲话。’/漫长的十五年啊,/海涛也诉尽所有的话语。/而漫长的十五年,/小树失去所踪,/连‘墓木已拱’也说不上。/放在你底坟头的/诗人虽亲手为你摘下的红山茶,/萎谢了,/换来的是弄潮儿失仪的水花!
“浅水湾不比‘呼兰河’,/俗气的香港的‘商市街’,/这都不是你的‘生死场’。/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缸子,/都不能安容于大海的边缘;/但缸子所容的有比海还大的/是你馨香的民族魂。
“像考古家发现了古代文物,/像勘察队发现了历史宝藏,/缸子终于出土了,/在白云故乡,/为你筑一座巍峨的萧红墓,/而你的墓志:/是民众作家,/是民众的女儿。/在你底墓前,/民众要为你栽上矗立的英雄树。”
这最后一节里,出现的是“民众”,“民众”,第三个还是“民众”,而不是“人民”。是不是觉得有些别扭?猜想这中间有苦心,避免“人民”的红。这多少有些像是我们办《海光文艺》时的心态。不过,这已经无法向我们的诗人问个明白了。
他已经在一九八五年四月病逝。猜想是很寂寞的。没有看到什么悼念的文字。
他是个老实人。不屑于逢迎,也不懂得吹捧自己。他老实而朴素,看起来不像一个画家,也不像一个诗人。
但他却实实在在是诗人而兼画家。在香港这“商市街”中,他虽然做过小生意,却是属于“文艺世纪”的人。
一九八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