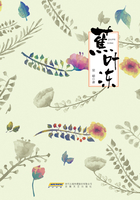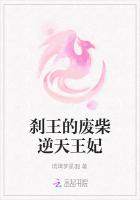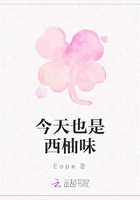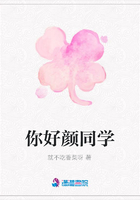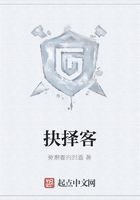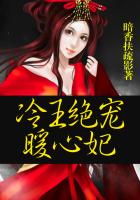在特殊情况下,胡风成了《人民文学》的编委。但早在成为《人民文学》编委之前,与主流歧异的文学主张,使他在私人空间中就对《人民文学》进行驳难;成为编委之后,胡风在这一公共空间中遭受到真实的隔离。
□一封退稿信
胡风在私人空间中对《人民文学》的驳难,典型体现在胡风给诗人胡征的一封信件和他的《三十万言书》中。人们对《三十万言书》基本已耳熟能详,但对给胡征的这封信却少有留意。王丽丽女士在自己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一书中曾经注意到这封信,但并没有展开。应该说,这是胡风直接针对《人民文学》、明确阐释不同的作品发表标准的潜在文本。
这封信写于1950年9月1日。胡征来信所谈的是自己的诗集《七月的战争》被《人民文学》退稿一事。胡风在这封信中并没有提到与胡征所谈的诗名。笔者曾致电给胡征,经其家人回忆及涂光群推测,应该是《七月的战争》。其实胡征的《七月的战争》并非什么异类,而是对刘邓大军南下那场战争的全景式描写和英雄人物的歌颂。胡征是参与这场战争的随军记者,初稿完成于1948年9月10日的战争征途中,到1950年才修改定稿。195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53年,这首长诗再度辉煌,与《大进军》和小说《红土乡纪事》同时获得西南军区文艺检阅一等奖,荣获贺龙、邓小平亲笔签名的奖状。此后,《七月的战争》又与《大进军》合编一集,由刘伯承题字,再次出版。在短短的时间内,这部诗集连印3次,累计印数接近8万册。随信件同时寄来了自己的诗稿和《人民文学》的退稿信。
1950年时,胡征的身份是西南军区的随军记者、诗人、来自解放区鲁艺的学生。按说,这是与胡风对立的一种身份,但胡征选择把信和诗稿寄给胡风并不是心血来潮。1939年在鲁艺的时候,胡征曾经读过胡风编辑的《七月》,对胡风的文艺观点比较赞赏,并由此对自己的老师周扬心生异议。《诗人胡征的遭遇》,见涂光群《人生的滋味》,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8页。胡征的诗作曾由周恩来带到重庆,发表在胡风编辑的《希望》上,但胡征并没有看到发表后的作品。这样,胡征与胡风早有了文学上的渊源。胡征将诗稿寄给胡风的另一个原因,恐怕在于胡风的长诗《欢乐颂》在1949年造成的广泛影响。作为《时间开始了》的第一乐章,《欢乐颂》1949年11月2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时《人民文学》已经创刊)。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的报告不点名地批判胡风的境遇下,《欢乐颂》的发表确实让非主流的作家感到振奋。胡风在1949年12月3日日记中记载:“下午,鲁煤来,谈到《欢乐颂》。他们那里已注意到创作方法,要写性格了。”12月11日,“得葛一虹信,想印《欢乐颂》”。12月15日,“王朝闻来,设计《时间开始了》分册封面”。12月18日,“下午,牛汉来,谈到《欢乐颂》。他开始写诗了”。显然,《欢乐颂》的发表、写作方法(性格),对胡风派作家牛汉重新开始写作,起到了鼓舞的作用。见《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但《时间开始了》其后的三个乐章却遭到了《人民日报》《文艺报》的拒绝。胡风在1949年12月4日日记记载:“得马凡陀电话,《赞美歌》他们嫌长,不想用了……”见《胡风全集》第10卷,第129页。胡风在1949年12月15日日记记载:“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全集》10卷,第132页。胡风认为这“意思很明显,逼我向《人民文学》低头”。胡风1950年1月5日致路翎信,见《胡风全集》第9卷,第270页。胡征不可能知道这些秘密,但他的来信就像一把火,点燃了胡风的激愤,在激愤之中其文学观念也自由地表达了出来。
胡风认为《人民文学》编辑就像“一个疲乏了而又低能的官员”,并没有深入到作家创作时的心理过程,只是从一套概念化的“官话”来给作品加以判定。在这种官僚性编辑的“形式主义都说不上”的教条说辞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将他人视为听命、臣服的“老百姓”的权力色彩。
胡风反驳《人民文学》编辑将主题是否突出作为审定稿件的尺度。退稿信认为这部长诗陷于对战争的全景式描绘之中,冲淡了作品的主题。胡风则认为,审稿者自身的鉴别能力阻碍了对诗歌的把握,诗歌不是主题不明,“恰恰相反,作者是被战争这个主题束缚住了”。胡风认为对战争的表现,需要的是作家对战争这一客体的情感融合、然后在这样的情感中来表现战争。但是,胡征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不能从生活感应和对于具体的人的感情出发,却从一角来透出这个战争的活生生的内容”。
退稿信同样要求作者在表现战争时要注重情感表达,只是在《人民文学》编辑看来,在诗歌的前后部分,作者的感情“没有相互关联”。胡风的意见则相反:“应该说,太‘联’了,感情几乎是一个,是同一个感情写出的不同的、发展着的战争行为。弱点恰恰在这里。”诗人的情感并没有融化进自己的描写对象,没有随着对象的变动而表现出情感的起伏。诗人在过于单一的情感中,体现出的却是对客体的冷漠。在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表现了出来。在胡风看来,“诗人应该通过被生活斗争所形成的自己的情绪感受去拥抱对象,感觉对象。对象无论是事件、自然、人物,就会以它自己的特征和你相融合,现出它自己具体的情绪感受来”。也就是说,对象本身在主体情感的感染、溶解下,才能被赋予一种感情色彩。胡风所反对的不仅是教条主义的概念化,听任主体单一的热情冲动,将诗人心中那一点“感情胚胎”不加审辨地膨胀,使作品流于空洞的气势;而且也反对客观主义,只是简单地让对象平面地进入诗作,而没有发现对象与诗人相融合中产生的情感意味。
最后,胡风认为《人民文学》退稿信指出的建议根本“走不通”,它只能使诗人向教条化的、无个性的道路走去。强烈的主体意识,使胡风对诗人的用语也产生了厌恶,他希望胡征将诗中的“我们”字眼取消。
针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这封退稿信,胡风具体而微地传达了自己的文艺观念。主客体的相生相克,是人们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观念的通常解释。胡风在这里对作品的分析,恰是这一文学观念的流露。他所希望的是创作主体与客体与之间的感应、融合,诗人应有饱满而独立的主体姿态,让这一主体在情感和智性的能动发挥中拥抱对象,即真切地感知对象,并随着对象在主体那里的不同投射而变化;同时诗人在艺术表现上也充分尊重主体的认知与感受。胡风这一观念,因为是直接针对着《人民文学》的退稿信,所以更明显地体现着他与《人民文学》的迥异。
□《三十万言书》中的全盘计划
如果说这封信还只是在观念里与《人民文学》驳难,那么,在同样有私人空间性质的《三十万言书》中,胡风的驳难则不限于文学观念了,而上升到整个文学体制。
胡风对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文艺体制提出了改组的建议。胡风始终将自己当做真正懂文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由茅盾、周扬主持的“文艺领导”将使文艺陷入“枯死”的境地。他们在文艺观念上仍然持续着30年代“左联”时期的教条主义和40年代的“客观主义”,而由此建立的作协、出版社、期刊杂志因有绝对权力的保证,更成为培养“大小教条主义的温床”。胡风并不否认党对文艺的绝对领导,相反,在坚持这一点的前提下,他认为当前的文艺体制是来自周扬、茅盾等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主张的有意误读。抱着“清君侧”的愿望,胡风递交了《三十万言书》。
在这份给中央的报告中,胡风对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机制建设提出了异议。胡风首先提出改变《人民文学》等刊物的行政性质。各种等级的刊物都应该取消其“国家”、“大区”、“领导”或“机关”的依托。“驻会作家”、“创作所、创作室、创作组”等等行政管理或变相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应该取消。正是这些行政制度将作家纳入了权力的控制之下,其刊物也被某些人“独占”,非党的作家得不到发表作品的机会。同时,丧失独立性的刊物,不得不看权力者的眼色行事,使刊物“总是处在摇摆不定的情况之中,弄到只好在有力作家之间敷衍,连一个编后记都没有勇气写出负责者自己的意见”。
胡风认为刊物的改变方向,应该是更有“公共性”的“群众刊物”。作家协会的刊物不是行政强制下的附属物,而是“作家协会支持下的群众刊物”。编辑部不应以权力大小、行政级别来安排编辑,而是由真正懂得文学创作规律的作家来担任,成为作家的联合体。主编由知名作家自愿担任,实行主编轮流负责制;编辑成员为“二十名上下到三十名上下的作家和青年作者”。在发表作品时,主编具有超越行政命令的决定权,“选约文艺稿件完全以自己的见解和要求为标准,独立负责”。由此,是刊物而不是作家协会成为联系、培养和组织作家的中心。任何作家都有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权利,能否发表所依据的是作品的质量,《人民文学》1955年6月号,集中登载了众多人士批判胡风的文章,刘白羽的《胡风——最阴险的敌人》是当头文章。
而不是党员或其他的政治身份。如1950年5月15日自上海致路翎的信中,胡风写道:“我到上海三个月了,什么也没有写。一动笔就要挨骂……而且,不动笔也要挨骂,因为国统区写过一点的。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会。但当然,国统区作家也大约不是一概而论的。”见《胡风全集》第9卷,第38页。又如1950年7月12日自上海致冀汸的信中说:“现在是,当权者窘得很,没有作品,但又拼命打别人,真是滑稽得很。路兄剧本,几次决定又几次推翻,最近又推翻了,说是‘时机未成熟’云,可作为‘排练剧本’云。他们一方面树‘人’,一方面造无人地带。”见《胡风全集》第9卷,第128页。“属于每一刊物的作家”,“创作活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党对于任何作家都不予以凭‘资格’保证作品的权利”。对于作协设置于期刊内部、保证上下服从的党组织领导渠道,胡风提出打破其等级关系,“作家协会的党支部和各刊物的党支部是平行的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见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第406~425页。编辑们应该将精力转到发表作品、繁荣文学上来,那些例行的政治学习,应该“完全废除强迫”的学习制度,转变为“自学为主”。
胡风事实上是以自己创办《七月》《希望》的经验来提出这些改组计划的。相比于50年代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文学期刊,《七月》《希望》堪称主编自主下的同人刊物。在那里,胡风保持着充分的独立性,以自己的文学主张作为取舍作品的首要、甚至是唯一标准;以作品本身和编辑的明确倾向,作为吸引、聚拢作家的手段。更为关键的是,发表其上的作品,如路翎的小说,艾青、田间、绿原、阿垅的诗歌,胡风、舒芜的论文,东平的报告,无不以鲜明的主体性表达着主客体融会而出的文学个性。胡风在这里对《人民文学》所附属的文学体制的明确批评,是由文学“枯死”的现状向现实制度上的自然延伸。但在后来的批判者看来,胡风在这里提出的是争夺“文学领导权”的、一套全面的“反党”计划。如郭沫若就说:“胡风这位自命不凡的人物真是了不起。他不仅要争夺文艺的领导权,而且要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社会改造国家!”他认为胡风的一套改组计划,“其内容实际上是解散文艺界统一的组织,分裂作家的团结,取消集体领导,停办现在的文艺刊物,代之以在文艺思想上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个人办的刊物,进行资本主义市场式的自由竞争”。见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人民日报》,1955年4月1日。
在私人空间里对《人民文学》从文艺观念到体制制度的这种批评,明显体现出胡风与《人民文学》的分歧。即使成为《人民文学》的编委,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胡风能在《人民文学》的文学生产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也成了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身陷八卦阵
1953年,在文协改为作协之前,《人民文学》第一次大改组:被胡风称为“编辑之官和小说之匠”胡风:《鲁迅先生》,见《胡风全集》第7卷,第92页。关于胡风与茅盾之间编辑思想、个性、文艺观念的矛盾,参见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504页。的茅盾不再担任主编,1948年“香港批判”的主力邵荃麟接任主编一职。
《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又集中发表了一批老作家批判胡风的文章。
胡风同时成了《人民文学》的编委。此后,路翎接连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胡风也有文章发表。胡风与《人民文学》的交往,终于从私下走到了公开。这里所要关注的是,胡风是怎样成为《人民文学》编委的?胡风在这一公共空间中面临着什么样的境遇?
胡风成为《人民文学》的编委,并不是主编邵荃麟所能决定的。在此之前,抱着从“大前提”上改变文学实践的胡风,一直采取与周扬、茅盾“不合作”的态度。坚持自己文艺“政见”的胡风,其实已经洞察到其时文艺政策、实践的本质及其带来的危害。“现在所要达到的,是单线的绝对清一色的领导方式,这和现实的要求完全相反,这必然会招来几年的枯死。”胡风1952年3月30~31日致路翎信,《胡风全集》第9卷,315页。但胡风自信于一个判断: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并不了解文艺界的真实情况,即便了解也因现时的需要还无法向文艺界开刀。如胡风1950年11月10~13日致张中晓信中说:“思想上的混乱和现实的要求,上面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以坚强的宗派主义和顽固的机械论为中心的实际关系,是很困难的事情。上面把这当作‘现实’,得依靠它,事情就很困难了。”胡风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胡乔木、茅盾、周扬等与胡风的多次谈话、工作安排正是出于最高领导层的意旨。他们在促使胡风作出深刻检讨的同时还保留着将其收编的期望。胡风多次的“不合作”,终于将这一收编转为批判。《人民日报》内部通讯第28期向全国通讯员发出《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接着《文艺报》开始批判路翎的《朱桂花的故事》。之后,作协在小范围连续召开四次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在会议批判的同时,1952年9月25日《文艺报》又发表了舒芜反戈一击的《致路翎的一封公开信》。1953年1月31日,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在《人民日报》发表。2月,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在《文艺报》1953年第3期发表。面对来势凶猛的批判,胡风采取了“消极坚持”的策略。其实,几乎在1952年9月6日,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正式开会之前,胡风就已经明确了消极坚持的策略,“在内心深处,胡风已经关上了与座谈会的参与者进行思想交流的大门”。
胡风消极坚持的策略,首先建立在对自己的文艺主张正确性的自信基础上。其次则来自对上面不再抱积极希望的心态。四次思想座谈会以及“升级”为正式的会议,同时夹杂着胡风间接获得的不祥消息,使胡风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无法走出的“八卦阵”中。在1952年9月13日致王元化的信中,胡风说:“现在,事情只能就消极方面着想。从积极方面着想,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了……只有奉陪拖下去,舍此便无他道。”《胡风全集》第9卷,第568页。另一方面,这“消极坚持”也表现为不再直面抗争,甚至作出妥协的姿态。如四次座谈会之后,胡风表现出“屈从”的姿态,写出了《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和《一段时间,几点回忆》。但前一篇文章送座谈会参与者看后,并不让胡风在会上宣读,认为没有抓住实质。后一篇送《文艺报》发表,却被拒绝,夏衍认为“不该在文章里做了解释”。胡风虽写这“检讨”文章,其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见解。
同时,胡风也将“消极坚持”的策略向拥有一个刊物、从作品上来实际改变文坛“荒凉”、“沙漠化”上调整。“只要争取到一个滩头阵地,我想总能够对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为党的事业做一点什么的”。胡风1952年1月4日致牛汉信,《胡风全集》第9卷,第445页。罗洛在90年代时回忆说,尽管胡风50年代与文化部、作协等不合作,但心中还有一个梦,“胡风最大的心愿,给中央写了30万字,就是为了有一个自己的刊物,但一直没实现,后来倒因此而受批判了”。转引自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345页。1952年正在受批判的胡风,显然没有独立主持一个刊物的权利。但是,这种拥有刊物的渴望,无论就胡风对形势的判断,还是自己内心的梦来说,都为他接受《人民文学》编委的身份准备了条件。另外一个条件是茅盾的卸任,以及周恩来对批判胡风行动的直接干预。1953年5月,随着何其芳、林默涵两篇总结性的文章发表,胡风在沉默中又呈现出一种屈从姿态,这次批判才似乎到了告一段落的时候。此时,“周总理指名我参加了到东北访问直接遣返的战俘,我才算脱离了这样的处境”。《胡风全集》第6卷,第138~139页。来自周总理的直接指名,以及参加“访问战俘”的活动,向批判者暗示一个信息:胡风仍然可以使用。
也许正是在胡风的服从态度、内心之“梦”,周恩来的直接指名,使胡风最终能有了担任《人民文学》编委的荣誉。
胡风显然很看重《人民文学》编委这一“滩头阵地”。他曾为《人民文学》在教条主义文学观念桎梏下的“荒凉”感到痛心。胡风1952年8月致王元化的信中说,“看一看情形,真是空虚得很,一个《人民文学》,都苦于没有文章,一个《报》,也是七拼八凑,这中间又急于以棍子征服人或甚至杀人”。《胡风全集》第9卷,第563页。进入《人民文学》,胡风确实想有所作为。不过,刚刚消歇的批评,使胡风真切地感受到对手力量的强大,也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自由空间十分狭小。
刚一开始担任《人民文学》的编委,胡风似乎还能赢得编辑部的尊重。主编邵荃麟每次召开编委会,“总要关照编辑部的人去请胡风,并让他畅所欲言”。涂光群:《回忆邵荃麟》,《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5页。胡风后来也曾说:“将近一年,只开过三次编委会。”这些会议,胡风也都列席参加了。编辑部分工给胡风承担的工作是“每月看一个或两个短篇”。开始时是副主编严文井亲自与胡风联系,听取他对稿件的意见,“后来就完全是编辑部的青年同志们”。即便胡风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但他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条件,总是竭力避免发生误会”。比如在编委会上,胡风表达意见时,总是用他“认为适当的方式”来表达;遇见特别重要的问题,“就在个别谈话中向邵荃麟同志提一提供他参考……但谈话内容似乎不能从一般性的程度更进一步”。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第140页。一种无形的隔离始终存在于胡风和《人民文学》之间。涂光群曾告诉笔者,有一次编委会研究《人民文学》的封面及组稿工作,正在其他人讨论纷纷时,胡风冒出一句“还不如画个八卦”,然后拂袖而去。涂光群对“八卦”二字印象深刻,但不明其意。2003年8月5日涂光群口述。其实,在成为《人民文学》编委之前,正在舒芜的《致路翎的一封公开信》和作协内部批判会议召开之时,胡风在对可能的结果进行估计时曾告诉友人:“看罢,是要做成一个基本上是小资,个人主义的结论的。这使人无味,但已堕入了八卦阵中,只有缠一些时再看。困难的是,连步骤都很难安排。真不知要缠到什么时候为止。”胡风1952年9月13日致王元化信,《胡风全集》第9卷,第569页。在《人民文学》,胡风所感受到的也是陷入了这种无结束、无出路也“无味”的“八卦阵”中。
由此,胡风在行使编委义务时,处处警惕着自己的“罪人”身份,小心谨慎。作为编委,胡风有组稿的义务。但是,胡风有意避免接受稿件,一旦有“读者寄稿给我,要我转投《人民文学》,我总是回信他们叫他们直接寄去”。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第140页。《人民文学》时常面临稿荒的问题,邵荃麟、严文井总向胡风抱怨缺稿,让胡风凭借自己在作家中的影响力,给《人民文学》介绍稿件。胡风难辞其命,有选择地介绍稿件。据胡风后来说,1953年担任编委到1954年7月这一年间,“只谨慎地介绍了三次稿件。但结果是使我觉得我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三次稿件”要么没有发表,要么如石沉大海,再无音讯。“第一次介绍的关于北京的几首抒情诗,是发表了三首,但后来却成了严重的问题。袁水拍同志在作协诗歌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三首诗在总的倾向上是错误的、有害的,非严加批评不可。原来同意了这些诗的艾青同志还在会上作了检讨,还准备要袁水拍同志写批评。”同上注。
这种介绍稿件反受其累的结果,甚至使胡风不敢承认路翎的小说与自己有关。谈起路翎接连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胡风说,路翎是被文协组织到朝鲜的,他的稿件是直接寄《人民文学》的,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这也是路翎的小说第一次被放在小说的头题位置。发表是由编辑部和主编同志决定的。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第140页。其实,按照路翎视胡风为导师的态度,路翎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几篇小说,胡风事先肯定要过目的。胡风回避不谈,不过是划清路翎与自己的关联。
《人民文学》这一时期与胡风之间,至少在表面上维持着友善的关系。当胡风的诗作在《人民文学》发表时,有人心生异议,主编邵荃麟专门在编辑部解释:胡风的思想虽然有错误,但写出了好的作品就应该发表,应该鼓励,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涂光群:《回忆邵荃麟》,《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6页。路翎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人民文学》显要位置接连发表,被认为来自于一个重要的前提:深入到了朝鲜的生活中去。可以说,路翎获得《人民文学》的礼遇,一方面的因素在于他实践了作家“深入生活”的要求,同时也借此向胡风及“胡风小集团”的其他作家暗示一条信息:
遵从“深入生活”的要求,即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经过改造,也可以从错误中得救。如胡风曾说:路翎“的小说发表了以后,给以肯定批评的巴人说:路翎同志写出了那样使他惊叹的作品,是因为改正了过去所受的错误的文艺理论的影响”。见《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第143页。但是,当路翎的小说真正感动一些人的时候,作协的领导者就提高了警惕。据涂光群记载,当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有几位参加过战争、富有经验的女同志(她们的任务是读作品、专门研究创作的),读了《洼地上的“战役”》也感动得流下眼泪,对小说赞不绝口。可是文艺界领导层的某些人,似乎已酝酿一股强大的反对路翎小说之风。有一次周扬到作协来,创作研究室的女同志们向他称赞《洼地上的“战役”》这篇作品,周扬笑笑对他们说:‘怎么你们还没学会区分资产阶级感情跟无产阶级感情啊!’
在这种明暗相间、走不出也摸不清门径的“八卦阵”中,胡风能在《人民文学》上有多大作为就可想而知了。胡风想认真做好编委工作,却无法走入《人民文学》内部,无法了解读者真实的“思想特征”,“因而也就不能看清这个刊物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及其正负成分了”。胡风所能悟出的是《人民文学》为无形的“人事观点”所左右。即便以“读者”名义发表的所谓读者来信,也让他怀疑那“是否真是读者来信”。胡风有句话可以总括《人民文学》对他的真实态度:《人民文学》“好像多少有点保密性质”。
□《睡了的村庄这样说》
在1955年被判定为“反革命”之前,胡风在《人民文学》以作品的方式只出现过四次。第一次是1949年10月25日创刊号上的《鲁迅还在活着》,与巴金的《忆鲁迅先生》、《人民文学》创刊号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欢呼声中,胡风的《鲁迅还在活着》这篇文章显得刺目。
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冯雪峰的《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一起构成了《人民文学》上“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专题。第二次是1953年4月号上胡风哀悼斯大林逝世的诗歌。这篇文章的题目长得出奇,叫《永远地,永远地,你活在我们的血里,你活在我们的心里》。哀悼的人很多,包括茅盾、邵荃麟、老舍、楼适夷、艾芜等共二十余人。第三次则是采访被释放回国的被俘志愿军战士所写的散文《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以及翻译法国古典作家拉伯雷的《毕可肖之战》。这两篇文章发表在1953年9月号。第四次出现是1953年12月号上的诗歌《睡了的村庄这样说》。也就是说,成为编委后,胡风只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三篇作品。
在成为《人民文学》编委之前,胡风文章中引人注意的是《鲁迅还在活着》。这篇文章与周扬、茅盾的第一次文代会报告并置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就在周扬的报告宣布“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时,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见《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号。胡风思考的却是鲁迅。周扬宣称:“我们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这是……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同上注。胡风在文章中则表达出“国民性”精神负担的延续。他并不认为目前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质变,而认为今天是“过去的‘将来’,是从深厚的历史负担——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意识的毒蛇怨鬼似的搏斗中间出来斗争的;但这个‘将来’还刚开始,还得和深厚的历史负担——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意识的似无实有、似弱实强的持久斗争当中争取发展,争取完成”。胡风:《鲁迅还在活着》,《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号。胡风实际上表达的是同样深刻的历史和文学意识——1949年后,文学依然不能舍弃“鲁迅方向”,文学仍然需要批判和启蒙精神。在1949年充满歌唱和宣告的文本空间中,这篇文章显得冷峻而刺目。
到1953年发表《肉体残废了,但心没有残废》时,胡风在“消极坚持”中出现了变化。这篇文章所写的是美军对待被俘战士的残暴,以及战士们的英勇抗争。身体残废的战士心灵中仍然激荡着战斗的英雄主义情感。文章是周恩来指名胡风到东北访问战俘后的一个成果。《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在胡风从东北回来后,鼓励他写这篇文章。胡风的写作过程变得谨慎起来。为写这篇文章,他先是“费了将近一星期”来考虑“着眼点和写法”。因为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对象是被美俘虏的志愿军战士。
充分考虑并“经过曲折的修改过程”后,胡风将文章拿给邵荃麟、严文井审稿。严文井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都写的是解放军战士,不写老战士党员?”在胡风解释后,文章终于发表。不久,上海文联负责人之一章靳以就在两次群众大会上提出来:写战俘的英勇斗争,不写老党员,只写新战士,说明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不经过思想改造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胡风为这种指责“奇怪”得不得了,“好像他以为当俘虏是光荣,非得老战士党员不可以似的”。胡风有意为党员讳饰,却不料自己处心积虑的选择仍然撞破了规则:无论1953年4月,在《人民文学》众多悼念斯大林的文章中,胡风这首诗的最大的特点是题目奇长,达25个字。
是否战俘,凡有英勇的行为,都应该归于党员。
胡风的散文《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发表在《人民文学》1953年9月号。
与这篇文章同期发表的译文《毕可肖之战》才真实曲折地流露了胡风对战俘问题的思考。也许是翻译文章为胡风表达自己的思想设了一层安全的屏障。他没有再歌颂战俘的英勇,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直接谴责战争本质上的非人道。这一立场不从战争正义与否的价值尺度来立论,而是否定战争本身。在解释这篇译文的意旨时,胡风特意说明拉伯雷“如何酷爱和平,谴责穷兵黩武的侵略者,而且主张对俘虏要给予人道的待遇”。从人道主义来衡量战俘作为一个人的遭遇,不从阶级性质而从人道主义来质疑战争的正当性,这才是胡风思想中的“鲁迅方向”。此后胡风还计划以战俘问题到朝鲜实地采访,写出另一篇报告;周恩来也再次点名要胡风去做。但是,章靳以等人的附会批评,让胡风找借口推掉了这一创作打算。胡风就这一题材、作为领导交代的任务而写的其他稿件送到《中国少年报》《人民文学》,往往是永无音讯。不久,围绕路翎小说的批评多起来,胡风能发表的刊物只剩下了《人民文学》,但“正在受攻击的编辑部”也不敢再与他联系了。
1953年12月发表的《睡了的村庄这样说》显出少有的静谧、端庄,就像谢幕前的安魂曲一样给人诸多的想象。诗歌其实写于胡风从上海来北京接受批判的1951年。在4月的春夜,呼啸的列车外是宁静的村庄,破败、肮脏的一切笼绕着流动的夜气,村庄在“沉睡”中暂时隐藏了苦难和喧嚣——在火车上的胡风也许没有意识到北京将改变他的命运,竟在柔和、澄净的诗篇中表露出一种通达和喜悦:“夜/慈爱的夜呵/她为我带来了休息/我的肌肉在新陈代谢/我的疲劳《人民文学》1953年12月号发表了胡风的诗歌《睡了的村庄这样说》。在一点一点退去/同志/痛苦的夜过去了/流血的夜过去了……”但是,诗人在想象未来的时候,不乏警觉:“同志/为了黄金色的未来/我要睡得安静/我要睡得深沉/但在我睡着了的身边/还是跳跃着一粒火/还闪耀着一盏灯/它是我的一只不睡的眼睛/为了黄金色的未来/它警戒着/祖国土地上的旧社会的毒虫/它监视着/祖国边疆外的旧世界的黑影……”“黄金色的未来”,让人想起鲁迅文章中的意象。胡风在“沉睡”中并未忘怀大地上的封建承担,而那只“不睡的眼睛”则监视和警戒这些“毒虫”。
这首安魂曲一般的诗歌,成了胡风在《人民文学》上的绝唱。当胡风的名字再次出现时,已是公开的“罪人”身份。胡风被撤销了编委的名誉,批判胡风的文章也成了《人民文学》持续数期的一道景观。一度风头强劲在《人民文学》连续发表《初雪》《战士的心》《洼地上的“战役”》等等作品的路翎,随着胡风的命运转折而在《人民文学》上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