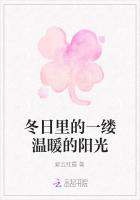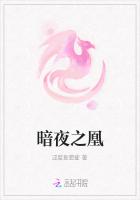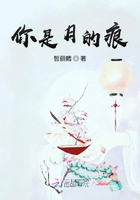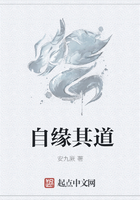上世纪50年代,期刊传播是在国家垄断下进行的。1949年的国家政策就已规定,禁止设立新的私营出版业,对1949年前就已成立的私营出版社采取了逐步“消灭”的政策。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在1951~1953年间,一度允许私人成立出版社。但1953年之后,私营出版社迅速消亡。私营出版社的数量显示出这种状况:1950年全国的私营出版社有184家,1951年为321家,1953年356家,1953年290家,1954年97家,1955年16家,到1956年6月为零。数字来自1954年的《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业的报告》,见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第3卷,第138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私营出版社建国初期一度还存在,但它们基本上是代售或代印国营出版社的书刊,自身没有独立出版书刊的权利。期刊的发行由国营出版机构根据专业分工的原则,由专门的发行部门去发行。1949年之前传播发行中重要的因素——商业利润化追求——从期刊编者、作家那里被排除掉,即使在期刊的经营者(出版和发行单位)那里也被尽量淡化。由此,编者、作家依赖期刊销行收入的生存方式发生了转变,期刊迎合读者以追求发行量的必要性也丧失了,期刊成为集中宣传思想、政策的“纯”文学的空间——它为后来的“纯文学”准备了条件。正由于这种不以读者实际需要为主的“纯”文学条件,中央级的《人民文学》在流通之中赋予作家、作品以象征性的效应,作家的命运缘此而改变。
□剔除商业因素
《人民文学》创办伊始,编辑者的经营权就被剥离出去。前文提及,《人民文学》创刊号在国家出版部门登记时,注册者即是《人民文学》之外的黄洛峰。出版、发行两种工作,由新华书店一身兼有,三联书店作为私营公司短时间内也部分承担《人民文学》的发行工作。随后,《人民文学》的出版发行单位几经变化:1950年出版界专业分工政策出台,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分别承担《人民文学》的出版和发行工作。1951年专业化继续加深,专门出版文学作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人民文学》转由该社出版。1953年,新华书店与邮政部签订协议,《人民文学》的发行业务由邮局接收。至此,一直到1966年停刊,《人民文学》的编辑、出版、发行单位才基本固定下来。出版和发行有两次差点归于《人民文学》的编者,一次是1956年推行“双百”时期,一次是1958年。1956年中国文联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期刊编辑会议上,曾提出期刊实行企业化,但并没有实行。1958年1月,《人民文学》不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营,改由《人民文学》编辑部自己发行。但是,其发行方式依然是邮局征订、邮购和新华书店代售两种方式,并没有脱离原有的模式。在50年代至70年代,《人民文学》流通传播中的经营权,一直不属于自己。新华书店或邮局对《人民文学》的独家经营权,既有政策的规定,更有协议上的保障,《人民文学》的编者们丝毫不能越界。如1951年3月1日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签署产销合同规定: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由新华书店总店总发行,不得委托第三方发行或自办发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当然要遵循这样的规定,编辑部是没有权利自办发行的。
编发分离的体制,等于将商业利润因素从《人民文学》编者那里剔除。一般来说,期刊之所以能激励文学的繁荣,一个重要因素是期刊的商业化经营能够给作家带来生存方式的转变,为作家的独立写作、文学的某种变革提供可能。陈平原指出,正是晚清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出版业的繁荣,职业作家得以出现;这些作家在迎合读者的同时,为现代小说摆脱“说书体”向“书面化”的转变提供了条件。旷新年在对1928年前后的文化研究中也指出,商业化文学期刊的繁荣,使沈从文赢得了更多的发表机会,促使了沈从文写作风格的形成。分别参见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在《人民文学》这里,利润收入并不为《人民文学》的编者或主办者所有;编者或主办者无权也无能力对不同的作家、作品支付不同的报酬。《人民文学》的编者没有这种从稿酬上来调控作家、作品的自由。《人民文学》的编者、作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商业关系,只表现为定时定额地从经营者那里领取政策规定的编辑费和稿费。17年期间,政策所规定的稿费本身就不高,加上版税制的去除,期刊不能像图书那样可以按照印数定额法来支付稿费。1953年,参照苏联稿费制度,稿费首先去除了1949年前常用的版税制,而以另外两种方式支付:基本稿酬,指一次性付清,翻译文章是千字4~13元,非译文为千字6~18元;印数定额方法,指先付基本稿酬,然后根据印数定额给以浮动。印数定额制是对1949年前的版税制的改造使用,而单纯依据印数确定稿费的“完全版税制”事实上已经消失。相比图书来说,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付酬方法更为简单,只按千字标准一次性付清,无论期刊销量多少,稿酬不变。刊物付酬办法,一直沿用至今。只是稿酬标准有了变化。1953年标准:千字6~18元;1958年标准:千字4~15元。1961~1966年,稿酬时有时无。1966~1977年,无稿酬。1977年的标准:千字2~7元。所以,那种由经济收入来刺激作家创作的模式,在《人民文学》这里不起作用。同时,编者、作家在50年代后已被干部化,他们各自有依附的单位。这些国家单位给他们的工资,成为他们稳定的生活来源。某些作家从主观上似乎也并不重视稿费收入,有些作家甚至主动提出取消和降低稿费的要求。如赵树理1953年成为作协“驻会作家”时,提请取消自己享受的版税和稿费,“否则连现有的供给也不应领”。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830页。1958年11月,《人民文学》的主编张天翼,编委周立波、艾芜首先提出“降低稿酬”的建议。此后,引起作家们的普遍响应。而那些希望以稿费来发家致富的人则受到道德和政治上的批判,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王子野在《对降低稿酬的倡议有感》说:“整风一年来提出了不少的材料证明:凡是在稿费问题上争执不休的绝大多数不是右派分子,就是插白旗的教授、学者和作家。”王子野点名的人有丁玲、刘绍棠等。见《人民文学》1958年11期。对注重稿费者严厉的政治评价由此开始形成。李准曾说:“拿稿费等等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尘埃。一个人有了这种意念,他的作品就一定写不好。因为他首先考虑的不是革命利益……而是追求个人名利。”见《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言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第306页。对稿费的这种政治、道德评价,一直钳制着作家的认识。总之,商业性的利润追求,在《人民文学》的流通传播中并没有构成积极的因素。这样,无论《人民文学》是否符合读者的需要,无论杂志销路如何,都与编者、作家的经济收入毫无关系。
不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原则,也贯彻在《人民文学》的经营者那里。在1949年1月7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当前出版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规定》中明令规定,书店出版经营“切实执行企业化的方针,一切应从计算出发,必须精确计算成本”,但“不能追求利润,以做到实物保本(以纸张、铅字、小米计算),维持再生产为原则”。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那个时期的经营,目标不是利润目的下的增大市场占有率,而是将杂志作为精神产品送到更多读者手里。如1950年6月出版的《人民文学》专门登出《本刊降低基本定价启事》,“为减轻读者负担起见,自第二卷第三期起,减低基本定价:甲种纸本每册五元三角,乙种纸本每册四元七角。”发布这一启事的是新华书店。经营者将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期刊、图书几乎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发行单位甚至要赔本发行。如1951年3月1日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签署的产销合同中,规定折扣为65%。这一折扣使新华书店每发行一种书要亏损3%;一直到今天,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发行折扣基本上还是这一折扣。新华书店将《人民文学》的总发行转给邮局后,这一折扣并没有变更。从1949年以来,邮局系统对期刊的发行量连年上升。《人民文学》在创刊时发行量为2.2万册,划归邮局后,发行量上升,到1955年达到13万册,1956年达到20多万册。以后一直维持在20万册左右。参见廖盖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刊》,《光明日报》1955年5月20日;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1949~1952),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人民文学》的发行量同样如此,其覆盖范围到了全国各地,包括偏僻的农村。巨大的发行量和覆盖范围,为《人民文学》拥有众多的读者、为其作品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准备了重要条件。同时,邮局发行系统又为《人民文学》发行量和覆盖范围的极大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邮局发行实行预订和分设网点两项制度,其网点在全国有上万个。凡是有网点的地方,就必须发行《人民文学》。邮局的预订制度,又保证了《人民文学》不受季节、地域的限制,也不受刊物波动的影响,一直能够保持稳定的读者数量。邮局所规定的预订时限分为6个月或12个月,最短为3个月。因为是提前预订,《人民文学》一般不会在预订时限内出现销量突然降低的现象。相反,因预订外辅以网点零售制度,《人民文学》在预订时限内只会销量突然增加。这样,《人民文学》的读者群在预订时间内就会维持一个稳定的数量。
各单位分工合作的生产、传播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大工业生产的模式。这一模式有其优势:各单位能集中和专一地发挥自己的效能;相互间的合作又避免资源的浪费和无序的竞争。但大工业生产方式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又造成了一种弊病:在“施与者”(作家、编辑)与“接受者”(读者)之间,横亘着一个中间环节,即发行部门。于是,双方不能自然、直接地交流,而这一中间者的转述又有误读的可能。比如,邮局在《人民文学》的广告信息中这样写道:“该杂志……所发表的文章较长,内容比较深,理论文章所阐明的是一些大问题,适合于大专学生及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阅读,发行限于大、中城市。”呼延虎:《积压了“三百多万册”的反面》,《人民文学》,1956年11月号。这种看似明确、其实限定的解释,并不完全合乎《人民文学》的实际。这里的表述,不是来自《人民文学》的文学特色,首先是对读者的分级。无怪乎有人说:“这本‘文章长’、‘内容深’、再加上定价也高的‘大’杂志,它在发行部门当然不会受到很高的礼遇;同时,它想从读者那里得到太好的礼遇,大约也有困难的吧?”呼延虎:《积压了“三百多万册”的反面》,《人民文学》,1956年11月号。
一旦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中断,刊物的发言基本上成了自说自话。它要么成为一己思想的论坛,要么根据“假想的读者”来编辑作品。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这两点都为《人民文学》所具备。而对这些读者的“假想”,自然就时常从政策对现实和人的规定上来寻找根据。由此,《人民文学》主要成为“纯”文学的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解释者和权力文学观念的实现者。到80年代中期,由于作家主体性的张扬,“纯”文学才向“纯文学”过渡。在笔者看来,“纯文学”概念只能在两个方面才能证明自己的内涵:1.抵抗商业侵蚀,探讨严肃命题。2.追求创作的主体性,以开放的形式向精神心灵开掘。“纯文学”与商业性、媚俗性,即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方面是相对的。这样,“纯文学”的生长空间,就需有强大的保护力量和体制,以利其生长。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商业因素的加强,当代文学才从“纯文学”的迷梦中走出来。20世纪末,中国文学之所以能那么迅速地被边缘化,人文精神讨论之所以能那样沉痛和急切,追根溯源,与文学期刊这种“纯”文学空间的生成有关。
□沈从文的复活
拒绝商业利润侵入的《人民文学》成了类似于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学场”。文学自主是“文学场”历史演变中的一条主线。影响“文学场”确立自主原则的,是其他“场域”对“文学场”的侵入和挤压。布尔迪厄将我们通常所称的领域称为“场”,与领域内涵不同的是,“场”是个有自己独特逻辑和必然性的空间。布尔迪厄认为,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的和谐统一体是由这些相对自主的微观世界即“场”所构成的。同时,布尔迪厄又指出,“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不同“场”之间存在着权力关系。在纯文学领域,“文学场”拒绝采取“经济场”在短时间内追求利润的逻辑,而采取不从众、不追求短期利润而在将来获得利益的做法。参见〔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5页。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对“文学场”形成钳制的主要是“政治场”和“经济场”。也就是说,“文学场”一直是在对“政治场”和“经济场”的反驳中谋求自主原则的。《人民文学》以主动的姿态拒绝了“经济场”力量的直接渗入,但以“纯”文学的空间接纳了“政治场”的力量。
《人民文学》弥合“政治场”和“文学场”的手段是象征策略的运用。也就是说,“政治场”借助象征手段将文学纳入政治的体系;“文学场”同样借助象征手段将政治纳入文学的血液。这种互相借助、终于弥和的方法,构成了《人民文学》传播的特色。当然,需要说明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民文学》在新中国的期刊体制中位居顶端,属于中央级。其他刊物与《人民文学》地位悬殊,在实施“文学场”与“政治场”的象征性策略中缺乏威力,也不具备典型意义。
沈从文的《跑龙套》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消失”多年的沈从文第一次浮出水面,象征着沈从文在文学上的“复活”。
这一象征策略在《人民文学》的运用,典型地体现在沈从文等一批作家身上。众所周知,在1949年的历史转折中,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们在筛选中纷纷消失。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是沈从文、钱钟书、朱光潜、穆旦、张爱玲等等。此外,还有五四以来的老作家周作人、汪静之、康白情等人。这些作家中的一部分人去了海外,张爱玲1949年后曾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做编剧,后到香港、赴海外。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留在大陆的并非没有继续创作的念头,但最终不得不改行。然而,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周作人、穆旦、沈从文、汪静之、康白情等集体复出。
周作人以“启明”的笔名发表《梅兰竹菊》。
周作人以“启明”的笔名发表《梅兰竹菊》,汪静之和康白情分别发表诗歌《第一个天堂》《山栖夜兴》。此外,被周扬评为“毫无进步”的徐懋庸也发表了《“蝉噪居”漫笔》(署名“回春”)和《我的杂文的过去与现在》。
沈从文的《跑龙套》、穆旦《诗七首》、徐懋庸的《“蝉噪居”漫笔》还分别成为当期散文、诗歌、杂文栏的“头题”。《人民文学》自1949年创刊以来第一次给这些消失的作家以极高的礼遇。在当期的“编后记”中,《人民文学》欢呼这些作家的出现是“文坛的喜讯”,是本期刊物最鲜明的特点,“体现了风格、题材以及表现手法上多样化”。至为重要的是,《人民文学》给这些老作家以政治上的正名,肯定其作品是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贡献,并且热情洋溢地表示,此后“愿意用我们所能尽的力量,支持各方面老作家的创作”。《人民文学》发表这些人的作品以及“编后记”的大胆用语,给整个文坛传达出的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
从1956年的“双百”方针到1957年的大胆“鸣放”,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在内,都大量发表批评性的言论和文章。由于1955年“反胡风”的余悸犹在,文艺界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热烈“鸣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要求各刊物更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在作协参与审干工作的李清泉受命回到《人民文学》,准备加强“鸣放”的力度。但如何“鸣放”,李清泉似乎有些茫然。《人民文学》此前发表的一批“干预”作品,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等正受到批判。无奈之下,《人民文学》向周扬请示,周扬直接指示,向沈从文等一批老作家约稿。原因在于,穆旦的诗作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但《诗七首》成为他在1949—1978年间的绝唱。
“沈从文一出来,会惊动海内外”。涂光群回忆道,为贯彻“双百方针”,主管文艺界的周扬一再“耳提面命”中国作家协会各刊物的负责人,要请动多年搁笔的老作家写稿。周扬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严文井随后和李清泉一道向沈从文约稿。见《沈从文写〈跑龙套〉》,《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73~274页。自认写小说已经失败的沈从文并没有参加“鸣放”的意愿。沈从文在1956年7月《致沈云麓》的信中写道:“近来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到处都鸣起来了,我似乎已没有什么可鸣处,却只想把所学的好好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见《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但沈从文还是拿出了一篇短文《跑龙套》,被编入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
沈从文等作家在《人民文学》上的这次复活,是《人民文学》作为传达“鸣放”气候的象征策略所决定的。他们以自己的亮相,充当起其时文艺气候的符号。在《跑龙套》中,沈从文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激烈的言论,只是在不无怨尤的情绪中津津有味地说明戏剧舞台上跑龙套的小角色也有了不起的作用。这是沈从文从事服饰研究、无法再写小说的一种心情自况。但是,“革新号”的油墨未干,“鸣放”的浪潮就成了“反右”的运动。事实上,毛泽东在1957年5月就在高层传达了将鸣放者定为“右派”分子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国作协的邵荃麟于5月18日得知“转向”的情报,但《人民文学》并不知情。所以,7月号依然按照“鸣放”的方针发表老作家如沈从文、周作人等人的稿子。至于8月号上沈从文发表第二篇文章,自愿的成分恐怕更多一些。见《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姚文元指责“革新特大号”是“毒草专号”。中国作协也编辑了《〈人民文学〉毒草集》内部发行,以供批判使用。
为表现出对“右派”的批判,《人民文学》1957年8月号即改变了态度:同样以老作家作为传达文学动向的策略,《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汇聚了周作人、沈从文、徐懋庸、宗璞等人的作品,而到8月,反右派的风潮就猛烈而至,叶圣陶的《右派分子与人民为敌》成为了《人民文学》8月号的第一篇文章。
表达的却是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本期第一篇文章是叶圣陶的《右派分子与人民为敌》,第二篇则是沈从文的《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在《一点回忆,一点感想》中,沈从文从《跑龙套》那种曲折流露心情的散文写法转为明确的事件叙述:“右派”分子曾经在“鸣放”期间“心怀叵测”地来访问,试图让他说出自己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之类的话。但是,沈从文告诉来访者的却是:“不,我很自由!”
在1949~1966年期间,沈从文的文章在《人民文学》上总共出现五次,出现频率最高的时期即在1957年的7期和8期。两篇文章显示出思想上的对立,前一个还有委婉表达不甘心于小角色的自我要求,后一篇则是对个人要求的彻底否定。但无论如何,两篇文章都显示出《人民文学》的传播特点:它不一定是靠作品本身与读者的审美共鸣来实现传播,而时常将作家、作品作为显示某种政治、文学、人的命运转变征兆的象征符号。在60年代初逐步摘去1957年8月,沈从文刚刚发表《跑龙套》之后,又发表了《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右派”帽子和七八十年代“拨乱反正”时期,某些作家在《人民文学》上的亮相,常被作为恢复写作权利和改变政治身份的前奏。
如丁玲、艾青等人在政治裁定正式作出之前,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回归”。就这方面来说,《人民文学》传达文学气候的能力,带有强烈的政治威力。《人民文学》这种特殊的象征效应一直延续到今天。地方级的文学刊物也模拟《人民文学》这种策略,但它们显示文学气候的能力要弱得多。其原因主要在于它们不具备《人民文学》和权威顶峰那种近距离的优势,也不具备《人民文学》在国内外发行的条件。
□文学新人的突变
“象征收益”的概念也来自布尔迪厄,其内涵指作家由作品获得的声望、知名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益。参见〔法〕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102页。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从《人民文学》获取“象征收益”的主要是文学新人。有政治问题的作家一般情况下没有被《人民文学》承认的资格,某些谨慎的作家通常又害怕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会“树大招风”。如孙犁1949年10月写一短篇《钟》,康濯想将之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孙犁却写信说:“《钟》能在‘文劳’(《文艺劳动》)发表最好,在《人民文学》发表不大合格,且易遭风。”见《芸斋书简·致康濯》,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5页。当然,这样的作家只是少数,大多数老作家更愿意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看作是自己在政治和文学方面的双重收获。而文学新人则普遍将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当作自己文学创作的制高点,或者文学道路上的一次质变,并可能由此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甚至在生活、地位、人生道路上得以根本改变。
由《人民文学》推出的优秀作家数量之多,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他当代文学期刊无法比拟的。无论从题材或体裁来看,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所讲述、研究的作品、作家,基本上都出自《人民文学》。这些作家在登上《人民文学》之前,也不是没有文学创作上的尝试,但在他们个人的文学回顾中,显然更愿意将《人民文学》上发表或为《人民文学》肯定的作品当作突变的开始。
王汶石在解放区时就已经有了文学实践,1950年还参与创办《西北文艺》,并担任该刊的副主编。但是,1956年经由《人民文学》发表的《风雪之夜》却是他创作之路的分水岭。
王汶石的成名作《风雪之夜》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3月号。
1955年前,王汶石发表作品的报刊仅限于《西北文艺》《群众日报》《剧本》和《群众文艺》4家,其体裁多为评论、剧本。在《风雪之夜》以后,王汶石发表文章的范围迅速扩大。1956~1961年期间,其作品频频出现于《人民文学》《延河》《长江文艺》《文艺月报》《新港》《收获》《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影响更大的媒体。其作品的体裁则转向集中于小说,单1958年他就在《人民文学》《长江文艺》《收获》《文艺月报》等发表小说9篇。《人民文学》给他带来的效应也深入到出版社。1958年8月,由11篇小说结集的《风雪之夜》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引起了更大的反响,郑伯奇、杜鹏程、巴人、严家炎等人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效应又反馈到《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在《风雪之夜》之后,接连转载他的《新结识的伙伴》《严重的时刻》,并发表他的《夏夜》《卢仙兰》。《新任队长彦三》再次登上《人民文学》的头题。《新结识的伙伴》首发于《延河》1958年11月号,《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转载。《严重的时刻》首发于《延河》1959年10月号,《人民文学》11月号转载。从时间上可以看出《人民文学》转载的效率之高。在转载的同时,《人民文学》1958年4月号发表王汶石的小说《春夜》,11月号发表《村医》,1959年1月号发表《卢仙兰》,1960年1月号发表《夏夜》,7月号发表《新任队长彦三》。王汶石这一时期在《人民文学》上具有极高的“出镜率”。高频率、高“出镜率”、发于“头题”,是《人民文学》帮助一位新作家迅速“走红”的常用的方式。这样推出的新作家,很快就为更多的刊物所接纳,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推动的效应。在《人民文学》转载、发表、“头题”这种高频率和多层次的推出下,王汶石走进了文学权威茅盾、叶圣陶等人的视野。茅盾对王汶石的关注,甚至已不满足于他那些公认的名篇,而深入到他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如茅盾在《人民文学》1959年2月号发表的《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评介的是王汶石发表在《收获》1958年4月号上的《米燕霞》。此篇小说后来被收入到《风雪之夜》短篇小说集。那一时期,对王汶石的众多评论文章总是从《风雪之夜》开始;即便到了新时期,这一叙述起点也依然如故。评论界这一叙述,显然与《风雪之夜》在王汶石心中的分量是一致的。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多次结集出版,两次被翻译为英文介绍到国外,但无论集子内的小说如何调整,《风雪之夜》都是压卷之作,单行本的名字也总是《风雪之夜》。《人民文学》发表的这篇《风雪之夜》,奠定了王汶石在国内外的作家声望,也成了他一生创作的象征。《风雪之夜》小说集,首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8年8月出版;1959年9月增加新篇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再次增订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风雪之夜》的英文版。1977年“拨乱反正”时,再经王汶石增订后仍以《风雪之夜》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篇小说经由《人民文学》传播带来的影响,还促使了王汶石创作风格的形成。《人民文学》发表《风雪之夜》后仅两个月,王汶石就开始了对风格的“醒悟”。在1956年5月15日的日记中,王汶石写道:“在写作过程中,忽然想到风格问题,对风格问题有了如下的醒悟……”王汶石所“醒悟”的是,“力求最朴素最巧妙最完美地表现你的新的主题,新的题材和新作中的人物”。朴素、新、人物:这三者正是当时评论者对王汶石小说风格进行概括的出发点。写这则日记的两个月前,《风雪之夜》刚刚在《人民文学》发表。见金汉编:《王汶石研究专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王汶石在“文革”以后恢复创作自由时无所作为的事实,与其对风格的过早“醒悟”不能说没有深刻的关联。尽管在《风雪之夜》发表之初,王汶石警醒自己不要为风格所束缚,但后来为《人民文学》转载、发表或重点推荐的作品,可以看作是《风雪之夜》在不同材料那里的延伸。这些作品“带着微笑看新生活”,着眼于“合作化运动中农村的新人和新生活”,倾力叙述的是“一点优点”,而不是生活中可能有的“九点缺点”。王汶石曾说:“假如生活中有九点缺点,可那一点优点,就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值得高高举起。”《亦云集》,见《王汶石研究专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对“对立面”或杨朔的成名作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在《人民文学》1952年10月号开始连载。
“缺点”的疏忽,或者缺乏进一步去理解的意愿,扼杀了王汶石文学探索的可能。王汶石盛极而衰的文学命运,与《人民文学》发表《风雪之夜》后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以及由此给予王汶石的创造风格暗示和文学自觉,有着深刻的关联。
对《人民文学》给作家创作带来的“醒悟”作用,郭风曾有一段更明确的表述。在1989年《人民文学》庆祝创刊40周年纪念时,郭风说:“1957年3月号上刊用了我的《散文五题》,其中《叶笛》也许是我的成名之作,这促使我有勇气继续写作诸如此类的散文”。摘自《人民文学40周年纪念册》,内部本。
与王汶石等文学新人不同的是,郭风在40年代就得心应手地创作过此类散文。但正是在《人民文学》的发表以及随传播在读者中得来的肯定之下,郭风才获得创作的新生,并沿着这成名之风格走下去。
《人民文学》带给文学新人极大声望的同时,又给了他们一种文学标准——这是一种为中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所推崇的标准——这一标准成了他们的作品获得成功的保证,也成了他们很难突破的樊篱。与王汶石一样,王愿坚、孙峻青、杨朔等大批五六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都在《人民文学》那里获得了自己最高的声望,但也都在重复着一种相似的文学命运。从这一角度来说,《人民文学》所给予他们的巨大的象征收益,其实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