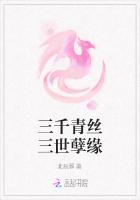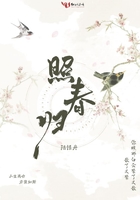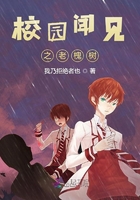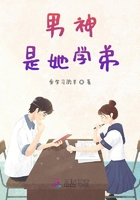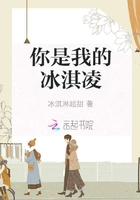巴那斯主义:一个文化学的定义
巴那斯派(又译帕尔纳斯派Le Parnasse),指的是法国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个诗歌流派,它反对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反对所谓“浪漫的感伤”,讲究“不动感情”、“取消人格”的客观化,倡导艺术形式的“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诗歌造型精巧美丽。这一艺术渊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戈蒂耶。戈蒂耶曾当面批评泰纳“居然要求诗歌表达感情”,“光芒四射的字眼,加上节奏和音乐,这就是诗歌”。巴那斯派的另一个先导是维尼,他认为诗歌应该客观、冷静地表现世界。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巴那斯派的出现,实际上典型地代表了西方文化内部自我调节的有效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互补性“一体化”结构迥然不同,西方文化从它一诞生就包孕着相互抗衡、相互否定的自我调节力量。各种基本矛盾永不停息地推动着整个文化系统呈螺旋型上升。古典主义的冷血动物式的理智必将受到浪漫主义情感潮流的有力冲击,而放言无惮和缺乏深沉品格的浪漫式抒情也注定要重新受到理性精神的抑制。西方文化的否定同时也是垫高文化层次的有效方式。这样,也恰恰是在巴那斯派这种理性的约束中,个体生生不息的生命体验才最终被推向了象征主义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象征主义是对巴那斯派的否定,但象征主义却将浪漫主义的天真感情沉淀为更加深厚的生命意识。
由此看来,介于浪漫主义诗歌与象征主义诗歌之间的这种“巴那斯主义”,就富有了它非同小可的文化意义。鉴于此,我以为作为“主义”的巴那斯现象就不仅存在于法国,也同样表现在其他西方国家。比如英国,在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华兹华斯与20世纪的意象派之间,就表现为倡导情感节制和严格音律的维多利亚诗风,重要诗人丁尼生、布朗宁就以隐匿感情于唯美的形式而闻名,同样地,西班牙19世纪后半叶也出现了何塞·索里雅这样讲究辞藻和韵律的诗人。
仿佛与世界文学的进程相一致,中国现代新诗在郭沫若一代的浪漫主义与30年代的象征派、现代派之间,也有这么一个以理节情的巴那斯主义——新月派。也正是在20年代初期的浪漫主义“泛滥”中,新月诗人展开了自己明确的追求:“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光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情感不能不受理性的相当节制与调剂”。“感伤主义”是“现在新诗的途径”里“一个绝大的危险”。使“感伤”规范为“健康”,让文学接受“纪律”的约束,新诗的格律化问题应运而生。闻一多讲“建筑的美”,饶孟侃讲“格调”,孙大雨讲音步、音组的建构……新月诗人广泛引进西方诗歌的多种格律体制,探索着中国现代新诗最为精美的形式。
看起来,巴那斯主义是注定要走遍世界诗坛了,东方西方,本土异域,谁也避免不了。
新月派的启示
但情况对中国诗人来说,又分明没有那么简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文化自身并不具备西方那种自我否定的因素。“五四”新文学是依靠对西方文学的引进、学习才实现了对传统文学的反拨。巴那斯主义亦如此,它也并不是在中国固有文学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巴那斯主义,是混杂在中国文学开放之际滚滚涌入的林林总总的思潮、流派中为中国诗人所接受的。西方文学史上呈纵向递进的浪漫主义、巴那斯主义、象征主义在中国20年代诗坛则表现为横向的并列——李金发早在20年代初就开始了象征主义诗歌创作,而在此之前,一些中国诗人如周作人、沈尹默就已经注意到了象征主义的艺术方法;至于浪漫主义,我认为它从来就没有在中国诗坛消失过。
在如此驳杂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的巴那斯主义是很难保持自身的“纯度”的。
师从拜伦、雪莱的徐志摩曾“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闻一多也有过“烧沸世人底血”的《红烛》时期,尽管一些新月派成员在后来也攻击过卢梭,挑剔过拜伦,但却远不具有维多利亚批评家阿诺德的尖锐和严峻。在阿诺德眼中,“拜伦如此内容空虚,雪莱如此涣散,华兹华斯尽管深刻,却仍然缺少完整和多样”。华兹华斯与自然的亲和之情始终吸引着新月诗人,给他们的创作涂上了一层清远飘逸的色调。
可以说,中国现代诗坛并不存在纯粹的戈蒂耶与丁尼生,中国的巴那斯主义也并不完全是根植于对浪漫情愫的反抗、对立,它的发展、壮大还有着更深刻的渊源。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理想使新月诗人接受了巴那斯主义的节情与格律却又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包容浪漫式的抒情?
这就还得回到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中来。我们曾说,巴那斯主义是“移植”的,不是我们这块土地自然生长的。这是就这一思潮“进入”中国的方式而言,而一种外来的文化因素能如此顺利如此广泛地为我们的诗人所接受,则无疑是与我们古老文化的特征有关,与我们源远流长的诗歌美学传统有关。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传统,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合二为一的奇妙世界。
自先秦中国诗歌的滥觞期开始,中国人的理想就是理智与情感的相安无事。“发乎情,止乎礼义”。道家尚个性、崇感性,但却根本无意与儒家观念分庭抗礼,相反,它们把感性抽取得近似真空,以达到与儒家最大程度的互补效应。而儒家虽然趋向于理智地把握世界,也根本有别于西方道德理性的冷酷无情,也没有那种穷追不舍的玄思苦想,这是一种温情脉脉、循循善诱的教化,儒家完全可能最大程度地包容道家的感性而为自己服务。儒道互补的人格造就了中国古代诗人的平和、余裕、“哀而不伤”的独特心境。恰如著名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所说: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儒道互补是诗人生命的稀释,理性与感性的互补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萎缩。中国古典诗歌对人内心世界开掘的“类型化”、“模式化”也因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如此,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品格对每一个在她怀抱里长大的中国人来说却无疑具有永恒的魅力;就一个弱小民族所无法避免的文化自卫心理而言,越是“西学东渐”,倒越可能加深我们的民族情感。比如闻一多在阅读济慈等人的诗歌时,就时时不忘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沟通”,维多利亚诗风的“节情”与音律更是让他一见如故。闻一多这样描述这种心情:“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一想到至少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弱于人,于是便有了安慰。……这是紧急关头的一帖定心剂。”
看起来,巴那斯主义的音律和唯美的形式首先在新月诗人那里唤起了似曾相识的认同,而民族审美理想中对感性的部分保留又让这些诗人并不能真正取消浪漫主义的“抒情”——新月诗人最终是在传统审美心理的制约中抒发着一种疏淡的情性,同时也试图在形式上回归和谐整一的传统境界。这种疏淡的情性也已经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的丰富情感,而闻一多创立新格律的目的也显然是为了达到传统诗歌“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效果:“律诗乃抒情之工具,宜乎约辞含意,然后句无余字,篇无长语,而一唱三叹,自有弦外之音。”
新月诗人中将恬淡的意境与严格的音律完美结合的当数朱湘。徐志摩在形式上要舒卷自如一些,而且大概是因为所谓“思想杂”的原因吧,他的诗风也呈现出了一些自身的变化,只是,徐志摩予中国读者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再别康桥》、《山中》、《沙扬娜拉》这些诗,柔肠百结、纤细飘逸,说它们是“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茅盾语),这多半含有贬义,不过就传统审美理想来讲,构成这样一个空疏的境界,“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谢榛《四溟诗话》),倒是最绝妙的手法。
闻一多倡导音律最力,公开宣扬感情克制的声音也最高,但闻一多却具有中国20年代诗人中罕见的自我分裂人格:诗人的理性与感性体验各自都怀着十分倔强的性格,互不相让。在《死水》时期,诗人的理性自制达到了空前的强度,“不要想灰上点火,我的心早累倒了,最好让它睡着”。但非常明显,诗人并不可能“睡着”,他那汹涌的生命之流在死火山般的胸膛中冲撞、振荡,越是自我压抑,倒越聚集了内在的可怕力量。传统心理迫使诗人自制,但一个现代诗人的生存体验又让他很难控制自如,在这难以平衡的精神痛苦中,闻一多终于结束了巴那斯之路,他实际上是以自己艰难的探索宣告了中国巴那斯主义的终结。
恐怕问题还在于:中国化的巴那斯主义——在一定格律限制中的“哀而不伤”能够如此真切地传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吗?
现代派的余韵
马拉美是巴那斯派到象征主义的关键人物。在《关于文学的发展》这一著名谈话中,他在诗的观念上完成了对巴那斯主义的否定。
卞之琳、何其芳是中国的马拉美。徐志摩是卞之琳的老师,而何其芳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就“温柔而多感地读着克利斯丁娜·乔治娜·罗塞谛和阿尔弗烈·丁尼生的诗”,法国的巴那斯派(何其芳称之为“班纳斯”)也予他很大的影响。但卞之琳、何其芳这一代现代派诗人又都由巴那斯主义出发,进一步接近了波德莱尔、叶芝、艾略特、庞德,30年代现代派的诗风也明显区别于前辈的新月派。
但是,中国诗人对巴那斯主义的情感却仍然藕断丝连,卞之琳、何其芳并没有从诗歌观念上根本否定巴那斯主义。何其芳在自己的创作中大大地呈现着巴那斯的精美形式,卞之琳的“客观化”、“戏剧性独白”也与维多利亚诗风不无关系,直到1990年出版诗歌总集时还取名为“雕虫纪历”,“让人想起法国诗人戈蒂叶的代表诗集《珐琅与雕玉》”(蓝棣之语)。因为,戈蒂耶在《序诗》中就说:“不管那狂风暴雨,打我紧闭的窗户,我制作珐琅与雕玉。”而我们的诗人卞之琳也有这样的小天地——圆宝盒:
别上什么钟表店
听你的青春被蚕食,
别上什么骨董铺
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你看我的圆宝盒
跟了我的船顺流
而行了,虽然舱里人
永远在蓝天的怀里。
——卞之琳《圆宝盒》
的确,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也讲究“客观化”,但那主要是为了避免陷入无边的伤感而有碍于诗人对生命深沉的思考。中国30年代的现代派却总在这么一个“别”字中回避了生命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这又是为什么?
认为中国现代派黏滞于巴那斯主义而踯躅不前固然也是一个原因,但仔细分析起来,中国现代派甚至与巴那斯主义也颇不相同。英美的巴那斯主义在一种情感的节制中,已经试图传达出一些对生命的深沉理解。如戈蒂耶《死的喜剧》就集中描述了一种人生的虚妄体验和对死亡的恐惧感,丁尼生的某些诗也“表达了对生命之谜的敬畏之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新月派、现代派与巴那斯主义三者中,前两者显然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中国现代派与巴那斯的巨大差别也完全可以视作新月派与巴那斯的根本差别。
不言而喻,事情又追溯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事实上,30年代现代派诗歌本来就是在“中西融合”的追求中建构起来的。
“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的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诗人卞之琳的论述准确地道出了这场“汇融”的实质意义,即并不是中西文化各取一半,互为充实,而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建设现代新诗。
与20年代的新月派相比,这种向民族传统复归的理想更为明确、更为自觉。如果说新月派诗人还不时为同时代激动人心的浪漫主义所吸引,写出过数量不少的激奋之作,那么现代派诗人则把自己的感情雕琢得格外的精致了,他们最理想的作品已不是一种什么明确的爱憎之情。请看他们评述自己诗歌时常用的词:情调(何其芳)、意境(卞之琳)……这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逼近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层次,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浑成境界。
这是一个和谐宁静、空明澄碧的理想世界。“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时候,一定的和谐的音律是它的必然要求。何其芳、前期戴望舒的一些音律优美的诗作恰好就此达成了美妙的效果。只是,这种理想境界一经达到,又总给人一种“离尘别世”的隔膜感,你看何其芳的梦境:
你梦过绿藤缘进你窗里,
金色的小花坠落到你发上。
你为檐雨说出的故事感动,
你爱寂寞,寂寞的星光。
——何其芳《花环》
相比之下,卞之琳的一些自由体诗倒试图容纳较多的现代气息,但这样一来,显然把内容弄得复杂一些了,构成“浑融一体”的情调就不再那么容易了。以前人们读卞之琳的诗总觉得有些“涩”,其实就是这种很难调和的时代差别,古今文化因素的不和谐性。
如此看来,在一个开放的纷纭复杂的现代世界中,诗人运用传统意义的审美手段,最终还是难以传达出新的时代性体验的。
30年代的这些诗人同20年代的前辈一样,从小就浸泡在中国古文化的营养液中,他们对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诗传统的向往是这样的难以遏制,以至总是在各自不同的道路上向想象中的中国传统靠拢着。对于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关键的任务是如何“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象征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因为与中国古典的“兴”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由此就非常容易为中国诗人所接受——至于象征主义所完成的对巴那斯主义的根本观念上的反拨,予我们则并不那么需要,而且巴那斯主义的许多艺术手段,也仍然是中国古典诗歌削弱感性强度所不可少的——就这样,巴那斯主义与象征主义一起被中国现代派诗人包容了下来,又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再构,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综上所述,当中国诗人怀着莫大的民族屈辱之情引进西方诗艺时,是巴那斯主义这个西方诗歌史上自身并不显赫的思潮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启示,让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重新开始了感情的调制和音律的研究,这种探索甚至又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诗人经过自己卓绝的探索,终于在现代白话的条件下,找到了一条复归传统审美理想的诱人之路,这一过程呈现出的史实在于:
1.巴那斯主义的启迪让中国新诗开始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2.巴那斯主义却又最终没有把中国新诗导向现代人的审美高度。
而在这两种现实之下一个更加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中国诗歌也没有真正接受巴那斯主义,就像它同时也不曾真正接受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