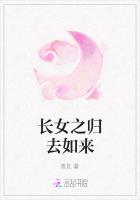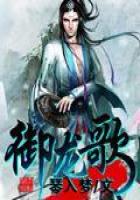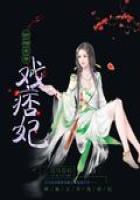他的思想在世界各个角落漫游,希求超脱尘世的束缚,试图洞察浩渺的宇宙。他的思想钻进人类灵魂的深处,力求认识自身。
——阿·古留加:《康德传》
一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愿意相信,作为西方古典艺术典范的《浮士德》是完美和谐的。自然,这有它比较充分的根据:就在诗剧《浮士德》的“舞台序幕”中,歌德提出了所谓“大自然赐与他的那种人权”的艺术理想,歌德认为,这一艺术理想、艺术精神自有其神奇的威力,在它的泽被之下,杂乱无章、平淡无奇、单调沉闷的世界“和谐”了,“个别纳入整体的庄严”,四面“奏出一种美妙的和音”。后人弗利特纳确认《浮士德》一剧有着“匀称的统一的建筑艺术”特征,并由此对诗剧的整体结构作出了精湛而影响深远的描述:全剧在整体意义上的框形结构和“内部情节”都遵循着由“小世界”到“大世界”的人生历程。实际上,弗氏的结论几乎可以成为所有关于《浮士德》艺术成就讨论的最终结论。不言而喻,弗利特纳(也包括卢卡契等人)的阐释对中国批评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近年来,一些谙熟西方学界发展情况的中国学者虽然已较多地意识到了《浮士德》内部的某些“罅隙”,却又最终把这类现象归结为艺术“多样性”的表现。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真正探讨这部巨著的内在裂痕,或者说,论者仍不愿相信这样的经典之作会存在这样的自我分歧。
我们无意诟病关于《浮士德》的“统一性”的理解,更无意将这部辉煌的巨著肢解得七零八落,而是仅仅想认真观察其始终未能裸露毕尽的“罅隙”部分。我们认为,这种新的探讨有利于我们重新开掘作品的深层意蕴:一以贯之的哲学把握是一种意义的开掘,凿壁偷光式的“窥视”倒又是另一种意义的探测。或者说,只要我们的审美观照处于流动当中,就可能与《浮士德》文本产生不断发展的新的“视野融合”,“窥视”出新的东西来。
传统的(包括西方批评界)关于《浮士德》艺术特质“多样性”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作品第一部与第二部的风格结构方面,第一部显然是“主观的”、“个人的”(按歌德自语),浸透了日耳曼现实主义精神(菲舍尔语);第二部则显得客观、理智,充满了“枯燥无味的比喻”。出现在这两部中的浮士德形象也略有差别。第一部的浮士德情欲勃勃,忽喜忽忧,浑身上下都释放着一个血肉之躯的生存要求;第二部的浮士德则较多地传达着某种抽象的精神品格,尽管歌德宣称:“作为诗人,我的方式并不是企图要体现某种抽象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看来,《浮士德》的内部分歧远远不止于此,我们至少还可以找出下列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全剧整体框架设置的“缝隙”。弗利特纳总结的所谓“匀称的统一的建筑艺术”,天上序幕启动的“框形情节”与尘世生活的“内部情节”互相吻合,最终又在“埋葬”、“山谷”等场面的“框形情节”中宣告结束。实质上,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我们再深入下去,结合全剧提供的情节意蕴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首尾贯通的框形分明是不够完善的:在“天上序幕”中,出现了两个奠定全剧基石的对立形象,天主与靡非斯特,各自代表澄明的、超越的、真善美的天堂与混乱的、堕落的、假丑恶的地狱,在他们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性、人的出路的争论和打赌,可以说,这场争论和赌博是全剧基本情节的依托。在浮士德的人生历程中,不断接受靡非斯特的诱惑,不断陷入尘世的烦恼,但又似乎总不甘堕入凡俗,不懈追求。但最后时不待人,忧愁女神一口气封闭了他那双好高骛远的眼睛,在满世界的黑暗中,他满足了。至此,天帝与魔鬼的打赌有了分晓:魔鬼靡非斯特赢得了胜利。如果顺理成章地返回“框形情节”,应当是:浮士德从此沦为魔鬼的侍从,靡非斯特戏谑地向天帝炫耀自己的远见!众所周知,歌德没有这么处理,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深入考虑,但我们因此却也同样可以挑剔地认为,这个框架是有“缝隙”的。
据此,我可以断定,进入实际创作状态的歌德,也因此逐渐陷入了多种情绪的复杂支配当中,他一方面似乎意识到了浮士德夹迫于魔鬼与天帝、堕落与超越之间的“二重性”,并且终究也不大可能勇往直前,他会停下来,也会说“满足”(不管是因为什么)。但另一方面,他又的确对浮士德的奋斗颇为“偏爱”,这样他又该为浮士德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首尾兼顾、两厢讨好的人生历程呢?实际上这种设计是非常困难的,歌德他根本就不可能为浮士德提供一个十全十美的奋斗模式。于是在《浮士德》中,我们发现了那种貌似强悍的“浮士德精神”的内在虚浮性,从所谓知识、爱情、政治、美和事业这五个不断超越、扩张、上升的人生历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次比一次惨痛的悲剧性结果。知识让人索然无味,爱情让人陷入痛苦的纠葛,政治把人变成俳优,美可望而不可及,而所谓事业的成功呢,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觉,人陷入了自我欺骗的泥淖。这不是更加深沉的悲剧么?这个时候,浮士德还企图总结性地宽慰自己,开导别人:“要每日每天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这不就有点空泛,或者说荒唐了吗?他自己实在没有获得真实的自由与享受!这样的“开拓”、奋斗,一次比一次地陷入更难堪更尴尬的境地,似乎又谈不上什么“扬弃”,什么“超越上升了”!
既然“浮士德精神”多少有点“外强中干”,那么他的化险为夷的“获救”也就难以自圆其说了。当浮士德已经落入到一场万劫不复的怪圈当中:愈是奋斗愈是悲剧,那么,双目失明、鸣金收兵、急流勇退似乎倒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歌德让他“获救”了。歌德宁可让天帝自食其言,放弃“君子形象”,也要把可怜的浮士德超度上天。对此,他还解释说:“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宗教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在这里,歌德实际上是承认了自身力量的软弱与不可靠:如果没有“神的恩宠”,如果不借助宗教信仰的力量,浮士德将完全是另外一种下场!而宗教力量出现这一事实本身总是与人自身的迷惘、无可奈何的体验相伴而生的。从逻辑上讲,它的效果是在反过来动摇瓦解了浮士德满怀信心的“立人”观念:“是痴人才眨眼望着上天,幻想那云雾中有自己的同伴;人要立足脚跟,向四周环顾,这世界对于有为者并非默默无语。”果真如此么?浮士德的经历显然并非如此,正因为“并非如此”,才又迫使歌德尴尬地重复着基督教义“不断努力进取者,吾人均能拯救之。”当一个真诚的接受者追随着浮士德的足迹四处辗转之后,都难以相信这突如其来的“皆大欢喜”——救赎升天那一道圣洁的光辉终于不能掩饰作品内在精神的裂痕。
这样,返回头看,诗剧的基本性质也颇令人费解。当我们考虑到浮士德实质上是愈加走向苦难的深渊时,就毫不怀疑这是一出典型的悲剧。自古希腊以降直到本世纪以前,所谓“悲剧”的戏剧性内涵尽管也发生了诸如自外而内、从人与客观自然力量的冲突到人与人的冲突这样一系列的转变,但在基本精神上却是一以贯之的,即我们最珍视的、无限向往、苦苦追求的某种理想或价值形态被毁灭。亦如中国鲁迅所概括的那句名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浮士德的人生价值中所谓“自我实现”这个最高理想恰恰是幻觉,是生命行将结束,事业即将毁灭前的掘墓之声,它是大悲剧于浮士德自己,于他所代表的人类皆如此。但是,在事实上,浮士德的确又意外地“获救”了,他告别艰难的此岸人生,步入光辉灿烂的彼岸,自我超越了。这令人想起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具有近代意识的诗人但丁,在经历了地狱、炼狱的艰难跋涉之后,终于在情人贝亚德的引导下进入天堂。(浮士德则由情人玛甘泪迎接,冉冉飞升。)既然《神曲》因此被称为“神的喜剧”(La Divina Commedia),那么《浮士德》又未尝不可呢?尼柯尔在考察了西欧戏剧理论史之后提出:“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的办法。”显然,《浮士德》既提出了人生存的窘迫、超越的艰难这一问题,却又勉力提供了宗教式的解脱之路,它的戏剧本质是不统一的、不严格的,难以定位的。
在人类文化史上,如此伟大的震撼着好几个世纪的作品,却竟然在基本的艺术精神上蕴藏着这样的裂痕,这几乎是不可思议也实在不能让人接受的。所以自《浮士德》问世以来,关于其戏剧性质的阐释就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展开了,但都又不自觉地将它引向一个“统一”的结论。我国学者接受苏联戏剧理论的影响,提出:“乐观主义的悲剧说”,试图消除传统的“片面”,以求对浮士德精神的双重意义都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但这依然是在另一个层次掩盖了我们对作品固有“裂痕”的深入认识,实际上也改变了西方文化固有的悲剧观念。我们认为,将作品固有的各种特征(包括缺陷)发掘出来,这才是接近“全面”认识的第一步。
西方现代阐释特别注意“裂痕”这一概念,在巴尔特、德里达、卡勒等人看来,那些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主要作品都存在“由于运用语言所难免产生的矛盾和不确定性,因而早就有了裂痕”。因此,这些作品的意义都可能在一片“符号的游戏”中被颠覆、被解构,解构主义由此诞生了。当然,西方解构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的意义,把读者的个体消费与阐释自由夸张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本文无意如此“偏激”,我们仍然充分重视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威性”,而只是强调,即便就歌德自身的创作历程、艺术经验及人生态度而言,《浮士德》的“裂痕”也大有认识的价值。
二
结合歌德的人生、创造境况来分析,《浮士德》的“裂痕”似乎还是事出有因的。
首先,这是歌德创作过程的漫长性所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浮士德》的创作囊括了歌德的三个主要时期:狂飙突进、魏玛古典主义以及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前后时间跨度60余年,歌德从18岁到82岁,其不同的时代特征、不同的人生感受都渗透到了创作之中。如“天上序幕”中天帝与靡非斯特打赌这一情节创作于1797~1801年间,其时歌德正值壮年,他系统地将这以前创作的若干片断整理成文,是为《浮士德》第一部。在这时候,诗人心中较多地激荡着青壮年时期的激情与个性,他有信心接受人生的一切艰难,包括天帝与魔鬼的这种赌博,有毅力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顽强奋斗,也敢于开拓“无穷无尽的奋斗”这条遥远的道路。但是30余年过去了,已经走向人生尽头的这位耄耋老翁算是历经了沧桑,许多早先浪漫的激昂的理想在大浪淘沙中被磨蚀了,扬弃了。所以歌德自己也说第一部“几乎完全是主观的,全从一个焦躁的热情人生发出来的”,属于“个人的半蒙昧状态”,第二部“所显现的是一种较高、较广阔、较明朗肃穆的世界”,属于“几乎完全没有主观”的理智状态。
一般地讲,理智是老人的特征,但这样笼统地概括也容易混淆问题的实质,在我们中国文化的观念中,所谓“老人理智”就意味着与世无争、息事宁人,意味着洞悉人生世事之后的世故与矜持。但歌德的“老人理智”显然不是这个涵义,老意味着日趋接近生命最大的奥秘——死亡之际的特有的那深刻而坦荡的选择,这有两个前所未有的收获,其一是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反省与思忖,其二是对整个人类进化历程的探索和小结。
晚年的歌德是如何看待他这一生的呢?就在他即将开始《浮士德》第二部创作的时候即1824年他总结说:“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这话在现在听起来有点像出自存在主义者加缪之口,其中的人生悲哀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歌德无意识体验的一个层面,他不可能拒绝自己渗透这种人生叹息的努力。于是,浮士德终于未能获得他所希望的那种成功。
但同样是在75岁的这一年,歌德又说:“到了75岁,人总不免偶尔想到死。不过我对此处之泰然,因为我深信人类精神是不朽的,它就像太阳,用肉眼来看,它像是落下去了,而实际上它永远不落,永远不停地在照耀着。”这是歌德人生态度的另一个主导方面,即乐观旷达,将个体的生命与整体人类的漫长存在相联系,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依托。
一是实际的人生体验,一是顽强的人生态度,两者是有矛盾的,问题就在于歌德如何处理了。歌德曾将自己的性格与莱辛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莱辛本着他的好辩的性格,最爱停留在矛盾和疑问的领域,分辨是他当行的本领,在分辨中他最能显出他的高明的理解力。你会看出我和他正相反。我总是回避矛盾冲突,自己设法在心里把疑问解决掉。我只把我所找到的结果说出来。”这样,歌德就终于在两难中找到了宗教这条不是解脱的解脱之路。“基督教本身有一种独立的威力,堕落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往往借此来提高精神。”歌德解释《浮士德》的结局时自述说:“得救的灵魂升天这个结局是很难处理的。”如果不借助宗教的形象和意象,使“诗意获得适当的、结实的具体形式,我就不免容易陷到一片迷茫里去了。”我认为这里所阐述的绝不仅是一个艺术形式选择的问题,而是歌德主体创作意识的“迷茫”,这反映出自身精神所赖以栖身的宗教之舟终究无法托起茫茫苦海上徒然挣扎的灵魂。
从《植物的变形》、《动物的变形》直到“人的变形”的《浮士德》,歌德贯穿着他对整个自然界与人类进化发展的探索,这种探索赋予了浮士德这位人类的代表强劲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人类的文学史上,如此伟岸而卓绝的浮士德精神实属第一次。但同样在这个时候,人究竟能在多大的意义上自我超越,进入永恒的自由王国也成了高悬于我们上空的一个或隐或显的巨大疑问。晚年的歌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茫,因为像他那“老一辈欧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点恶劣”,他说:“如果在忧郁的心情中深入地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就会感到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末日了。罪恶一代接着一代地逐渐积累起来了!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罪孽受惩罚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的罪孽去贻祸后代。”
三
歌德的矛盾与困惑绝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至少,他的这种强悍与孱弱、自信与卑怯的复杂结合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近代文化史上的革命性哲人康德。康德缺乏文艺创作的天才,艺术鉴赏也不时显示出蹩脚的外行特征,但他在哲学思辨的领域对近代人类的思索却无疑具有《浮士德》式的划时代革命。康德在近代文化史上第一次鲜明地划分了自在之物即超验的形而上的东西与经验世界即我们所置身的现实,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在之物,超验的东西是作为某种假设或某种信仰而存在。康德把神学的存在贬为实际理性的一种假定。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人类却具有自身的主体性。正是从康德这里,近代人猛然意识到:“每一种自愿的活动,都是有理智的品格、纯粹理性的直接结果,人是自由的主动者,不是自然原因链条中的一环。”但自由创造中的人类却又难以摆脱“二律背反”的残酷命运(浮士德不正是这样么),人类理性的终极目的(即道德的目的)只在上帝那里,这样,我们达成自我超越(至善)又是由上帝决定的,这似乎又与歌德的体验有联系。实际上歌德也自知他走上了一条类似于康德的道路。而康德却又在晚年对上帝救赎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
自信力、主体性、创造精神、超越的渴望,这就是所谓的近代精神,而怀疑、困惑、迷茫,又是其中蕴藏着的危机体验。西方近代文化自上完成了对中世纪文化的反拨,自下开启了通往现代文化的道路。在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禁锢中,人的现实生命处于全面的萎缩当中,文艺复兴使人的感性生命复活,新古典时代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又开始了以人为主体的理性精神的重建,而18世纪启蒙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则将这一理性体系推向完善的境界,康德的探索因此也被称作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至此,人确立了自我,信心百倍,似乎时刻蓄积着开天辟地的伟力;但近代文明的进程却又同时日益暴露出不可克服的痼疾,人不断创造着辉煌的文明成就,但人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却又不断在这些创造成果中饱受挫伤和损害。人究竟算个什么,该有怎样的人生理想,人的自我超越又有多大的可能,前途在哪里?敏感的近代人已陷入了迷茫当中,由此也展开了伸向现代文化的思路。
在这条近代精神的发展线索中,歌德的体验和追求上贯康德,下通黑格尔。较之康德,歌德似乎更为开朗、乐观;而歌德的密友席勒则较多地接受了康德的悲观主义,他从“二律背反”中悟出人的“断片”形态。黑格尔比歌德小21岁,他对这位文学大师推崇备至,甚至自称在精神上是歌德的“儿子”。国外许多评论家如卢卡契、考夫曼都注意到了《精神现象学》中,人类历史的发展恰如浮士德式的自我否定、螺旋上升。
黑格尔认为《浮士德》是一部“绝对哲学悲剧”,其主题是“企图在对主体的有限知识与绝对真理的本质和现象的探索这两方面之间的矛盾中找出一种悲剧式的和解。”显然,他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从“正-反-合”命题出发,特别看重的是“和解”,不完善的人消亡了,生命演进的真理永存,“理念”永存。上帝的救赎在这里成了黑格尔维持他那庞大的体系继续运动的助力。在这里,人类文明作为“理念”的体现将永远合情合理地运演下去,扬弃缺陷与片面,趋于全面与永恒。于是,近代精神的危机性体验被巧妙地掩饰了起来,那些迷茫与困惑似乎都获得了一种“辩证”解决!
但这恰恰是黑格尔的庸俗之处,是他对《浮士德》的悲剧作了这种不无庸俗的“和解”。
人类历史一再表明,任何的“和解”都是短暂的、虚幻的、一厢情愿的。《浮士德》的光芒倒来自那些真诚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