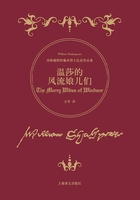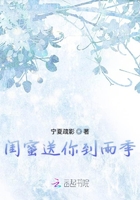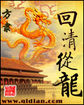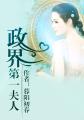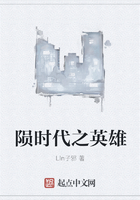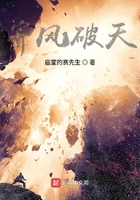提笔写下这篇不得不为之的“小引”,脑子里一片茫然。关于现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我究竟读懂了多少,读懂了些什么,那沉淀于诗中的人生与生命的奥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我所捕获?这是个殊难回答的问题——或许有过行文时短暂的畅快和自得,但一旦停下笔,一旦合上书本,却总是有更多的疑惑和茫然涌上心头。有时想,这样的茫然恐怕得永远伴随着我了,因为我事实上也将永远无法读懂人生、生命以及我自己。鲁迅在《三闲集·怎么写》中曾这样描述独立于浓夜中的自己:“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我的头里是如此地荒芜、浅陋、空虚。”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仿佛对这番体验略有所悟了。
我属于“60年代的人”,这种出身也先天性地将我与荒芜与空虚联系了起来。儿时并不知道什么现代文学(当然也不知道多少中国文学“经典”),我的极其有限的文学阅读经验只能来自那些同样荒芜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和连环画。真正“进入”文学的内在世界则是进大学以后的事了。不知为什么,有一天我忽然对新诗着迷起来,在图书馆里读着一本本的现代诗集,甚至自己也开始在纸上涂抹着。在这期间,谢冕先生应蓝棣之老师之约来北师大讲演,那分明带着“朦胧诗论争”岁月所特有的情绪和在此以后蓝棣之老师本人的同样富有情绪感染力的“现代诗”选修课更是大大地增强了我对诗的兴趣。不过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学术”的意义上解读和研讨中国新诗。
我的“学术”兴趣倒是来自于诗歌之外,来自于王富仁老师那篇著名的《枙呐喊枛枙彷徨枛综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晚在《文学评论》上读到此文时的那种不可遏制的激动。在那里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种真真切切的极具力度的对学术发展所产生的“整体性”影响。(整体性,这词儿到今天似乎又不那么时髦了,但它对我却还是那么亲切。)正是这种“整体性”的思想掀动,让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似的写下了《论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这篇十分粗糙却又洋洋数万言的处女作,并且是半不安半自得地将它送到了王老师面前。初稿苍白可笑得实在难以见人,但我还是十分珍视自己当时行文的勇气,因为正是它定格了我走进学术世界的第一个形象,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似乎勾勒了我学术思维的最粗大的线条。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一个人踏入学术世界的第一形象或许会对他的整个一生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就好像是一位作家的处女作,透过多年以后的成熟来看处女作,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挑出其中的幼稚和简陋,也可以滔滔不绝地描述他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自发到自觉的种种“发展”和“变化”,但是只要你平心静气地细细揣摩,就会分明地觉察出其中那些已由处女之作所显示出来的稳定性的东西,并且这种稳定性的东西并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经过多次修改,这篇《进程》数年后发表于《文学评论》。又过了这么些年,当我回头重读它时,也依然会为其中那些明显的粗疏感到汗颜,只是它的确是我走向新诗的第一个足迹,所以我还是几乎一字不动地将它收在了我的第一本论文集《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之中。
对中国新诗进程的这种过于“宽广”的概括也给我以后的思考留下了许多问题。在这以后,我陆陆续续地写下了《论中国现代新诗的价值取向》、《巴那斯主义与中国现代新诗》、《赋与中国现代新诗》、《对于“后新诗潮”的两种阐释》等文,作为对“中国现代新诗进程”若干细节问题的展开。其中,《论中国现代新诗的价值取向》一文试图跨出流派的界限,从传统-现代的潜在取向上来重新梳理中国新诗的种种选择,《巴那斯主义与中国现代新诗》一文则试图在世界诗歌的潮流冲刷中观察中国新诗的特殊反应。以上这些“细节展开”,都或多或少地在学界有一些反响,不过我自己对它们却似乎有了更多的不满意,尽管在所有这些文章当中都贯穿了我对传统/现代、西方/中国这类“重大问题”的紧张思考,而且这种思考在今天看来也很有必要继续深入,然而我也隐隐发现了自己行文中的一种趋向,有时是有意无意地过分突出了“文化”的鲜明形象,似乎中国现代诗人首先要在思想上解决若干“文化问题”,然后才从事诗歌创作。显然这种假设本身就是大有问题的,文化决定了诗人的选择,但诗人的个体创造本身又构成、充实了“文化”的内涵,文化也依然处于永远的被创造过程当中;对于既有的文化规范而言,恐怕鲜活的富有创造天赋的个体恰恰是最不“驯服”、最难“消化”的东西。扪心自问,或许在理性的意义上我自己也并不承认有过那样的“假设”,但事实上这种行文的趋向却是若隐若现地裸露着,并且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化研究中的类似的思维方式彼此粘连。我认为,在今天如果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走向深入的话,就应该自觉地检讨和反省这种不自觉的思想方法。有人已经将“失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误区,而我感到,以简单的文化概念来代替复杂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失语”的一大表现。稍可宽慰的是我现在对自己过去所可能出现的“失语”趋向开始有所察觉,于是也就禁不住要在这里写出来,既作为自我的警戒,亦是对愿意阅读此书的读者的提示。我盼望着一种“批判性的阅读”,请注意那些较有价值的关于文学现象的具体描述,而不要为另外一些空泛的概念所左右。
较之于这些现代诗史的宏观描述,我自己倒是比较偏爱关于个体作家和具体文学作品的阅读经验。在关于郭沫若、李金发、穆旦、卞之琳、何其芳、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绿原及鲁迅的评述中,我都努力提出过一些与过去不同的看法:关于李金发与中西方诗潮,关于穆旦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的估价,以及关于鲁迅那样并不太好的新诗创作的文化启示等等。我之所以比较偏爱这样的阅读经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更多地是从诗歌作品自身出发得出的结论,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更好地避免了“失语”误区的羁绊,而更是因为正是在这几个地方,尚保留着我对中国新诗与中国文学的那种持久不衰的兴趣和热情,正是这几个地方,牢牢地吸引着我求知与探究的目光。对于李金发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扭曲心态,李金发与中国现代诗人自身的“失语”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展开,而写一部《穆旦评传》,全面追踪中国现代诗坛这一不可多得的奇才,深入开掘穆旦诗歌之于中国20世纪诗歌的重要启示则更是我多年以来的愿望,也正是在鲁迅那些并不像诗却总是别具一格的作品里,我仿佛更进入了“鲁迅式”的文学视野——其实,何止是诗,鲁迅的杂文、小说、戏剧不也同样引起过别人的不适而又难忘的感受么?这是不是说明,鲁迅对文学(文体)的理解,确乎与相当多的(或许是大多数的人)很不一样,这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
关于鲁迅特别是《故事新编》的阅读迄今也是那么的令人难忘。那是1989年的深秋,我所在大学的积极的“支教”运动将我输送到了四川渠县一个不通公路的乡村。每天晚上,我都蜷缩在一张窄小的课桌前阅读鲁迅。外面是深深的夜影,鲁迅的作品是那所乡村学校里最容易找到的东西,在经历了那一年燥热的春夏之后,那是怎样的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与《故事新编》之间,又建立了怎样的一种生命的联系呀!一篇又一篇的阅读之后,我记录下了我一篇又一篇的阅读经验。在浓密的夜色包裹的灯光下,我曾将这些阅读的经验低吟给身边新识的朋友,然后在第二天渡过河去,通过小镇邮局寄往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感谢这段经历,它让我第一次深刻地领悟了文学阅读经验的生动的人生基础。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某些“文抄公”们的自毁声誉的行径),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被许多人看作为一件简单而没有多大意义的工作,而且,与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标准”相适应,我们在今天读到的某些文学批评,它们的整个思想框架也显然是直接取自另外一个更宏大的思想系统。仿佛是为了证明这种思想的合理性,文学作品被随手拈来当做了“例证”,或许这种思维也自有它的意义吧,不过我却始终感到如果文学批评的“思想”不是从作品内“蒸发”而出,那么这样的“思想”恐怕还是得大打折扣的,因为文学批评活动终究是以对文学作品的“感觉”为基础,批评家的意义正在于他能对文学作品提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感觉,最终“思想”是对“感觉”的升华。当然,纯思想的探究是有它自身的价值的,问题在于所谓的“纯思想”并不是我们所误解的纯粹逻辑层面上的推导,它实际上仍然是思想家对世界崭新的、独特的“感受”的升华,只不过可能由于他所感受的对象本身的某种宏观性、抽象性使得对这种“感受”的描述也呈现出了某些“纯粹”的理性的形式,但这与那种纯粹逻辑层面上的语言游戏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作品的鉴赏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低层次”的,它恰恰就是所有文学研究活动最坚实的根基。基于这样的观念,我自己是比较重视作品鉴赏与解读的,尽管我知道自己的领悟力并不甚强。几年来,但凡有师长或朋友“拉差”参加“鉴赏辞典”一类编写,只要作家作品是我愿意阅读的,我一般都参加了,虽然谈不上“乐此不疲”,但至少在“鉴赏”过程中我自己是比较投入的,而且还总是力图捕捉一些新鲜的感受。书中所选的几篇解读文字大体上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像这样的解读最终推动我走进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学中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对新诗艺术的全面把握。我很愿意继续这样的工作!
以上的这些阅读文字,除部分收入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外,均悉数收录于此。在这里我还想特别补充一下《鲁迅旧诗新论》。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现代诗歌”实际上多半都是指“中国现代新诗”,而与之同时,那些大量存在的同样属于“现代”的旧体诗词却被排斥在外了,这固然是出于对新诗“现代精神”的推重,但却不能不说缺少了一种更宽阔更有高度的“视野”。同样作为“现代的”文学现象,旧诗的存在本身就指涉了中国诗人那复杂而微妙的精神世界,何况当绝大多数的新文学作家都在“现代”的领域上兜了一圈之后又纷纷地不约而同地返回了旧诗的境界,这样的“旧诗”也就与“新诗”产生了对话性的关系,旧诗也成了新诗发展的一种有趣的参照。追根溯源下去,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关于中国现代诗人在艺术理想与语言意识上的某些深沉的困惑。关于这方面的成果我集中在了第三部分。当然它们实在是太肤浅了,也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触及现代旧诗词这一庞大的阵营本身,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展开,今天重读之,倒似乎只有这样的句子还在激发着我继续探索的兴趣:“现代中国作家大量创作旧体诗的远非鲁迅一人,众所周知,许多早年慷慨激昂地献身于新诗创作的人最终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旧诗的道路,新文学的开创者、建设者们多少都抛弃了‘首开风气’的成果转而向‘骸骨’认同,这究竟是为什么?”
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有四篇阅读体会是在“被动”中完成的。其中收录于本书的《初期白话诗研究综述》、《穆旦研究综述》是应徐州师院徐瑞岳老师之约所写。另有《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是奉钱理群老师之命在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西安年会上的发言,而《2000: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则是赵园老师布置的任务(这两篇文章已收入我的第一本论文集)。虽然它们仿佛都是“命题作文”,但显然对我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关系,我才迫使自己阅读了大量的关于现代新诗的研究成果。那一段时间,我完全陷入到中国新诗研究的又一重“历史”语境当中。中国人向来有“读史”的传统,认为历史会给我们无穷的智慧,其实,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历史的长河里照一照自己,读一读自己所置身的“历史关系”的世界。看来,这样的一次次“被动”终会成为我以后的“主动”,我们都还有必要不时到历史这条大河里去照一照。
十余年来,由于中文系教学工作的需要,我的部分精力曾分配于西方文学的问题中,应当说,这种“分配”对我自己是颇为有益的。它不断督促我从一个更广阔的方向上来阅读文学,阅读文学的现代,也反过来阅读我们的现代中国文学,在督促中,我写下了《走向文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世纪病”、“多余人”与“孤独者”——中西近现代文学一个基本精神之比较》、《枙浮士德枛的裂痕与近代西方的精神危机》。在专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工作者看来,它们多半是粗疏的,但对我自己的阅读实践而言,却也有着特殊的意味,因此今天我也将它们收录于此了。
回首十余年来自己的阅读经历,1994年我完成的一个课题《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似乎不得不提到。关于它的基本思想我想应当由那本书自身来展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赋与中国现代新诗》一文大致上可以见出我在这一课题上的原初思路。)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出版以后有过种种的评论,师长的提携、朋友的赞赏都是对我的鞭策。不过,有的朋友也从我的书中读出了“弘扬民族传统诗学”这样的思想。平心而论,这倒的确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显而易见,在20世纪的中国,无论是西方诗学还是古典诗学都不可能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法宝”,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只能来自中国现代诗人对20世纪人生的真切的独特的发现和对现代汉语的富有创造性的操作,中国现代诗人个性精神的发展比任何形式的单方面“弘扬”都要有意义得多。但是分明有不止一位的朋友和读者对我的那个课题作了类似的“读解”,这就迫使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我自己所提供的“文本”支持着这样的“读解”,是不是我自己的思想本身亦存在着这样可供“解构”的缝隙?或许是出于一种“自我申辩”的目的吧,我竭力展开自己的下一步工作“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研究”。我试图通过自己的这一番努力向朋友们校正着什么,也借此整理整理自己那不无纷乱的思绪,但是这一新的工作实在太宏大了,或许真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幸好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给了我这样一个整理自己的机会,我也可以趁机将这十余年来文学阅读的一些成果总结面世。一方面,通过这种形式的自我展示,朋友们、读者们不难从中见出我对中国文学现代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尽管它是那样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更是一种有效的自我回顾和自我反省。
我十分珍惜这样的一次自我回顾,虽然回顾本身并没有减少我内心的茫然和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