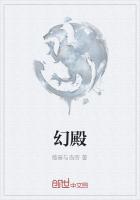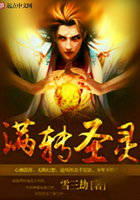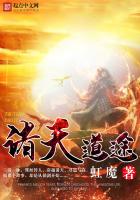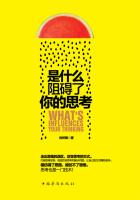我们坐在靠近大伦敦巴尼特区的屋子[32]里,沐浴在上层资产阶级的光芒中——我父亲和我正一起喝着一杯午餐前的酒,讨论着他第一篇发表的小说,《乌干达的圣犀牛》(1932年,当年他十岁)。这时是1972年,他刚过了五十岁的生日。为这一生日,他写了一首诗《献给自己的颂诗》(“今日五十岁了,老家伙?/嗯,也不见得那么糟啊……”)。当时他正处于声名和创造力的高峰期,他和简的婚姻也依旧毫无阴云——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乌干达的圣犀牛》:
——都是常见的那些坏处。尽是些没有分量的用词。比如说:“在炽烈蒸腾着的热气中,咆哮着,诅咒着……”
——这有什么不对的?我是说,我知道这挺老套的……
——你不能那样子连着用三个“着”。
——是吗?
——不行。应该是这样的:“在无法忍受的热气中,咆哮着,诅咒着……”
你不能那样子连着用三个“着”。有时候你还不能连着用两个。好多表示名词的后缀也同样,前缀也是如此。
吃过午饭,我上自己的房间待上几个小时,写一篇我打算投稿出版的小说。后来,喝晚餐前的酒的时候,我说,
“我把我在写的书过了一遍。猜我发现了什么。原来是首打油诗啊。”
“肯定不是那样的。”
“是的。就是‘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的那种。像是童谣。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你言过其实了。”
我说的是真话,但我又把小说修改了一遍:把所有这些前缀后缀都好好修理了一遍。
这是他给我的唯一一点有关文学创作的建议。当然啰,他也从来没有表达过让我追求文学生涯的愿望,尽管所有迹象都表明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以前我以为他完全是出于懒惰,不过现在想来他只是遵循父亲的直觉,而且是良好的直觉。五年之后,我做《新政治家周刊》文学编辑的时候,有一位知名作家带着儿子上我的办公室来。我得到的解释是,那男孩(大概十七岁吧?)写诗,父亲希望我能看看,或许能挑上一两首刊登。我比这位诗人大了十岁。我理解他。不过,当时我马上指出来,没有哪个用英语写作的在二十岁之前出过什么成绩(连可怜的汤玛斯·查特顿[33]也算不上。那位出色的男孩,经历了早年的成功后,穷困潦倒,十七岁那年,服用砒霜自杀)。知名作家彬彬有礼地坚持着。我想着,好吧,也是有可能的:兰波写《醉舟》的时候,也就那年龄。我读了那位儿子的诗。我寄回了给他,附上一信说,我认为这些诗都大有潜力,(同样真诚地)我会很乐意关注他之后的写作……
在文艺领域,如果父母邀请孩子紧随其后——这是件挺复杂的事,总会让人觉得有点儿自大自恋在作怪。倘若孩子应诺了,算不算是对父亲的馈赠的致意?纵观历史,要兑现诺言的几率太低啊。有特罗勒普夫人也有安东尼·特罗勒普,有大仲马也有小仲马,也就这么几个了。通常是这样的,孩子能写上一阵子,接着超越父母的竞争心就淡了。我认为文学的天赋有极强的遗传性。但写作的毅力没有遗传性。
过了没多久,我听说知名作家和诗人儿子闹翻了。这是长久龃龉的开端。儿子寄给我的最后一首诗是有关父亲的:一篇稍稍隔成了诗行的檄文。
我难以想象我的成年生活会是怎样,如果我和金斯利之间发生这样的冲突。促成文学志向的背后,暗昏昏的,看不清楚——对过去的怀恋,酸涩的孤独。而且在父子之间的事已经够多了。金斯利声称他喜欢我的第一部小说,却说“看不下去”第二部,当即我就感觉到了被拧了一把的疼痛。但事实是如此:任何的文学问题,他都没法模棱两可或闪烁其词,这一点我是了解的。而且,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睛里有着几乎是恳求的神色……(他也不喜欢纳博科夫,其实除了安东尼·鲍威尔[34],他谁都不喜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过不少激烈的争辩,也狠狠吵过架,但没有哪一次不是到了第二天就云过风轻的。唯有一次,我快到三十岁的时候,想过要和金斯利冷战一番。金斯利是这么粗鲁地评论那位我爱上的姑娘(出于对我的前任女友的喜爱)。“你觉得她怎么样?”把她介绍给金斯利的第二天,我在电话上问他,等着听到一长段像模像样的赞美——一首十四行诗,或是一首赞美诗。“我不介意你带她来家里,”他说,“如果这是你想知道的。”[35]我的不快升级了。有那么几秒钟,与金斯利的裂痕似乎挺浪漫挺吸引人的,像是黎明时分的一场决斗。我记得咂摸着这种滋味,这种冷冰冰的滋味。随后,我像吐痰似的,把它咳了出来。咳咳,啊呸!再加上个念头:可千万别再那么想了。我快三十了,他离六十也不远了。我们都到了关键的年龄,很快会以更复杂的方式需要对方。我父亲从来不鼓励我写作,从来不邀请我追求那遥不可及的事。[36]他表扬我的次数要比公开批评我的次数少,但效果不错。
对我自己的孩子,我打算更多一些赞美。虽然我要比金斯利更喜欢作家的生活——每一天过的日子,我不会鼓励他们。不会。绝对不会。
1973年11月中旬,“打油诗”对话的十五个月之后,那部处女作即将出版。[37]小说出版的整件事都平静极了。如今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没有访谈,没有朗读会,没有拍照推介。而且,也没有新书出版庆祝会——或者说,没有出版社的新书出版庆祝会。没错,这是第一部小说,不过,等我第二部小说出版的时候也没有,第三部也没有。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的。少数人感兴趣的领域。一切静悄悄的。
那时,1973年,没有正式的庆祝会——我打着这些字的时刻,几乎正好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同一个时刻。不过我还算是有过庆祝会的。[38]我和罗伯及其女友奥莉薇亚一起住在一座漂亮的小屋子里。我买不起,而罗伯把一整笔的小额遗产付了租契,她也买不起。这个安排很快就崩了:不到一两个月,我发现自己在伯爵宫区[39]积了厚厚灰尘的小房间里。不过,那天晚上,我们过得开心极了。我哥哥菲利普带来了一大瓶的威士忌。妹妹也在,父亲也在。我记得他走上楼梯,跨入客厅时,眼里闪烁着期盼的光芒(任何做客的机会,他都会期盼,带着孩童般的热切。我想,这是他孩童时代、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也没有兄弟姐妹相伴的结果)。金斯利的老朋友,研究苏联的专家和诗人罗伯特·康奎斯特[40]也在。克里斯托弗·希钦斯[41]也在。他英俊,会玩会闹,左派的那种消瘦。克莱夫·詹姆斯[42]也在。他有着骑车者的身型,蓄着胡子和头发。他从澳大利亚过来还没多久,到了这座文字之城,都“兴奋得发狂了”(就像贝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人物查理·希特林一样)。
我能告诉你什么呢?那是七十年代,笑话百出的年代。克莱夫穿着低腰牛仔裤和猎装,希区[43]大概穿着令人褒贬不一的打着补丁的牛仔裤,扭曲的拉链右侧有一坨污渍,就像是一个沉闷的主权国(我记得他是在莫斯科讨价还价淘来的,也可能是用了这个方法脱手的)。我和罗伯一样,几乎可以肯定是穿着一件尖领的花衬衫和绿色的丝绒喇叭裤,还是经过压皱处理的丝绒,没磨光的那几块发出一种病态的光泽。连金斯利的裤脚都大了一两寸。现在看来,那十年,我们都蠢到会穿喇叭裤,居然还能写出些有意思的字,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那天晚上,罗伯和奥莉薇亚送了我一件蓝色的T恤,上面用紫色的大写字母印着我的书名。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我都穿着那件衣服。小小的电视上,立着一本我的书。
聚会大概在四五点钟之间结束,像是败军溃退,乱得令人目瞪口呆。第二天碰到一起吃中饭的那几个看起来像是《星球大战》中星际非法售酒沙龙场景中的群众演员(这电视剧要等四年之后才会出现,是未来的事)。那天晚上,开始了几段新的浪漫故事。比如希钦和我妹妹萨丽去了附近的旅店。黎明时分,罗伯和奥莉薇亚一起上楼去睡觉,我独自去楼下的床上睡觉。我无爱可谈。事实上,我似乎连一个女朋友都找不到。我至今还时不时在梦中唤起那段相对短暂的时光:梦中的感觉充满了孤单隔绝,无人牵挂——自然啰,还有觉得自己毫无魅力。彻头彻尾的毫无魅力。你身边没有一个姑娘的话,你会开始厌恶自己,这变化快得令人吃惊。而且,这消息马上四处传遍,也快得令人吃惊:你碰上的每个女人似乎都知道了这一点……一切最终会有所改善——后来发生的事即使在那个年代,也完全称得上引人瞩目。1974年早夏,我也会去附近的那家旅店,和十来岁的姑娘蒂娜·布朗还有她的父母喝茶。这是我第一次被介绍给她的父母,他们彬彬有礼地探问着我的底细。不过,我还得度过在伯爵府区的那段日子,没有姑娘的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份。
“把头发剃了,”金斯利紧追不舍地说,“把头发剃了。”
房间里没有其他的人,但他不是告诉我把头发剃了。这些年来,金斯利已经说过一万两千遍把头发剃了的话。但他不是告诉我把头发剃了。这一年是1984年。我刚和一位叫安东尼娅·菲利普斯的美国学者结了婚,孩子快要出生。我没必要去把头发剃了。
“把头发剃了……把头发剃了。”
这是给电视机的建议。具体点说,每次琳达·汉密尔顿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她都会得到这条建议。我们正(又一遍地)在看《终结者》的录像带。金斯利是科幻小说的老行家,是《终结者》的大粉丝。七年之后,我带他去西区大理石拱门那一带的一家影院看《终结者2》,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钦慕之心(称之为“完美的杰作”)。
“把头发剃了……把头发剃了。”
在《终结者2》(1991)中,琳达·汉密尔顿把头发扎在头顶或者脑后。但在《终结者》里,她满额头堆着鬃毛,1984年那会儿,人们都是那个模样。
“把头发剃了……把头发剃了。”
“我希望你会坚持不懈,我说老爸。要有谁说你无聊唠叨,你可不会泄气让步哦。”
“把头发剃了……把头发剃了。”
“可能会有谁指出来,这部电影早已经拍好了。即使琳达·汉密尔顿能听得到你,即使她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她也没法儿回去把头发给剃了呀。”
“把头发剃了……把头发剃了。”
“不过,可别听他们说的,老爸。你已经表明立场了。这下轮到你坚持下去不退却了。”
“把头发剃了……把头发剃了。”
过了一会儿,激烈的打斗开始了,而且很明显琳达·汉密尔顿不会有时间也没空闲去把头发给剃了,金斯利就不再告诉她把头发剃了。
1980年12月,简离开了金斯利。这差不多是四年前的事了,还没有其他人出现。我打算离开的时候,说道:
“爸爸,你到底怎么样啊?”
“哦,还行吧……但你知道的,没有女人的人生只好说是活了一半。”
“真是这样?”
听到他这么说,我挺吃惊的,又有点儿高兴。这话听起来宽容厚道,不像他,之前我一直觉得他常年都是怨恨不已的。长长一段时间里的种种让他生出的怨恨,不是表现在他的举止或是言谈中。而是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再明显不过了,特别是反浪漫的转折,从《杰依克的东西》(1978)一直到《斯丹利和女人》(1984)。这一些年的作品中,似乎把那一方面的希望、连令人安慰的记忆都一并摒弃了。我不是把作家和作品合二为一,犯下这一基本的错误,但所有作家都知道,真相就是在虚构的小说中,精神的温度计能在这里测出读数。金斯利在那段时间的小说在我看来,道德上处于退缩状态。他像是关闭了一整个维度——那个有女人和爱情的维度。所以,令我吃惊的不是他的这种说法(我知道说法本身一点不错,活了一半的人生远远不够),而是这话是从他嘴中道出:
“真是这样?”
“千真万确。”他说道,扭过了头去。
此后,金斯利余下的人生中不再有浪漫的爱,但爱又回到了他的小说中。《老魔怪》(1986)中宽恕的爱,《你不能两者兼得》(1994)中怀旧的爱,《俄罗斯姑娘》(1992)中坚定的甚至是强劲的爱。在《杰依克的东西》中,他让男主人公宣称:
她们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不是一回事,她们用语言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延伸自己的性情,她们把所有的不同意见都视作是针锋相对,确实是这样,连她们中最聪明的也不例外,寻求真理至此也就到头了,哪怕谈论本身就是为了寻求真理。
在《斯丹利和女人》中的酒吧氛围里,我们得到如下对女性的表述,“违背常识、仪态、公道、真理等等,不一而足”(说这些话的是一个叫伯特的中流电影制片人。至少对他醉醺醺的腔调的嘲讽,效果不错):
你可以灌她些那个药,叫什么来着,对了,东莨菪碱,你可以把她上足了那操蛋的东莨菪碱,她还继续会否认……她是……她是个前操后肏的东西,就是那样儿。该收起来藏好。可是为了保护她自己啊。
所有这些调子都变了(我知道背后的原因)。在他七十岁写的《俄罗斯姑娘》中,爱情被提升到不仅超越了政治,而且极其令人吃惊的是,还超越了诗歌[44],超越了真理。
在《杰依克的东西》和《斯丹利和女人》两书中四处渗透着对女性的批评,可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趣味,不着调(两本小说都充满着邪恶的生机)。也不能这么总结:听着,女人对真理的态度正好由男人的习惯来平衡(女人写的成千上万本小说中探索了这一点);后者的言谈举止一贯的正确,富有权威性。我反对这两部小说的原因要简单得多:我能感觉到爸爸的拇指摁在秤砣上。T.S.艾略特建议文学是“非个人化”的用词。我觉得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诺斯罗普·弗莱对这一说法作了改进。他说,文学是“不带偏见”的用词:你不能在写作中夹带私货。而金斯利是有偏见的。他是为了报复爱情和女人,报复简。
他一向都知道怎么做才更好,后来又会做得更好了。早年写的一首题名为《书店田园诗》的诗中,有个和他本人相近的角色随意地在翻阅一本从诗歌架上拿下来的一卷“薄薄的诗集”:
和所有的陌生人一样,它们以性别来分:
《帕尔玛的风景》
让男人感兴趣,还有《双漩涡》
还有《里尔克和佛陀》。
“看,我旅行”,“我思考”,“我读书”
这些题目像是在说;
可是《我记得你》,《爱情是我的信条》,
《写给J.的诗》
女士们的选择,让我的喋喋不休黯然逊色……
诗人是应该给人类的心灵打气
还是将之使劲压压碾平?
男人的爱情和男人的生活完全是两回事;
而姑娘却觉得那样子不行。
我们男人掂量好爱情的重量;没了爱情
我们的日子还照样过。
女人似乎不觉得那样其实也行;
非要拿笔来涂涂抹抹,
她们写的诗呀坦露了她们的心声
却打动不了他们。
女人其实要比男人温柔多萌:
难怪我们喜欢上她们。
明白了这一点,就能忘了那些时光:
呆呆坐到夜半
胸口呛满了爱,塞足了五彩的念头,
还有名字和诗行,
却一字不能落在纸上。
诗写得再机智谐趣,技巧高明,这也是一首年轻人的诗。在最后一节里,我们感受到了对男性不足之处的遗憾,但我们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很快就会坦然接受。[45]男人无法在情感的高峰期写作。情感必须是华兹华斯所说的在“平静中回忆起来”。而另一方面,《书店田园诗》暗示了写作最终也因此变得更好,更精确、更具权威性,也更有其它(男性)的优点……现在读来,让我吃惊也让我感兴趣的是诗中用口语体引用拜伦的诗行:“而姑娘却觉得那样子不行。”替代了拜伦原诗中的“这是女人的全部生命存在”。或许,这首诗也暗示了反过来可能也说得通:女人的生活和女人的爱情完全是两回事,而小伙子却觉得那样子不行。艺术是男人的全部生命存在,至少试图如此。对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诗人来说,可能确实是这样子的。不过,到了六十来岁,当他不再有女人的爱情,他承认留下来的是:一半的生活。
听爸爸讲那事儿
五十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夏日下午,在南威尔士的斯旺西,我母亲告诉两个儿子去书房见父亲,他有话要说。金斯利在他的《回忆录》的开头不久写到此事:
菲利普和马丁走了进来,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极其天真……我想他们一个七岁,一个六岁。随后我脑中的简短独白就溜了出来,尽管我知道我用了一堆生理解剖术语,也可能用了很多次“东西”一词,提了父亲播下一颗种子。要不然,你能说什么呢?他们听我说完,平静而严肃,我从未比那一刻更加喜爱敬佩他们。我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我知道他们知道,可这有什么要紧呢。他们默默地离开了,而且体贴地继续沉默着,直到我不再能听到他们的声响……没有哪一处能更正确地说明什么叫“必言不必言之事”。
后来也有过一次介绍,那次少了点解剖术语。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正专心致志地玩着弹球机——地点换到了西班牙,我的年龄也增长到了十二岁。哥哥走过来说了一句:“快点,马特。爸爸要和我们讲那事儿了。”我玩得再起劲,也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了。我们坐在饭店的桌前,一言不发地听着……五岁那年,在湿漉漉的学校操场,我已经听过一个朋友介绍生命的真相。我当时的反应是:我妈绝不会让我爸干那事的——这王八蛋。我敢说这反应挺普遍的。不过,1962年,在西班牙,我听完后,满心喜悦的想法和感觉:我爸和我妈相爱,我、我哥和我妹都是爱的结晶……我们全家去马略卡岛旅行十天,正开车搭船回程。那次我们是住在罗伯特·格雷夫斯[46]的旅店里。我们从巴塞罗那往北开的时候,汽车开始出现严重的故障:十三岁的生日,我高高兴兴地帮着把汽车推上了比利牛斯山。六个星期之后,金斯利遇上了伊丽莎白·简·霍华德。[47]到了第二年夏天,他的婚姻结束了。在此之前,父亲没有停止过爱我的母亲;在此之后,也没有停止过爱我的母亲。然后,就像在《书信集》里明确表现的那样,简·霍华德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
“一个男人若没有永久地受到从父亲那儿听来的性理论的影响,他就是个罕见的聪明人……”索尔·贝娄在《银盘》(这是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中写道。在我们十五六岁的时候,金斯利继续用浪漫爱情的格言警句来哄骗我们。“一个裸身女人最吸引人的部位是她的脸蛋,”他说。这听起来还挺不错的。但最不招人待见的是这句话:“爱情极大程度上放大了性的生理快感。”哦,那才是你追求爱情的原因:为了性。菲利普与我和我们同龄的大多男孩一样大大咧咧精力充沛。不过,要是我们有耐心去经历“真事儿”,我们也就不会是我爸的儿子了。我十六岁时,看了打字稿的《反死亡同盟》(1966)。有两句简短的句子让我迷醉不已。之前没有被爱过的女主人公被男主人公吸引,感受到心中的涌动,问自己:“是现在吗?是你吗?”然后,过了一阵子,两句没有出声的答案:“就是现在。就是你。”我一直问自己这两个问题,一直盼望着听到那两个答案。
1973年11月,除此之外,我过得怎样呢?
落在纸上的生活看起来挺不错——事实上,落在纸上的几乎也就是我经历的生活。
第一部小说的出版花了很长时间。等出版时,接下来的一部我已经写了一半。我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有份全职的编辑工作。[48]我替《文学增刊》还有别的刊物写评论和文章。《新政治家周刊》11月第23期书刊版的开篇是我写的一千五百字书评,评论约翰·凯里[49]的狄更斯研究著作《暴力的肖像》。一个星期之前,也是过早出现了一个星期,书评版是以彼得·普林斯的五百字书评结束(是三篇书评中的最后一篇),评论的是《雷切尔文件》。书评现在[50]就摆在我的面前,只有几处,我不甚赞同。
一位写了第一部作品的年轻小说家被认定是写他自己的意识,但普林斯先生看不到其中的讥讽和艺术化。我的叙述者说些“肉麻风趣的小话”和“故作惊人的小话”,而我与我的叙述者之间毫无区别。不过,就奥斯力克要素(“早慧的,瞧不上高中课程的,中产特权加上凭成绩考大学的”)还有盲从的性别歧视来看,他说对了一半。这是我见到过的书评中最坏的一篇。其他每个人都表现得相当宽容,有几位还表现了宠溺。[51]他们似乎觉得从我父亲的背后迈出来,一定特别的艰难,其实不是,他的影子成了一种保护。而且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感。成了一名作家,这是挺奇怪的意外,可是,这对你来说,又没有什么比这更普通不过的了,因为这是你爸整天在做的事。因为,作为作家的痛苦,或许也有些乐趣,对我来说,也变得不那么新鲜了。不过是些例行公事。那时,我非常努力,使足了劲,而我能做的至少也就这些了。
再说了,我仍旧觉得自己像是个学生。《文学增刊》像是座图书馆,和文学编辑开会像是在上研讨课,而我的文章就像是每周的论文。伯爵府区那个大宅子改建的公寓,空空旷旷,地面光着没有地毯,尘土飞卷,住在那儿让我觉得像是个学生。我的衣服,特别是那件工人服似的外套,让我觉得像是个学生。一个人的晚餐,一杯接一杯的速溶咖啡,让我觉得像是个学生。我一阵阵犯的头痛和面部神经痛(还有余留的一点皮脂腺分泌过多的皮肤)[52]让我觉得像是个学生。我绕着转的那个姑娘道德高洁,或者根本是毫不在意,令我徒然耗神(只能亲个嘴,没有更进一步的了),让我觉得像是个学生。与此同时,成人世界中的提拔、垂青在我看来仍旧陌生而可怕,虽说我自己正慢慢地朝此爬去。目前种种的迹象再明显,也仍旧会疑心自己不但会失败,而且还一败涂地。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念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也有过:我们把这种念头叫做“流浪汉恐惧”。在伯爵府这一区里,多的是流浪汉、醉汉、叫花子、话也说不清的人。在那幢公寓楼里,有个老医生,快退休了。他晚上有时候会敞着门,我能看到他倒在塑料布铺的厨房台子上,身旁是一只雪利酒的酒瓶,有时是穿着没有腰带的睡袍和难以置信的前裆呈Y形的内裤(深灰色,裤裆处毫无形状地晃荡着),趔趔趄趄地挥着手臂……
那年我二十四岁,而这就是我的状态:假装啥都明白,其实什么都不懂;假装啥都确定无疑,其实内心总是惶惑不安。我觉得像是个学生,又没有爱情。幸好另有个世界,一个我自觉能够控制命令的世界——那就是小说。而对此,我自此一直都深爱不移。
1973年的圣诞期间,某种经历进入了我的人生,并且长久地驻留在我的无意识世界中,在现在看来,“经历”呈现的形式是让我熟悉了无边无际的恐惧。在漫长的回顾中,这次偶发事故让我意识到连小说也是不可控的。你可能认为自己能控制小说。你可能觉得自己能控制小说。其实并没有。
但在我们面对“经历”——那个令人痛苦的敌人——之前,让我们再多一点天真,再多一点儿。
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1949—),诗人、新闻人、评论家,曾任牛津大学的诗歌教授。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小说家,曾以《终结的感觉》获得2011年布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