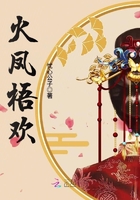中国两部书——《大易》与《春秋》(《公羊传》),绝不能自己看。你们听一遍后,将来老年回头看,就可以讲学。
不知《大易》与《春秋》,就不知中国文化。《大易》由隐之显,由体而用;《春秋》由显之隐,由用而体。天天于日常行事上,显;返回我们的性,隐,微。“克己复礼”,由人之道(诚之者),至天之道(诚),至天人境界(天人合一),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
元,含乾元、坤元,“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坤顺承天,“至”,乃一点距离也没,乾元有多高,坤元就达到那般高;坤元就是乾元,乾元就是坤元。
人虽性善,但易受外诱之私。年轻荒唐,而立之年体悟,克己复礼,亦即复性,即由人事之用返回道(体),“率性之谓道”。《大易》讲生生之道,是体,生生之谓易;《春秋》一切采之于礼,是用,《春秋》为礼义之大宗。
生生之谓易,生生就是仁。礼义即中,仁之用也,生之用也。礼义,中之用,《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国,礼义之国,以礼义作为标准,一切裁之以礼义。“礼之用,和为贵”,礼以和为本,“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太和。
《春秋》别嫌疑、明是非,而最难的是辨是非。孔子删《书》,《尚书》以《甘誓》作为划分,之前为法(以尧舜为始,王制之道为法),之后为戒(“至禹而德衰”的证明,乱制之道为戒),有所立义,一般人不讲,但今文家很重视此篇。甘之战,首反乱制之战,存此篇意义深长,天不佑扈,他这一败,几千年家天下乃起,天民尽制于鸟兽之群。《淮南子·齐俗训》云“有扈氏为义而亡”。
乱制之下人民受苦,应起而拨乱反正,孔子乃删《诗》《书》、订《礼》《乐》,其修《春秋》必有所为。故《尚书》与《春秋》相表里。《五经》皆相表里。
《春秋》讲思想,思想难以毁。“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即指《春秋》。《春秋繁露》(以下简称《繁露》)、子书讲术。
孔子修《春秋》,与历史不同,“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离娄下》),是借事寄义,皆为况,是经。“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在史实之外,另立新义,后人称《春秋》为经。
孔子修《春秋》,在未修之前必有一部“不修《春秋》”,以之作为依据;“其事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修《春秋》后,史实无变,“义则丘窃取之”,成为修的《春秋》。
按己意写史,往往难为人接受,与史实距离远,乃有爱史实者按史实传之,故有“不修《春秋》”。《左传》为保存真的历史,又称“不修《春秋》”,以《春秋》为史。《左传》作者左丘明,与孔子为同时代人,以孔子修《春秋》为索隐行怪,为了保存《春秋》史实,保存历史原貌,故详于事。自《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以及《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看出,孔子有两个崇敬的人:左丘明、老彭。
《春秋》有三传:《公羊传》《穀梁传》重义,《左传》重事。《公羊传》,修的《春秋》,继孔子之义,微言大义在其中。修的《春秋》称经,重义者为经。
读书要了解义,才有趣。过目成诵,皆不成器。哪个成功者是天才?要下功夫。
《穀梁传》在《公羊传》之后,与《公羊传》颇有近似之义。《春秋》三传,经皆同,均为口说,其后方笔之于书成传。传,谓解说经义者也。
今古文之争,专制时代以为是“文字”不同,实则为“思想”之争。伪古文,乃汉后为维护帝制的文人造出的。今文家一抬头,就起革命。
“公羊学”讲的是思想,要重思想演变的程序。思想影响一个人极重要,用智慧启发智慧,找出一条可行之路。读“公羊学”必要勤,不然读不下去。
“《公羊》由子夏口授,传之孔子,故圣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传焉”,《公羊》传授即师承。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东汉何休(129—182)注。何注并不难,必要耐心地读。但注中有些讲乱制,要勾去。
伏生(即伏胜,口述《尚书》,诸儒以汉隶录之,故所传曰《今文尚书》),今文家祖师。何注必要细看。《说苑》《白虎通论》《新序》皆汉初文,与何休的笔法同。汉用《春秋》决狱,影响最大,所以汉儒的书,如《新序》《论衡》也要看,以树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春秋》纬多与公羊说比附”,故熊十力(1885—1968)以纬书得今文家说为多。
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七经纬,即《易纬》《尚书纬》《诗纬》《礼纬》《春秋纬》《乐纬》《孝经纬》的统称,篇目极多。
《论语谶》,共八篇。在汉代,《论语》和《孝经》本不属于经类,而属于“传、记”类,地位低于《五经》,所以不列入经典。但它记录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儒家书籍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也为它造了纬书,因为不是经,所以不能称纬,而称谶。
汉时是谶纬之学最兴盛,尤以西汉末年及东汉末年为盛。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对儒家传统经学有了全新的解释,谶纬之书渐遭毁禁。至宋后,谶纬学说更是式微,其书籍文献多散失不传。
清代陈立(1809—1869),凌曙学生,其《公羊义疏》讲考据,微言大义少。
陈立少时客居扬州,师事凌曙,博稽载籍,凡唐以前《公羊》大义,及清代以来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选精择详,草创三十年,书写成长编的巨作,当他南归后乃整理排比,融会贯通,撰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清史·儒林传下》称此书“渊雅典硕,大抵考订服制、典礼及声音、训诂为多”。陈以汉学手段治《公羊》,此乃乾嘉以来汉学之门径。
清人到处抄书,材料丰富,太平时代写了很多本子,有时还没说出哪个对,大杂烩也。
熊十力讲的是智慧之学,陈立疏缺少微言大义。旧社会,师说不笔之于书,怕祸灭九族。
清中叶,常州公羊学兴,以常州人庄存与(1719—1788)、庄述祖(1751—1816)、庄绶甲(1774—1828)、庄述祖外甥刘逢禄(1776—1829)及宋翔凤(1779—1860)为代表。清代公羊学复兴,肇始于庄存与,有《春秋正辞》十一卷、《春秋要指》一卷及《春秋举例》一卷,犹存乱制,但隐藏微言大义。庄存与今文家东西没能完全把持住,刘逢禄较好,著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以下简称《何氏释例》)三十卷、《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后录》(以下简称《后录》)六卷、《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及《答难》二卷。
刘逢禄以《春秋公羊传》诠释《五经》要义,将公羊学扩及今文经学的全面研究,对当时及清末学术界起了莫大的效应。其《公羊何氏释例》云:“故不明《春秋》,不可与言《五经》。《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刘氏将《五经》之要义与公羊学相互参证,实为清末公羊学的肇端所在。
凌曙(1775—1829)问学于刘逢禄,著有《春秋公羊礼疏》《春秋公羊礼说》《春秋公羊问答》及《春秋繁露注》等。
凌曙之学,本于《礼》及《春秋》,首创将公羊义例引入礼学之中,以公羊学诠释《五经》,远承董仲舒阐扬公羊义理的精神,再振董氏以《公羊》援经议政。其《公羊礼说》《公羊礼疏》《公羊问答》《四书典故核》《群书答问》皆以公羊学的精神来阐发礼义之要旨。尤其《春秋繁露注》更开启研究公羊学的另一扇门径,梁启超谓“晓楼传庄、刘之学,谙熟公羊家法,故所注独出冠时”。
孔广森(1752—1786)著有《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经学卮言》等,其《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以下简称《通义》)十一卷,毛病多。
孔广森受业于戴震,从庄存与习《公羊》,又心仪郑玄,名其书房“仪郑堂”,颇致力于训诂考据,从而以朴学解释《公羊》,开启清末公羊学者以《孟子》释《公羊》的先声。
清儒读书多半好古,讲许多例,但不讲微言大义。
清末说经较为客观、平整的是皮锡瑞,有《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其《经学通论》有关《春秋》部分为师说,但有不同。《经学历史》可暂时不看。
皮锡瑞因景仰西汉初年传授《尚书》的伏生,故名其书斋曰“师伏堂”,学者称其“师伏先生”。皮氏以为尊孔必先明经,谓“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订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
陈柱(1890—1944),唐文治的门生,著《公羊家哲学》,纳公羊大义为十五目,但太简。
民国以来,皆有目的地讲今文学。讲学有目的就低,学术本身是无所不包的。廖平(1852—1932)自谓:“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其讲学有目的。号六易。康南海(1858—1927)有目的地讲学,借古书发挥己志,假孔子之名,行自己的主张。臆说,成己之私见,不算学问。梁启超(1873—1929)论《春秋》部分,犹能守一点家法。
要用智慧看中国东西,不同于迷信式。
熊十力《读经示要》(1945)有关《春秋》部分要看,所论高于今文家。《原儒》是1956年在上海时所写,与前书的观点不同,如以董子讲乱制之学。
熊十力《读经示要》以“西汉《公羊》之学,董氏为盛……东汉人又重胡母生之学……何休作《解诂》,虽云依胡母生条例,而义据亦大同《春秋繁露》,故治《春秋》者,当本之董何……使两汉无董何,则《公羊》之学遂绝,而《春秋》一经之本义,终不得明于后世矣”。
《原儒·绪言》谓:“六经皆被汉人改窜……汉武与董仲舒定孔子为一尊,实则其所尊者非真孔学,乃以禄利诱一世之儒生,尽力发扬封建思想与拥护君主统治之邪说,而托于孔子,以便号召。”
《春秋》用殷历,值元述志。
孔子志在《春秋》,故《春秋》之志即孔子之志。《礼记·学记》云:“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此志,乃祖师爷之志,即孔子之志。“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义,乃孔子之义。“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繁露·俞序》),注意“吾”字,孔子用《春秋》之义表其志。
古书难懂,因历代皆有改经以合其时代思想,如宋儒之改经,故经书的真面目难求。
在专政政体下,往往以“今不如古”,净神化古人,此为愚民政策的第一招,使那时代的人亦步亦趋学古人,而失去了自我。
孔子思想,“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配合“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正与“愚民政策”相反。“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父母的好坏,并不影响子女的纯正,有其存在的价值。封建思想异于孔子思想,故要拨乱反正。
改革社会,要不惧恶势力。英雄怕太太,此外谁也不怕。不要找事,但有事不要怕事,得行正走正。怎么树威?抓住理不让人,但不打乱仗。事来不躲,得面对之,解决之。问题永远躲不了,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愈怕事,人愈欺你。骂人,也要有机术。
要养成群德,花好亦需绿叶扶。吃小亏能树誉,有容人之量。理事,脑子要灵活。
《春秋》讲“拨乱反正”。拨乱反正,“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正名,必有其名,然后再下功夫。索隐行怪,标新立异,均不能成事。不必求创新,纠正社会既有的就足矣。
正,王道也,中国倡王道,“王,天下所归往”,即归往之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霸必有国大,霸者难永存,因为有敌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王者无敌,“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尧舜为王道,政治上的模范,“仲尼祖述尧舜”(《中庸》);“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亦讲王道。
讲王道,必有王制,《礼记》、子书均提及,但都与乱制混了。孔子倡王道,讲王制,是新王之制,公天下之制;有别于旧王之制,家天下之制。王制与乱制,相对。
“文家尊尊,质家亲亲”(何休语),尊则笑贫不笑娼,怎能不忘本?文,饰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亲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是有理智的,由近及远。周尚文,殷尚质;《春秋》则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此周、殷,皆况。
为文,必须考虑别人能看懂否,不是要保存。我看书,必了解了,再批评。有志,空的不行,自己必得升华。读上三年书,应自己能读书了。
我在屋中读五十年书,除孙女外,谁都不应付。
以蒋庆《公羊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作入门,但并非金科玉律,我订正很多。作者年轻,至少没走错路,有厚望焉。
做学人、文化的领导人,必要脚踏实地读书,先把自己点亮了。中国人都应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绝不能兼差,还得智慧不错的。医书比经书还难,今天中医的针灸、麻醉震惊全世界!
真想做学人,得自己真读书,我也帮不了忙。修业,就是修,才有学问。学、习、修:学而时习之,学了就习。但仍有偏差,必要修之。天天学习,但结果有别。不论好什么,也得修。
“率性之谓道”,根据标准修一修,懂标准——性,就知怎么修。修,去掉没用的、不合标准的。修史,历史是一阶段一阶段的记录,把与大道无关者去之。“修道之谓教”,教(jiào)为名词,教育;动词,教(jiāo)人,传也。学、习、修的原动力,在传。学什么,都有一定的理路。理路必要清楚,否则怎么走路?传,也分很多层次。传承、传习、传统。
传承,我传的是什么?你们承的是什么?传学,承学,是专修的那一部分。传习,“传不习乎”?自己干什么不知,岂不是盲人瞎马?我并非有人格,不做狗扯羊皮的事,因为没有用,即使日进斗金,生活也不会改变。传统,你们都得了,是自老祖宗留下,一直演进到今天的。
笔记要整理,否则如杂货铺,最慢明天就要整理。得随时发神经,想到就写。作书,将时时刻刻想的结晶凑在一起。什么也不整理,怎么进步?不勤,绝对不行。如听戏,台上三秒钟,可是台下十年功。我昨天讲《易·屯卦》“六二”,乃前人所无,自《小象》“六二之难,乘刚也”印证的。
在台五十年,如无一个明白的,岂不白忙!写读书报告,才知你们懂否。再怎么乱,最后也得归于平静,这时就看实力、真功夫了。有正确观念了,就知怎么奋斗。女子肯用心,在厨房也能成家,诗、词将心里话说得明明白白,叫人懂。
曾约农(1893—1986,曾国藩嫡系曾孙)有学问,但不讲学。孔德成(1920—2008)两个老师:丁鼎丞(1874—1954)与李炳南(1891—1986)。
孔家正统随宋室南渡,在衢州(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康熙帝分南、北二宗,因不能打祖宗的脸,多花点钱成立二宗,此即“干祖之蛊”,补过。此乃人生要道。我到曲阜住一周,深思熟虑怎么解决问题。
我这支是太祖嫡子礼烈亲王代善(1583—1648)之后,正红旗。人要自觉才能成才,我“长白又一村”。想怎么样没用,得怎么样才有用。
“学”与“统”有何区别?通人,承统;专学,承学。有《学统》一书,可以参考。《春秋》讲一统,又称“元经”。重视根,本是同根生。代代相承文化的责任,所以“素王”比“时王”尊贵得多。
文王,何休注“法其生,不法其死”,人人皆为活文王(周文王为死文王,谥号)。《论语》“文没在兹”,每个人都有“文”,即性之用,亦即“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文道,“纯亦不已”(《中庸》),行健不已;武道,“止戈为武”(《说文》),“全敌”(见《孙子兵法·谋攻》全国、全军之说),“聪明睿智,神武不杀”(《易经·系辞上传》:“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武,止戈,研究怎么不动武。一统,元统。用什么可以不发生战争?唯中国人有这个智慧与能力。
中国讲“天下”,不讲“际”“界”,“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得用中国思想,看中国人的“天下观”是多么进步,将星球都包括在内。
秦时,李冰(前256—前251)担任蜀郡郡守,在蜀郡修都江堰,现仍维新,经两千多年了。何以都江堰能够历久弥新?智慧产物是颠扑不破的,后人加个“神”字,乃因猜不透。今科学家犹不真懂。李冰父子治水,顺水找水源,研究水文到“神”的境界,被称为“二郎神”。今天研究中国思想,比李二郎找水源方便得多。
今天生活安适,何以不关门好好做学问?一天不知为什么而活,难道不会不舒服?千言万语,就是要自觉。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虽愚必明,虽柔必刚。笨并不可怕,肯努力就没有“愚”与“柔”。说一千道一万,人心实比天地宽。
《春秋》思想,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高的智慧,必慎思之、明辨之。真明白,三年绝对有成。一切之始,另辟天地,值得传承的以“性”为标准,要承、传。
读《公羊》前,有些重要问题要先了解。
一、《公羊》传承
《公羊》由子夏口授传自孔子,故圣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传焉。
公羊者,传者之姓氏。旧疏引说题词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公羊高,子夏弟子,五传而著竹帛,弟子不敢斥言师名,故以氏传也。
“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又称《公羊旧疏》,下简称“旧疏”),二十八卷,不知何人所著。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所作,不知何时人。其书在隋并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问答……按问答语甚精赡。
《公羊》传文,初不与经连缀。《汉志》(《汉书·艺文志》)各自为卷……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古者经传异本,汉古经《公羊》有传无经。故蔡邕《石经公羊残碑》无经……后儒省两读,始合并之。分经附传,大抵汉后人为之。《开成石经》始取而刻石焉。
二、何休学
《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学”。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谦辞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己”。《论语谶》云:“语‘学’者,识也。盖谓有所得即识之。”
《拾遗记》曰:“何休,木讷多智……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废疾》,谓之三关。”
三、三科九旨
公羊家旧有三科九旨。《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者,其义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事)。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
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是谓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谓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谓三科九旨。”
宋衷注《春秋说》,为另一种说法:“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
孔广森《公羊通义》,遗何氏而杂用宋氏。其说云:“《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者既布,而一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相须成体是也。”
九旨:在《春秋》常用的几个观念。
五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七等:州、国、氏、人、名、字、子。
六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士,事也,最低公务员。士大夫阶级,乃士至大夫。
二类:人事与灾异。
七缺:《春秋》有七种缺德的事:为夫之道缺,为妇之道缺,为君之道缺,为臣之道缺,为父之道缺,为子之道缺,周公之礼缺。
四、存三统
存三统,夏、商、周。因三统,才知有所“因”,“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孔子以《春秋》当新王,新周,故宋,黜夏,即宋(商)、周、春秋。否定周,自设一个朝代,即《春秋》。故汉以孔子为汉立法。汉纬书,亦为伪书。
孔子周游列国尽碰壁,乃“志在《春秋》”,“加吾王心焉”。《春秋》乃孔子为后人所立之大法,并非历史。孔子之前也有《春秋》,为“不修春秋”,是历史。
亲周,有今文家以为应为“新周”,说法不一。《大学》“亲民”“新民”,两种皆可。“亲民”,入手处;“新民”,终极目的。
元者,源也,本也。“周因于殷礼,其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矣”,道统、政统由此生,有源有本,不可以闭门造车。祭在报本,“水源木本”,慎终追远。
祖宗: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祖,对时代最有贡献者,开国的称祖。圣祖,乃入关后最有成就者,康熙称“圣祖仁皇帝”。
中国讲存三统,至清犹保存。今文家的责任,存三统。
五、张三世
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政治上的三个历程。
《读经示要》曰:“盖借十二公时代之行事,而假说三世,以明通变不倦、随时创进之义……与《大易》‘穷变通久’之旨相发明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书读多了,遇事笑一笑,所见都异辞,所闻、所传闻能不异辞?
张三世,即新三世,“因不失其亲(新),亦可宗也”(《论语·学而》),既能因而知祖,又知新而能进步,亦可宗也。以《春秋》当新王,新周,故宋,通三统。
“因不失其亲”,因,承受别人;亲者,新也,不失己新,建树自己。根据传统,不失其时。不知因,不知数典、不知祖,因此往往忘祖。做事由“因”处理,如一人说话于你有利,抓住,借以解决问题。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不近于礼的为“足恭”,不恰如其分的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治长》)。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义者,宜也”(《中庸》),信近于宜,不可以愚信,如召忽乃不近于义之信,管仲则“乃其仁,乃其仁”(《论语·宪问》“如其仁”,如,乃也),是近于义的“大信”。“言可复也”,言行能合一。
“自禹而德衰”,开启家天下之局,夏、商(殷)、周为世及制,家天下之制。孔子有志立新王,周于其意念上已经亡国。新王要复于正,《春秋》目的在拨乱反正,以天为正,政治上以尧舜公天下为正。孔子时,已历经夏、商到周,说“三世必复”,要复尧舜的公天下之制;三世不能复,再说“九世必复”,虽九世、百世亦得复。
孔子为宋之后,“少也贱”(《论语·子罕》),但学为贵,“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把乱制摧毁。今后中国再怎么乱,也没有人敢当皇帝在此。
新王,是孔子之志。讲“王制”,即新王之制,是“天下为公”之制。古时有“王制”与“世及制”,但被调包了,自“天子者,爵称也”,是唯一可看出的,天子非生而贵者,“人无生得贵者,莫不由士起”(《白虎通·爵篇》),天子之子曰元士,不过是士的领头而已。《孟子·万章下》问“周室班爵录”,答“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但“天子一位”,此为新王班爵录。《孟子》内存有一些,可见还有《春秋》之义。
“《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天子,“继天之志,述天之事”。《尚书》“天工人其代之”(《尚书·皋陶谟》),人能代天未竟之工。法天,法天之工,智周万物,道济天下,“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尧则天之道,天道无私、尚公,尧舜公天下。“拨乱反正”,正,乃天之道,尧舜之制为正。
六、风内外
此“风”同“春风风人”之第二个风,音fèng。指德化之风,使远近大小若一。表一人有德,受其化,曰“如坐春风中”,春风风人。如解作讽刺,我不首肯。
风内外:第一,与“内其(己)国,外诸夏”义同;第二,善其善,恶其恶,也有此解。我喜前一解。
内其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四夷;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
夏,夏历,夏声,夏学。“夏,大也”,“唯天唯大,唯尧则之”,无所不包。
“内其国,外诸夏”:个人“内其家”,先把家弄够标准了,才“外亲戚”。先把自己国弄好,再去帮诸夏。先有“夏”,才有“诸夏”。诸夏之邦,每一夏有一侯,故曰诸侯。侯,是最有聪明、智慧的君,即领导者。
“内诸夏,外四夷”:“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中国,礼义之国。中国的“夷狄观”,非以民族分,知礼义即为“夏”,故有“诸夏”。“因其国以容天下”,有容乃大,因己国,把自己的国看得特重,修好,因我们自己的国而容天下,是循序渐进地容天下,是有知识的容,将诸夏也看成内,故“内诸夏”。
三夏,夏、诸夏、华夏。华夏,将“夏”华于“天下”。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公天下,一切力量、东西皆天下人的,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与三代之英”,三代,夏、商、周,家天下,“小康之最”,应是汉儒所加,不是孔子之志。
“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在大处同,人性同,面包不必同,同而异。
“大同”与“小康”相对。“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接着讲小康:“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小康,小安也。历代皆有小安的局面。
小康,“世及以礼”,家天下世及制,“谨于礼,以著其义”,用“礼义”控制天下人,为其一家“尽忠”。“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乃小康的代表。显见上面“与三代之英”有问题。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一切决之以礼义,以礼运天下,据此拨乱以反正。正,止于一,止于元,元胞,同元共生,共生共荣,大居正,大一统。
“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到夷狄进至于爵、远近大小若一了,就成为“华夏”,此时,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见群龙无首,吉”(《易经·乾卦》),为终极目的。
心静,不厌其烦,多看几遍,才能读《公羊》,躐等才费劲。《春秋》讲“性”之书,为人性之书。
练习读书有耐力,定而后能静。隔行如隔山,今文家今后必出在你们。别人会当我们是笑话,但是笑话也得传下去。一个人是人,就不错。
大目标必要把持住,开始即要掌自己的舵。小做可以积沙成塔。时间真是金子,做的经验很重要。要实际,一步步去做,有抱负必要实际,脚踏实地去做。靠什么都不行,得的多去的也多。天天不做,总是空的。谁不会想?不去做,只是白日梦。
公羊学是个思想,用以启发自己的思想。读书贵乎真知,不在快慢。有思想的人,压迫越厉害,越会反抗。《公羊》既然已经传这么久了,不得不承继下去,不在乎有用与否,为往圣继绝学。
董仲舒《春秋繁露》是重要的政治哲学。繁露,是皇冠前后的流苏,做定镜之用。《春秋繁露》是解释《春秋》最重要的一部书,读《春秋繁露》,要一句句读,不必重其连贯,此书只字片语皆有用。“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繁露·重政》),即化繁为简,此为智慧。化繁为简,化博为约,即“属万物于一”,“一致百虑,殊途同归”。
《春秋》为一部政书,《易经》也是,“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易经·乾卦·文言》),昔有“体仁阁大学士”。中国无一书不谈政。
没有比老、庄再残忍的了,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必要恰到好处,放冷水,热气一起,东西即可食。小鱼一烹,骨头都酥了!保持小鱼样,要小烹。蒸,用大锅,小鱼既小又嫩,一不小心即成肉松。
“大明终始”(《易经·乾卦》),“大”为赞词,赞“明”能由“始终”成“终始”,赋予其新生命,终而复始,生生不息。能者,能起死回生;不能者,就把事弄糟。“圣人贵除天下之患”,无智焉能除患?今“剩人”贵制造天下之乱。
有志,能发挥之处太多,边读书边贡献智慧。手要勤!如好吃懒做,只好抢了、烧了,就吃软饭。一国至此,不亡哪儿跑?是是非非,应由理智决定。
《说苑》《白虎通》必要看,里头是今文家的东西。《白虎通》为今文经,原名《白虎通德论》。东汉朝廷召开“白虎观会议”在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老道都用“观”。
称“六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汉书·艺文志》),此按经书的历史排列,古文家的排法;“《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天运》),今文家按经的难易排。
刘向《说苑》、东汉《白虎通》按古文经排法。古时可能无今、古之见,那时无今古文。鲁恭王坏鲁壁,《汉书·艺文志》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因孔壁藏书的发现,乃出古文书,而开启“今古文之争”。
清儒作书,不厌其详,材料极为丰富。陈立《公羊义疏》详细,但内亦有引古文经,不属于今文家的东西,乱。做学问,不能只看一两本书,打好基础不易,今人无古人的耐力。
任何民族皆有不可磨灭的思想。乡下人没读什么书,但会处理事。拿西方思想到中国以强中国,民初有“全盘西化论”,也没能成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干总比不干好,应开拓自己的心胸。
《春秋》仁者之位,仁者之时,创此思想者很进步,合乎《大易》“时”的观念。“时”必跟着“位”,《易》六爻,“六位时成”(《易经·乾卦》)。
人境界不同,几年后可以看出。何必以自己的智去肯定一切,几年后看,其实很幼稚。“所见”,以自己智慧的最高境界去看。了解之所以不同,因没经过那么多的历程。见什么事越肯定,越显自己的幼稚,胆越大的越跋扈。
失本,不能成其功,做事业必要立本。问:“学《礼》乎?”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能立本。识本,必要下功夫。
净读《学英文百日通》,外语绝对学不好,应不能使之流通,助长取巧心态的产生。要读字典,下笨功夫,单字记得才多。读《千字文》,至少识千字,才能为文。大小事皆必立本,才能深入。
说话,必要言中有物,因“圣人贵除天下之患”(《繁露·盟会要》)。《诗》可以兴、观、群、怨,多言民之“怨”。
国家要好,上下皆要发愤,才有希望。学东西,绝不能走快捷方式,不要净耍小聪明。必要仔细看书,不能以术欺人。现在做学问,净查字出现多少次,非饿死不可。
看了,懂不懂?看了,总比数(shǔ)字强!有根,叶才能茂。看书,才能言之有物。
读书,贵乎有耐力。做学问,要客观,不能把主观摆前头。
一个人应做自己应做的事,不以一言而动你的初衷,不能没有自信心。
做事要有大计划,准备好了再做。按计划,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做,不要好高骛远,自欺耳!立下标准,往前奋斗。懂得人生是什么,就应面对之。按己才智,立下目标,往前奋斗。有一分才,干一分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名实相称。际遇不错,乃“志相得也”(《穀梁传》:“遇者,志相得也”)!
做事必要想三段,知自己应怎么做。不找事,但事来了,绝不能躲事。必自己有食了,才能别人助一饥。朋友只能供一饥,不能供百饱。行有余力再去助人,乃能正天下之是非。
丁日祭文圣,戊日祭武圣。春、秋上丁(二月、八月)祭孔,是一年中的大事。
汉高祖十三年,高祖过鲁,以太牢祭孔,开启帝王祭孔之始。曹魏正始二年(241年),令太常(礼官)释奠孔子于辟雍(帝王授课讲学的专属学宫),以颜回配享,乃以释奠礼祭孔之首例。东晋以后,历代皆为定制。
唐玄宗崇道尚武,开元十九年三月,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以每年二、八月上戊日致祭,如孔子礼。玄宗比姜齐太公为“武圣”,故与孔子“文圣”比,后世则以关羽为武圣,太公乃入道家。
“子入太庙,每事问”,人就有话说,孔子问“是礼也”(《论语·八佾》)?可见恢复一个“礼”,多不易!虽不用,但不可以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保留之,此为文化。
读书,字面明白了,还要前后要义贯穿之,“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乃是各方面的融合而成。中国东西是提炼出来的,不是一般人马上可以领悟的。
政治必须立本,政术为其次。树人即立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一般人往往舍本逐末,舍近而求远,“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孟子·离娄上》)。“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中庸其至矣乎”,越是平常的越是至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中庸》)。
治非莫过于敛己,要不自欺。来日方长,应洁身自好,德行必要重视,君子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学术是责任,必向历史负责,此亦道德。一个人必得进步,必要有德行,天真造成许多的是非。做学问要改变气质,学问深了意气平。
教书不同于法院,不能动辄开除学生。
言行必要注意,不要学伪君子,就爱摆样,如李光地(1642—1718)。
全祖望认为李光地是个伪君子,其《鲒锜亭集外编》卷四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说:“其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
人就是人,是个人就够了,失去“人”,就完了。犯伦者,非人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在于有伦,凡入了伦,皆不能侵犯。人必要平衡,否则虽不失伦,亦失德,人亦耻之。失伦与失德,皆可怕。
有德者,人尊之,才能领导群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活着据你的势,死时估你的德。成就自己很慢,而败坏就在刹那间。人非不能,乃不为也。人在一起久就有味,臭味相投。收敛自己,于言行上要有个标准。
想将来有成就,不能忽略今天。没有今天,哪有明天?重视现在,才有将来。学得不好,可以慢慢学。有学,无品,不是人。失德事绝不可为,伤品败德足以祸国。活一天就得守分一天,失分就是失伦。
人爱儿女甚于爱父母,不能在人面前道其儿女之短。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人有正气,则邪气不能侵。
真学问必下真功夫,改造自己必自心理改造起。人内心如卑鄙,行为绝对卑鄙。必要有浩气,养浩然气,想有成就必严格修己。
一国之强,完全靠物资办不到,重要在精神,如日本、德国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复兴,不在于美援,贵在其本国固有之精神,即其特殊文化。应发掘我们自己的民族特殊性、民族性。政治上姑息可以养奸,治乱世当用重典。
书读百遍自通。读书得心勤。有智慧,还要有恒力。如同开矿,每天要有新发现,为了发现去读书。八岁读《论语》,八十岁还读《论语》,境界绝对不同。突破难关了,才能有新的境界。
政治之道是实际的,是非不论,但一离开实际,就不能谈政。真正读明白《论语》,必能用上。文人大抵只能说,不能做;人家做了,还嗤之以鼻。此专制下之余毒,读书人往往自以为清高。书生论政,外面啥事也不知。昔日致仕教书,将一生的经验配合学问讲。会讲书的,深入浅出。
切合实际地看书,当求智慧读,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心看,要有所悟,而非守着书本,整天坐着看书。“学而不思则罔”(《论语·为政》),随时随地思,有所得记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为吃忙为生存忙,久则厌倦,凡事被动则成机器。素养极为重要,日常用事,在乎平时的准备,不能到危难时才要求解决。
年轻时必要有所事事,光阴不虚度,智慧不虚发。任何学问均有一定的途径,离此即索隐行怪。
字是门面,学写字,要练习怎么拿笔,练“永”字八法。近什么体,就写什么体。成家,必天才加上功夫。溥二爷(溥儒)随时手不停笔,没事时净画小纸条。要成书法家,按字的源流写,至少由篆开始写。今天由老师的字入手,害人一辈子。正规格学完之后,再以天才去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