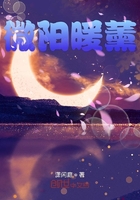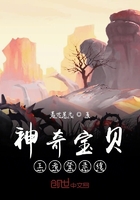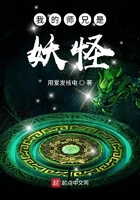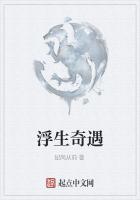一 悟性的本质
我们说一个人聪明而有智慧,常常说“这个人悟性很高”,这是就能力而言。传统艺术哲学妙悟说中的悟性不仅限于能力,它还表示一种独特的心灵素养,是心灵修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传统艺术哲学中的悟性说有其特殊的内涵,我将其概括为三种样态:一、悟性是“本来有的样子”;二、悟性是人“应该有的样子”;三、悟性是“自己之独特的样子”。容我就这三点稍加疏说。
在传统艺术哲学中,悟性即人的本来面目,是人“本来的样子”,是人生命本来具有的觉性。若要悟入,必回归本然,这个本然就是未被污染的真实心灵,也是人的自然之性。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展开。
在传统艺术哲学的语汇中,有一重要词汇:“元”。此字甲骨文像人首之形,后引申为初始、原初义,《说文》:“元,始也。”由原初义引申出本原、根源,并被赋予抽象的道的意义,所谓“元本”。《春秋繁露·重政》:“元,犹原也。”《潜夫论·本训》:“必先原元而本本。”元为本,为道,为玄,所以元又有万象之统领的意义,《广雅》:“元,君也。”
艺术理论中,以悟为元,颇有深韵。从初上说,它是开始,是悟的起点,没有这个“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悟”;从源上说,它是根源,是种子,是智慧的种子、创造的种子,生命的飞跃全赖这种子;从本上说,它是人性灵的质,也就是人的性,是人心之“天”;从存在特点说,元就是玄,这两个字在古汉语中可互通,它是人心灵中最渊奥的存在。综此四点而言,元作为描述人体悟心灵的重要语汇,含有中国人对悟性特点把握的内容。[47]
五代荆浩《笔法记》在评价水墨山水的出现时说:
如水晕墨章,兴吾唐代。故张璪员外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旷古绝今,未之有也。麹庭与白云尊师,气象幽妙,俱得其元,动用逸常,深不可测。王右丞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巧写象成,亦动真思。李将军理深思远,笔迹甚精。虽巧而华,大亏墨彩。项容山人树石顽涩,棱角无踪,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然于放逸,不失元真气象。[48]
荆浩认为,山水画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新的创作方式,就是动“真思”。何谓真思?世俗之论、欲望之想、理智之思,都是假思,都是对世界不真的反映。而真思,是贴近生命根源处的思,是不假思量、真实无妄之思。《笔法记》中所说的“真思”就是悟——由真实悟性所传导出的妙悟。这里涉及悟由何起的问题。荆浩认为,唐代新兴山水画大师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在于他们“俱得其元”“独得玄(元)门”,溯向生命的纵深,解除外在附加的心意,以赤子的心灵、“一丝不挂”(禅语)的精神去体悟,在自己的生命深处体会大化的妙用,由此启动他们卓然的“真思”。真思是由本源的心灵转出的,是“元之思”。荆浩指出,只有得此“元思”,所作山水画才能“不失元真气象”。什么是“元真气象”?它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创化之元,也就是大自然深层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一是人心灵中的元真气象。二者是一体的,回归元初,就会在心灵深处与真实的自然境界照面,契合创化之元。创化之元和心灵中的真元境界是不二的。所以,《笔法记》中提出一个对后代影响深远的观点:“须明物象之原。”原,通“元”。意思就是回归心灵的元真悟性,再以“性”的真实去体悟造化。就像清画家恽南田所说的:“冰鳞玉柯,危干凝碧,真岁寒之丽宾,绝尘之畸客,吾将从之与元化游。”[49]“元化”就是造化之元,即真性,乃生命的本真世界,如佛教所谓如来藏清净心。
石涛所说的“一画”,也是“元”。石涛提倡“一画”是要建立“性”的觉体。从心灵的角度言之,“一画”说的主要内涵是提倡妙悟,在心灵的源初境界中去创造,排除理智、欲望等传统概念的缠绕。他将一画溯向“混沌”“鸿蒙”,就是溯向原初境界,以真元之思去创造。石涛的一画是“从于心”的,但不是简单地“从于”感情知识,而是“根于性”,由“性”而起,才是“一画”最终落脚处。“一画”所要建立的不是心的本体,而是性的本体。石涛说要回到一画,也就是回复人的自在之性。在性中,才能没有机心,没有解释的欲望,像鸟儿那样飞翔,像叶儿那样飘零,这样才能真正与山光水色相照面。以一“性”通万象,就能以一“性”控笔墨。石涛强调一法见万法,这个万法只能在性中显现,而不能通过心识达到。如慧能所说:“于自性中,万法皆现。”性为心之本,而心包括意志、情绪、知性活动,这样的心无法显现诸法实相,所以也就无法在小中现大、一中现一切。石涛的一画是绝于对待的,绝于天人之对待。他要画家奉行“一画”,即要解除心与物、天与人之间的冲突,从世界的对面回到世界之中,从“万”回到“一”,也就是回到创化之元和元真境界相合的“元”中。
中国艺术论中的“心源说”也与此有关。此方面的论述,如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刘禹锡的“心源为炉,笔端为炭”说,郭若虚的“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说,以及康有为“吾谓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50]的观点,都强调妙悟必发之于灵魂的根性,非根性之悟则非真悟。一知半解,未及骨髓,无法探得艺道骊珠。
悟性不仅是“本来有的样子”,而且是“应该有的样子”。另一个概念“天”,便与此有关。上面所说的“元”强调的是悟性的本原性。“天”在本原性特征之外,又突出悟性的自在性特征[51]。即是说,悟性是人心灵自然而然的存在,是一种自在显现的境界,悟说到底就是生命的原样呈现。悟性是在解除人意识基础上形成的,它所要破除的主要对象是“我执”。人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的意念,在中国哲学上称为我执[52]。执着于我见,则不得真见。儒家哲学以为,人为五行之秀气、天地之心灵、万物之精英,这种观点从强化人创造力的角度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但这一理论又衍生出另外一种思想,就是强化人控制世界的观念。我们说物我关系、心物关系、天人关系,常常不自觉地将人从世界中抽出来,站在世界的对岸来看待世界,用人的眼光打量世界,用人的意识去解释世界,用语言——人所创造的一小打符号去整合世界,所以,只能得到世界虚妄的印象。传统艺术哲学中强调以“天”去妙悟,就是从“人”回到“天”,回到人应该有的位置,去扮演应该有的角色。
所以,作为悟的“天”是“应该有的样子”。“天”是人存在的真实样态,“天”是作为人心灵本体的“天”。具有“天”的心境,就是“无”,它否定以知识去把握世界的可能性。在《庄子》和禅宗的语汇中,“得其天”不仅是“得其本”,更是“得其真”。悟性就是认识世界的真实本体。在庄禅哲学看来,没有一个在世界对岸打量世界的认识主体,也没有作为此一主体对境的客体。由此,哪来世界的印象,哪来世界的图景?所以世界是“空”的,苏轼所说的“造物初无物”,说的就是这层意思。这“空”既不是心灵的属性,也不是世界的属性。它不是一个空间的度量体,不是体量的概念。它也不是人心中感受的空,如果人心中感受到空,那么这个认识主体又复活了,则非真空。中国哲学强调“放下心来与万物一例看”,实际上就是不看,不是只在心中存有要建立与万物平等关系的欲望和意识,连这个意识也消解了,与万物一样地成长。
北宋董逌说: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吴道玄往图,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敢不有一于此也。诏大同殿图本以进。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尽,远近可尺寸计也。论者为丘壑成于胸中,既寤(按:同悟)则发之于画,故物无留迹,景随见生。殆以天合天耶。李广射石,初则没镟饮羽,既则不胜石矣。彼有石见者,以石为碍,盖神定者,一发而得其妙解,过此则人为已。能知此者,可以语吴生之意矣。仲穆于画盖得于此。[53]
在这里,吴道子作画和李广射石,都不能以技来论之,而是天性所悟而得。就吴道子而言,他何以能一日尽嘉陵江三百里之景,那是因为他心灵中有,所以笔下才会汩汩流出;就李广而言,他射石,发于天性,一矢穿石,欲再射则不能。二人都是凭“天性”之资,“以天合天”。所谓“以天合天”,第一个“天”是人心中之“天”,并非是人心中映照的外在“天”的世界,而是说人的心灵达到“天”的境界。吴道子融进山水,就像石涛所说的,他“迹化”于山水,山水都归于吴道子,他成了山水的代言人,不是以自己的言去代山之言,而是以山之言为言,所以他能在贴近嘉陵江的心境中画出嘉陵江。李广也是如此,悟在刹那间,刹那间他解除了要射石的意识,而再射则不能中石,不能穿石,乃是因为“彼有石见者,以石为碍”,他失去了他的“天”,他成了自我意识的奴隶,“我执”控制了他的心灵,悟性已遁然而去。
《庄子·达生》中曾以一位神妙的木工梓庆之口,来阐扬其天运境界:“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林希逸注:“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庄子口义》)斋戒多日,渐入悟门,至最高境界忽然物我都忘,理智全除,心中朗然清圆,如太空,故此谓天,就是回到了自然。即传统艺术哲学所谓“唯自然能知自然,唯自然能言自然”。以自然合自然,谓之以天合天。所谓“天”在此表示人的悟境,是“天赋”之,而不是人成之。庄子将人妙悟的心灵称为“天府”,就强调惟此心灵才是真实的,是自己应该有的真实状态,而念念在庆赏爵禄、非誉巧拙,时时思四肢形体之欲望,则是非真实的存在。
悟性还是一种自性,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样态”。北宋韩拙说:“天之所赋我者,性也。”性乃悟之基,然而若心为物迁,情为象使,以乱人之本性,则无法得出天地之“真”,只能得到天地的虚假影像,所谓作画的关键在于“悟空识性”,识自我之性,回到自己的真实生命。董香光说:“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当念即永嘉所谓一念者,灵知之自性也。”[54]李伯时说:“自在在心不在相也。”[55]正是此意。
在佛学中,法性,或称为法界、真如、法身,即万法之体,它永恒不变,常住不改。法性是法的本体,法是一至大无外的概念,宇宙间一切有形之相和无形之理都可称为法,或者叫作法相。但一切有形之相和无形之理,都根源于法性,法性不灭,法相随缘流转,性不改而相多迁。唯识论认为,法性有一重要特点,就是自体任持,万相根源于一法之性,必有任持,不舍自性,山林任持山林之自性方为山林,红叶任持红叶之自性方为红叶,万法不逾自性,一逾自性,即同他流,红黄间出,自性即失。熊十力说:“凡言法者,即明其本身是能自持,而不舍失其自性也。”[56]
如在石涛的画学思想中,他所强调的妙悟之法,就有任持自性的特点。《画语录》的“资任”一章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万物受任于天,皆有其存在之合理性,也决定了其存在的差异性。石涛伸展个性的画学非常重视这种差异性。万物本于天,因而各得其性,其性之完满展开,即自然,即本性。石涛“资任”学说的核心就是“任性”,也就是万物的自在呈现。虽然万物都是生生联系中的一个纽结,但都有其存在之特点,丧失了这一特点,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即失去了“自性”,负于天之所任。万物各有自性,人也有其自性,人必须不舍自性。石涛由此展张了他对人受任于天因而自任其性的思想,所谓“天生自有一人职掌一人之事”[57],正是指此。他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归复真性,则是圆满俱足,这是天资之性、天赋之权,古人不能剥夺我,古人以其差异性展现了他的独创性,我也应以我的差异性展现我的独创,一切外在的力量均不可剥夺我的权利。我只要做到自任,自性展露,才不枉于天任;回到“一画”,回到蒙养之源初,即回归自性;回到纯一不杂的本性,就是自性。如何回到自性,就在于悟,只有在妙悟的心灵中才存有这样的真性。
以上所言悟性的三个特点(它是人本来的样子,是人应该有的样子,同时也是人独特的存在样子),一在得本,一在得真,一在得己。悟性是人的本性、真性、自性,以悟性去妙悟则是本然的判断、真实的判断、独特的判断。探其本而舍其末,取其真而去其妄,尊自性而黜他性,方可搜妙创真,归元得奇。
二 悟性的动力
悟不期然而至,你没有想到,它来了,是巧遇,是偶然,不可逆料,这就是悟的随意性。悟不由人的意识摆布,但并不等于说,悟只能是一场难以预料的等待。悟不期然而然,若期然,则不然;然而不期然,则未必不是必然。传统艺术哲学有一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只要你恢复灵魂的悟性,那么妙悟则是可以期望的现实。悟性是因,妙悟是果,有此因必有此果,即性即悟。但问题也正在此,为什么会即性即悟?本节便讨论这一问题。
在艺术妙悟活动中,构成内在的推动力又是什么?艺术妙悟的动力就在悟性中。正因为假设人有这个性,它是妙悟过程中惟一的动力,这个动力推动人放弃原来的世界而选择它应该有的世界,或者是曾经有过的那个世界。因为在悟中再也没有知识的选择,知识控制的愿望已退出,如果不退出,也就没有妙悟;当知识控制的愿望退出以后,维持妙悟,就是这一自然的倾向性。这是一种源于生命的深层推动力。
在传统艺术哲学中,回到本元,回到自性,回到性灵之“天”,叫作进入“天机自发”的境界。悟性就是这一天机自发境界的深层动力。北宋张怀说:
且画者辟天地玄黄之色,泄阴阳造化之机,扫风云之出没,别鱼龙之变化,穷鬼神之情状,分江海之洪涛,以至山川之秀丽,草木之茂植,翻然而异,蹶然而超,挺然而奇,恢然而怪。凡域于象数,囿于形体,一扶疏之细,一帡幪之微,覆于穹窿,载于磅礴,无逃乎象数。而人为万物最灵者也,故人之于画,造于理者能尽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何哉?盖天性之机也。性者天所赋之体,机者至神之用。机之一发,万变生焉。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挥一毫,显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故昧于理者,心为绪使,性为物迁,汩于尘坌,扰于利役,徒为笔墨之所使耳,安得语天地之真哉![58]
清布颜图说:
夫境界曲折,匠心可能,笔墨可取,然情景入妙,必俟天机所到,方能取之。但天机由中而出,非外来者,须待心怀怡悦,神气冲融,入室盘礴,方能取之。悬缣楮于壁上,神会之,默思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峰峦旋转,云影飞动,斯天机到也。天机若到,笔墨空灵,笔外有笔,墨外有墨,随意采取,无不入妙,此所谓天成也。天成之画与人力所成之画,并壁谛观,其仙凡不啻霄壤矣。[59]
这两段论述都涉及“机”的概念,在传统艺术哲学中,“机”是审美体验中的关键性因素,在西方艺术哲学中没有与此相对应的概念。它是传统艺术哲学中关于审美心理动力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
性是悟之体,机是由此体所转出的用,而妙悟则是这一“机神之用”的结果。“机”是悟性和妙悟这个因果链中的动力因素,是显现悟境的心理空间。“机”既不是“性”,又不是悟,是介于性与悟之间的因素。在这里,中国艺术论没有将此导入心理的分析,还是以哲学的推论为基础,导出“机”的结论。(此为传统艺术哲学之长处,也即其短处)
機的本义为弩機,由此引申为发动。《说文》:“主发谓之機。”[60]在哲学中,此字又由发动义引申为造化之元的意思。《庄子·至乐》:“万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成疏:“機者发动,所谓造化也。”《列子·天问》:“皆出于機。”张湛注:“機者,群有之始。”进而,機由造化之機引入人心灵之機,即人心灵中创造的母机,此创造的母机就是从根性上发出的力量。妙悟就是对悟性的复归,也是对人内心中创造能量的提取。所以,機为性之用。
在中国哲学和艺术理论中,“机”具有神妙莫测的巨大功能。“机”又用为“几”。《说文》:“幾,微也。”“微”就是微妙玲珑,如上引张怀所说的“机神之用”,《二十四诗品》所说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通过微妙玲珑的感悟过程感悟那个微妙的意旨。《二十四诗品》是元代诗人、思想家虞集《诗家一指》的一部分,在《诗家一指》的后序中,虞集说:“心之于色为情……拾而得之为自然,抚而岀之为几造。自然者,厚而安;几造者,往而深。”这里将“自然”与“几造”(同机造,即心灵的独造)相并而言。其实,自然即几造。此几造,就是发之于“自然”——生命根性的创造动能。
在《易传》中机(几)和神具有相同含义。《易传》说:“阴阳不测谓之神”,“神无方而易无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又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几通于神,几是动,所谓“几者,动之微”,微妙玄深的动,不可预测的动,神妙无穷的动,体现出天地无穷的变化,再现出阴阳不测的神秘。
“机”又常常被冠上“天”字,成为“天机”,如上布颜图所谓“必俟天机所到,方能取之”,天机到,即意味妙悟开。宋包恢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61]明谢榛说:“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62]此“天机”并不是俗语中“天机不可泄露”的神秘启示,而是如“天”之“机”,是自然而然的机缘,天机自发,自然天成,不待他力。所以,由根性发出的妙悟,是自然而然的悟,是“随物应机,不主故常”[63]。布颜图所说的“天机由中而出”是很有价值的思想,“天机”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宁静的悟入过程,机由悟出,无悟则无机。沈宗骞这样描绘天机的作用:“当夫运思落笔时,觉心手间有勃勃欲发之势,便是机神初到之候,更能引机而导,愈引而愈长,心花怒放,笔态横生,出我腕下,恍若天工。”[64]
天机的状态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全由“天”力,不由“人”力。中国诗人说“万物各天机”,天机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人恢复根性,就去除了理智、知识、欲望等的羁束,进入一片天然的状态中。《二十四诗品·冲淡》品说:“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悟入根性,如清潭照物,影象昭昭,饮太和之气,得自然真髓,如独鹤轻飞,冥然于物,无所对待,像山风轻拂,似修竹潇潇,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自在显现,一片天机。
因此,“机”(或“天机”)的另一特点就是其自发性。所谓自本自根,自发自生。传统艺术哲学中,常常将悟机解释为“势”,妙悟的过程就是蓄势的过程。机的语义,与弓箭有关,本指弩機,由悟性到妙悟的过程,在艺术论中常被形容为“机发矢直”[65],归复生命之本,也就蓄聚妙悟万物之势,恢复悟性,便获得启动创造母机之能力。箭在弦上,力蕴其中,不容思量,不容他务。明项穆《书法雅言》列“神化”一节,他说:“书之为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欲书必舒散怀抱,至于如意所愿,斯可称神。书不变化,匪足语神也。所谓神化者,岂复有外于规矩哉!规矩入巧,乃名神化,神化也者,即天机自发,气韵生动之谓也。”书法在于抒发怀抱,此怀抱何以酝酿而成,则在于妙悟,而达于神化的境地。达到神化境地,就会不动而动,不发而发,其中蓄聚的创造能量喷涌而出,这就是天机自动。沈宗骞说:“机神所到,无事迟回顾虑,以取出于天也,其不可遏也,如弩箭之离弦,其不可测也,如震雷之出地。前乎此者,杳不可知其所自起,后乎此者,窅不知其所由终。”[66]
机更强调机缘,它标志一种相互逗发境界的形成。机微是深层的契合。机中含有“时机”的意义,即是在特殊顷刻的特殊感悟。这特殊的顷刻就是瞬间契合,突然切入对象之中,不期然相遇。所以在“机”中“遇”,妙悟的结果就是这一审美的“机遇”。机的时机性特征,是妙悟的一个重要特点。明袁宏道说:“博学而详说,吾已大其蓄矣,然犹未能会诸心也。久而胸中涣然,若有所释焉,如醉之忽醒,而涨水之思决也。虽然,试诸手犹若掣也。一变而去辞,再变而去理,三变而吾为文之意忽尽,如水之极于淡,而芭蕉之极于空,机境偶触,文忽生焉。”[67]空淡即妙悟之空性,机境乃是妙悟之际会,如风行水上,涣然而成涟漪。这就是妙悟中的“机遇”。所以,袁宏道这里所说的一变、二变、三变,乃是对妙悟过程的描述,悟则当下便彻,在于一旦,在于偶然。这个一旦和机遇,是悟性所发的“时机”,稍纵即逝。“古人作画,其精神贯注处,眼光四射,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68]王孟端的这个体会,正是妙悟的时机。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艺术论中有这样的观点,即学不能至,必由悟至,当然这不是排斥学,而是如董其昌所说的“学至于无学”。妙悟不受知识控制,并不意味知识退出。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一说:“古人之奇,有笔奇,有趣奇,有格奇,皆本其人之性情胸臆,而非学之可致也。学者规矩而已,规矩尽而变化生,一旦机神凑会,发现于笔酣墨饱之余,去其时弗得也,过其时弗再也。一时之所会,即千古之奇迹也,吴道子写地狱变相,亦因无借发意即借裴将军之舞剑,以触其机,是殆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意求也。”所表述的正是这一思想。
三 关于养性
水墨画的创始人之一、唐代画家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著名观点,此一观点在中国绘画乃至整个中国艺术中都产生深远影响,它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纲领之一。这是一个与悟性有关的观点。
张彦远在叙说张璪提出这一观点时说:“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阁笔。”[69]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张璪作画常常“用紫毫秃锋,以掌摸色,中遗巧饰,外若混成”[70]。而符载在一篇描绘其作画经历的文字中,更是叙其离奇的创作过程:“是时坐客声闻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视而观之。员外居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激空,惊飙戾天。摧挫斡掣,霍瞥列。毫飞墨喷,捽掌如裂。离合惝恍,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鳞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渺。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71]张璪这样的作画方式,并非出自表演性的欲望,而突显的是“解衣盘礴”的胸襟,说明张璪作画并非如寻常画家那样谨守秩序,他荡去一切机巧,追求灵魂的表达。其所画,非技也,乃道也。他要在这一过程中追求性灵的自由。所以符载在记录这段过程后,说他“得之于玄悟,非得之于糟粕”(糟粕指为外在物象拘束、为目的性心情所控制等)。张璪画学思想的关键词应是“玄悟”,或者说妙悟。而妙悟也是解读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惟一入口处。
张璪此一画学纲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强调主客观或情景结合的问题,[72]而强调的是妙悟。任何心物二分的解读都不合于此一学说。张璪强调的是造化和心源的合一。在心源中观(印)造化,在造化中见(现)心源。
“心源”一语来自佛学。在佛学中,心为万法的根源,所以叫作“心源”。心源也即人心之本,所以,心源就是人的根性,是人的“本有”或者说是“始有”。佛教哲学以“心源”为本有之境。《华严经》卷十二说:“我王心镜净,洞见于心源。”同上卷十五:“涤除妄垢显心源,故我归依无等者。”《菩提心论》云:“若欲照知,须知心源。心源不二,则一切诸法皆同虚空。”
禅宗由佛学中的佛性理论引发出心源为本的思想。“悟心容易息心难,息得心源到处闲。斗转星移天欲晓,白云依旧覆青山。”[73]以心源为本,悟是心源的展开。北宋杨岐派禅师道完有一次上堂说法,有云:“古人见此月,今人见此月,此月镇常存,古今人还别。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洁。决定是心源,此说更无说。咄!”(《五灯会元》卷十八)心源就是恒常不变的明月,就是那依旧在青山中缭绕的白云。
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的义涵接近于禅宗,它强调的思想是:心源为本,以心源去妙悟,艺术创造的根本就在于归复心源,以人的“本来面目”去观照。这本来面目就是艺术家最弘深的智慧,而艺术妙悟过程乃是发明此一智慧。所以这里的“外师造化”,并非强调注意观察外在世界,而是要解除人与物的判隔,解除主体客体的对境关系,以心源去观照。心源观照,就是妙悟,此即符载所说的“意冥玄化”。惟有如此,才是“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所以张璪疯狂作画时,遗去机巧,解衣盘礴,超越感性,建立以心源为核心的逻辑。在庄子所说的“听之以气”的境界中去“师造化”,师造化之伟力、造化之真元。这个造化乃是悟中之造化,造化和心源完全合一。造化不在我的心外,心源不出于造化,也就是清戴熙所说的“心源即造化,造化即心源”。
在艺术理论中,对心源一说阐述比较充分的是北宋绘画理论家郭若虚,他在《图画见闻志》卷一中列《论气韵非师》一节,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学说作了创造性的发明:
谢赫云:“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尝试论之: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迹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故杨氏不能授其师,轮扁不能传其子,系乎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爰及万法,缘虑施为,随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书画发之于情思,契之于绡楮,则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诸贵贱祸福,书画岂逃乎气韵高卑?夫画犹书也。杨子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从绘画理论的发展看,这段话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涉及传统画论中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如六法说、心画说、妙悟说、心印说以及心源说。郭若虚认为,六法之中,气韵为要,气韵非得之于娴熟的技巧,而发之于心源,得之于由心源所发的妙悟,而妙悟就是心印。郭若虚建立了一个以心源妙悟为核心的绘画理论体系,他的绘画批评即是此一体系的展开。郭若虚这里最具创造性的,是将心源和生知联系起来。这里以郭氏此一思想为线索,对心源和生知之间的观点稍加辨析。
艺术的飞跃来自悟性——艺术家独特的禀赋。然悟性由何而起?是先天赋予还是后天习得,是本来具有还是修养所得?在六朝的艺术理论著作中,就有不少论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的论者对妙悟这种超出于常人常规的能力迷惑不解,如庾肩吾在《书品》中评张芝、钟繇和王羲之三家书法时,对他们的成就感叹道:“疑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是先天赋予的,是天赋的能力,是不可预测的,不可解释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期望的。
郭若虚赋予妙悟生知说以新的内容。他这方面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成书稍后于《图画见闻志》的《宣和画谱》在评价王维之画时说:“出于天性,不必以画拘,盖生而知之。”北宋末年邓椿作《画继》,也接受了郭若虚的观点,对文人画极尽推崇。邓氏在《序言》中明确宣示,世上流传绘画的最高品第,都是由妙悟得来。[74]他说:“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虚深鄙众工,谓虽曰画而非画者,盖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而若虚独归于轩冕、岩穴,有以哉!”[75]他以为,气韵是天地间的独特精神。在妙悟中,这微茫中的“些须精神”流入画家心中,才会有一流作品出现。明董其昌推崇妙悟,也以为:“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在生而知之,自然天授。”[76]
郭若虚等提倡妙悟来源于生知,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首先,强调生知意在强调妙悟由人的根性发出,也就是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另一种表述。郭若虚说:“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他以如此肯定的语气,强调气韵只能来自“生知”。他说:“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这心源就是人的根性,人心灵深层的智慧。但如何将这一本然的知性或者觉慧的能力引发出来,则要靠悟。因为即使你有“生知”之性,但若无觉悟,则此慧将隐而不露,不可能转化为绘画中的气韵。所以他接着说:“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对根性的觉悟,不能靠机巧,不能靠知识的推证,也不是凭借时间的积累,像“众工”那样,它是一种灵魂的悟得,是对自我内在觉性的毫无滞碍的引发。郭若虚这里特别强调“印”,他说:“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爰及万法,缘虑施为,随心所合,皆得名印。”所谓心印,强调觉悟过程排除一切干扰,恢复灵魂自性,不沾一念,不着一思,洁净无尘,空明无碍,在这样的心境中印认世界。
总之,气韵非学出,而是印出,以心源去印,以灵魂的觉性去知,这就是“生知”。非学出,并不代表排斥学,而如董其昌所说的“学至于无学”,“学”可以培植根性,滋养根性。“学”又会构成对根性的破坏,但如果不能摆脱“学”的影响,以悟去创造,就有可能造成对性的阻碍,所以“学至于无学”是非常重要的。
郭若虚论艺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生知”之“生”,有二义:一、“生”与“性”相通,“生知”即“性知”,从“性”上知,即由生命根性上培植,也就是妙悟,这是达至气韵的根本途径。二、天地之大德曰生,传统艺术哲学最重活泼泼的生机,风月无边,庭草交翠,到生生不已的世界中去体验,才可有审美的飞跃,故郭若虚等的“生知”,又有“通过生生去体知”的内涵。
其二,妙悟在于生知突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养性。妙悟本于根性,此根性必须颐养,艺术之悟和养性是密切相关的。如郭若虚所说:“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迹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77]这段话将绘画的成就和人品联系起来,认为有什么样的人品,就会有什么样的绘画,绘画是看人品的重要窗口。初看起来,这是一种充满偏见的说法,因为艺术毕竟是艺术,它需要艺术家的表现能力,人品好了,但对画一无所知,难道就能创造出好的艺术作品来?所以,在当代学界这一观点引来的非难也很多,甚至被指为士大夫阶层荒唐的自恋。但这样解读郭若虚,并不切合,是对郭的一种误解。
郭若虚这一观点在传统艺术哲学中具有普遍的影响,与此相近的论述相当多。元杨维桢说:“故画品优劣,关于人品之高下,无论侯王贵戚,轩冕山林,道释妇女,苟有天质,超凡入圣,即可冠当代而名后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拟,难入谱格,而自家所得于心传意领者则蔑矣。”[78]明李日华论画也推重人品,他说:“姜白石论书曰:‘一须人品高。’徵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79]在李日华看来,欲人品高,必重德义,“士人以文章德义为贵,若技艺多一不如少一,不惟变役,兼以损品”。他反对俗念不断,推重洁情高韵。清王昱(1714—1748)《东庄论画》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80]邵松年《颐园论画》云:“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吾辈学书画,第一先讲人品。”[81]
人品和艺品联系的理论,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性。其一是道德主义倾向,它是文以载道文化传统在艺术领域中的体现,像上引王昱、邵松年的观点就属于此一类别。其二是重妙悟的倾向,这以郭若虚为代表,像上引杨维桢、李日华的论述就属于此一类别。后者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艺术的妙悟和性灵的觉悟是不二的,这是传统艺术哲学妙悟论中包含的重要思想。艺术领域中的妙悟不能简单理解为艺术创造过程,虽然审美意象创造是艺术妙悟的目的,但不是惟一的目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对人的灵魂觉性的恢复。所以,在艺术中,妙悟既是艺术创造的过程,又是灵魂颐养、心灵拯救的过程。传统艺术哲学常常坚信这样一个观点:人原来存在一个清净微妙玲珑的本原世界,这就是人的本觉;而这个本觉的世界被世俗染污,如堕入迷雾中,由本觉到不觉;而妙悟就是恢复这一灵魂的觉性,通过宁静的证入,由不觉而达到始觉。由此,妙悟的过程是灵魂的功课,是灵魂修养的过程。妙悟理论同时坚信,艺术构思的飞跃只有在洁净空灵的心灵中才能出现,最高的艺术只能由人本源的灵觉转出(即由心源导出),而不是从技巧中得到,也不是从刻意的意象捕捉中就可以实现,更非理智可以控制。所以,灵魂觉性的恢复是根本,艺术意象的创造则是由这个本中演化而出的。郭若虚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这个“人品”,不是简单的人的道德品格,而是人的品位,人的觉性,人的根性。所谓“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迹钩深”,这个“仁”,不能简单地从道德角度解读,而应作根性的理会,是一种“高雅之情”,是李日华所说的“胸中廓然无一物”。
石涛所说的“呕血十斗,不如啮雪一团”,就是对以上养气和人品说的生动概括。呕血十斗,是知识的积累,技巧的满足;啮雪一团,则是精神的超升。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左斟右酌,反复琢磨,技巧当然是作画之必备,但一个成功的画家不能停留在技巧上,而应超越技巧,由技而进于道。知识的积累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心灵的气象和格局。中国艺术强调的是“心印”,养得一片宽快悦适的心灵,就像石涛所说,吞下一团洁白的雪,以冰雪的心灵——毫无尘染的高旷澄明之心——去作画,才能自创佳构。
其三,妙悟在生知的理论还突出了悟性的差异性问题。大乘佛学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虽一阐提,也有佛性。但小乘佛教则强调人的差异性,有的人并没有佛性,除了释尊及弥勒之外,其余的声闻皆不能成佛。佛教常将人的自性称为“慧”,佛教证悟的最后目的在于悟此智慧。慧有层次阶级之分,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世俗欲界的有漏智慧,一是证悟佛性的无漏智慧。有漏智慧并不是佛的智慧,凭此智慧并不能证成佛性。这强调的是人根性上的差异。
在上引郭若虚等的相关论述中,实际上也涉及人根性的差异。在郭氏看来,悟性只属于那些具有高雅之情的轩冕才贤、岩穴上士,属于那些胸中廓然无一物的人。而一般人无此心源,没有生知之性,缺少这一微妙玲珑的悟性。他说:“扬子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悟与不悟被作为邪、正的区别标准。在郭若虚等的论述中实际上涉及悟只属于那些“人品”高的人,而“人品”低的人则没有这样的悟。郭若虚强调,艺术创造来自心印,心印本之于人的心源,人的心中有了,画中才能有。而“人品”低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源呢?从他的论述中得不出肯定的结论。
严羽的妙悟说与郭氏所论大旨相当。如其说悟有透彻玲珑的第一义之悟,又有一知半解之悟。这虽然说的是悟的差异,其实也涉及悟性的差异,如他对韩愈和孟浩然的评价,似有以悟性来评人的痕迹,在严羽看来,他们之间不是悟的差异问题,而是悟性的差异。悟的一知半解并非意味悟得不够深入,因为它不是量的缺乏,而是质的问题。外在的差异是可以弥补的,而根性的差异则无法通过学而得,必须通过养而致。
四 艺术悟性与佛性
艺术悟性和佛性具有密切的关系,传统艺术哲学中的悟性学说主要来自佛学中的佛性理论。[82]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很多笔墨,这里主要谈谈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在佛学中,众生之所以能觉悟,原在于心中所存的性,这个性是悟性,是悟之体,因性而有觉悟,因觉悟而见性。而觉悟的终极目的是对佛性的觉悟,所以佛性的本明世界是清净空。大乘佛学强调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佛性,悟的过程就是对这一本原世界的回归。传统艺术哲学中的悟性理论虽然主要来自佛学,也强调“一超直入如来地”(董其昌语)。但这个“如来地”与佛学有很大区别,它强调的是审美的穿透力和洞察力,强调摆脱一切干扰之后的审美自由境界,所以悟性的获得不是成了佛性,而是审美自由的获得,是创造动力的获得。如董其昌引赵州的话:“诸人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辰”,这就是自由创造的精神。悟性是创造的母机,而不是如来藏清净心。
在中国佛教中,关于佛性的思想有两个侧面,一是人心本净,客尘所染,所以觉悟的过程就是去除这些染渍,恢复原有的觉性;一是佛性具有“自性善净”的特点,佛性是不可染的,先染后净的思路不符合佛性的特点。吕澂先生谈到佛性不可染时说:“如日月之明,而有云雾之障,然云雾终不碍其自性之明。去障明显,分位有殊。但不可以分位染净而混言自性染净也。”[83]而在艺术哲学中,虽然借用佛学中的悟性之说,用悟性表示人的本原性,提出“因性而悟”,但对这个本原的悟性是可染还是不可染并没有作细致分别,只是强调悟性是自然之性,是人本然具有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真”的,人平常为理智、知识、欲望包裹的世界是“伪”的,悟就是回归“真”。这与佛性显然有所不同。
佛性是一种自性,但佛学在谈自性时又摆脱不了佛教思想中的因果缘起理论,所以对这个问题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佛学强调自性,另一方面又反对自性,佛学提出“自性执”,将此作为众生迷妄的根源。在佛学中,一切事物的实相和内在所依存之理都可称为法。这内在所存之理就是法性,或称为法界、真如、法身,即万法之体,它永恒不变,常住不改。法性是法的本体,法性不灭,法相随缘流转。自性是万相之法,万相均由自性转出,是一切存在的因,而一切存在都是它的果。佛学中又有自性谛的说法,《华严玄谈》卷八云:“自性是第一谛,古称冥性,亦名胜性。”[84]自性谛指过去八万劫以前冥然不可知的本体界。自性谛是第一原因,乃惟一常住之法。
佛教是讲究缘起的,强调一切事物的因缘和合的联系,而自性强调的是自我存在之性,所以缘起和自性是矛盾的。因为自性有即自有,自成,自己规定着自己,是不待他的;缘起是他成的,他有的,受他规定的,待他的。中观学派就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不能和合处。《中论·观有无品》说:“众缘中有法,是事则不然,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义?性名为无作,不待异法成。”[85]强调二者不能并存,有自性即不是缘起的,缘起的就不能说是有自性的。
但这一矛盾在传统艺术哲学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传统艺术哲学中,恢复自性就是恢复自然之性,于是有了一个更大的假设,就是和外在的一切实现了和谐,因为你的自性也就是无性,就是“天之性”。恢复自性,并不是落入“自性执”的魔障中,自性就是无性,就是人的自然之性,人如自然一样展现自己。你没有意识你自己的性,但以自己的面目,而不是以情感的取舍(这是欲望导致的),也不是以理智的判分来作别,你回到了自然之中,你在恢复自性之时,也就是实现自己的无性,于是与山山水水共优游。所以有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之显现。恢复了本元,通天地,尽人伦,在一个微小的对象中,都可以实现真正的超升。
在佛学中,万法唯心是其根本观点,种种意生身,一切唯心造,三千大千世界就在一念中,世界的存在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佛性映照的世界才是真实的。而艺术悟性的理论当然强调心的重要性,悟是心灵之悟,如将气韵归于生知的悟性,就强调人心灵的作用。但艺术悟性的理论并非否认外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只是强调在悟的境界中,溪涧桃花不因人的意识的干扰而恢复了它本原的真实性,一切存在在毫无机心、毫无目的的观照中显现了真实,所以在悟性中所“见”(现)之性,乃是物我自然而然之性。这与佛学也是不同的。
在传统艺术哲学中,“悟”是与“境”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妙悟伴着境界的创造。元刘埙云:“故(儒)不以悟为主,然前辈又有谓人患不入悟境耳,果能妙悟,则一理彻、万理融。”[86]清王士祯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87]境是由悟而得,所以又叫作“因定得境”。唐刘禹锡云:“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乎声。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88]
在传统艺术哲学中,境(境界)的概念非常复杂。通常艺术哲学中所说的境,有几个不同的意义指涉:一、指世界的存在;二、指人的意识活动的对象;三、指人的精神层次;四、指体验所创造的世界;五、指艺术作品的审美层次。而妙悟中的境界和这五个方面都有联系。本章拟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予以初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