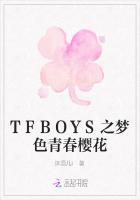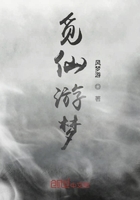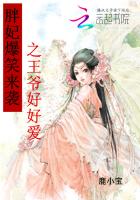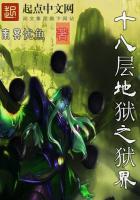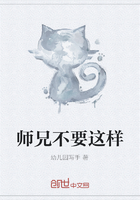看多了当代艺术,反而不敢谈论当代艺术。仿佛一谈起来就是错,容易“各执一端”,最后发现双方连基本概念都未统一,一时鸡同鸭讲,倒也呱呱唧唧,令人想见魏晋玄学的风度。
“当代艺术”之概念,时有论争,竟无统一。日前去三里屯PAGE ONE书店,翻阅到一本老外写的当代艺术普及类图文书,竟也是自己给的概念,可见无一定之规。前几年墙美术馆组织过中外艺术批评家搞“当代艺术论坛”,发给我的文献资料,打开首先看到的就是对“当代艺术”概念的探讨,但据说下结论的人多,不服气的人更多。这倒也民主,不用权威教科书,不要联合国的修订,泥沙俱下,“日用间”形成共识。
李陀先生前几年居京时,我向他请益对“当代艺术”的看法。他遂发表了“烂柿子”理论:大部分当代艺术作品都是坏的,像一筐烂柿子,但里面总能挑出几个好的来,要把好的择出来,发扬光大。他还主张中央美院搞“大师班”,请大师来,给有大师潜质的人授课。 ——这些出发点都是好的,尽管我常常要跟他争辩几句。记得他有一句启发了我:“常人把当代艺术和艺术的当代性混为一谈,以为当代性和当代艺术是一回事。”
后来我便将“当代性”作为衡量当代艺术的一个特征纳入,它对于指导我在《新周刊》艺术栏目的建构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显然,“当代性”只在艺术领域内发生作用,不像“现代性”、“后现代”那样,几乎可以一个词概括历史、哲学和文化领域,翻着篇“崛起”。后现代之后呢?是什么样态的文化景观?似乎我们还没走出理论家构筑的“后现代”城堡。“词”飞速地走在“物”的前列。倒是媒体技术和信息工具的变革,向外,催生和演变了社会、商业的革新,形成了社交网络;对内,使人的孤独境地和神经元的应激模式都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我们越来越被“卷入”了。这些,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都做了相应的预言:“地球村”、“你不是你,你是你自己的拟真物。”
倒是有位老先生看得很透彻,百岁又五的周有光先生,言人类社会的当下形态是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巨变。
在这个背景下,最初我建立当代艺术的分析模型,是沿用社会学思路的,空间轴是“全球化”,时间轴是“当代性”,驱动力是“消费主义”。这个模型一开始分析起来得心应手,无论是所谓当代艺术的 F4(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还是海外 F4(徐冰、黄永砯、蔡国强、谷文达),在这个框架设置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坐标、他们的位置。
全球化的理论太好用了,所谓全球化几乎是“美国化”的代名词,而所谓“美国梦”也几乎是“成功学”的另一个名姓。当代艺术可以说滥觞于美国,有学者称起源于中情局的政治阴谋,河清著《艺术的阴谋》说它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意图在欧、俄之外,建立一种文化霸权的谋略。中情局完全可以揽功于自己,正如一场战争,双方各自宣布胜利,没有失败者。只是不知道杜尚、博伊斯、安迪沃霍是否该苦笑了。
有人又将当代艺术等同于观念艺术。认为当代艺术是“玩观念”的。最早,则是“点子艺术”。似乎只要有一个好点子,便能博得眼球,吸纳媒体、公众和藏家的青睐。这招也的确有效,可惜的是行之不远——因为点子是可以模仿的,一旦模仿开来,艺术家变成智力比拼、创意发明,与文化创意公司无异。但是这条路,还是有艺术家在往下走,也不知走不走得通。互指对方模仿剽窃的,也不在少数。创作从模仿开始,本也无可厚非。中国艺术家中,几乎都是从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中汲取的营养,要说模仿,可谓是全体的事。只是有的拙劣,有的高超。
因此,还有人说当代艺术是“转换的艺术”。丹托是我颇欣赏的美国艺术哲学家,他便写过一本书《普通物品的转换》。以杜尚为例,他将小便池签上名拿到美术馆,便成了艺术品。为此还派生了一个门类:“现成品艺术”。越来越多的美院学生,将现成品艺术看成是“最高级”的当代艺术。有一年我去央美毕业生展,便看到主办方将现成品艺术给予“头条”和“显著”的位置。而对于现成品艺术的理解,一直有诸多不同意见。深入者则能深深体会现成品艺术只是个概念和形式,用这个形式装什么思想、表达什么意念,才是重要的。也有徒慕其形者,以为现成品艺术是时髦,做出的作品轻飘飘没有感觉。
“现成品艺术”极易和“装置艺术”混为一谈,它们有相类似的地方,但又全然不同。装置艺术使美术从架上延伸到全方位的空间中,它又不同于雕塑,而是有艺术家对“材料”运用的理解。颇似一个小孩子玩玩具,用自己的心得和手法把玩具拼成自己要的东西,从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现成品艺术是“及物”的,以物及物。装置艺术也是“及物”的,但其材料不全然采用现成品,有时也加上绘画、录像等各种方式。
“心”和“物”的相通以及交融,由“心”及“脑”产生心智,心智产生“观念”与“思维”,“观念”与“思维”产生行为,行为产生“物化”的对象。这就是“心与物游”的道理。观者则从“物化的对象”中,寻找创作者的“初心”。从而完成一次审美的解码。从这个角度讲,当代艺术是转换的艺术也不为错,上帝在编码,艺术家在解码;艺术家在编码,观众在解码。
还有另一种转换,是媒介或媒材的转换。叶永青“画鸟”就是这样:他用速写的小稿,投影到画布上,放大处理,再将它描画成作品。这中间运用到现代技术的方式,经过媒介的转换,其意义发生了不同。因此,也有人将当代艺术称之为“媒介的艺术”或“材料的艺术”。这种理解,完全看艺术家的会心——他更倾向于或善于用怎样的表达方式。
而对我自己来说,我更倾向于将当代艺术定义为“观念艺术”。“观念”这个词很好,字面理解就是“看念头”。佛经讲“念念成形,形皆有识”。拿到当代艺术中来说,也是很好的思想资源。但是“观念艺术”有一种流弊,就是拼点子、拼创意。这不是真的观念艺术。真的观念艺术是“心物一元”、“心物同游”的。观念有其纯粹性,而非驳杂的集合。“以一念代万念,以一念入无念”,这才是观念。观念艺术能够让你体悟到人生和宇宙的真谛,让人彻悟何为当代、何为当下。为什么只有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当下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只有一个时代,那就是当代。
当真正了悟观念艺术之后,便能“观空”了,也能观到“空”原来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一场“欢喜”。
作品没有伟大与渺小、重要与次要之分,它们都是宇宙进化到当下,所能体现的最好的样子。因此,只有全然接受当下,心平气和地专注与致力于手上的技艺,才是艺术家的本然写照。
但是,我们的艺术家常常耐不住寂寞,这又回到当代艺术的生态圈来。这个圈子有几个特点:一、它是个名利场,艺术家都想出名,出名能带来各种好处,足以变现;二、它自说自话,当代艺术的圈子有些固化,热衷于在小圈子中自我陶醉,尚未有伟大的人,能将其带入到“大文化”的圈层中来,大家几乎在“近亲式繁殖”,用京不特的话讲叫“思想的乱伦”;三、这个圈子也不太爱看书,几乎总是从他人嘴里得到一知半解,然后胡乱消化,壮壮门面。偶有诗人与学者的加入,但有谋不大。总体而言,当代艺术的圈子,颇似寺庙里的坐佛,外表金光闪闪,内里泥胎土坯——我更爱那户外的大佛石雕,无论风吹雨打、日侵月蚀,仍以艺术的质感,千百年不变。
不仅是在当代艺术,文学界也如此。“智力”显然成为最高的范本。卡尔维诺说另一个小说家博尔赫斯,便赞不绝口:“这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
但我们对“智力”有一种误解,以为它与心灵和情感不发生作用。于是产生了所谓零度写作、客观写作。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如此,有时会变得沦为机械、冷漠的填充物。这种危险是有的,尤其是西方的设计与艺术大行其道之后,到处是工业的美感,包豪斯气息统治了一切。各种金属、塑胶、玻璃、冷冰冰的线条横亘在那里,影响并改写了我们的审美观。如果其中出现禅意倒也罢了。但偏偏是“会错了意的禅意”。铃木大拙对西方最大的贡献是催生了“垮掉的一代”和“乔布斯”。但我要讥讽的是,凡有流布、必有流弊。大多数西方人误解了禅宗,从而产生了“会错了意的禅意”。“垮掉的一代”就是最大的代表,他们是用习气在做艺术,而不是用心性做艺术。因此,他们的艺术是“半成品”,是半路上的产物,未真能脱俗离尘。所以,凯鲁亚克说“在路上”,崇尚“自动书写”,这都是禅宗玩剩下的东西。关键是他们还要借助大麻与性来达到某种艺术状态,这已经落入狂禅境地,是足可让人摇头的。
它们只在西方横行也罢,与我无涉。偏偏这等思想流脉不仅跨海而来,几乎又反哺了整个东方,当代艺术原是西方的产物,更不用说,其受害更甚。
我这几乎是在清算西方了,但此非我本意。相较西方的物质进步,我是崇拜至极,尤其是西方正在回归人类文明,不再以“欲望”为主导。爱默生所倡导的“美国文化精神”,他对“学者”的理解,继承了苏格拉底“爱智者”的传统,不仅影响了一大批政客和文艺家,也影响了留学美国的胡适,并使这种精神东渡回中国来。“美国文化精神”和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精神”,构筑成了西欧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两大支柱。它一定让东方的前贤们欣然,而让我等后辈汗颜。
现在,最伟大的东方文明不在东方,而在西方。东方的哲人与西方的哲人,他们要么一脉相承,要么心意相通。无论是黑塞、叔本华、尼采还是基尔凯郭尔,我总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东方圣贤的硕硕身影。
但目下东方是不堪的,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与物质,却未能引进制度,于是,便成了一个成本很高的“风险社会”。“欲望号列车”横冲直撞,“成功学火箭”扶摇上天。生命被漠视,情感被归零,众生如山下蝼蚁,苟且而活。我心痛哉。
我想提出“格”的问题,可以讨论一下“人格”、“国格”与“艺术格”的关系。人若无格,等同于动物,人若有格,方趋完善,完善的人格,西方有富兰克林,东方有孔孟老庄。民国北大校长蒋梦麟尚有“三子说”:“做人学孔子,处世学老子,做事学鬼子。”这种人格包罗东西。民国时期,北大尚是教授治校,不让国民党派代表入驻,学术氛围空前自由,从而形成历史上最后一座高峰。便是因为他们有人格,因这人格去做学术,便有了北大的校格,因这人格去为民族奋斗,便有了“国格”。
而当今的大国崛起,是血酬的代价,是国格凌驾于人格之上的。我们的艺术家往往纸醉金迷在功成名就的路上,自然联想不起来人格与国格的事。倘有人做点有人格的事,引发讨论和话题,便说人“出风头”。每念及此,艺术家“人格”的小,在我心里,就大大地萎缩成一个灯草和尚了。
吴冠中一语中的:“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齐白石是小乘,自我完善;鲁迅是大乘,无我而济世。二子都在仙佛之列,只是从事的“工种”不同。艺术家受限于形式,不同于文学家的拍案而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的“人格”就可以萎顿了,恰恰相反,人格的不同,作品境界的高低自然不同,泾渭分明得很。
故王国维《人间词话》对艺术创作有“境界说”,山底、山腰、山顶的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风景已经是最美的了,但“远近高低各不同”,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境界说”之外,我提倡“艺术的教养”。艺术的教养,不同于安迪沃霍所言“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能做十五分钟名人”。木心说:“人,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艺术的教养,与美学家朱光潜所认为的艺术的审美有相通之处,它是纯然而然的,无功利性的,以直觉直达事物的本质,最终与事物交融为一体。这也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引用而言的“无目的的目的性”。另外,这也是蔡元培所大力提倡的“美育替代宗教”。什么是人间宗教,艺术就是。为什么人在美术馆、剧场、书店能变得安宁下来,因为它部分的替代了教堂的功能。人们徜徉在这些场所,取得超然物外的游历经验,进入一种审美的生命意识状态。这种生命意识是恍惚的,它不用你变得虔诚而迷信,而自然有净化身心之功效。
所谓“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说法,极容易让南郭处士来滥竽充数。而“人人能当十五分钟名人”,本质上又是功名思想在驱动。不若艺术的教养来得好,坐卧立行,皆有礼数;洒扫庭除,皆懂应对;诗画酬唱,皆能敏制。人心陶醉在天地间,顺应时节天地,“宇宙大千皆是自家心地,牛角微尘无非佛门性天”,有这份教养,自然能入宗教门庭,修禅问道,自然也不是问题。艺术代宗教,蔡先生说了一半,还有一半是,艺术入宗教。艺术代宗教,是暂且的法子,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最终是艺术入宗教的。艺术广摄一切学术,即一念摄万念;艺术入宗教,即一念入无念。
如果再深入一步,提倡“艺术的教养”,也是权宜的法子。更准确的说法是“艺术即教养”。因艺术之熏习,得种性之真谛,从而触类旁通,体察世间万情,不过是一场“欢喜的空无”。
天地相交,万物有情。人情世故,最终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无非“交情”二字。
“仁”、“义”皆是阴阳相交所产生的“交情”。触缘则交,有种即生情。艺术的自为天地,是以人的方式,与天地发生沟通,认清自家本来面目,也就是古希腊哲人所说的“认识你自己”。
人的艺术,超不过梁漱溟先生所言三圈层: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可以将其转化为人的三个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专业属性。有时,艺术家往往将艺术的专业属性发挥到极致;社会属性也能呼风唤雨,整合社会资源;但常常未能扪心自问,忘了人的根本属性是自然属性,这个自然属性就是王阳明所讲“良知”,也是“人格”的表现。只有在自然属性中,才是心之体性之本,由自然属性生发,才有社会及专业属性。自然属性,即“初心”。人首先是个自然人,其次才是个社会人,最后才是个专业人。老子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之在损,就是回到初心,从专业人回到自然人的状态,否则极不小心就会变成巧取豪夺的职业动物,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而有违艺术的本质。
调动七情六欲的艺术,是往外放;必须要往回收一下,使心向外驰后,回到自己的本位上来。此前,我说凡是调动七情六欲、使人心向外的艺术,都是坏的艺术;凡是让人收心、向内寻找的艺术,都是好的艺术。此语独断,有失偏颇,但我仍思忖,艺术的外放,仍要回收,否则,变成各执一端,外和内需统一。真空生妙有,妙有发挥了之后,仍要回到真空。虽然是一场空,但也是一场欢喜。
正如许多人不明白李渔《肉蒲团》的苦衷,为啥要在表现色情后,回到佛教思想中来。假如没有最后佛教思想的“收摄”,则不成其为艺术。有论者认为是打着佛教的招牌,宣扬淫秽晦盗。那是论者自身心地的糟粕所致。《红楼梦》之成功,也在表现“一场欢喜一场空”。空与欢喜,实在是“负阴而抱阳”的太极图。不可分割成二元论,它们是一元的,一体的,浑然的,只是为了知解的方便,才予以二元表述。
袁了凡讲,人之性,分“天性、禀性、习性”。观当代之艺术,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性”在哪个层次。天性,是与宇宙同一之性体;禀性,是先天带来的慧根;习性,是后天影响所形成的。那个天性一直在,但为后天习性所包围遮弊。而艺术家多少有些先天禀性的聪赋,有对才、艺、色的直觉力,但也会因之产生执著和贪恋。
以此观之,艺术家的作品粗略可分为两类:习气的艺术、心性的艺术。好多作品,不过是在习气上做文章,受污染、受不良的影响,天性未发出来;而心性的艺术呢,则能“艺达性天”,进入一代宗师的化境,影响后世,泽被一方。
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我看当代艺术的理论和方法发生了变化。不再以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方式来探测当代艺术的标尺。而是更多回到人性的方式,知识不再是一种生产和耗费的关系,跨学科、跨领域、跨媒材的那些当代艺术作品,无论形式上多么引诱人,但我似乎可以观察到他最终要表达的本质:是否进入到一种彻境里。
但我仍然要对当代艺术的概念作出说明。当代艺术有其强大的内涵和外延。比如,什么是当代艺术的修辞方法?至少,拼贴、挪用和并置是大多数当代艺术家驾轻就熟正在采用的方法。之所以称之为修辞,是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在运用,就像写文章要用到比喻、对仗、排比等修辞格一样。
但并不等于知会了当代艺术的修辞,就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艺术来。这真的是很难判定。艺术在于“度”,“太过”与“不及”都诞生不了完美的艺术。艺术是圆融的,即便生硬,也是有内在圆融的生硬。有时我们占有“符号”,便以为自己占有了“艺术”;有时我们占有了地位、金钱和话语权,便以为自己进入不朽之列——这都是想当然的误认与自我陶醉。艺术家不停地被高估和低估,像伏在大海中、受其抛来摆去的浮游生物一样,那些不稳定、不可控的结构与系统与它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它,有可能将偶然性当作了必然性;也有可能将必然性当作了可能性。但终归历史将淹没这一切,“名可名,非常名”。在词语的裂变、意象的抽取中,艺术家的思想与形式确立为“造物”般的、新的创造冲动。但,那是危险的,也是可耻的,艺术家要有一种意念去注视他,正如注视一个期待救赎的罪人。
“符号艺术”往往被当作当代艺术的又一个别称。早期,艺术家认为自己作品的“份量”不够(现在他们用能量一词代替),故他们往往会挪用一些具有重量的符号:长城、宣纸、自然生态、人文系统、社会热点、历史伤痕。美术家冀图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乃至于新媒体技术专家共同完成当下的、碎片式的写照。艺术家步入了某种黄昏,这种光线产生的错觉,是学院派的知识生产和繁殖左右了艺术家的直觉。艺术家不得不将自己变成自己作品的阐释者——这是有争议的——当你阐释自我时,要么过度阐释,要么力有不逮,可那又有什么可以值得阐释的呢?
会讲故事的人,选择不讲故事,是一种能力。而讲不好故事的人,选择不讲故事,则是一种逃避了。换成当代艺术,讲故事对应着素描、造型、色彩等一些基本训练。“技艺”仍是当代艺术中最基础的一环,它具有地基的性质,地基越深,则大厦越高稳。
“技艺”是不容忽略的,“道在技中”。折磨与磨练都是成为艺术家的必然之路。任何妄图取巧的方式,都像猛然爆发的火焰一样,很快又黯淡下去。我们必然有支持自己内心的手段,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用之不竭地去粹取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形式。“跨界”也是当代艺术经常采用的一种“修辞”。跨界即打通各专业领域,形成一种“自由联合”或“万物皆备于我”的艺术生产方式。在跨界艺术中,艺术家充当着导演、总控制人或协助人的角色,他必须冒险、实验,动员诸多工匠和专业人士,以配合他艺术实践的完成。有时,他是设计者、蓝图绘制者,而更多时候,他是一个妥协者,向方方面面的集约生产妥协,在不断的坚持与妥协中,作品一步步表现出它的本体样态——至此,“阐释”又开始了,当代艺术最吃惊的成就是,离开阐释就无法独立存活,这也因之养活了一条“生产-消费”的产业链。在这样一个链性结构中,每一个份子都是共谋中的一员,即便反对者的存在,似乎也是天然的合谋者,他厘清了道路的边界。
因为“阐释”,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哲学”如此之近。本来艺术、诗歌和哲学就是近亲关系。但今天的艺术,落入某种哲学的阴谋之中,艺术家希图他者从自己的作品中辨认出“哲学”的意味出来。艺术家希图作品是所指,而哲学是能指。但当代艺术作品更像快速的搅拌机,总是来不及消化哲学体系与大部头著作,便只能在一种“半吊子哲学”的状态下游离和搭讪。
当代艺术的兴起与全球性“中产阶层”的形成不无关系。当布尔乔亚都演变成新贵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渴望满足自我权力地位的确立及形成新的意识形态。而新的审美观正是自我意识形态刷新的一部分。冷战之后,庞大的资本主义集团与东方阵营的独裁在玩一种利益交换的对冲游戏,全球化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意识形态集团向利益集团折衷而互渗。在横向扁平化的物质世界中,每一个城市都变得同质化。人类制造了历史上最高数目的城市化部落。与此同时城市化的膨胀也容易变得失控了,人们的生活在失重的状态下,精神也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这种精神化抵制的局面似乎等待艺术家们的拯救,但荒诞的是:病人找到了病人。艺术家群体本来就是精神性疾病的受控者。但似乎我们的批评家有意识在回避这个局面——没错,当代艺术需要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的介入——但我们只能在一些哲学家那里找到思想资源,弗洛伊德、福柯或荣格。然而大师显然是不屑于当代艺术的弹丸之术的,毕竟,当代艺术的版图并不辽阔,它仍然是少数圈层的玩物,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大师们生不逢时,他们无法插上一脚。
而意图将当代艺术“学术化”的种种考量,几乎都是“失效”的。除了忠诚的纪录以留待后人之外,学术对此实在无能为力。它唯一的好处是制造一种“虚假繁荣”。也就是说,“当代艺术”与“学术”在一起炮制“幻觉”。没错,当代艺术因其视觉的特殊性,它易于“制幻”。它是一门制造幻觉的艺术,有时,它让你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有时,它让你认为生活需要批判。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再充当先锋而前卫的代名词,一切回到“当代”,每天产生一个主义的当代,每个主义都可以存活十五分钟。“后现代之后再无理论”的理论,本身也是一种理论。
当哲学已经每况愈下的从关注心灵一路滑下语言分析哲学时,你又期待理论有怎样的建树呢?无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德里达,他们在陈述什么呢?维氏言:“对当下的兴趣不过是一种哲学的、或者也有可能是艺术的职业癖性,一种需要哲学批判去疗救的形而上学病症。 ”(谢谢,你发明了新的说法。)德氏则擅长解构,他指称“在场”原是被过去和未来所腐蚀的,存在的核心总有不在场,历史不能被理解为“在场的接续”。(那么好吧,你说出了你新的发明。)
与其说当代艺术从语言分析哲学家那里找到了灵感,倒不如说存在主义哲学家更能激发他们。尼采所言“一切价值重估”的重要性,在当代艺术领域内震耳发聩。“一切价值重估”,多么令人兴奋哇。它意味着“翻盘”。意味着崔健那首歌《从头再来》。当代艺术正是这么干的。一切名目和现有的格局都被摧毁性的革新、创新式的破坏。“观念”解放了,但手艺跟上了没有?这是存疑的。
以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全方位的实验也发生在中国画一支中。水墨实验,中西嫁接的手法,有些是成功了,但有些也真是难堪,愧古惭今。
有人言,任何东西传入中国,都会变成“怪胎”。当代艺术,概无例外。“怪力乱神者”,大行其道;矫饰袭染之风,正在流行。798厂区,沦为一个怪胎,外表恶俗,内藏少数人的真趣;宋庄,几乎是中国边缘地带的一个缩影,这里城乡结合,权力杂乱,朝不保夕,人心荒芜。
一旦谈论到目力所及的当下,在这样一个时间与空间的联结点,在这样一个北京城,我总是产生一种“无力感”。我的所有谈论是虚弱的,轻飘飘的,人微言轻的。它难以改变什么,但又总在探测什么。我希望坐在我的对面,有三五好友,他们能理解我只是在自说自话。
《新周刊》艺术栏目的建构,迄今已有七年。多少艺术杂志都死掉了,它还在。而多少综合性的时政杂志并无常规栏目,而《新周刊》的领导者一如既往将当代艺术家视为同道,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在一个人心荒芜的大时代里说话,彼此抱团取暖也是必须的、必然的。适时而动,为艺术的“存在的接续”尽一己之力,也是必然的本分。
因之,我在操作杂志之余,也介入了一些策展与批评性质的讨论、撰文。但终归不成体系,它是零乱的线条,潦草得一塌糊涂。但亦有其精进的余地,可以看见“观念”的位移——保持关注比关注到什么更重要。
尽管我对当代艺术抱有整体的怀疑和冷感,但我总是被它的引力牵涉其间,难以逃身。这被我看成一种宿命,或许是我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想拥抱我们想拥抱的,但我们只能拥抱我们能拥抱的。
回到当代艺术的宏大命题中来,要想建立“一个真实而负责任”的当代艺术版图,艺术家更需要“不假外求”、排除杂念和外在干扰,潜身心于安身立命之所,如孔子所言“依于仁、游于艺”,得涵泳之乐。此则,艺术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生长,最终枝繁叶茂。因为除了拥有自己的心性之外,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悟“空”,即了悟“欢喜”。
上帝已死,当代艺术尚生。里尔克言:“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谁此时没有房屋就永远不必建造”。这是一种建立在此时此刻、与当下时空联结在一起的“当下性”。活在当下,洞察本质。正如一句“古今一体,恒久当代”所言,“当下的力量”是无穷的。德国心灵导师托利说:“没有过去和未来,过去和未来都是以当下的形式发生。”把握好当下,便是当代艺术的核义密要。也是我曾提出的“本质主义绘画”的重要指征。要想重估一切价值,洞悟美学的本质,进入艺术殿堂一窥奥玄,必然要对其“本质”予以追问和跟随。那么,则人人可以一心印万物了。
最后,我要说:当代艺术试图联结权力与资本,回到布尔迪厄所指称的“文化场域”。它正在这么做,而且相当有效,但它总是很难建立起思想资源的高地,它可以在时尚、媒体与消费之间合纵连横,但从一种更宏大的角度来看,它扎根之处的根系尚浅,它并没有将自己融入到一种伟大而自觉的文化传统中。
这意味着它有着大有可为的余地,这值得庆贺,正是由于当代艺术的“不足”,才成为广阔天地。以上便是我对当代艺术的全部意见,我必须宣称我只是在自说自话。
完稿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