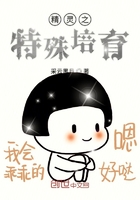"在教室里面学不到任何我想学的知识。那个老师讲课又太枯燥乏味了,听他讲课,就像在听催眠曲,整个人昏昏欲睡,浑身都不对劲,只想逃开。"
"话不能这么说,凡事有好有坏......"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学究,讲起话来十足一个学究。
"老师,你不必说了。"我打断了他,"课堂教授的知识,除了应付考试外别无他用。这样就向学生灌输一个观念:使他们站在对考试有用的立场上来看待知识,而不是看知识的趣味性及其重要性。
更惨的是,学生判断一个人学习好不好,只看他考试分数高不高。这太可怕了,这样下去,我们都成了考试机器。而这东西除了戕丧性灵之外,一无所用。"我越说越激动,把帽子脱了下来。
"你太偏激了。要是考试不过关,你就毕不了业,毕不了业,你就拿不到文凭,拿不到文凭,你就很难找到工作。"李教授继续学究,真受不了。
"这就是现在教育的弊病:升学主义和文凭主义。我问了很多人,发现他们上大学就只有一个目的:拿大学本科文凭。至于学到知识与否,他们是不考虑的。
"他们纯粹是在混日子,等着四年一过拿文凭。要是这样,我宁愿不上大学,花了四年的时间和金钱,就为一张废纸,值得吗?"
"每个人都得按一定的规矩和顺序成长,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上学。"
"规矩?规矩一词跟我们神话中的伏羲女娲有关,女娲右手执规,伏羲左手拿矩。他们手中的规和矩,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社会秩序的象征。
"还有一种说法,规主圆,矩主方,两人以手中的规、矩开天辟地,正合古时天圆地方之说。可现在的知识告诉我们,不止天圆,地也是圆的,未曾方过,但也不是全圆,正确点来说是像球而略扁。"
"老师,规矩也有出错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就非得要遵守那些陈规陋习呢?再说,美国并没像其他国家一样经历过封建制度,就走到了民主政治;我们的西藏地区从神权统治直接走向了民权统治。这该怎么说呢?有些事情是可以跨越发展的。
"我感觉我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我国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并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结果,供大于求,很多大学毕业生因此找不到工作。我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到七成,这就意味着近三成的人一毕业就失业。"
接着是一阵冗长的沉默,中间伴随着几声咳嗽声。时针指向下午四点,窗外面一片绿色,微风从窗外吹进来,让人颇感惬意。
为了打破沉默,我先开了口:"老师,梭维斯特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什么?我听不清,请你再说一遍。"
"梭维斯特。"
"没有。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个作家,有着和乔治.桑、巴尔扎克诸人的成绩,《屋顶上的哲学家》是他的代表作。我看到教材上并没提到这个人,因此想问你一下。"
"我实在对他一无了解。"我真怀疑他做学问的广度。
"老师,你还年轻,可以多写几本学术以外的经世济民的著作。"
"可我毕竟老了,你看,头顶都快可以煎蛋了。"我被他这句话逗笑了。
"哈哈。你不老,姜太公八十才遇文王呢,西德总理艾德诺七十三岁才当上总理,干了十四年。老师,人生八十才开始呢。"
"我不是说我年纪老了,而是说我心老了。有些人说人老心不老,其实人老的同时心也老了。我的思想在你们年轻一辈看来也迂腐了。我们中国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即当仁不让于师,可惜这一传统没能成为正统,没落了。我看你颇有这方面的潜质。"
"可是,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年轻,有血性,有冲劲,但也可能是蛮干。你是大学教授,是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利用你的人望和知识,为社会做点开路的工作。"
"你太抬举我了。屠格涅夫写的《父与子》,父亲想跟儿子好好沟通,减少代沟,跟上儿子的步伐,可是儿子还是走在了父亲的前面。我是被时代抛在了后面的淘汰者,可你不一样......"
"老师,你究竟在怕什么?"
我打断了他的对话。他没回答我,我继续说,"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职守是不谄媚权贵、不合作、敢说真话、站在无人代表的一方的,如同警察的职守是抓小偷,医生的职守是救人一样。如果一个警察以不抓小偷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