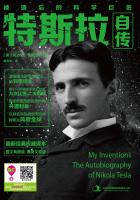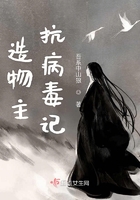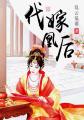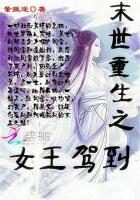——丁玲与沈从文的两次精神危机
我从小生活在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熟悉他笔下的乡妇、船夫、士兵、苗女,也熟悉他笔下的大庙、渔船、水凫、木筏;前些年回乡,还特意瞻仰过他的故居,探访过他就读的凤凰小学。上初中时,我也沉湎于丁玲的作品。这位刚刚逃出魍魉世界的女作家,为了追求希望和光明,历尽艰难险阻来到延安,用她那支纤笔歌颂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我至今仍能背诵《三日杂记》中一些优美的文句,眼前浮现出九曲十八弯的山沟,淡紫色的丁香,刚吐嫩叶的狼牙刺,以及在深邃树林中跳跃着的野兔,耳边仿佛响起了麻塔村青年男女演唱的《顺天游》《走西口》《五更调》《戏莺莺》……如果说,沈从文和丁玲,一位好比沅芷,一位好比湘兰,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领风骚,读者大多是能够认可的吧。
然而,这两位共患难过的友人在20世纪30年代却彼此心存芥蒂,到了晚年矛盾则更为激化。这种分歧在媒体上公开化之后,又引起了局内局外观点不一或跟他们关系不一的人们的不同评说。就我的阅读视野而论,似乎同情沈从文而责备丁玲的文章要多一些,其观点大体是:
丁玲在新中国成立后地位比较高——用沈从文的话来形容就是“在天上飞来飞去”,而沈从文此时在政治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人生处于低谷,以致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作为老友的丁玲在沈从文身落陷阱时,不但不援之以手,反挤之而又下石。“如果这时丁玲出来帮帮忙,也许他要好过一些”。也有人在热情赞扬沈从文“侠义之气”的同时,又严词谴责丁玲的“忘恩负义”。须知,评析沈从文跟丁玲的交往史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其中不但会涉及政治、文艺、道德理念,比如什么叫“道义之交”,什么叫“非功利的友谊”;而且必然要牵涉一件件、一桩桩的具体史实。本文不可能全面论述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是非功过,仅依据故宫博物院的一些档案资料,围绕“丁玲跟沈从文的两次精神危机”这一中心话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沈从文第一次陷入精神危机是在1949年初。当时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北大学生曾对沈从文进行严厉的批判。有一条大标语从教学楼上像瀑布一样悬挂下来,上面写的是:“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还有一份大字报重抄了郭沬若1948年初在香港发表的文章《斥反动文艺》。该文以对解放战争的态度作为分界线,把沈从文的作品称为“桃红色的”反动文艺,把萧乾的作品称为“黑色的”反动文艺,把朱光潜的作品称为“蓝色的”反动文艺。关于沈从文的一段论述是:“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我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千万道重’……”
神经纤细的沈从文自然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尤其害怕由此引发家庭风波,导致夫妻离异,于是在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中陷入了“灵魂的迷乱”。1949年3月9日,这位可以跟哈代和福克纳比肩的文学大师竟用保险刀割开了脖子上的血管,想要结束仅仅47岁的短暂人生。幸亏此时他妻子的堂弟张中和正在家做客,听到沈从文书房中传出一阵轻微的呻吟,心生疑窦。门推不开,他只得砸碎玻璃,从窗口跳进房中,将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沈从文送进了医院……
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1991年初,有一位跟沈从文有59年交情的老人发表文章,将沈从文的这次精神危机跟丁玲直接挂上了钩。文章中说,1949年3月上旬的一天,沈从文带着儿子到北池子中段一个大铁门里去见丁玲,想弄清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是不是如郭沫若文章中那样把他看作“反动派”。“谁知道见了面,从文大失所望,受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站在他面前的已非昔日故旧,而是一位穿上人民解放军棉军装的俨然身居要津的人物。”“从文终于意识到北京大学的大字报非事出无因,《斥反动文艺》对他的评价与丁玲的态度有某种一致性。他20多年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受到了有生以来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得到证实。他意识到迟早会被‘清算’,被当做一个‘反动派’在广大学生面前加以清算……强加在他头上的政治压力终于帮助这个五溪蛮的后裔自然而然作出天性中最佳的选择,在1949年3月9日决心以自杀来自白于人世,来抵抗这场横祸。”(刘祖春:《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凡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从以上文字中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沈从文的自杀不仅跟郭沬若的文章有关,也跟丁玲的态度直接相关。
这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事实的真相是:沈从文自杀之前,丁玲不仅跟他毫无接触,而且她远在辽宁沈阳,正在聚精会神地研讨陈其通的剧本《两兄弟》。丁玲是1949年6月8日下午才从东北抵达北平的,此前她从未拜读过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根本不了解沈从文的自杀事件。到北平定居后,她先后的住处在东总布胡同和多福巷,也根本没住进过北池子中段的什么“大铁门”。人命关天的事情,居然失实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丁玲风尘仆仆地从东北抵达北平后,仅隔了一天就去辅仁大学看望表哥余嘉锡,又去沙滩中老胡同看望沈从文。同年6月11日,丁玲在致丈夫陈明的信中提到“昨天去看了表哥和沈从文”。可见丁玲是主动拜访沈从文,并将他置于亲友之列。6月下旬,陈明也从沈阳来到北平。在全国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他们夫妇又约了何其芳再次去拜访沈从文。邀何其芳同往也体现了丁玲的一番苦心,因为何与沈曾经同为“京派”作家,有他同往,沈从文可能少一分顾虑,多一分温馨。这次会见时,丁玲反复劝慰沈从文:“你一定放心,不要再疑神疑鬼,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的头上。你一样可以写你的文章。”丁玲还关心他的生活,他的健康,他的情绪。(陈明:《澄清几件事》,《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丁玲这次来访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证据就是沈从文1950年9月8日写来的一封长信。信开头写道:“丁玲,自从你和其芳来谈过后,我总想写个信和你商讨一下自己……”沈从文在信中坦陈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态:他当时之所以“神经失常”“转入变态”,一方面是“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怕夫人张兆和离他而去。信中说:“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全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一离开,不问是什么方式,我明白我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什么都完了。”“如第一步就是家庭破裂,我想我神经崩毁将无可补救,任何工作意义也没有了!我明白我自己神经所能忍受限度。改造我,唯有三姐(按:指张兆和)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对于沈从文的这种心态,夫人张兆和在事隔40多年之后作了如下反思:“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转引自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沈从文的第一次精神危机很快就度过了。自杀获救后,他被安排到中央革命大学学习了十个月。常风在《留在我心中的记忆》一文中写道:“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谈起在‘革大’的学习生活高兴得像一个天真的儿童。不仅在他到‘革大’学习前脸上的那种抑郁苦闷的表情不见了,而且声音也特别高昂洪大。”沈从文从“革大”毕业后,随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土改,返京后由北京大学正式调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初,陈赓将军以老乡身份邀沈从文到北京饭店吃饭,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抗战时期,你的作品在解放区也很流行。现在在博物馆工作,这也很好。”陈赓的谈话使沈从文明白,有人一时在文章中将他置于“反动派”之列,并不代表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有趣的是,30年后沈从文的力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公开出版,为之作序的也正是这个在文章中将他置于“反动派”之列的人。)
195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又请他跟老舍、冯至、周培源等人吃饭。李维汉恳切地对他们说:“党的事业需要知识分子,希望你们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愿意,也可以加入九三学社。”(参阅凌宇:《沈从文传》,载于《长篇小说》第19期)1953年,沈从文出席了第二次文代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同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参阅王珞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460页)。毛泽东见到沈从文时,询问了他的工作和身体情况,而后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从1953年至1954年,沈从文的论文《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的陶瓷》《略谈考证工作必须文献与实物相结合》,先后在《新建设》《新观察》和《光明日报》等全国第一流报刊发表,说明他当时虽然没有受到理想中的信用,但他的才能也并没有完全被埋没。这一时期,沈从文仍然给丁玲写信,托丁玲代转稿件,甚至向她要钱。这至少说明他跟丁玲的关系还处于基本正常的状态。如果丁玲对沈从文“非同寻常的冷淡”,清高自爱的沈从文又何至于仍然以这些细琐之事相扰?如果1949年丁玲的冷淡就凉透了沈从文的心,他何至于后来发生精神危机还会想起丁玲?
沈从文的第二次精神危机发生在1955年,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他当时又感到“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根据故宫博物院现存档案,沈从文这次精神危机的诱因是在编撰《中国历史图谱》过程中面临了困境。这个选题是根据某苏联专家建议立项的,具体工作由出版局金灿然同志领导,但提纲却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崇武先生撰写。王与金的意见不一,而苏联专家每周只能来一两次,沈从文负责实际编辑,夹在矛盾双方当中不便说话,又没有助手,因此内心十分焦躁——他其实是很愿意把这个项目完成的。但发生这次精神危机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他在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两者之间的艰难选择。沈从文虽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京派”作家,但他的创作题材和写作风格跟当时的政治环境已不大合拍。而在文物研究方面,沈从文却具有十分渊博的知识,除了熟悉绸缎史之外,还熟悉家具史、漆工艺史、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马的应用和装备史、乐舞杂技史,等等。当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的印象是:“看情况,他是思想上有些矛盾,又想搞创作,但生活没有,又怕受批评;又想搞文物,又怕不受人重视。”“他愿多做些工作,但就是不知做哪样好。他自己说‘没主意,脑子乱得狠。’”跟王冶秋谈话的过程中,沈从文有几次要掉眼泪(王冶秋致周扬的信,1955年12月14日)。
在陷入第二次精神危机之时,沈从文曾找过严文井,又给陈翔鹤和丁玲分别写了信。给丁玲的信全文是:
丁玲:
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感谢党对我一切的宽待和照顾,我正因为这样,在体力极坏时还是努力做事。可是怎么做,才满意?来帮助我,指点我吧。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我通信处东堂子胡同廿一历史博物馆宿舍(是外交部街后边一条胡同)。
从文 廿一
凡是公正的读者都应该承认,丁玲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即1955年11月21日,她自己的处境远比沈从文的处境更为险恶。因为这一年8月3日至9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把丁玲和陈企霞定为“反党小集团”;陆定一和周扬又雪上加霜,要求跟公安部联合成立专案组,再次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然而,在自己身处逆境遭受到严重政治迫害的情况下,丁玲仍在收信后的第二天,将沈从文的来信转给了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和中宣部文艺处长严文井,并希望严文井能跟她一起去看看沈从文,劝他迅速振作起来。这难道也是“以政治划线”,用“冷酷”回应“真诚”吗?记得巴金在《怀念从文》一文中责备自己,说沈从文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替他讲过话,是因为他不敢,“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然而,丁玲1955年为沈从文转信时,“达摩克利斯的宝剑”却已经正端端地劈到她的头上了!她这时仍然在替沈从文转信,这即使谈不上是什么“侠义之气”,即使谈不上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但也总不能说成是“冷酷无情”“忘恩负义”吧!
丁玲替沈从文转信时还亲自给刘白羽和严文井写了一封信,除了交代新中国成立后她跟沈从文交往的情况之外,还极其委婉地反映了沈从文的工作情况,试探着询问有没有给他调动工作的可能。这封信跟沈从文的来信一起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里,篇幅要比沈从文的来信长三倍多,全文是:
白羽、文井同志:
转上沈从文给我的一封信给你们看看。
一九五〇(四九)年,我同何其芳同志去看过他一次。那时他的神经病未好。五一年土改前他来看我一次,我鼓励他下去。后来他又来信说不行,我同周扬同志说,周扬同志说他要王冶秋打电报叫他回来好了。可是沈从文给王冶秋的信又说得很好,可能是后来回来的。五二年问我要了二百元还公家的账,大约他替公家买东西,公家不要,我没有问他,他要下就给他了。去年他老婆生病想进协和,陈翔鹤同志要我替他设法,好像不去不行,我又向陈沂同志替他要了一封介绍信交陈翔鹤同志给他。现在又来了这样一封信。我知道他曾经同陈翔鹤还是谁谈过想专搞创作。过去好像周扬同志也知道。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搞创作是有困难的(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行),在历史博物馆还是比较好。看现在这样子,还是不想在历史博物馆。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如果文井同志能够同我一道见他则更好。我一个人不想见他,把话说扭了就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的萎糜(靡)不振,彷(仿)相隔世之人的样子,也忍不住要直率地说吧。有另外一个人就好得多了。怎么样?敬礼!
丁玲 廿二日
丁玲转信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但这并不是因为特别给丁玲“面子”。作为“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丁玲当时已无“面子”可言。转信能得到反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大气候比较有利,当时“中央正在考虑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不晓得对(沈从文)这样的人如何安排”(刘白羽致周扬信,未署日期,大约在同年12月初);二、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领导人对沈从文一直比较关心——至少要比对丁玲的态度友善许多。刘白羽因为对沈从文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于是直接请示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周扬,并在致周扬的信中明确表示还是应该有人出面给沈从文以开导(比如丁玲、严文井、陈翔鹤),“如有问题需要解决也解决一下”。周扬于同年12月7日在刘白羽来信的上端作了批示:“俊瑞、冶秋同志,送上有关沈从文材料,请阅。他最近精神又不正常,除由作协方面丁玲、严文井等去看看他,安慰他外,望社管局方面予以照顾。对他的工作,请考虑重新安排。结果望告知。周扬 十二七”当时钱俊瑞任文化部副部长,王冶秋任文化部文物事业局副局长。他们看到周扬批示后,由王冶秋出面,跟沈从文恳谈了两个小时。沈对王表示,他搞创作还是搞研究,由组织决定,因为他“虽然跟生活有些隔绝,但也参加过土改等,再钻进去还是可以写的”,“搞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工作,明锦、丝织、瓷器、玉器等都有些常识,而且能钻进去,也愿意搞出些成绩来。愿意到各地去看看藏品,及现在生产情况”。王向沈表示,周扬同志及文化部几位部长都很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他搞创作的愿望可以请领导考虑,如愿研究文物,明年可以主持故宫博物院织绣服饰馆的工作(王冶秋致钱俊瑞、刘白羽、陈克寒并转周扬的信,1955年12月14日)。在王冶秋的这封信上,刘白羽的批示是:“文井同志,请考虑如何办好。”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的批示是:“请考虑能否让他搞创作。”周扬12月20日的批示是:“写些通讯特写之类,也是有好处的,把这样的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如作协不好安排,可否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这样总比在历史博物馆和文艺界接近一些,也许于他的心情有好处。”
根据现存档案记载,沈从文的这次工作安排问题经过反复商榷,最后由他的夫人张兆和拍板定音。严文井跟张兆和洽谈的结论是,张觉得沈从文还是调到故宫博物院主持织绣服饰馆为宜。“这可能是对他搞创作前途有顾虑,此外也许还有生活保证问题。”(刘白羽致周扬信,未署日期。)刘白羽还向周扬建议,给沈从文一个位置,但不要要求他工作太多,同时组织他出去跑跑,写写东西。这样做比较稳妥。这个想法,刘白羽跟杨刚商量过。杨刚也认为沈不适宜行政工作,还是挂个名,跑一跑。周扬1956年1月19日再次批示:“同意这样办。他的行政职务问题,须与文化部商量决定。”1956年2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致函文化部党组,根据周扬等人的批示建议沈从文去故宫博物院主持织绣服饰馆,同时进行写作,并给他配备一个得力的助手。他的待遇以专家兼行政工作的办法解决。同年5月7日,文物局下发调令,正式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这样,丁玲替沈从文转信终于得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至少他的夫人会感到比较满意。但是,沈从文本人最后又不愿来故宫,只是在故宫陈列组担任了兼职研究员。沈从文的第二次精神危机,也就这样得以平安度过。
最后还想补充几句。新中国成立后,丁玲的处境总的来说并不比沈从文好多少,特别是1955年之后,她的命运可以说比沈从文更坎坷。沈从文说丁玲“在天上飞来飞去”,是用文艺笔法形容丁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身居要津”,同时也可能暗指丁玲乘飞机多次访问苏联及欧洲其他国家,如参加世界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参加纪念十月革命32周年、果戈理诞生100周年活动,以及参加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这一时期,的确是丁玲一生中昙花一现的巅峰时期。由于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丁玲确曾表面上风光一时,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权——仅仅在《文艺报》当过一年零四个月的主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主持过两年零九个月的工作。至于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一年多的文艺处长,更可以说是“混事”——她在那里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上述几项工作,后来仅仅给丁玲增添了不少罪名。从丁玲的角度看,她可能感到已对沈从文尽了绵薄之力,正如同沈从文也感到他对丁玲和胡也频尽了能尽之力一样。但从沈从文的角度看,丁玲的所作所为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正如他在致徐迟的信中说的:“当她(按:指丁玲)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靠她谋过一官半职。”双方由心存芥蒂到隔膜日深,终于在1980年矛盾激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关于80年代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那场冲突,我在《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在此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