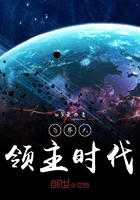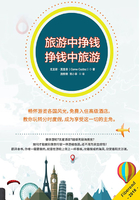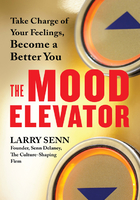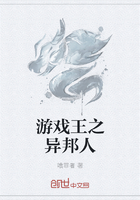程德培
阿波罗神殿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表达了人期求认识自身与他人。这条格言乃是全部心理学的渊薮。
——E.弗罗姆
王安忆的那篇题为《面对自己》的精彩发言,不仅博得了同行们的许多掌声与感叹,而且也使得以往许多对作者创作的精彩判断和展望,重新面临着一次考验。当王安忆在1986年写作她的“三恋”时,当她在构思那篇精彩发言时,事实上,她也正面对自己以往所有的作品,同样,当我们面对作者1986年创作,事实上也面对了自己以往对作者的评论,我们欣喜说过的话已经应验,我们惊讶以前未曾被发现的新景观,很有可能,我们曾经自信的判断已经开始部分失效,我们曾经有过的错误猜测现在更加刺目,我们曾经忽略的现象变得愈加耀眼,我们消除了旧有的谜团继而又陷于更深的困惑……评论如同创作一样,都是一场面对自己的角逐。
一
王安忆的创作犹如钟摆,她不仅经常变化,而且频繁地来回于钟摆的两端:论题材,从农村到城市;论体裁,从散文到小说,从理论、评论到人物印象;论叙述的变化,从关心自身的命运到冷眼的旁观;论风格的不同,从主观的“自我中心状态”到冷峻的“非自我中心状态”;论笔墨,从重人情到重世故,从重抒情到重心理分析……由于她富于变化的多产,致使对其创作的描述与概括,多免不了马不停蹄式的浮光掠影。对创作来说,即使是表面轨迹,也是活动体,而对批评来说,即使是再灵活的观照,也不能摆脱其静止的命运。这样,静注目与活动体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活动体的运动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而静观不仅是有对象的,且本身人是有视角限制的。所以,把王安忆1986年引人注目的“三恋”,作为一个创作过程,又放在这么一个认识的侧重面来考察,其不全面也是难以摆脱的。但是,对此刻的我来说,没有别的路可选择。没有片面性的创作面面观,此事古难有,想到这,我心安了。
王安忆的早期有过写“我”的阶段,所谓“雯雯的情绪天地”的概言便是一说,那时候叙述的,是“我”的插队经历、“我”在劫难平复后的骤变、文工团的琐琐碎碎,甚至在隐隐约约之中还追溯到了儿时的经历。这种种叙述之中又包括了这样一些冲突:舒适家庭之中娇小躁乱的心灵;热闹的儿时生活所掩饰的孤独;养尊处优、衣食无虑的女孩的自寻烦恼和心绪不宁,轰轰烈烈时代混乱中的寂寞与慌乱……那时候叙述的对象是“我”,但“我”所要叙述的动因则更多是为摆脱某种外在的压力,尽管如此,照作者的说法,也是很累人的,压力非但没有解脱,反而为外在的沸腾的生活激流所吸引,“和那些心与心彼此能够关照的平庸之辈,携起手来,开始了另一种远足与出发”。从此,叙述“小女孩”命运的“我”开始偏向了局外人,而关心局外人的命运又使得叙述者本身成了局外人。她开始冷眼,亦开始了旁观。她那与“雯雯”同声息的暖色曾赢得了许多许多的读者,而如今她那不露声色的说话竟也同样使许许多多的人感到吃惊,人们不免担心这位叙述者成熟得太快,忧虑她有没有老得太快的危机。持这种担忧的心理,事实上是太执着叙述视角与口吻的外在差异,当我们被作者创作上的变化所吸引的时候,是很可能忘却那不易被人注意的内在共同体的。要感谢作者1986年的献礼,以往的作品一旦与作者这“三恋”放在一起的时候,那遗忘了的共同点就作为另外一种差异而浮现在我们面前。在一个更大的钟摆面前,那原先小小的摆动也只能局限在大钟摆一端的那个变化不大的弧度之中了。
王安忆最初的作品,是让情绪沉浸在“我”的眼睛与话语中,而后的作品,的确又是过滤掉这种沉浸的情绪。这一点是变了,但是,有一点根本性的东西则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困扰作者的人与环境的冲突,人在某种环境压抑的苦闷、烦恼,以及人对环境的抵触与对出路的渴求。“雯雯”的命运是如此,《大刘庄》《小鲍庄》中的村民与知青们依然如此,还有那长期生活在都市中的好阿姨、谢伯伯们仍然如此。
而这种“依然如此”一直延续到眼下的“三恋”才有了改变,从《荒山之恋》到《小城之恋》到《锦绣谷之恋》,作者开始燃起了愈演愈烈的面对自己的战火。面对自己,谈何容易?一个人要看自己的脸,除了借助镜子一类的手段外,还能如何观照自己的容貌呢?然而,灵魂与心灵的面对自己毕竟有其奇特的效应,所谓反省自己,不就是把灵魂与心灵的一半分裂出去,作为另一半审视的对象。而我们呢?当我们面对这些作品的时候,不又是从另外的角度观望这一半灵魂与另一半灵魂的角逐、一半心灵与另一半心灵的撕咬吗?
二
三个作品因同有一个“恋”字,被我们放在一起,而它们本身又都因有着“荒山”“小城”“锦绣谷”的不同地名,表现了各自的独立性。三个“恋”字,归根结底都是几对相似而又不同的他与她、她与他,三个地名尽管不同,但却又都是“恋”的所在地,不同的是“荒山”是她与他的殉情之地,它是结尾,亦是开始;“小城”是他与她纵欲与灭欲之地,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回顾起来则已是瞬间;“锦绣谷”则是她聊以寄托愿望的地方,它是短暂的,却要长久地保存在记忆之中。若硬要说,三个“恋”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实际上三个作品是涉及了情爱、性爱与婚外恋三个不同的母题的。
一个拉大提琴的他,一个生长在金谷巷的她,命运使他与她在应该碰见的时候没有碰见,而又使他们在不应该碰面的时刻走到一起,结果导致了一场荒山的悲剧。一场荒山的殉情是足以使人感动的,人们还能指责他们什么呢?而活着的人们偏偏又要讨论他们为什么而死。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为了爱,为了诅咒今生今世命运分离了他们,无奈以求来生来世的拯救,为的是回报那些蔑视他们的眼神与口舌,他们的死不但结束了这场沉闷的故事,同时也确实摆脱了所有的烦闷。人们都说爱情是幸福,而他们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了,结果却适得其反,情爱收获的是一片烦恼,如果事情果真是纯粹的话,如果爱情果真就等同于幸福,那么他们聚合的愿望与爱情的等号,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在于,这种烦恼的到来,还掺杂着种种社会的烦恼、焦虑与偏见。
可以说,荒山的悲剧不仅是爱的悲剧,同时也是性格的悲剧。他过于纤弱与卑微,他对强大有着一种天生的依赖感,从小有着需要保护的欲望,他没有力量,从来都是孤独地和看不见的障碍作战,寂寞地在无名的苦闷中挣扎,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折磨,他是个太畏缩太懒散又太呆板的人。因之,他听到大哥洪亮的声音,就有了依靠,见到哥哥的魁梧,便有了安定感;他喜欢老师,喜欢老师是女的而又不像一个女的,实质上,他喜欢的是一位母亲的形象,母爱的力量与温暖,这也决定了他以后那又幸又不幸的婚姻。他的庆幸在于,当他处于最孤独、最寂寞、最懦弱的时刻借助婚姻的爱才得以安慰,他的不幸也恰恰在于他并不会适可而止,继续地把他对母爱的贪恋扩大到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依恋,他超越了对母爱的需求,事实上也就宣告了原有家庭的破裂。事实上,他的幸与不幸在一段时间里便构成了他的幸福与悲痛,对他来说,幸福就是对昨天的遗忘,忘掉昨日的畏惧与屈辱,打消那纠缠不清的自卑情绪,同时,他的悲痛也正始于这种幸福的到来,一旦他得到了充分的母爱,一旦他那颗弱小的心灵在母爱的庇护下成熟了,他的男性的自觉也随之到来,他事实上已成熟到了不需附加条件地去追求爱的时候,于是,那以母爱作为基础的婚姻便受到了实质性的挑战,尽管他的挑战依然是不露锋芒的,甚至外表上看也是胆怯的。
《荒山之恋》在结构上是双轨型的,这位叙述者在为他铺下一条通往荒山的轨道时,也同时把另一位的她推上另一条与之平行的轨道。她的行程恰恰与他相反,她的幸与不幸偏偏在于她的早熟,太有主张,太懂得如何支配别人,她是一个精力与智力都过剩的那种人物。当他因着惧怕回避世间的一切而独独面对自己的时候,她却因着不怕嘲弄世间的一切而独独忘却面对自身,他有着太多的孤独、寂寞,她却过于喜欢崇拜、羡慕和豪华,他是个自卑的畸形人,她却是优越感很强的人物,他与她,在各自的墓穴解脱了各自的负担,终于有了这么一场情爱的殊途同归,共演了弃家庭婚姻于不顾而走向荒山的一幕。悲剧导源于人生出路的泯灭,而对他与她来说,这没有出路的悲剧才是可能的出路。没有出路的出路并不一定都包含叙述者的多少用意,对创作来说,完全可能的顺序有时是倒过来的。当人们在搜索着荒落落的山村,“一片草丛里那四只交错在一起的脚”惊动了发现的人们,也许正是这幅图景,才唤起了叙述者的许多灵感与追寻,才打开了通往《荒山之恋》的大门。
三
“荒山”中他与她的命运,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性格,可到了“小城”,甚至连性格的作用也开始消退了。叙述者在《荒山之恋》中种种关于男女爱的战争的描述与言语,在那枯燥乏味的小城,在那积蓄情欲的练功房,在那顶楼永远没人的房间与那瞬间没人的幕后更衣室里,像命中注定的预言一样应验了。她与他这才开始了一场真正耗费情欲的战争,一场命中注定的没完没了的劫数。他与她的在一起,我们尽可以为他们寻找千条万条的理由,可以理解的理由与应该指责的理由,但有一条是最基本的,那就是作为符号的他与她,其性爱的不可避免。精神有自己爱的位置,性爱自然也应有性的位置。性爱是男女,所有的爱恋,不管其呈现的外观是如何地奇不可言,实际的基础却离不开性的本能。但是,性爱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它既能把人带入天堂,也能把人推入地狱。现在,圆胖肥硕的她与有着孩子般形体、加倍成熟心灵的他,正在这地狱之门进行着一场真正的角逐。性爱无疑为情欲提供了宣泄处,性爱的爆发又以其奇特的快感满足了男女间原始的生命活动与同样原始的贪婪,平复了他与她无名的狂躁。但恰恰也在这满足的同时,他们却也跌进了那无底的深渊,被一种破坏力所驱赶、所逼迫而难以自制、难以自拔。当爱展现出原始的形貌,不可抗拒的本能便以欲的骚动驱迫着他与她的结合,同样的冲动迫使他们的肉体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结合扯离了他们的灵魂。当他们拥抱的时候,夹杂着同样的依赖与孤独,夹杂着同样程度的爱与恨,他们彼此没完没了,涨潮落潮似的揪斗、撕咬和角逐,亲近与疏远、虐待与苛酷培养了同样的对虐待的期望,她与他加倍地消耗精力来寻求自身的喜乐,但也同样加倍地承受彼此的苦痛,他们付出一切与承受一切都是为着一个未具的生命。果然,新生命的到来也改变了这场战争的进程。在这个新生命面前,他们所面对的再也不是孤独的异性了,他们要摆脱这精疲力尽“游戏”的渴望也有了一个阶梯,顺着这个阶梯,他们各自跨出了相反的一步:对他来说“那生命发生在他身上,却不能给他一点启迪,那生命里新鲜的血液无法与他交流,他无法感受到生命的萌发与成熟,无法去感受生命交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与爱”。奇怪,这生命中明明一半是他的,他将自己的生命分出去一半再面对他的时候,竟然却不能与他交流,而叙述者甲认为“需要隔着肉体去探索”的理由又委实太牵强了。不管怎样,这不能交流便沦陷了他,我们便认定这是堕入情欲所应得的惩罚,却又很少把他的必然归宿与叙述者的主观意志放在一起加以认真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最终被流放在赌博台上的根源,明显地是由于他对新生命的抛弃。
相反,她没有这层肉体上的隔膜,她一旦熟悉了新生命,就和他疏远了,时时感到他的陌生,而那多年来折磨她的那团烈焰终于熄灭,在欲的熊熊大火之中,她获得了新生命的启悟,“心里明净得如一潭清水,她从没有这样明净清澈的心境,新生命的声音对一个母亲来说,犹如来之天穹的声音”。叙述者如此宽厚,以一种崇拜母性的仁慈,让她升入天堂。这位“腿粗、臀阔、膀大、腰圆”而又缺乏心计的她终于超越了他。透过这归宿性形象,自然地使我们联想起“荒山”上的那位拉大提琴的他第一次对女性的选择——他以其忧郁格外打动了她的柔情,唤起了她那沉睡着的母性,她不是那种女人,表面上柔弱文静而内心却很强大,有着广博的胸怀,可以庇护一切软弱的灵魂。心中洋溢的那股激情,是爱情还是母爱,永远也分不清……从“荒山”到“小城”,女性的美德之中竟有着那么多的“强大”“广博”“圣爱”的桂冠,使我们不得不为之感叹:女人!你的名字原来叫“强者”!
四
现在该轮到“三恋”之中最辉煌亦最需有诗意的一个名字“锦绣谷之恋”。这个作品显然是涉足了婚外的第三者,由于这样,以往几恋中的男女平衡在这里被打破,她首次面临着两个男人,但这并不妨碍女性依然是作品的主动脉。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女性的心理开始蔓延开的,连景观也是颇具情结色调的:最后一号台风、最初那秋叶沙沙、腐烂的落叶、凉爽的秋风、清澄的太阳,宁静的心绪、平静的叙述之中映现一对夫妇平凡乏味的日常生活,当大自然要进入收获的季节时,这个由他与她组成的家庭都开始进入了它们的疲惫状态,彼此间的深知底细,使双方都不留恋对方,双方都互相不能彻底战胜,又不能相互地彻底打败,难以逃脱的微微恶心,时有的发作与争吵,时高时低、忽明忽暗的心理。一切的矛盾纠葛都似乎是由着她的情绪挑起来的,而一切的道理又似乎是生来为她准备的。
叙述者试图证明一种精神的需要,也就是人的精神世界不能全然的公开化、规范化,犹如夫妻间的那种知己知彼,那种习惯化的沉闷与疲惫,所以不止是男女间,而且就是人世间的许多东西,凡涉及精神,便免不了有更新的欲望,这如同人体内的呼吸系统与血液循环,总包含了大致上的新陈代谢。这种需求,从本质上讲,一方面是残酷的,一方面又是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包括了它的宽容与未解的期待。《锦绣谷之恋》的他与她之所以能恋得那么美好,是因为它事实上是他们俩都参与否定过去的行为,他们之间全部关系的美好,虽然是和她的全部心理上的预感有关,但根源还是在于他们对各自过去的厌倦。叙述者对她与他采取一实一虚的叙述方法,使得我们在了解了她是如何从这种新的关系中获得新的激情、灵感,如何重新体验到女性的魅力与男性的魅力,一种天底下只有俩人才知的隐私以及它的神秘感,一种彼此间美好的诱惑哪怕是当中掺进了大量的幻象与虚构也不会逊色,因为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未曾有过的,能容纳期待与美好寄托的,能克制与隐藏个人陋习,能为已经陈旧枯燥的自我提供一次重新塑造的机会……所有这一切,我们能从实在的心理情感活动中想象补充影子般的他。应当说,他们之间的所有美好都是建立在希望扼杀旧有家庭关系的基础上的,但是,他们必须保留这旧有关系,如果不是在扼杀过去的同时又容纳、保留过去使它继续存在的话,新的关系又难以继续地保持自己的一切美好,而最终做否定对象的预备梯队,重蹈被否定的命运。
所以,她在经历了锦绣谷的一番欢恋之后,又心安理得,甚至带有某种侥幸心理回到那个令她非常厌倦的家庭,而那场全然由她一手导演的婚外恋则纯粹地退回到了记忆的领域,它不仅是一段美好的回忆,而且还是这对夫妻处理相互间关系的理想平衡器,靠着它,她才能有效地平息内心的一切不耐烦;靠着它,她才向婚姻的宿命表示了她的默认与虔诚。锦绣谷之恋成了一种记忆,一种永远留存精神之中的逝去,也只有这样,记忆才对她有了管束与督促,她才避免了那难以避免的自暴自弃。锦绣谷之恋就这样给予了一个家庭以平静,以维持生存的能力,这到底又算得什么呢?这个家庭毕竟有其可怕的一面呀!问题还在于这种家庭生活的厌倦情绪是偶然的一个回合,还是所有家庭必然的一段,如果是前者,她的平静也同样令人吃惊,如果是后者,她的选择才表现了耐人咀嚼的深层。
《锦绣谷之恋》大概并无意去向人们证明一个家庭是否应该重新组合,它恰恰向我们证明了关于解决家庭疲倦的改良性对策,正如她最后所悟到的那样,“只是,有一串闲话,如同谶语一般跳到她脑子里,放大在她眼前,那便是:
算了
你要走了
我不和你吵了
屋里挺闷的
还不如出去走走——
——再说
走吧
时间到了
要回去了!”
五
统观“三恋”,恋的核心无非就在于审视男女间对于融会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无非正是“三恋”的三种出路:要么在一起,人体的一起留在荒山,而让灵魂的融会留在对天国的期待;要么是“小城”那样的分离,它是天堂与地狱的分离,也是灵与肉的共分离;要么就是“锦绣谷”的分离,让现实的可能成为逝去,而让渴望的可能留在了永远的记忆之中,这是可能与不可能的分离。
把“三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这个世界的缔造者无疑将是叙述者,这个叙述者与作者有着很多不同,考虑到作者对叙述者行使自己艺术职能只是全部艺术活动的极小一部分,考虑到作者已将其部分的愿望、思考、意图、情绪的宣泄“托梦”给了叙述者,考虑到叙述者的另一半主人已是叙述语言的生存了,那么我们对叙述者的考察,完全可以不必太多考虑作者本人,作者也许现在正在把其另一部分的生命交付给另一位叙述者。叙述者是这样的一位角色,他一旦出现,就脱离了作者,但你要他脱离作品,那可是万万办不到的。当然,这位叙述者在“三恋”之中还是扮演了三个不同的角色的:“荒山”之中,叙述者是全知型的角色,因为知道的太多,才导致了小说的双轨型结构,叙述者不仅知道这一男的过去与现在,而且还知道这一女的过去与现在,甚至连祖父隐秘的身世也都知道,他不但知道这一男的心里在想什么,而且也知道这一女的心里在想什么,因为知道的太多,以至我们都难以确知叙述者本身了;到了《小城之恋》,叙述者有所收敛,他的视线不仅局限于小城文工团中的这一男一女,而且也是很晚才认识他们的,连他们的身世都不太清楚,自然也无法交代他们各自的性格历史,所以,叙述者的话语画面感、动作性都很强,分析、交代、描述则停留在“旁白”的位置。整个“三恋”,在叙述者知与不知的问题上,基本是处于越来越少的减退过程,发展到了《锦绣谷之恋》,叙述者不仅不在幕后,而且登台表演了,做了女主角的朋友、影子、心理活动的话筒与辩护者,但是,他(她)对故事知道就更少,几乎仅局限于那个女的一个了。而对其余所有的人物的了解开始与读者处于同一视界,唯有通过女的才能了解他们,也正因为知道的少,才决定了《锦绣谷之恋》的叙述特色在于出色的、细腻而富有女性魅力的心理分析。至此,我们才可以完全地看清,小说是如何地完成那面对自己的审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荒山之恋》讲的是四个人的故事,《小城之恋》讲的是两个人的故事,《锦绣谷之恋》则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
既然三部作品都涉及男女之恋,又都涉及家庭、爱情、婚姻诸般问题,那么,我们探讨叙述者对于性爱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荒山之恋》中的那个类似妖精的金谷巷女人,她尽管早熟,尽管有许多相好,尽管过早地从母亲那里知道了一些她不应该知道的男女纠葛,尽管她也有着无尽地折磨男性与吸引男性的本领,但是在女人应该信守什么的问题上,她独独坚信“只有将这个藏着,才是神秘的,深不可测,有着不尽的内容,叫男人不甘离去,叫男人爱也爱不够”。无独有偶,《锦绣谷之恋》的她,在男女问题上,那叫她等了几十年,又是意味着一生灿烂的锦绣谷之恋,其最精彩不过的剧目,也不过是一次次的精神之会,一次次记忆的陶醉。不错,《小城之恋》是彻彻底底地越过这个防线的,可敬的读者与评论家也为此争论不休,但是,叙述者又是毫不留情地使他与她彻彻底底地告别了性欲,无论是上“天堂”,抑或是下“地狱”。这样,叙述者就露出其厌弃具体性爱的面目。“三恋”的字里行间处处隐匿着一种为难的情绪,那就是他一方面承认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异性间的需求,或者是因异性而带来的情爱、性爱、婚姻诸方面需求的实际,叙述者用其锋利无比的叙述解剖了想掩饰的内里,但另一方面他(她)又确实否定了因需求而引出的行为本身,追求的必然与改变处境的必然;叙述者一方面让他与她认清改变现状的必然,另一方面又让他与她静静地默守着存在的事实,不管它如何需要改变。同时,叙述者又在这两难的抉择中,胜任地完成自身的美学,一种旁观者静默的美、一种叙述者透辟的美,对作者来说,这种美学在《锦绣谷之恋》中表现得最为圆满。我曾经说过,“三恋”实际上就是作者让自己的一半成为审美的对象,而自省另一半则又悄悄地糅合到了叙述者身上,然后通过叙述来看他与她的心理,来讲述他与她的故事,这样,既满足了人要窥视他人隐私的欲望,同时又悄悄地将某些自爱、自怜、自尊、自我掩饰欲、自我满足欲付诸可能的现实,这实际上是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正因有了滔滔不绝的叙述与默默无声的窥视的双重满足,才造成了“三恋”的叙述,在畅快淋漓的心理分析之中又完满地透露出解脱、豁达、理解的喜悦。关于这种喜悦之情,我们只要看看“三恋”中一个个结尾的念头就可以了。一个是“荒山”那女孩儿妈想:“女孩子在一辈子里,能找着自己的唯一的男子,不仅是照了面,还说了话,交代了心愿,又一处去了,是福分也难说了”;一个是“小城”中那位刚做母亲的她,陶醉于孩子把“妈妈”叫得山响,这声音令她感到一种博大的神圣和庄严;另一个则更是在透明的阳光里穿行,仰起脸,让风把头发吹向后边,心情开朗起来。这些心安理得的自我净化的收尾法,不仅是王安忆一贯的收尾模式,而且更是从作者在面对自己的角逐中,不断认识自己,解剖自己、掩饰自己、反省自己、升华自己的一整个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我们也可以同时把它看作是角逐之后独有的静穆。
如果我们把“三恋”之中那一对对的“他”与“她”重新组合成一对他与她的话,那么,我们所指的自己并不是指的作者本人,而恰恰是那个可以作为集合概念的“她”。“她”是某种女性的细胞,“她”包含了女性所独有的敏锐、自私、偏见与局限的生命经验,对神圣母爱的崇拜,对女性一切力量、长处、智慧的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柔弱男性、差劲男子、不堪崇拜的男子陋习的印象与厌弃。实质上,作品中所表露出的对男女间的那些不满,归根结底都是由男人来承担的。天哪!在这个世界里,男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名字,而写上“弱者”两个字,他们不是窝囊地、糊里糊涂,没有主见地跟着别人去死,就是永远进了那个该死的赌台,他们不是被抛弃,就是做一个靠着女性的宽宏大度过日子的丑陋角色,而那唯一的一个侥幸地成为值得女人爱的男人,至多也只能生活在女人心里“怀着的一个灿烂的印象,埋葬在雾障里,埋葬在山的褶皱里,埋葬在锦绣谷的深谷里,让白云将它们美丽地覆盖”。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它充分地说明这场面对自己的角逐有着很大程度上的自我欺骗,所谓面对自己,就是一种自我的分裂,它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的偏爱,它一方面是自我的解剖,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自我辩护。这个“面对自己”的头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被一个问题所纠缠,“究竟,男人是怎么一回事,女人又是怎么一回事?”她的思考是很有意思,至少她那种女性中心状态的思考与特有的敏感,确实纠偏了世界上许多男性中心状态的偏见。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一下作者的那篇引人注目的关于男人与女人的思考录就清楚了。但是,很有可能的是,这种颇具锋芒的思考也会同时带来另一种偏见。这位曾决定叙述者思维命运的作者曾直言不讳地写道:“上帝待女人似乎十分不公,给了女人比男人长久的忍饥耐渴力,却只给更软弱的臂力;生命的发生本由男女合成,却必由女人担负艰苦的孕育与鲜血长成,承继的却是男人的血缘和家族,在分派所有这一切之前,却只给女的一个卑微的出身——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女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受苦、孤寂的、忍耐的,又是卑贱的。光荣的事业总是属于男人,辉煌的个性也总是属于男人。岂不知,女人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人。”这些再明白不过的话,完全可以看作是“三恋”的注脚。于是,这位女性在不平中呜呜不已,于是,便给了那位男人下“地狱”的出路,因为他被新生命的到来吓昏了头,所以理所当然地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剥夺了他们的光荣与辉煌,给了那位纤弱而又缺乏忍耐力,并不十分地爱情至上而又有许多牵挂的男人以荒山的丢弃;叙述者在所有这些对男人的贬斥之中唯独给了那寻找自我局限于迷惘的女性以很高的境界。小说的成因当然是复杂的,如果我排除去许多因素不论的话,光就这一点,作者却是为女性结结实实地出了一口气,而且这口气是如此不露声色、妙不可言,以至“三恋”中许多披露男性弱点的笔墨是那么地酣畅。如同女性的诸多特性只有男性才能觉察一样,这位“女性中心论”者在保卫女性尊严时,也主动地揭穿了男人们惯于掩盖自身的隐私。也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那样,这种成功的主动出击及时地满足了女性的窥私欲。有人说,“三恋”写了“男人与女人”,我说,“三恋”写的是一位“女性中心主义”的目光是如何审视情爱、性爱与婚姻中的男人与女人。
概言之,还是那句话,面对自己的角逐,事实上也包括了认识他人,如果这“自己”是指的女性的话,那么解释一下就是,面对女人的角逐,事实上也包括了面对男人,而这种对女人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认识,还会带有几分自爱,那么,它也必然地包括对男人的几分洞察与几分偏见。上帝把智慧与眼力给男人与女人,那么谁也别想占全。
1987年元月写于上海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